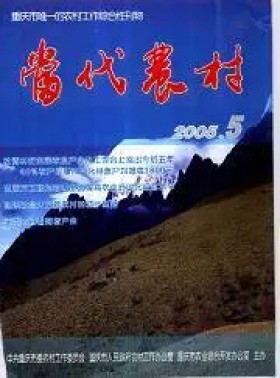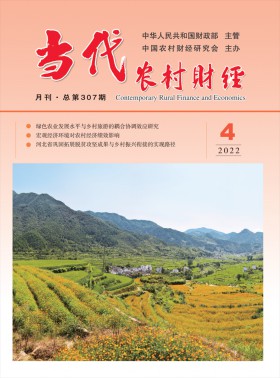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新农保”与60岁以上农民家庭基础性消费支出显著负相关,对60岁以上农民家庭高层次消费支出有负影响的倾向,但不显著。进一步将样本按家庭收入水平分类研究,发现“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农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但是不显著。
一、引言
养老保险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要民生问题,特别是农民养老问题更是重中之重。1986年起,政府在部分地区试行农村养老保险(简称“老农保”),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是由于当时时代背景等原因,“老农保”的推行并没有改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为了解决新时代我国农民养老问题,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2012年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2014年“新农保”与“城居保”并轨,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预计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新农保”政策受到国家政府强力支持的同时也担负着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带动农民消费支出、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新农保”真的对农民消费水平有影响吗?如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如无影响,为什么?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收集60岁以上农村家庭参保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自2009年提出以来,就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但却一直没有一致的结论,反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范辰辰,李文(2015)对山东省的实地,张芳芳,陆习定等人(2017)对浙江省的调研,黄宏伟,胡浩钰(2018)使用CHARLS2011和2013年两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得出“新农保”对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农保”对农民家庭消费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抑制作用。于建华,魏欣芝(2014)运用“新农保”正式试点前后共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Data线性模型,实证证明制度建立与否对农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于大川,赵小仕(2017)认为“新农保”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有文献虽采用较多实证模型实证分析,但是时效性较弱。此外,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新农保”政策的影响作用,对“新农保”政策前后具有针对性的对比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本文利用CFPS2010年和2014年两期全国性数据,采用更契合当下经济发展的数据,让研究更有时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本文把消费支出分为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进一步把样本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使得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更具有针对性,为学者们进行此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对比2010年和2014年的农民家庭参加新农保前后消费水平的变化来估计“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为了减少不可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优势,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CFPS调查问卷把居民消费细分为不同的种类: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交通费等以及过去12个月的衣着消费、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家具耐用品、医疗保健等。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把农民消费支出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础性消费,基础性消费主要是农民的日常消费支出:食物、衣着、水电、交通通信支出及其他家庭杂事支出等;二是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消费支出,定为高层次消费,包含医疗保健、家具耐用品、旅游休闲、购房、汽车等方面的支出。其中,CFPS调查问卷对基础性消费支出均以“每月”为时间单位进行询问,本文为了其与高层次消费较好的比较均把他们乘以12,以12个月为计量单位。高层次消费支出仍是按照调查问卷单位以“过去12个月”为计量单位。两个层次的消费支出均为数值型变量,为方便比较分析,因变量采取自然对数形式。
2.关键解释变量
关键解释变量treatment为领取养老金家庭与未领取养老金家庭的虚拟变量,当赋值为1时,意味样本家庭中户主与配偶至少有一人在2014年领取养老金,赋值为0表示该家庭在两年均没有领取养老金。关键解释变量aftert代表年份虚拟变量,将2014年赋值为1,2010年赋值为0。另外treat-ment×aftert是“新农保”制度与年份变量的交互项。3.控制变量农民的消费支出与其个体、家庭、经济特征等有密切关系,本文将这三种影响因素细化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资产积累。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其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的数据来反映社会的变迁,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基础。CFPS调查问卷由四种问卷类型组成: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和2014年成人问卷和家庭问卷中的相关变量。在数据处理上,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地区2010年未参加“新农保”的家庭,且该家庭在2014年家庭所在地区已经纳入“新农保”试点,此外,该家庭成员2014年至少一名达到60岁以上。样本选择依据为:①受访者家庭2010年未参加新农保;②受访者本人及配偶在2010和2014年均为农村户籍,且至少有一人在2014年时年龄达60岁以上。本文将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定义成一个虚拟“户主”,剔除包含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以及户主2014年不足60岁的样本后,剩下415个家庭样本,其中228个家庭2014年领取“新农保”养老金,187个家庭2014年没有领取“新农保”养老金,领取率达55%。
2.统计描述
如表1所示,2010年未参保家庭基础消费均值为14917.91元,2014年参保和未参保家庭基础性消费均值为22995.1元。2010年未参保家庭高层次消费均值17220.33元,2014年参保和未参保家庭高层次消费均值为13805.75元。这似乎预示着参与“新农保”对农民基础消费有促进作用,而对高层次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但是描述性统计没有同时控制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影响,因此还不能得出结论,需要进一步地进行实证检验。2014年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率分别为59.9%和50.5%,较接近。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2010年到2014年,基础性消费增加了6847.975元,高层次消费减少了7642.89元。可见,从2010年到2014年,“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基础性消费起促进作用,高层次消费起抑制作用。对高收入家庭而言,基础性消费增加了9312.35元,高层次消费增加了834.16元。可见,“新农保”对高收入家庭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都有明显促进作用。由于没有控制其他变量,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方法上,利用面板数据的优势,采用二重差分法(DID)对模型进行回归,在实证分析思路上:首先从总体上检验2010年和2014年“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然后把参与调查家庭年收入按从高到低排序,大于中位数的家庭视为高收入家庭,小于中位数的视为低收入家庭,考察“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家庭群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样本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分别检验“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工具上,本文利用的是stata15.0。
(一)“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总体样本回归分析
模型1为只估计“新农保”养老金、年份和两者交互项对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的影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对于农民基础性消费而言,模型1和模型2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且模型2在10%的水平下显著,而模型1不显著,这表明“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民基础性消费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和描述性统计结果不符,原因可能是“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于当下农村生活成本来说相对偏低,农民特别是60岁以上的农民家庭无劳动力或者劳动力少,在养老金难以满足基本生活成本时,他们会会相应地减少当期消费。而对于高层次消费来说,模型1和模型2的交互项系数都是负,且都不显著,这表明“新农保”对农民高层次消费有潜在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相符,但是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本文数据收集的是60岁以上农村家庭的数据,他们大多处于非劳动力阶段,虽然对医疗保健服务要求强烈,但是由于可支配收入的欠缺,他们仍然会尽可能地降低高层次消费。从其他控制变量分析,家庭资产和家庭年收入与基础性消费显著正相关,家庭资产与高层次消费显著正相关,可见家庭经济实力对农民消费影响重大。对于基础性消费,户主性别对其也有显著负影响,可能是60岁以上男性户主相较于女性户主而言对“新农保”标准持更悲观的态度。对于高层次消费支出,户主教育程度对其也有显著负影响,可能是教育程度较高的60岁以上户主虽然对医疗保健文娱休闲有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他们对养老金标准的认知,以及对养老金未来的清晰测算,使得他们更谨慎的消费高层次消费。
(二)“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群体样本回归分析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农保”虽然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水平有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虽然从回归系数符号来看,享受“新农保”具有抑制低收入家庭基础性消费和促进其高层次消费倾向,以及享受“新农保”具有抑制高收入家庭基础性和高层次消费的倾向,但是这一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不符。可能是因为,虽然领取“新农保”能够增加60岁以上农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但是并不意味着消费支出也会增加。因为领取“新农保”收入远远低于生活成本,而且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农民消费项目丰富化,微弱的养老金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细微提升,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表4得出,控制变量在分群体样本中和总体样本中的回归结果存在些许差异。第一,不管是在低收入家庭还是在高收入家庭,家庭资产对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都是显著正相关,这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一样。第二,家庭年收入在总体样本中,对基础性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在分群体样本中,对低收入家庭基础性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而且对高收入家庭高层次消费支出正相关,但是对高收入基础性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第三,年龄和家庭成员在总样本中不显著,但对分样本群体部分有显著影响。年龄对高收入家庭高层次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影响,家庭成员对高收入家庭高层次消费支出有显著负影响。年龄越高、家庭成员越少的高收入家庭高层次消费支出越多。因为年龄越高,家庭医疗支出消费越多,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他们也有能力负担得起消费支出;家庭成员越少的高收入家庭,收入越大于支出,相对的他们对文娱休闲活动支出就会增多。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对高收入家庭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有负影响倾向。加大“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刺激作用,政府及社会各界仍需加大努力。政府加大宣传力度,从多方面增加对农民的生活保障力度。农民积极参与“新农保”养老保险知识,正确学习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1]范辰辰,李文.“新农保”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以山东省为例[J].江西财经学报,2015(1):55-65.
[2]张芳芳,陈习定等人.“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7(8):17-24.
[3]黄宏伟,胡浩钰.“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8(5):18-26.
[4]于建华,魏欣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4(8):66-71.
[5]于大川,赵小仕.社会养老保险与消费支出: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17(10):81-88.
作者:刘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