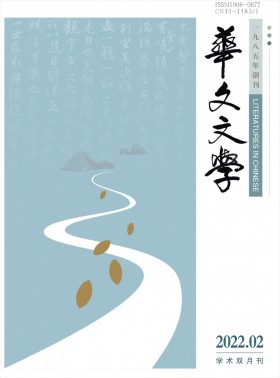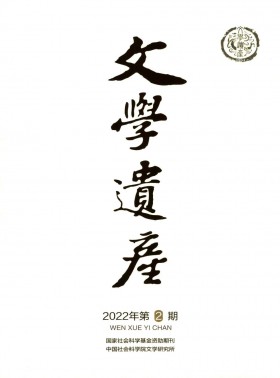文学叙事论文范文1
【关键词】英雄叙事;“十七年”文学;意识形态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英雄叙事是“十七年”文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那一个时期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的文本。面对如此之多的英雄叙事文本,通过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进而对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获得进一步的认知,这不但能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存在的某些缺失有所匡正。“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正是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英雄叙事的不足,对各自的发展脉络起到了潜在的规范制约作用。
一
根据“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所显示出来的美学风格的不同,最为清晰并占据着主流的发展脉络,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这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所以,这些文本基本上保持了《新儿女英雄传》的叙事风格。“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从时间上来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早些,在共产党基本获得全国性胜利的情形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就进入了蜕变定型的阶段,具体来说,《新儿女英雄传》是其起始的标志,这在根本上确立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基本模式;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文艺政策在理论上标志着英雄叙事范式的定型;《保卫延安》的出版标志着英雄叙事的定型;《红岩》的诞生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新儿女英雄传》标志着“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在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之后的定型之作。严格讲来,《新儿女英雄传》在时间上要稍早于“十七年”,但它却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特别主要的是,其英雄叙事的模式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获得了已经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新儿女英雄传》被当作实践《讲话》的精神的成功之作,其所规范和确定的方向就对嗣后的英雄叙事具有了规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雄叙事的文化品格:其一是农民和革命具有天然性的联系,主流意识形态视阈下的农民个体行为被充分政治化,凸显了农民在和革命融合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其二是大团圆的英雄叙事模式。这就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尽管也会出现一些悲剧,但从总的结局来看,基本上都遵循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大团圆叙事路径,而英雄则是这一先验性存在的一个明证。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郭沫若才会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显然,这成功的重要标志在于“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在这里,论者凸显的是《新儿女英雄传》的教化功能,把文学作为鼓舞人民革命的重要武器。这样的阐释,实际上也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即历史中客观存在的英雄怎样是一回事,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怎样又是另一回事,那么,裁定其是否符合规范和要求的标准则是能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起到强化作用,能否对“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儿女英雄传》标志着“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模式的基本确立,从而客观上规范了“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沿着《新儿女英雄传》的叙事模式展开。正是在这一模式的规范导引下,作家们在文学中所进行的英雄叙事就特别凸现了英雄之作为“英雄”的那一面,而相对来说,那些无助于凸现“英雄”的方面则被遮蔽了。如刘白羽作为战地记者对战争有亲身感受,这就使他的英雄叙事最大限度地切近了真实生活。作者通过渡江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一群只要“火光在前”就“永远前进”的指挥员英雄形象(《火光在前》),但它同时遮蔽了战争中人的其他属性。这奠定了后来的英雄叙事昂扬向上的革命基调,即便是死亡这样的沉重的话语,也通过“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完成了向革命的精神家园“回归”并存在的形式。《铜墙铁壁》是柳青的一部有关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文本,其讲述的是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支前故事。柳青在此塑造了石得富这一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巨大的历史主动性。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则用粗犷的笔法,其所讲述的是一批活跃在铁道上的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其所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有刘洪、李正、王强、林忠等,知侠在英雄叙事中,注意把民间传奇和革命历史有机融合起来,这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其他英雄叙事相比,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如果说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其英雄叙事还显得粗犷豪放的话,那么,还有与此相对应的一支英雄叙事脉络,这就是峻青和王愿坚的英雄叙事,他们似乎更喜欢在短小而严谨的结构中,以写意的笔法来塑造英雄。峻青所塑造的英雄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他把刻在自己记忆里的英雄,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英雄叙事的文本世界。峻青的代表作是《黎明的河边》,峻青在此把革命和亲情设置于同一场景中,凸现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英雄小陈在和敌人对峙的过程中,敌人为了迫使小陈交出革命者,挟持了小陈的母亲和弟弟作为“人质”,这就使小陈处于二难抉择的窘境中,要救出母亲和弟弟,就要交出自己的同志;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就要失去母亲和弟弟。作家在展开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没有详尽地观照英雄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而是让小陈选择了与还乡团头子同归于尽,由此把小陈从政治与道德的紧张对峙中解脱了出来,缓解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塑造了一个道德和革命和谐完美的英雄。其实,在这样的英雄叙事中,包含着峻青这样的一种英雄理念:革命和亲情是紧张对立的关系,二者在不可能兼顾时,牺牲亲情既然把革命者置于道德的对立面,牺牲同志既然把自己置于政治的对立面,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牺牲自己以舒缓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王愿坚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情有独钟。王愿坚最有影响的是《党费》,这是较早涉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生活的英雄叙事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有关这一题材的英雄叙事偏弱的局限。杜鹏程则善于从宏大的历史中把握中国革命历史,其《保卫延安》的英雄叙事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了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英雄叙事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作者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司令员的运筹帷幄,指挥员周大勇、卫毅等的身先士卒,战士王老虎、宁金山们的英勇顽强,都集中展示了英雄们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史诗性。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文本,在“”中却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之后说过:“你明明是在歌颂,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其实,我们暂且撇开其所涉及的问题,而是从另一面来看问题的话,也许就会发现,其英雄叙事先验地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这就使其英雄叙事当作了“歌颂”的具体注脚。这也就说明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都存在着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其他某些属性挤压的现实问题,这自然也就限制了其英雄叙事所可能获得的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能够代表“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准的是吴强的《红日》。吴强的《红日》出版于1958年,它采用纪实文学和小说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英雄形象。《红日》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作者并没有把英雄写成简单的战争英雄,而是把战争英雄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情爱关系中加以表现,使战争和情爱在对峙中获得了深层展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英雄所具有的本色。对此,吴强曾经说过:“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实际上,战争中的爱情以及爱情的毁灭,都更清晰地传达出了这样的意蕴:战争的最终目的恰恰是为了让人世间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美好情感获得健康的发展,而不是人为地扼杀这一美好情感,否则,这战争和政治就是反人性的。如此说来,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中的爱情主题,尽管在政治的夹缝中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机缘,但作家在严格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冲决了当时的文化语境的羁绊,依然为我们奉献出了诸多的“战地黄花”。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模式出现了新的突破,即把战争和人性结合起来。但这样的一种模式,并没有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十七年”文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另一重要英雄叙事文本是曲波出版于1957年的《林海雪原》。这一文本塑造的英雄杨子荣带有传奇色彩,其突破主要在于它把民间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到了一条融合的发展路径。欧阳山出版于1959年的《三家巷》是本阶段少有的反映20年代革命策源地斗争风云的文本,它拓展了本阶段英雄叙事的范围,把过去较为薄弱的都市生活纳入到了英雄叙事中。但相对来说,这一范式的英雄叙事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居于边缘化的位置。杨沫出版于1958年的《青春之歌》标示了本阶段革命历史叙事的另一发展纬度。它以林道静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最终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其作为具有较大影响的英雄叙事文本,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一是女性兼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这隐含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和女性个性解放的双重命题,二是这双重命题对主流意识形态命题的皈依。这样三个命题纠缠在一起,使《青春之歌》获得了解读上的多种可能性。梁斌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红旗谱》,则以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写出了农民英雄朱老忠成长历程。朱老忠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同时也带有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十七年”文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历史叙事还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标志着有关革命的历史已经被这是一个有关炼狱中的英雄故事。作家塑造的江姐、许云峰等许多坚贞不屈的殉道英雄,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魅力。《红岩》的诞生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革命的历史故事已经基本讲完;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问题更为紧迫的提到了人们的思考视阈中,这也意味着“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主潮将出现转向。在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定文化语境下,有关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的“准星”已经使作家们很难琢磨或追随。在此情景下,作家在英雄叙事中涉及革命历史中的“大题材”,就难免会和具体高级指挥员有所瓜葛,如果这指挥员将来有一天因为路线斗争而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循此展开的英雄叙事文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所以,衰退阶段的英雄叙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这就是作家从革命大题材转向了革命小题材或历史题材。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
二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所显示出来另一发展脉络,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具有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这一脉络和前者相比,显得处于主脉络的笼罩之下,仅仅是一个次脉络而已。代表性作家是孙犁,茹志鹃和路翎也应该属于此列。孙犁的代表性的文本是《风云初记》;茹志鹃的代表性的文本是《百合花》;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应该承认,“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这一美学风格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作家把过去封存于记忆深处的战争碎片,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起来,而那些曾经打动过他们的记忆,则获得了清晰的映现,于是,他们透过血腥与烈火,发掘到了那些被战争遮蔽了人性和人情,凸现在他们脑海深处的是这些依然还闪着光彩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碎片;另外,作家审美个性上的差异,促使他们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折射出了自我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情景下,洋溢着清新的审美情调的英雄叙事就应运而生。孙犁在个性气质类型上就属于那种非常注重审美情调的作家。孙犁早年受到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的小说影响,摄取了他们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这使孙犁的英雄叙事“兼小说和诗歌为一体”,从而“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实际上,孙犁所吸纳的西方审美情趣是以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审美情趣为基础的。然而,孙犁却因此而获咎:“摆脱不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情趣”。其实,孙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情趣,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人所具有的情趣更准确。如此说来,孙犁的英雄叙事就带有中西合璧的美学特质。《风云初记》是孙犁的代表性作品,他将散文的写意与诗的抒情融于英雄叙事中,在似涓涓溪流的笔法中,渗透着作家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念,折射了作家否定战争合理性的情思。所以,在孙犁的英雄叙事中,我们看不到常见的金戈铁马般的紧张对峙,在风云变幻中,作家用“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紧紧地把握民间自在生活状态下的“那股浪漫气息”。因此,在《风云初记》中,孙犁塑造的英雄既有血性男儿刚性一面,又有亲情男儿柔性一面,如春儿对芒种的爱,就在彰显了美好爱情的同时,隐含着对战争的否定。在孙犁之后,能够承继孙犁的英雄叙事的美学风格的是茹志鹃,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师承关系。严格说来,茹志鹃和孙犁在个性气质上和文学叙事上并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因为他(她)们的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下的宏大叙事不同,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她)们的文学叙事结合起来进行解读。茹志鹃的英雄叙事,几乎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她所塑造的英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她是站在革命历史的边缘上进行着诗意的叙说。茹志鹃说过,自己的记忆就像筛子“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这说明茹志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注重恪守自己的感性世界真实,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努力还原生活的真实。在《百合花》中,作者塑造的主要英雄是“小通讯员”。他的身上既有英雄战士那种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给他在异往有的矜持和羞涩,这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具有可以阐发的无限空间。不仅如此,作家还在小通讯员和小媳妇的交往中,凸现了男女之间的“非常情感”,成为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主流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语境下,茹志鹃的英雄叙事的确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美学品格,这也是该小说之所以获得茅盾肯定的重要缘由——自然,茅盾的肯定性价值判断,又反转过来促成了这一美学风格的发展。茅盾的肯定固然对茹志鹃的美学风格起到了保护作用,但依然有人在批评中要茹志鹃把英雄叙事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即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并“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这说明在50年代后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带有小人物色彩的、和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得不够紧密的英雄,已经失却了发展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希冀的是那些能够体现其要求的“当代英雄”,尽管这样的“当代英雄”还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英雄想象”中。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1954年。但从题材上来看,它所触及到的不仅是人性中的情爱这一精神现象,而且还带有跨国婚恋这样的敏感问题。路翎一反常规的英雄叙事模式,把爱情置于战争的中心舞台上,而战争本身则成为爱情故事展开的背景,这样的叙事彻底地“颠覆”了既有的英雄叙事模式,并由此通过爱情的毁灭而否定了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颠覆”与“质疑”,即便以如此温和的形式而出现,也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相爱了,这使王应洪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一方面,战争本身就构成了对爱情的压抑,另一方面,部队的纪律也构成了对爱情的排斥。王应洪面对这爱情有些惶恐,但也在“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最终,战争毁灭了王应洪的肉体,这就连同他那美好的爱情也一同埋葬于战争铸就的坟墓中,这既可以看作对战争的否定,也可以看作战争无法遮蔽人类美好情感的象征。但是,即便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也无法代表着“十七年”文学中有关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叙事的所达到的高度。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孙犁、茹志鹃和路翎这样一批站在时代边缘上的诗意吟唱者逐渐地失却了存在的机缘,这一英雄叙事的脉络也就越来越趋于边缘。甚至像路翎这样的作家,不仅无法居于边缘,而且还失却了创作的权利,成了“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主脉络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周扬对此就说过:“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周扬在这里显然不是站在私人立场上所作的阐释,他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说话”,这就很自然要求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用具体的“革命实践”来证明“的军事思想”这一“普遍真理”。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这些文本带有某些局限,但在一大批忠实于现实体验的作家努力下,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导引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英雄叙事重要篇章。这种现实主义的英雄叙事的结果,甚至演变成文本就是生活记事,如冯志曾经说过:“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正因为这样的文本一方面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打上了当时的文化语境的烙印;另一方面,受到了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受的制约,具有实录的某些特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获得了贯穿与实践。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次脉络的发展则经常被置于一个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位置上加以解读甚至批评的。其实,这一脉络的发展,严格讲来应该是对五四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命题的承继和发展,是对人回归于自身的一种文学尝试。它没有像主脉络中的英雄叙事那样,把人当作了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人只能在对战争功能需求的满足上寻找到存在的价值。那些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者,被作为战斗英雄放置到最崇高的位置上。而英雄身上的深层人性内容则被彻底地遮蔽了,即便是在英雄叙事中涉及到了人性这一面,也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趣排斥掉了。由此说来,当年的《文艺报》指认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恰恰道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真义:“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以‘写真实’的幌子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以‘艺术即政治’的诡辩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创作自由’的滥调来反对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显然,在这样的指认背后,隐含着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但恰恰是这“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促成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向人的本体回归,促成了文学创作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体认。
从根本上说,“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发展脉络,深受文化语境的规范和制约,它无法突破现实语境这一樊笼,它只能在时代为它余留的空间中找寻自我的发展方向,这并不是说“十七年”就注定无法诞生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英雄叙事文本,而是说无所不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把文学想象中的英雄压缩在了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把作家限定在了一个既定的“疆域”中,其英雄叙事只能循着这既定的轨道运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这两大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英雄叙事的不足,具有主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杜鹏程.杜鹏程文集(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吴强.红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4]孙犁.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林志浩等.对孙犁创作的意见[N].光明日报1951-10-6.
[6]孙犁.文学短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
[7]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8]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J].上海文学,1959(10).
[9]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A].周扬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2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3
论文摘 要: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即对原来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和用新文本作准确再现。然而,文本的意义受作者、文化系统、读者等多方面的制约,具有自身的语义不确定性和理解上的多重含义性。本文以人物形象,包括动作、对话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几方面的具体实例探讨了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如何使译文与原文达到语用等效。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必须对特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分析,确定有关成分的意义。并以不同的视角对意义的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准确恰当地译成目标语,达到与原文的动态等效。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例(1)语境:作者在“范进中举”一段文字里对其岳父胡屠户的描写:(范进)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 Hu gripped the silver tight, but thrustout his clenched fist, saying, "You keep this. I gave youthat money to congratulate you, so can I take it hack?"
“I have some more silver here,” said Fan Jin,“Whenit is spent, I will ask you for more.”
Butcher Hu immediately drew hack his fist, stuffed thesilver into his 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文中的“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几处动作语言是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胡屠户嘴里说着要把银子送给范进,但实际行动是一听范进说不要,他就立刻把刚刚伸出去的紧握着的拳头缩了回来,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想让范进把银子拿去。可是真正的意图是掩盖着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罗念生,2004,p.58-63)。译文中用了pipped the silver tight,thrust out hia clenched fist,drew backhis fist和stuffed the silver into his pocket几个动宾结构,勾勒出胡屠户原本不想把钱送给范进,而又要假装出送给的那个样子及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性格。grip,thrust out,clench,draw back,stuff几个动词用得非常贴切。仅仅运用一些动作语言就把胡屠户的内心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人物关系也变得非常清晰。译者保留了与原作者的相同叙述手法,不让内心活动在字面上有任何显露,而是留下空白和空缺给译文读者去想象。其方法是依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帮助与实证,根据原语作者的意图和期待选择词汇: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揣摩原作的语用用意,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的暗含用意,从原语作者隐含意图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深层含义,再把深层含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即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力求使译文真实表达出作者的真正用意。
情节、事件通常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位于第一。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均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翻译
人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铺之以语言。文学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才能站起来。因为人与社会及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自身矛盾,都无不在人物的心理上反映出来。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思想支配,为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变化,如喜、怒、哀、乐、犹豫、惊恐、嫉恨等。因此,心理描写极为重要。通过对话和行动可揭示人物的心理,真实、传神、感染力强,能让读者很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心理。而作品中微妙心理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所谓心理描写,即用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的描写。作家们不仅展示人物外在风采,同时也触及人物内心世界。文学作品中人物在特定氛围中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图,进而把握原作精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联想,在自己思想感情中寻找适当的印证。
翻译是把原语转换成母语的活动,其语用目的是使译文对读者产生预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人们交际时的话语不能只拘泥于其字面的意思。发话人(speaker)怎样设法表达其“言外之意”,受话人(receiver)又如何去理解发话人的“弦外之音”?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衔接和连贯均可实现。这种连贯性其实就是读者尽力使文本中的内容连贯的一种文本重构活动,这种重构行为又涉及读者本人的知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等。语用学理论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汉语语用学理论中的“智力干涉(the interventionbintelligence)是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p.131-134)。根据智力干涉原理,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使译文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人物性格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从下面对李白《静夜思》译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力干涉对动态对等翻译的解释力。
例(3)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 - and thoughts of my home arise.( Herbert A. Giles译)
译文 2) 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 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 s sweet memories. ( W.J.B.Fletcber译)
译文3)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I descry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I suspect it to be hoary frost on the floor.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as I tilt back my head.
I yearn, while stooping, for my homeland more.(徐忠杰译,1990,p.86)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其意蕴却深长,令人神往。诗的前二句描写了孤身远客在月明如霜的深夜不能熟眠的情景和迷离恍惚的情绪。诗的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意流畅,不加雕琢,直抒胸臆,借明月寄托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浓浓乡愁,道出了游子望月的万千思绪。它写了月,月总令人思乡思亲;它说到霜,显得凄凉;它写了抬头看月,低头思乡,显然是孤寂的。此情此景最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译文1)保留其隐含义“thoughts of my home”,留给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有淡淡的离愁或温暖的回忆,表达了天涯孤客在明净的月光下的旅思情怀,也符合英诗的表达习惯,易于接受。
译文2)中,以“Youth's sweet memories”形式出现。将隐含变为明示,结果使诗中意境转淡。
译文3)中,先后用了descry,suspect,watch,yearn四个动词,分别统领每行诗句的含义,语句简洁明了。其中descry是个正式用语,意思是notice something a long way off,watch与descry的相同之处是侧重于动态的描写。这里的意思是keep one's eyes fixed on someone or something,两个动词共同译出诗句中“望”的寓意。Suspect的意思是believeto exist or to bc true,yearn含有have a strong,loving,or saddesire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的意思。两者都常用于静态描写,这四个词译出了原诗蕴涵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译出了借助月光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将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委婉曲折,韵味悠长。译文3)凭借着浅显的文字却清晰地刻画出诗人客居他乡的思乡情怀,译出了常年寓居他乡之人的真切感受,达到了译诗与原诗的近似,再现出原诗的风格,令人读后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此例的译者是位外国译者,对诗人及其文化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国内译者的程度,推导出话语隐含意义的能力也逊色得多,就不容易完全达到语用等值。可见,译者既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对原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全面了解,又要兼顾译文不同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熊学亮,1999,p.122)。动态对等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原作者的意图的正确传达和译语接受者的正确理解为准。原文是作者交际目的和意图的体现,它面对的是原文读者,而译文面对的是译文读者。语用翻译不仅强调对原文意义的真实,以便做到真正的等效,还要使译文读者把注意力转到对话语隐含意义的推导。
例(4)语境: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the d'UrberviUes)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从野外过节的欢乐场面回到自己家。
原文:From the holiday gaieties of the field-the whitegowns, the nosegays, the willow-wands, the whirlingmovements on the green, the flash of gentle sentimen!towards the stranger-to the yellow melancholy of this one-candled snectac]e, what a sten!
(TXhoma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译文:从刚才野外过节那种欢乐的气氛里——白色的长衫,丛丛的花束,柳树的柔条,青草地上翩翩的旋舞,青年过客一时引起的柔情,一来到这蜡烛一只、光线昏黄的惨淡景象中,真是天上人间了!
(张谷若译)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若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无场景,最终将失去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用来描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本例的例子就是如此。当苔丝从野外过节欢乐的场面回到自己家中,家里仅有一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变了,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外面让人愉悦的节日气氛。原文运用了混合式手法,将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等描写方法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原文在描写苔丝的心理活动时,就把景物描写“the nosegays,the willow-wands”等细节描写,如the white gowns和感情活动描写what a step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苔丝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苔丝所见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了感情色彩,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
作家常常就是这样突破语言的常规,在特殊的语境中赋予语词新的涵义。翻译文学作品时,只有经过细致的玩味,才能透过字面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译者运用智力干涉原理,推测出描写词语里的隐含意义,把握其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将“what a step”译成“真是天上人间了”,显得自然、具体。这一夸张手法抓住在特定环境下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翻译,真实可信,恰如其分地译出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把她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体现在译文中。如果将其译成“真跨出了一大步啊”,既不能渲染烘托气氛、衬托人物性格,也不能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更无法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真实,因为人物的真情实感未能表达出来,心理活动没得到体现,人物形象也就逊色得多。所以,译者应根据文学语言的特点,借助于语境,灵活地选词择句,寻求最佳的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在原文语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显示译者的再创作功力。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4
关键词:现代文学;身体叙事;拟态狂欢;消费时代;视觉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32-04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于20世纪30年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预言着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转型。新媒体技术和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在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的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走入了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电影、电视、虚拟游戏等以影像和声音的形式将隐含的文字意义以透明化的方式诠释出来,直观的刺激显得更加真实,符合现代消费文化时代人们的视觉感受。视觉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张力效应使文学创作也越来越转向视觉性,体现了现代消费文化的思潮和趋向。当下文学创作因其受到视觉文化转型的“强力冲击”而超越了其原始的概念与意义空间,其叙事方式走向了视觉化的倾向。
一、拟态环境与文学的视觉化叙事转向
以视觉观念为媒介主导的后现代社会瓦解了形象与现实的界限。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和“仿象”的世界。人们的感性经验无法企及和区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异,只能更多地依赖大众传媒去认识客观世界。按照李普曼的说法,人们进入了“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P127)大众媒介以其特有的方式向公众展现了一个“超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景象,而广大公众却顺意地接受仿象世界及其所传递的意义。在现代语境中,“拟态环境”不仅仅构建特定的景象以及传达信息,而且引导和塑造着文化,其所展现的文化张力突破了传统文化的界限。景观社会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契合点在于:调动人的“本我”的内在欲望和冲动,从而使他们不断追求刺激、模仿和认同。当下形形的娱乐活动正日益成为人们建构自己身份认同的方式,并且以一种狂欢和欲望释放的形式来诠释自己的感知体验。在这样的“拟态环境”下,文学创作在审美转型的激烈挣扎之中深刻地被现代语境所渗透和异化,那些现代流行的消费元素正是加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符码,使其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时刻准备着去迎接这种新型的文化冲击,从而转向视觉化的叙事途径。
二、视觉化的文学叙事: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
当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在现代生产条件盛行的社会,整个生活本身都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变成了表象”。[2](P3)德波对于现代社会中商品的影像化、景观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定性以及景观社会的时空扩张的批判,正抓住了现代消费时代的显著特征:视觉消费。文学作品中的一切视觉元素,成为视觉消费的“产品”。而且这种视觉消费已经超越了看的行为的范畴,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即“看”成为人们建构自我认同的途径。“看制造意义,因此它成为一种进入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将自己嵌入总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一种控制个人特定社会关系的手段。”[3](P38)菲斯克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对于视觉消费作出文化关系诠释的,这与德波对于景观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德波认为在景观社会,人们的意识形态被影像的媒介所遮蔽,从而走入了视觉的幻象。人们服从于影像化的商品的说教,并且在模仿、崇拜、认可众多视觉形象的过程中建构关于自我主体认同。因此,消费社会的理论范式强调的是欲望的文化,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都市的生活方式。“行动取代了传统的审美静观,当下的即时反应代替了意味无穷的体验,这必然转向‘追求新奇、贪图轰动’”。[4]在这样的心理期待下,人们开始追逐大众文学作品中的种种视觉元素的奇观。这种奇观带来感性思潮的回归,将人引领进一个由感官经验碎片所拼合起来的景观世界。
现代消费时代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在现代的审美中,“狂欢和欲望释放已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游戏策略和叙事途径”。[5](P86)现代文学作品迎合这种心理,试图创设一种狂欢或模拟狂欢的氛围,使观众陶醉其中。“不论是反映都市人文知识分子精神颓废的《废都》,还是反映商州以狼为主体的生态文化小说《怀念狼》,或是以绝美而凄凉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社会病相小说《病相报告》,以及重返商州乡土叙事的凄美挽歌《秦腔》,主义的欲望叙述充斥着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小说文本,使他在恐惧与紧张的小说叙事路途上,在无奈的精神表征中,以越来越形而下的欲望表述及‘审丑’的文本范式,不厌其烦地唠叨着物欲的横流、权力欲的膨胀、的扭曲、的崛起。”[6]贾平凹的作品从清新的文笔转变为欲望叙事,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视觉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冲击:一方面,在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消费文化的双重夹击下,人们的思想走向了迷途,只能陷在迷茫的状态中被动地挣扎。另一方面,人们在视觉文化的语境中不断地刻意追求和模仿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从而在虚幻的想象中拯救自己的精神危机以及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消费时代,我们发现,对于现代流行文学形式(比如网络文学)追捧的群体具有年轻化的特征。这与视觉文化转向视阈下社会的结构与文化意识转型是吻合的。视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网络文学,这里的“看”并不是简单的视觉接触,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从视觉文化关系角度理解,“看就是我与他或世界的一种经验关系或存在关系,一种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7](P68)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网络文学狂欢群体的“年轻化”,便可揭示其中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意义。既然称其为“狂欢”,就包含着情感的一种宣泄或释放。首先,狂欢群体的年轻化,正反映了现代消费时代年轻人学习、工作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大。而网络文学的奇观景象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和精神抚慰的平台。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看的方式反映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它“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个体或社会群体的精神”。[8](P120)因此,看的方式很重要。我们如何看待文学与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同等重要。情感文化的当务之急不仅在于塑造当前的艺术实践,而且也在塑造着人们看的方式,以及对艺术对象的认同方式。这种现象从年轻人对网络文学的热衷与迷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网络文学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时尚元素。这也是吸引年轻人眼球的原因。“在当代视觉文化中,我们不难发现,时尚作为一种现代消费社会常见的现象,它具有某种召唤力和诱惑力,这与时尚借品位之力而形成对特定群体的吸引力有很大关系。”[7](P221)年轻群体对于网络文学的追逐,体现了他们对具有审美品质的对象的某种选择或评价。在社会文化意义上,这种现象是消费者个体审美情趣的表现,也反映了商品社会里个体身份的主体建构。作为网络文学的阅读者,他们的眼光“以激发生命的情感为鹄的,积极而充分地调动想象、直觉等身体的各种感知功能,通过凝神观照或亲历参与情感活动而创造出审美概念或美的意象,进而获得生命的意义”。[9](P205)最后,现代消费时代促进了新消费主义意识的发展。年轻人不再以传统的方式去看待生活世界,而是以新的消费观念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消费时代,物品(包括艺术商品)的高度丰富化颠覆了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使消费行为成为个体的身份认同的构建方式。网络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商品符合年轻人所倡导的视觉消费习惯,通过这种“群体狂欢”的体验过程来获得心理上的自我满足。
三、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奇观效应与心理狂欢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是一种“视觉文化现象”,也体现了现代消费时代的趋向与特征。当代视觉文化反映了现代消费时代社会文化的转向,即将艺术实践配置到拟态的关系中。传统文学所塑造的“经典叙事”在现代主义时代以“拟态”的形式回避它,将文学叙事连接到其意义更广泛的领域――“奇观效应”。在有关007小说的研究中,迈克尔•丹宁就提出了文学的视觉性问题,他将小说中对于邦德旅游、观光的景观描写诠释为文学的叙事奇观,体现了消费时代的视觉性话语。正如大街上我们所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广告一样,邦德的游历旅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消遣式的审美景观。这是我们人类心理的复杂需求,让我们看到自我的内心欲望和本能的追求。视觉文化的新的重要功能在于让人们日益依赖视觉感性经验,从而来满足他们作为个体的视觉需要。现代的消费已经呈现为对景象的消费,现代文学所制造的奇观景象使得人的原本欲望变得更加强化,从而让人们的传统感知意义失效。视觉文化景象教导我们看与思考的方式,由此来调解我们作为社会人的彼此互动,并且试图解释我们的视觉体验和可视化的主旨如何在社会制度、实践和结构中得到构建。因此视觉事件与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彼此相互修正。这些修正是文化和社会斗争的结果,通过社会的流行文学作品得以明证。毫无疑问,现代文学作品的世俗化是消费时代商业化驱动的结果,它的组织形式重新定位了目前视觉文化氛围的流行范式。“长期以来,由于作家的文学书写独立于导演的影像媒介之外,因此,作家主要依靠单向度的语言文字思维进行小说创作。到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媒介所带来的巨大威力对作家的世界观、审美观、创作观、价值观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家的文学书写开始从单向度的文字思维向文字思维与影像视觉思维相结合的双向度的思维转变。”[10]文学的影像化思维方式更符合读者对于视觉时代的阅读诉求。于是,受市场化运作、商业利益驱动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刻意地将文学叙事视觉化,使文学语言缺失了审美的艺术感,从而丧失了文学欣赏的价值。更有甚者,一些文学作品试图剧本化,成为影视片的附属物。爱德华•茂莱曾批判性地指出,“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句话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11](P302)
视觉文化似乎已经削弱了自我启蒙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适应现代消费时代的情感模型。在现代都市,现代藏了文艺复兴时期占第一位的人文的、持怀疑态度的方式,而将人类心理转向了不确定性和扭曲的“狂欢式”的宣泄。实际上,人们对于文学视觉化的接纳是有社会和现实的原因的。一方面是视觉化的文学带领我们走进了一种“拟态环境”,而遮蔽了我们对于现实环境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原因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受众对于文学作品中狂欢的热衷和沉迷,在心理上表现了人们在现代社会压力下的自我释放。如果我们注意到文学作品中的片段和叙事,它就变得很明显,为什么视觉化文学在现场特定时空中,有意营造或建构出“时空叙事”的奇观?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文学作品都在使用心理学上的技巧,使其展示的情景叙事实现与受众的“心理契合”。文学叙事的一切元素(等等)不仅给观众提供了一般性的视觉享受,还隐含了更为复杂的心理的欲望,那就是“观看癖以及窥淫癖”。[7](P78)其核心在于使观众的焦点建立在心理情感的依赖上,产生一个从情感认同到故事的情感体验的结果,从而实现最高潮的阶段,那就是心理狂欢。
四、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身体景观
进入现代社会的消费时代,身体,这个在传统意义上往往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被推到了视觉文化的前沿,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视觉符号。尤其是当人们将对于身体的研究置于庞大的社会体系中,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身体的复杂的社会关联性后,身体景观成为商业与现代消费主义极为推崇的话题。“在视觉审美中,身体是除大千世界外,最为引人注目、最具视觉冲击性的特定对象,身体既属于个人,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人们对待自身身体的态度是和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文化审美的进一步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和反本质主义的司空见惯,这种对自我观照的态度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时尚潮流、人际交往、审美观念、艺术创作、消费模式等各个方面。”[5](P81)在现代消费时代,人们在注重自身身体的感性体验的同时,也更加将视线投射到“他者”的身体和肢体语言上。于是,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于女性身体的描绘显得非常普遍。林玉蓉等通过对波德莱尔《恶之花》和艾略特的诗歌作品的解读,指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多涉及城市,城市是物质文明的集散地,是消费文化的推销者,是欲望停靠和释放的场所。城市在带来丰富的物质消费和享受的同时,也成为藏污纳垢的隐秘场所,滋生了许多糟粕,其中之一就是许多女性身体成为了消费文化的交换物,叙述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景观”。[12]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女性文学出现的“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和卫慧的《欲望手枪》等都将身体这个话题以文学叙事的形式进行了阐释和欲望化解构。这种视觉化的文学叙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审美倾向似乎是相背离的。但读者在惊愕、思考甚至愤怒的同时,也肆意地解读着“身体景观”。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将身体引入了艺术的殿堂,体现了美学的理念和独特的审美范式。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审美观的建立和男权主义意识的抬头,女性身体成为男权文化规训的视点和化的对象。从女权主义和男权文化的视角来看,女性身体的研究隐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话语:“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视觉伦理,作为男权文化和男性霸权视点下的欲望投射物的银幕呈现与物质载体的女性身体;作为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符号的女性身体;作为政治与文化霸权的规驯对象的女性身体;作为自觉与内省的女性意识载体的女性身体”。[13]很显然,文学作品中的身体景观,作为一套打上独特标记的符号系统,体现了前两种话语。其一,女性作为男性观众欲望的对象,成为被看的主体。其二,在消费时代,文学往往会选择以视觉为轴心来诠释女性身体的消费符号。在一场另类的“狂欢”中,大众不但用眼睛“窥视”与“消费”着女性身体,而且也发挥着自己无限的想象,处于一种“虚幻”与“真实”的臆想之中。这些正反映了消费时代人们自我社会归属关系的迷失,只能通过视觉消费来构建自我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美] 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周宪. 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5][14]金丹元. 电视审美与身体文化[A].孟建,[德] Stefan Friedrich.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赵学勇,王鹏. 欲望的纵情与狂欢――贾平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C]. In Slavoj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94.
[9]肖伟胜. 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李红秀. 影像时代的文学书写[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1).
[11]爱德华•茂莱. 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 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12]林玉蓉,刘立辉.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体叙述[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3]张彩虹. 身体意像:明星研究的新动力[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1).
The Visual Narr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Context
PAN Xiao-quan
(Xingzhi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 321004, Zhejiang, China)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5
关键词:金朵儿 儿童文学 叙事艺术
赣南青年作家金朵儿,虽然年轻,却有比较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开创了自己的独特天地。从她富有灵动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把自己完全潜入到孩子的世界里,以孩子的兴趣、愿望、感受为主体,忠实地记录着孩子们的成长。“儿童本位”在她的作品中的诠释是以儿童为中心,彰显“童真”、唤醒“童心”、激起“童趣”,尊重儿童的天性,亲近大自然。其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也是一个天真烂漫、想象力丰富的、很有灵性的女孩儿。此外,她又是一个很有思想力量的作家,她的作品要给予孩子们的是正面的熏陶,在他们的心上从小种下一颗小太阳,给他们以满满的正能量。因此,不管是从她对“儿童本位”思想要义的把握程度、作品本身灵动、清新的文字质感还是作品带给孩子们正面的精神力量来说,金朵儿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无疑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并孕育着无限潜力。
一.以儿童之眼,全知观世界
金朵儿的儿童文学是真正的儿童文学,她总能放下自己作为成人的身段,以一颗纯真无邪的童心去看周围的大千世界,写出了一个清纯、迷人、梦幻般的儿童世界,这容易让小读者产生一种亲近感,融入作品的场景之中。
金朵儿在“小贝卡奇遇记”系列作品中塑造的天真烂漫、很有灵性小贝卡和虹朵朵其实都是金朵儿自身的写照。她借小贝卡和虹朵朵之眼来观察、感受世界。“小贝卡奇遇记”系列作品以小贝卡这一儿童视角来叙述的,现实活动场所以贝卡家和学校为主。文中的故事,以贝卡的所见所想而展开,如在水果基地发现了会说话的草莓精灵多多,遇见“魔术师”树叶鸟谷谷,探险海底世界及救了神龟和人鱼公主。“虹朵朵的梦”系列的故事是以虹朵朵的视角展开的,帮助孔雀鱼苏菲娜找回自信后又救了阿波罗王子和小蝶的故事,帮助狸猫乌卡卡找到梦想及发现老狸猫经历的古老而神秘的故事。王子与公主,海底世界这些都是从孩童的眼中所看到的事物,折射出孩子们纯真而美好的心灵世界。给鱼儿吃巧克力,骑着项链变成的魔杖穿行于天空、海洋、陆地之间,海底王国和巫婆城堡之间的斗争。这一系列的事件着眼于儿童视角组成的故事从设置悬念、情节发展演变的几经挫折到最后结局的豁然开朗,极度契合了儿童探求冒险、故事有趣生动的心理需求,也表达了儿童对阳光正义善良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也使得读者能够近距离的把握故事的全貌。
二.多重互变的叙事时空
在儿童文学叙事文本中,灵活多变的叙事时间,改变了传统儿童文学中按故事时间发展顺序讲故事的方式,让时间在故事中被折回、重叠、扭曲,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层次感。金朵儿作品中对叙事时间的处理就很巧妙,《狸猫乌卡卡》就是一个恰当处理叙事时间的典型文本。这一作品没有按照传统的顺叙叙事模式,而是采用倒叙、插叙并用来设计故事的讲解模式。从一开篇介绍虹朵朵家搬到古屋的场景,搬到这里后发生了一连串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院子里的蟋蟀弹琴的时候,她似乎能够听得懂它们弹唱;发现了一只活了300岁的老狸猫,它还说虹朵朵书架上没几本有营养的书;墙角一只脾气古怪的老蟾蜍也活了300岁,说她家的到来搅乱了它的清静;那棵活了680岁的榕树肚子上有个洞,那里竟然是狸猫们的家;虹朵朵发现,乌卡卡是只特别有思想的狸猫,他不但喜欢爬到榕树上看星星,还喜欢趴在墙角静静地仰望玫瑰色的天空......面对这些,虹朵朵感到疑惑,为什么这里的动物好像都可以跟人沟通?为什么蟾蜍和老狸猫说话这么奇怪?这些疑惑和倒叙刚好就是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带有强烈的神秘气息,为下文设置了悬念。
空间指的是行为者所处和事件所发生的地理位置。带有幻想意味的童话故事,从一开始就领着读者进入一条可以多重互变的时光隧道。这样,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就可以很好地从“真实世界”跨入到魔幻般的“虚拟世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极大满足儿童的阅读期待和爱幻想的天性。金朵儿作品中的叙事空间发生了灵活的转换,《草莓公主》中的故事场景主要有两个:“真实世界”学校和“虚拟世界”草莓王国,从学校组织去水果基地参观遇见了草莓公主多多,引发了贝卡和周莉直接的争吵,到后来参加学校的校运会周莉被苦瓜妖利用,草莓王国面临危机,贝卡打败苦瓜妖救出同学这一故事链。这样的“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转换,丰富了行文的故事结构和情节,使得故事文本既充满童趣,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又紧贴生活。
三.巧妙介入的“景物叙事”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面对一种毫无变化的叙述节奏,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要想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必须要在叙事方式上进行改造,改变叙述节奏。[1]其实,在金朵儿很多儿童文学小说中,作家都喜欢借助景物描写来改变叙事节奏,或缓和或加快。而其中景物充当的是一种叙事的角色,所以称之为“景物叙事”。《狸猫乌卡卡》中开篇中写道“这里是小城最后一条老街,街上的每一座房子都被密密匝匝的爬山虎包围了,吊兰的藤蔓从各家各户的木窗台垂了下来,一直垂到地面上。不远处有棵活了六百八十岁的大榕树,树叶遮天蔽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只鸟儿在树叶间跳来跳去,唱着能让人的心窝流淌出甜甜汁液的歌。”就从老街入手,描写了老街周围的一些景物,包括爬山虎、藤蔓、木窗台、大榕树等景物,最后是落到大榕树这一处景物上进行详写,这里可以体现出大榕树的树龄之老,为后面老狸猫讲述几百年前的悠久神秘的故事叙写埋下伏笔,同时这里成群的鸟儿唱的暖人心的歌曲也对后面描写出虹朵朵和狸猫家族们相处很愉快,小狸猫乌卡卡也撒下了梦想的种子这些美好营造了氛围。《孔雀鱼苏菲娜》中开篇“傍晚,天空中的晚霞将海面镀上了一层玫瑰红,浪涛拍打着海岸,一望无边的大海雄浑而苍茫,数叶翩翩的白帆,在这水天一色的红海上,就像几片雪白的羽毛似的,轻悠悠地飘来荡去。”就描写了苏菲娜从海底游到海面前的景物描写,在海面或沙滩上看晚霞是她尤为喜欢的一件事,因为她在海底的家中被冷落嘲讽心里很自卑痛苦,而晚霞可以洗礼心灵,消除烦恼,这都为后面反复描写晚霞和太阳奠定了基调。尽管最后的结局是苏菲娜没能和阿波罗王子在一起,而且苏菲娜并嘱托虹朵朵不要告诉王子真相,苏菲娜在这个时刻完成了心灵之洗礼,是太阳王国里阳光有着金子般心灵的女孩儿。
四.缜密的叙事内在逻辑
叙事内在逻辑是否严谨、缜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儿童的阅读效果和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笔者认为,作家金朵儿在这方面处理的不错,既有谋篇布局这行文结构层面的,也有叙事过程中折射出的情感意蕴层面。她以童年经验中纯真美好的大山记忆为叙事内驱动力,捅马蜂窝、追彩虹、做蘑菇饼这些童年记忆都已成为她生命中的印记,影响着她个人的精神与审美,也影响着她的语言清新自然、叙事生动有吸引力的创作风格。还以营造魔幻诗意的童话意境为叙事主线,爱幻想,拥有成人群体所缺少的想象力,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金朵儿这位年轻的作家在“小贝卡奇遇记”和“虹朵朵的梦”系列作品中契合了儿童的这种天性和心理,处处可以感受到文中营构的魔幻而诗意的童话意境。《神奇的魔法师》中从小贝卡出生时不是哭而是大声唱歌开始就带有魔幻的色彩,而树叶谷谷鸟会变魔术有魔法都满足了孩子们丰富奇特的想象思维的需要。此外,金朵儿作品中的叙事主人公大都是阳光有灵气且能与动植物交流的女孩,并渗透出万物有灵的儿童思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叙事理念。这种缜密的叙事内在逻辑赋予了作品以巨大艺术张力和完整性的特点。
总之,年轻作家金朵儿儿童文学创作本着“以我手写我心”的美好童心,回归大自然的原点,从大自然中汲取无尽的养料,给大家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审美意趣,除了和金朵儿自身的童年经验有关,还和作品中所体现的独特叙事艺术不无关系。她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拓展孩子的想象力,给孩子美的熏陶。我想,她的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激发和拓展孩子们的想象力,同时让他们明辨是非和美丑,把成长中的正能量慢慢传递下去。
参考文献
[1]金朵儿.虹朵朵的梦[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2]金朵儿.小贝卡奇遇记[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5]韩巧花.曹文轩小说叙事初探.[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6]黄岚.论彭学军少年小说的叙事艺术.[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
注 释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修辞性;叙事批评;叙事学
一、叙事批评的转向
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是近些年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因不满于传统小说批评的主题学和社会学研究,着力对作品的系统和结构进行科学性研究;但因其只注重作品的静态结构和共性特点研究,忽略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遭到了评论家的批评,因此进入90年代后,叙事批评再次发生转向,并引起了叙事学研究的新革命,西方有学者称之为“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在《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中曾就此问题作过探讨,认为有关叙事学的发展学者们一般都持进化说的态度:
“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进化到后结构主义叙事学,要么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文化与历史叙事学,要么从‘严格的形式主义诗学’到‘语境主义叙事学’,要么从形式研究到注重实效的、以性别为导向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形式’的研究,要么从传统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理论。”但“叙事学”这一术语虽然作为对兴起于法国的叙事学研究的描述确实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使叙事批评发生“偏离”的“主义”或“理论”本身如果也被引入叙事学研究的讨论之中,不仅容易引起误解,而且是比较可怕的。申丹教授曾在论及解构主义与叙事学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把解构主义本身视为叙事学的新发展则忽略了二者之问的根本差异:叙事学有赖于叙事规约并在后者的范围内运作,而解构主义则旨在推翻叙事规约。”因此,厘清叙事学与受各种“主义”和“思潮”影响的叙事批评转向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叙事语法、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等。从学理上说,叙事学主要是通过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某种叙事规则,如普罗普对俄国民问故事的结构形态的研究、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事时间、叙事频率和叙事语式的探讨,格雷马斯的矩形语义方阵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这些理论家以语言学研究为前提,以艺术形式为对象,确立了意义稳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进而寻找文学形式构造的内在规律性,或者说,是从众多个性文本中寻求共性叙事规则。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文学性”就在于形式,无关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在寻求对文本进行科学性分析的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由文本的外部转向了文本的内部,或者说拒绝了传统叙事批评对作品内容的细读,而开始了对作品形式的研究。同样,也正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拒绝的”拒绝,后结构主义叙事学重新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意识形态以及文本外的社会历史语境。他们拆解了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建构稳定意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调作品意义的创造性及多元性,认为如果多种主题寄寓于文本的同一叙事模式之中,就表明一种叙事模式不可能只对应于一个主题。进一步看,如果一种模式能衍化出多种主题,那么这种叙事模式并不具有终极性地位,且这种终极性的叙事模式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先验预设。任何一种叙事模式,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历史语境中,完全有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意义内涵。
从某种程度上讲,叙事批评的“外一内一外”转向从历时性角度看是一种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对转向标准的“内”和“外”选取过分武断。作品的形式并非如传统叙事批评所认为的外在于作品,而恰恰是它的内部作品的内容却时常把意义指向作品的外部。或者可以说,作品的内部与外部之争,向内或者向外的转向,只是理论上的口舌之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从来都不可分的。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笔者认为,叙事学相对于传统的叙事批评和当代叙事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批评,它在突兀“形式”研究的同时,其他的因素相对淡化了。如果把叙事学影响下的文学批评放置于整个文学批评史,可以看出,传统的叙事批评在关注文本内外的同时,强调了外部,而叙事学批评则只关注文本的形式,完全忽略了文本的外部(社会语境);当代叙事批评在意识到并积极更正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把视野重新聚焦于文本的内外之间的关系。戴卫·赫尔曼曾指出,当前的叙事研究“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笼统地说,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问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叙事学是对文本形式的单向度强调,而当代的叙事批评并不完全排斥它关注的叙事模式在文本中的呈现,而是在继承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关心叙事模式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的特性。它不仅全面转向叙事语境和阐释语境,更将叙事研究与其他相关新兴学科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使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多元时代,从而大大拓展了叙事批评的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叙事学研究只是叙事批评传统中的一个“典型”,而两次的批评转向是叙事批评发展的必然。
二、修辞性:叙事批评转向的旨归
在叙事批评的“外一内一外”的转向过程中,叙事的修辞性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论题。尤其是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叙事批评的修辞性研究几乎成了文学评论界的一门显学,如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米歇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及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等都提出过这种修辞性叙事观,他们在坚守“叙事学”基本观点的同时,积极地把修辞学引入叙事批评,采纳从女权主义到精神分析学、从巴赫金的语言学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理论流派的典型观点,并整体形成了“叙事修辞学”研究的大语境。
但追根溯源,“在某种意义上说,修辞批评可以融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也可融入修辞批评,而二者都可以融人某种形式的文化批评”。这里,因为文化转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不是本文重点,因此不再展开。但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却是比较久远的。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是修辞学,而且从古代社会到19世纪一直是批评分析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考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为了反对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叙事批评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批评,即把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作为人类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视之为历史和文化的构成、伦理和哲学思想的体现,且“作为活动的形式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分不开的”。詹姆斯·费伦更是直接提出,“修辞是作者、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具体提出叙事修辞批评概念的是瓦特·菲希尔,他认为叙事修辞批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解读和评估人类文化交流的方法,是人们能够评判、断定某种具体的话语是否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实用的思想与行动指南”。回顾叙事的修辞特性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可以知道,修辞性其实直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而且是随着叙事批评的发展逐步登上了批评舞台的。
在传统的叙事批评中,修辞主要是指评价话语的劝说效果和作家用于以自己的观点来引导读者的方法。但是,在以再现和反映论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念中,文本常常被还原为某种社会现实或心理现实,以作品之外的世界为参照系去解释与评价作品。因此,批评家不可能产生明确的修辞意识,文本的语言、文体、叙述方式等修辞性因素必然被视为一种服务于内容的“外衣”。
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修辞研究主要是一种纯审美的观照。它们虽然注重艺术形式的修辞特性,努力探索作品叙事在修辞层面的结构和体系,却相对弱化或者取消了文本“意识形态修辞”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如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事时间、叙事频率和叙事语式的研究,达到了几乎微观的程度,但过于精细的语法化分析只揭示了修辞特性的描述层面,或审美修辞特点,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修辞的力度和意义。
与前两者相比,当代叙事批评者们对修辞性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体现为故事内外的各种关系,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行为与作者的视野不断融合,在“协同”下创造出文本意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这种观点旨在突破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作品的纯美学审视,而关注作者与读者经由了文本的连接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卡恩斯在他的理论宣言中这样说道:“就修辞性叙事学而言,我旨在通过问这么一个中心问题来有力地推动叙事学向修辞学转向:‘叙事文中的各种因素实际上是如何作用于读者的?’并通过采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解答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暂且不提卡恩斯是如何采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的,而是选取为大家所熟知的叙事视角和修辞效果评价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论证。首先,叙事文本中的叙事视角问题,因为文学作品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讲和从什么角度来讲的问题。叙事视角是叙事者的所见所闻及其价值观表达的焦点。选用叙事视角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叙事者(作者)的价值观或是对事件、人物的态度与评价。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可表明作者或叙事者(隐含作者)对叙事的介入程度,及其对人物和事件主观和客观的态度与评价。因为“隐含作者是叙事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更有可能把意识形态带入主题作用的有标记的事实”。因此,阅读就是接受隐含作者的邀请,按照特定社会程式来阅读作品,从而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其次,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评价问题。从修辞意义上看,叙事就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给特定的读者讲述某个特定的故事。所谓“修辞”指的不只是手段(如修辞格及隐喻式转义的运用),更是目的(传达知识、情感、价值、信仰等意识形态并由此“劝服”读者)。而这个叙事的“目的”就是作品的道德意义、价值观、政治功能等多维度聚合的中心,是用以说服读者的意义所在。这种通过以叙事的多维性来观望个体生命中的伦理之维,进而来了解叙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叫“复叙事”。
简言之,转向后的叙事批评不仅走出了单纯语法分析的“简单化”批评局面,不再囿于文本的内在技巧,而且还以多学科对叙事学研究的渗透来发展叙事批评,通过运用叙事学的术语和方法进行伦理、意识形态等批评,以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眼光,考察历史文化语境如何建构出某种叙事模式,又是如何把这种叙事模式加以修辞化的。
三、叙事修辞批评的积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视野中,被普遍关注的是文学的“走向”、“思潮”及种种“主义”。即使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也往往被作为“个案”纳入多种多样的当代批评视角中去,而这些批评视角对文本进行观照的理论依据及方法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如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接受美学及精神分析等,以此对当前文学创作进行多维的思考和评介。这种多元化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了叙事批评的力度,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为人们把握审美和艺术显示了宽阔的前景。它表明,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不应只允许唯一权威话语的“独白”,而应让种种不同声音参与“争鸣”,形成巴赫金提倡的“杂语”局面。对于叙事批评而言,这是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单向度走向当代叙事批评的多维度,是方法上的“视野扩展”,和批评走向上的“综合”,它意味着从以政治或审美本质为中心的单一分析转向对文学的多重属性的综合研究。它将文学的审美分析与政治、经济、社会、商业等属性分析结合起来。
相对于以前的一些批评方法如叙事学及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而言,它们由于相互对立,容易固定于一“点”而忽略其他方面。由于过分强调艺术作品的自足,而否定其他批评的合理性,也使这种批评方法走向了“固步自封”的怪圈。当代叙事批评的修辞观则避免了各种批评方法的相互排斥,使得在解释文本时既确保某一方面的修辞特点能给以最大的关注,同时也注意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修辞性在叙事中的更大修辞效果。
但是,这种由“一”向“多”的演进在丰富了叙事批评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个或隐或显的认知危机:如果各种理论流派和美学观点都仅仅满足于孤芳自赏或自言自语,那么,所形成的所谓的“杂语”对话局面本身就成了当前叙事批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不同理论及其冲突的真正意义在‘一勺烩’中相互抵消了。于是,我们都成了‘饶舌的哑巴’。或者说,文本的意义被严重地肢解了。例如,结构主义叙事学造成的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使得叙事批评未能兼顾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对文本内部的意义生成始终都持有“简约化”的认知理念。但是本着努力克服语言学分析兴起后引起的叙事和价值的分离,叙事批评的“复叙事”研究难免会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扩张化”处理。因此,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避免叙事研究上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极端,从而保证意义的充分阐释,便不能不成为叙事批评始终要加以关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