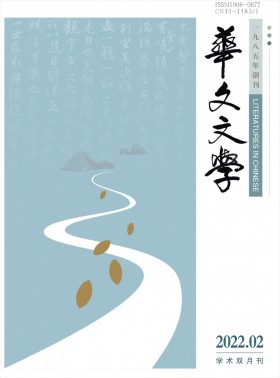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陈映真文学的叙事手法,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台湾当代文坛上,其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从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等外部视角切入所进行的解读,虽然可以展示出战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性,但所有内容的呈现最终都要落实到文本的层面,即叙事层面。作为小说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它在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相应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与作家创作理念的牵制。因此,立足于小说文本层面的叙事学研究,可以更加真切地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作家。茅盾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1]自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特别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细究他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便可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说在叙事结构重心上由情调转向情节。 一 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最后一个因素即背景很容易具有象征性,在一些现论中,它变成了‘气氛’或‘情调’。”[2]陈平原在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也把情节、性格与背景作为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他在论及“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时认为:“在‘五四’作家、批评家看来,这小说中独立于人物与情节以外而又与之相呼应的环境(Enviroment)或背景(Setting),既可以是自然风景,也可以是社会画面、乡土色彩,还可以是作品的整体氛围乃至‘情调’”,并把它看作“是对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突破”。[3] 虽说情节、人物和背景在小说创作中是密不可分的,但从小说的最初发展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看,情节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亚里士多德也曾说:“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4]但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走进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时却发现,他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情调步入文坛的。陈映真在论及自己早期的创作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惨绿”,他毫不掩饰自己早期作品所带有的那种“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有些作品干脆以此为题,如《凄惨的无言的嘴》《一绿色之候鸟》。在以许南村署名的《试论陈映真》中,他把投稿于《笔汇》月刊的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一年视为这种“惨绿的色调”最为浓重的时期,典型的作品即为他于1960年1月发表在《笔汇》上的《我的弟弟康雄》。作品虽以《我的弟弟康雄》为题,但通观全文,人物的形象却十分模糊。关于康雄,我们只知道,当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当他死了之后,“他的胴体白皙一如女子,头发多而秀美,眉目清秀,一身未熟的肌肉”。而“我”有着“几分秀丽的姿色”,婚后变得“懒散、丰满而美丽”。从“我”的回忆和康雄的日记中,我们大致知道了这姐弟俩的生活轨迹。因为母亲的早逝,让“我”对弟弟康雄疼爱有加,而他也像“爱着死去的妈妈一样”地爱着“我”,曾经的“我”很受弟弟康雄的影响,“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苦恋着一个苦读的画家,但在康雄死后不久,“我”却毅然地将自己卖给了财富,嫁进了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也许这一生就“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爱抚里”;而终其十八年生命的康雄,则经历了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虚无者的雏形,最后在与一个“妈妈般的妇人”的相恋中失去了童贞,在灵魂的自责中“终至于仰药以去了”,而留给“我”无尽的悲伤。如果我们从人物、情节的层面来评价这个作品,大概不能算是成功,但除了情节和人物之外,“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小说的色彩和情调。每一篇小说也像一首歌、像一幅画一样,是有它的色彩和情调”。[5] 这个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也正是它的情调。小说中情节的散淡和人物的模糊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气氛,并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给整个文本抹上了一种“惨绿的色调”。充斥着整个文本的是“我”的悲伤与思慕,也有敏感而脆弱的弟弟康雄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渎的喘息”,“自责、自咒、煎熬和痛苦的声音”,那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带来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这一抹“惨绿”在陈映真同期的小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故乡》《死者》《祖父与伞》和《凄惨的无言的嘴》等,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陈映真之前的阅读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早年的人生境遇有关。他曾回忆,1958年他到淡水英专注册,并在那时“突然对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他查英语字典读着英国文学史而不能满足,开始把带在身边的、从父亲的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不记得是什么人写的《西洋文学十二讲》,津津有味地啃着,写一本又一本的札记”。[6]20 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厨川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一文艺观已深入他心,并与他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身份、因家道“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6]4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继而用创作来舒解内心的这种情绪。从小说叙事的结构立足点看,本是作为背景存在的情绪氛围由于太过浓郁,如浓雾般遮蔽了情节。因此陈映真早期的作品更偏向于一种“情调小说”。 二 在《后街》中,许南村说:“他(陈映真)大体上是属于思想型的作家。没有指导的思想视野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6]27但是,“思想发酵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实践和运动的饥饿感”[6]38,一旦从咀嚼着个人悲欢的小世界中走出来,他的问题意识便鲜明起来了。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自述从1966年寄稿于《文学季刊》始,风格就有了突兀的改变。他这样描述这种改变:“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以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抒发。”[6]8这种思想上的改变,在叙事结构上的体现就是结构的重心开始由情调向情节倾斜。“所谓情节概括地讲,也就是对于人的行为有目的地加以使用,其功能是对生活的原在形态中的那些相对的混乱与无序状态作出挑战,这种挑战的实现前提是:被纳入文本的那些表现人的行为的事件,通过某种因果关系而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因此,“情节的魅力来自于其内在的整体性”,借助于情节,我们可以“从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里抵达理性的彼岸,对大千世界的奥秘与人生世相百态作出居高临下的把握”,从而达到一种“十分饱满的审美快感”。[7]#p#分页标题#e# 显然,从情调向情节的倾斜,意味着作家思想中理性成分的增加和对现实的关切。情节来自于对生活的提炼,虽然在陈映真早期的小说中也有情节可寻,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他太过于急切地表达某种情绪,所以对情节的逻辑性关注不够,这在他的有关精神病患题材的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凄惨的无言的嘴》主要以第一人称“我”这样一个内视角展示了一个精神病人的情绪流变,虽然间或描写了“我”与医生、高小姐、郭先生等人的交往,描写了散步时看到的一个被杀的雏妓的尸体,但所有这些事件的呈现都是被“我”的思绪所牵制,从事件内在的逻辑性来看是错杂的。相比之下,稍前的《文书》似乎故事性更强一些,在一份杀人案的卷宗中,作者在“自白书”中分别描写了“我”的童年生活、军旅生涯和婚姻生活。但正文开始之前有这样一个说明:“故血案之起,职以为出于疑犯劳碌终年,致精神异常所致也”[8]10,这一说明消解了故事的可靠性。而在文本中把“我”人生的这三个跳跃性极大的阶段联在一起的,是一只有着“翠绿的眼睛”的“鼠色”的猫。这只猫在文中应该是有象征意味的,自从十岁那年它嗅去了“我”的灵魂之后,“我”便再也无力摆脱了,这只猫的存在,让整个文本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氛围,主人公也在这种灵魂的审视下终于精神失常。在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叙事中,他把情调(或者情绪)作为他结构的重心,当他有意识地开始从生活中提炼情节时,则是他自称的风格突变的时期。在同样以人名为题的《唐倩的喜剧》中,由于作者自觉地采用了一种理智的、冷静的姿态,所以情感的抒发在这里被隐去,情节的演进有意识地走到了台前。作品的结尾处,有一则附记:本文系虚构故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倘有与某人之事迹雷同者,则纯系偶合,作者概不负责。又:文中所引里尔克的诗系李魁贤译文,载《笠》诗刊第十三期。[8]136 可见,在《唐倩的喜剧》中,作者构思叙事结构的情节导向是很明确的。与康雄支离破碎的人生碎片不同,作者决定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他截取了唐倩“在一个沙龙式的小聚上”出现到“离开了国门,到达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去了”这一时段,完整而又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时期她的婚恋经历和思想经历。以唐倩的婚恋生活为主线,先后引出了诗人于舟、以存在主义教主身份自居的胖子老莫、始而主张“新实证主义”继而持“质疑主义”的年轻的哲学系助教罗仲其及留美的青年绅士乔治•H.D.周(周宏达)。他们和唐倩展开了不同的人生故事,带给她不同的人生哲学,但最后却在唐倩的认识中归于同一。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然而,不久唐倩也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性生活里的那种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质,无不是由于深在于他们心灵中的某一种无能和去势的惧怖感所产生的。胖子老莫是这样;罗大头是这样;而乔治•H.D.周更是这样。[8]135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先以崇拜者面目出现的唐倩,最终却成了她所崇拜的对象的终结者。借助于唐倩的人生喜剧,陈映真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几乎是冷眼旁观式地完成了他对台湾当代知识界现状的理性审视,这里有对知识分子内心去势感的嘲弄,对标榜各种主义者的讥讽和对崇洋媚外者的不屑。《唐倩的喜剧》是陈映真小说叙事结构重心由情调向情节转移的有意尝试,从技巧的圆熟性来看是值得商榷的,情节的单线展开固然有利于故事的完整性,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个遗憾在陈映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创作中得到了弥补。 三 陈映真曾说:“一个作家要言之有物,要有思想,要有主张,可是呢也要有审美。”[6]47于1978年复出后的陈映真,在小说创作方面主要致力于两个题材:一是对上世纪50年的白色恐怖的表现,以此来升华历史的伤痕,见证人性的高度;二是对跨国企业中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扭曲的描写。与前期小说相比,他复出后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容量也更为丰富了,与此相应的,也越来越自觉地把情节作为小说叙事结构的重心。陈映真曾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因为是搞现实主义,不能凭空杜撰,那么我写小说,特别是后期的,总是要写笔记,我要表现什么,角色甲是个几岁的人,哪一省的人,他是干嘛的,等等,写了很多笔记。”[6]47 而1980年8月发表在《台湾文艺》六十八期上的《云》,就是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的小说化。可以想象,采访笔记上的材料是琐碎的,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而小说的展开则是连贯的,有其内在的整体性,所以,这个“小说化”的过程就是从原生态的生活中提炼情节的过程,并借此传递作者的看法与态度,同时,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接受这个故事,还必须有艺术上的技巧。因此,在《云》的写作中,他避开平铺直叙,而是以张维杰的回忆和小文的日记两条线索展开情节,详细记录了在美国麦迪逊仪器公司所属的中坜工厂中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从酝酿、组织、抗争到最后流产的全过程。张维杰作为公司组建工会的代表,从他与公司上层的冲突中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台湾经济的渗透和控制;而小文作为女工中的一员,见证了工会改革的艰难和女工觉醒的全过程。两条情节线索的交叉推进,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与人权的虚伪性。 《赵南栋》写于1987年,其素材直接来源于陈映真的狱中经历。在那里,“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6]23,同时又兼顾了台湾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在陈映真的精心组构下,历史和现实的完美对接成为可能。小说以叶春美、赵尔平、赵庆云和赵南栋四个人物为题,分四个部分,或回忆,或陈述,或无意识呈现,展示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在叶春美的回忆和赵庆云的无意识呈现中,宋蓉萱、许月云、张锡命、林添福以及蔡宗义等人纷纷出场,历史就在他们身上鲜活起来了,“五○年代初叶,台北青岛东路口军事监狱里,世纪的沉默啊,不是喧嚣地诉说了千万册书所不能尽载的、最激荡的历史、最炽烈的梦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飙般的生与死吗?”[8]313在赵尔平和赵南栋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则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曾立志磨砺人格人品”的少年怎样一步步地“滑进了一个富裕、贪嗜、腐败的世界”,“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怎样在“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中,崩解净尽”。[8]353-354在情节的交替演进中,让时间与空间交错,让历史与现实碰撞;既有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有“让身体带着过活”的随兴;既有时代错位所带来的隔膜,也有人性分裂后的温暖弥合;有一种历史的深邃感和现实的厚重感,升华了历史的伤痕,见证了人性的高贵。而多样化的叙事角度则使作者对情节的把握游刃有余。#p#分页标题#e# 如果说陈映真早期的小说是以情绪的抒发、情调的营造为主,情节是若隐若现、支离破碎的,那么,在他后期创作中所运用的情节策略则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出他对生活的理性把握,这得力于他对文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在《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中说:“文学的根本性质,我觉得,是人与生活的改造、建设这样一种功能,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予失望的人以希望,给遭到羞辱的人捡回尊严,使被压抑者得到解放,使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人有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和恋爱快乐的人一同快乐,给予受挫折、受辱、受伤的人以力量,那样的文学才有意义。”[6]40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鲁迅先生“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主张。陈映真小说叙事结构由情调向情节的重心转移,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思考者”思想的丰富性,从早期知识分子内心苦闷的倾诉转向对知识界现状的冷静审视与理性讥讽,对台湾社会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对历史的回顾与探究。从这条“历史的巷道”中走来,我们看到了陈映真与现实主义的深情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