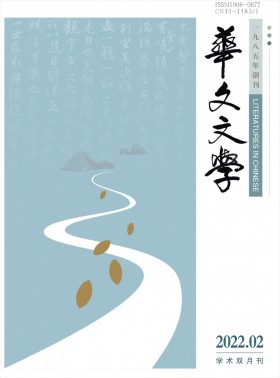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中的媒介叙事理念,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媒介叙事结构 从叙事上来讲,小说、电影同属于叙事艺术,它们都通过故事情节与结构展开叙事,不同之处则在于小说与电影在各自的叙事上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一方面,小说在叙事中通过人物、情节、环境展开具体叙事,依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叙事线索将全篇贯穿起来,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充分激发受众文本阅读上的审美感知能力。在审美感知中,通过对文本的赏析与解读在想象中完成对剧中人物、事件的评判,实现对小说整体叙事体系的认识与理解。不同的是受众对小说叙事体系的把握会因自身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小说的相关历史了解的深度以及对小说的熟悉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 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自古以来因其作品中蕴涵了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众所周知的是在小说中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家庭叙事体系,将人物、情节和环境有机贯穿起来,展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的演变过程。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对小说叙事体系的把握往往是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悲剧作为贯穿全篇作品的叙事主线,并以此展开对贾府中其他人物形象的理解与把握,并以贾府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进而延伸到对王、史、薛三大家族叙事辅线人物关系的认识。在叙事中,小说紧紧围绕三人的爱情悲剧展开,在四大家族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细节描述,以小见大地展现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读者在阅读中会根据自己对文本侧重点的不同而对小说的人物结构、叙事体系有不一样的认识。对以贾府为主的叙事体系的构建也会因对作品认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不同的人阅读《红楼梦》,对其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主体的叙事体系会有不同的感受与认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阅读中也会因认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不同的审美体验决定了读者在阅读中形成特有的审美价值,这也是《红楼梦》成为经典的重要缘由。 另一方面,在电影叙事中,小说经过改编将剧中的呈现对象主要是通过画面与声音进行视听化传达,在传达中充分调动受众的视听感官完成叙事上的感官传达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主要是通过独特的影像叙事手段———蒙太奇来完成,即通过剪辑使影片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影像片段衔接起来,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故事。与小说叙事不同的是,在电影叙事中,主要通过视觉与听觉的感官配合实现对故事的感知,在视听语言的刺激下结束对影片的审美体验过程。如在张艺谋根据严歌苓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从影片叙事的角度来说,全片紧紧围绕一座未被日军占领的教堂里的学生、风尘女子、殡葬师约翰、李教官等不同阶层的人在劫难面前的生死抉择展开叙事。影片用悲壮场面传达出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场景,全片以玉墨为叙事的核心,以约翰为叙事主体,以书娟等人为叙事辅线,在影片叙事中通过流畅的剪辑将故事的叙事重点放在了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片中张艺谋充分发挥影像的叙事功能,通过用影像对人物的行为表现、细节刻画展现他们在生与死面前进行的抉择,用影像实现对战争的追忆与思考,观众对这一切的把握往往是通过画面与声音的视听感知来完成对影片叙事线索的理解。 因此,从叙事上来说,小说、电影在叙事中都离不开人物、情节、环境等叙事要素,都是以人物为叙事核心,围绕特定的情节,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叙事。不同的是在小说叙事中,受众对叙事要素的感知是虚拟的、不可控的,不同的人由于阅历、受教育程度、知识素养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对同一部小说的叙事产生不一样的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对这些要素的感知没有固定的形态,在感知中服从的往往是受众对叙事元素的认识,而受众对这些元素的认识也在不可控的范围之内。在电影叙事中,受众对叙事元素的感知是有形的、可控的,电影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叙事元素是可视的、可感知的,这些元素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喜好而发生改变,而导演根据剧本对叙事元素进行的影像化呈现,叙事元素服从的不是受众意志,而是导演风格的体现。 二、时空叙事形态 在小说叙事中,一般认为,小说属于时间艺术,电影属于时空艺术。其实,从叙事角度来说,小说不单单属于时间艺术,也应该属于空间艺术,只不过这种空间艺术的影像显现并不像电影那样是可视的、可控的,而是伴随着读者阅读小说的时间进程,小说的人物形象、环境等影像会随着读者的阅读想象呈现于读者的头脑中,这种想象影像的呈现只有阅读者本人可以感知,虚拟空间影像的显现程度与效果因人而异。因此可以说,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显现在头脑中的空间影像是一个虚拟的时空。从这一点来说,小说同电影一样都属于时空艺术,二者都是在时间与空间中完成叙事。不同之处就在于,小说的时间艺术体现为在一定的时间段中完成叙事,传达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受众在阅读中处于主动地位,可以随意控制自己阅读的时间,从接受模式上应属于受众主动接受;小说空间艺术的体现则是在受众阅读中,在时间的延续中依托于受众的想象实现小说空间上的审美传达,也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等通过文字语言的描述,受众依靠对人物形象、生活场景的感官认知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影像,读者依据自己的阅读习惯将这些人物、场景等随阅读的进行一一地想象呈现,这种空间叙事的完成是受众在对小说的感知空间中独立完成的,空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一种假定的空间存在,只存在于受众的头脑中,被受众独立感知。 在电影的时空叙事中,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时空艺术形态,在时间上,则要求电影在特定的时间段中完成影片的叙事,要求电影在有效的时间中传达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受众在欣赏中处于被动地位,受众在欣赏中不能控制电影播出的时间进程与影像的呈现方式,只能用自己的视听感官进行被动的接收,在接受模式上属于受众被动接受;而电影的空间艺术则要求电影通过画面与声音的影像化呈现,观众通过银幕在视觉暂留原理的作用下看到真实、立体、可感的运动影像,听到同步的立体化声音。 #p#分页标题#e# 当然,这种空间叙事完成的前提,需要电影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而不单单是一些视觉符号的拼贴组合,这就要求导演在改编中不仅要为观众呈现流畅的视觉画面,更要用紧密的影像逻辑去讲述故事,展示电影立体化的空间叙事能力。 在改编中,小说与电影各自不同的媒介呈现形态,决定了小说、电影在叙事角度、时空叙事上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与视听体验。在改编的问题上,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曾指出:“小说通常采用假定的空间,通过情节的时间顺序来形成它的叙述,并通过时间的演变来造成读者心理上的空间幻觉,而电视剧通常采用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调度、画面的蒙太奇来形成它的叙述,并通过空间的演进来造成观众心理上的时间幻觉。”[1] 空间幻觉的出现是在想象中才能完成的,小说与电影、电视时空叙事艺术上的相近性也决定了小说成为影视改编最为主要的素材来源。在叙事转换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侯克明教授认为:“从小说到电影,故事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转换,必然产生畸变。一部分改变是出于适应不同艺术形式的需要,而另一部分改变则完全是出于叙述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2] 小说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呈现形态,在媒介叙事结构、时空叙事形态上带给受众不同的审美感知方式,二者在介质形态上的不同表现也决定了小说与电影各自在叙事上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正是在媒介叙事结构、媒介呈现形态上的相近性,才使得在改编中把小说转化为电影成为可能,在表现形态上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小说与电影在各自的时空中会带给受众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在当今电影产业发展中,如何将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影像化呈现,如何在媒介形态的转变中提升电影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品质,不仅仅是电影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电影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去研究与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