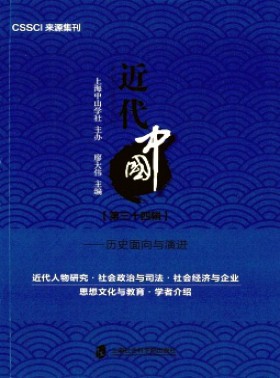一、近代化学教育变迁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教育回顾》将化学教育放入科学教育的视野,把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学习苏联阶段、探索阶段、十年动乱阶段、调整尝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周天泽、胡定熙的《化学和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拓》介绍了我国科学教育“准备”“启蒙”“开展”3个阶段中化学和化学家的推动作用,并从该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情况。WilliamH.Adolph是原齐鲁大学教师,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学课程、教材、学校状况以及人们的科学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了解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情况。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高等化学教育和基础化学教育,对于更为具体的近代中学化学教育,相关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4]、樊冬梅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878-1922)》、解亚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亚对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化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包含在科学教育这个大的范畴内进行说明。作者认为,从1878年到1922年,我国科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制度化、从学日到仿美的发展过程,1922年到1949年则可分为新学制颁布后的科学教育(192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1927-1937)以及战乱时期的科学教育(1937-1949)三个阶段。
二、与近代化学教育相关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化学教育有三个重要的起源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会学校。袁振东认为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它开办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江家发、陈波的《中国近代化学课程始端———“京师同文馆化学科”体系溯探》认为同文馆已经具备了学校近代化学的课程体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徐振亚的《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育》从化学课程的开设过程、师资、教材和考试制度几个方面对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他如《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自然科学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论文,对同文馆的科学教育及其在中国近代科教启蒙和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化学教育多有涉及。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事业。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综述》中从翻译馆发展、翻译目的、赞助人、书目考证、重要译者、翻译方法、译著影响、译名统一、相关个案研究等9个角度,对近3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而有关江南制造局对化学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门研究则比较少见。江家发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书籍,其中的《化学鉴原》被很多学堂、书院作为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译馆陆续译出的《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学专著,将西方化学的各个分支系统而完整地引入我国,对近代化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译馆的徐寿、傅兰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首创了中文化学译名原则,对中国化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年)》介绍了近代教会大学的化学科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他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化学课程与教材》中认为我国近代的教会大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保证了其培养水平与国外大学基本一致。对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论文《徐寿———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杨根的专著《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以及近年来汪广仁等人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傅兰雅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引进、传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徐振亚的《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等专著和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和思想。戴吉礼(FerdinandDagenais)的《傅兰雅档案》则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记、往来书信、翻译成就和相关论文集等资料,为研究傅兰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近代中国的不少化学教育家同时也是化学家,他们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学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而为基础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郑贞文和杜亚泉,研究者则较少关注。郑贞文与杜亚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编译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书,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郑贞文的研究仅有少量传记,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中的条目介绍,以及张澔的《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钱益民的《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等对其在我国早期化学教育、统一化学名词和编辑出版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对杜亚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处不赘述。对其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的研究,阎乃胜进行了综述[7]。李学桃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阎乃胜的《杜亚泉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研究了杜亚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其编写、编译的教科书进行整理,高度评价了杜亚泉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其在化学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辉认为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理科编辑,是“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8]。刘晓嘉的《杜亚泉编辑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编辑思想与贡献》、陈镱文等的《杜亚泉对我国早期科技编辑和科技期刊发展的贡献》结合杜亚泉所处的时代,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了其编辑出版的理科教科书、科技期刊等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与普及的重要贡献。
三、对中国近代化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化学工艺和经验化学有着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科学的近代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从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指出近代化学“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研究对于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化学史专著,如我国第一本中国化学史专著———李乔萍的《中国化学史》、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以及近年来周嘉华等的《世界化学史》,侧重化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涉及我国的内容多为古代化学成就,对中国近代化学、化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没有涉及。部分化学史专著,如赵匡华的《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郭保章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略》、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化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其中涉及化学教育在中国的起步与开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袁振东的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依据史料对1927-1937年“南京十年”时期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认为这10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为此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培富等的《书籍史视阈中的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考察———基于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化学著作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民国时期化学著作的出版要素进行计量分析,结合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书籍史角度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微观的历史考察。
四、近代化学术语研究
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名称是化学语言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构建化学学科的基础。由于东西方语言的差异,为元素、化合物命名首当其冲地成为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后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与人文学科,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比,近代中国的化学教育在翻译创制学科名词方面有着更为特殊的情况。这是在近代中国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领域。著名化学教育家张子高在《从〈化学初阶〉和〈化学鉴原〉看我国早期翻译的化学书籍和化学名词》中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化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上海、广州两地的知识分子在早期翻译工作中对化学名词术语的制定过程。WilliamH.Adolph在《SynthesizingachemicalterminologyinChina》一文中回顾了中文化学命名法的产生历史,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我国所使用的中文化学命名方法和基本原则。夏文华的《晚清民国时期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生成历史的文化考察》梳理了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生成的历史进程,从文化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的生成史进行考察,归纳出了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生成的一些特点,并对参与化学元素名称统一审定工作的化学家群体的各种背景作了分析。何娟的《清末民初化学教科书中元素译名的演变———化学元素译名的确立之研究》《清末民初(1901-1932)无机物中文命名演变》,江家发、冯学祥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法的演变》,张澔的《中文无机名词之“化”字(1896-1945年)》《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名词———中文有机化学名词系统命名的开始》,江家发、郑楠的《我国有机化学命名法的历史演进》,孔健的《有机化学命名小史》对化学分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中文译名和命名的演变情况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何涓的《化学元素名称汉译史研究述评》对化学元素名称汉译史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认为现有的多数研究在资料利用上层层相因,对众多科学期刊和化学教科书究竟如何使用元素汉译名的研究较少涉及,使研究的深度和视野受到了限制。温昌斌的《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及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介绍了于1932年成立的国立编译馆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认为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多批由该馆编审的名词,使国内科学名词,包括化学名词,逐渐趋于统一。张澔在《中文化学术语的统一(1912-1945年)》中对当时的教育机关、学术团体以及专家学者为化学术语的统一所作的努力、遇到的问题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国立编译馆和中国化学会相辅相成,在中文化学术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化学术语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近代化学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作为学校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在教育体系中意义重大。对教科书的研究向来为教育史和科学史研究者所重视,以上的几方面研究对化学教科书均有所涉及。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专门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问世,相关的专著和论文主要有毕苑的《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吴小鸥的《近年来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综述》。这些研究工作对我国近代教科书的出版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对教科书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百年来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在分析教科书的发展变迁时,研究者们多从文史类教科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说明,对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尤其是化学教科书的研究分析则相对较少。潘吉星的《明清时期(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和黎难秋的《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对明清时期我国出版的化学类书籍进行了考察与整理。潘吉星从内容分类、出版年代、原著来源、翻译情况、出版地点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在这些化学译著中,综合性化学学术著作(包括分析化学著作)占24%,农业和药物化学占7%,应用化学占36%,化学通俗读物占12%,中等化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占28%;译自英文的最多,占50%,多为学术著作,译自日文的次之,占36%,多为通俗读物和中级教材。在这些化学书籍中,部分综合性化学学术著作和化学通俗读物被用作清末洋务学堂的化学教科书。对这类书籍,汪丰云等人在《清末民初几本代表性化学教科书介绍》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化学初阶》《化学指南》《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卫生论》等早期化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和翻译、使用情况。作者认为这一批译著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化学教科书,其中1870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GlasgowKerr)与何瞭然译自《Wells'sPrinciplesofChemistry》的《化学初阶》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有系统内容的普通化学教科书。对这类早期化学教科书的相关研究还有王扬宗的《关于〈化学鉴原〉和〈化学初阶〉》、张青莲的《徐寿与〈化学鉴原〉》、吴又进的《晚清第一本分析化学译著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化学分原〉研究》、李桂琴的《晚清译著〈化学入门〉研究》、季鸿崑的《〈化学卫生论〉的解读及其现代意义》、吴又进等的《中国最早的分析化学译著———〈化学分原〉》、潘吉星的《清代出版的农业化学专著〈农务化学问答〉》等。梁英豪等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对几种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化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和编写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当时化学教科书的特点进行了总结。郭震在《化学与爱国———从近代化学教科书中看国情与爱国教育》中认为提倡爱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当时学校教科书无法绕开的主题,化学教科书的作者在编写时也非常注意在教材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以期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六、小结
从以上的文献分类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有关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研究多散布于近代教育研究和化学史研究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化学教育的系统化专门研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已有的成果对近代化学教科书本体的分析十分欠缺,对各版本化学教科书的源流演变、编写及使用情况很少涉及,这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近代化学教育和教科书图景始终是抽象的、模糊的。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是化学研究和学习的基础,化学实验教育始终是化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尚处于启蒙时期的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中显得更加重要,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欠缺。另一方面,影响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潮和百年来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促进化学教育和化学教科书发展的直接外在动力,已有的研究对于这两方面对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的影响则少有涉及,需要研究者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多地对此予以关注。
作者:郭震 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课程教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