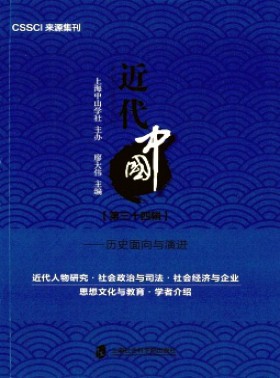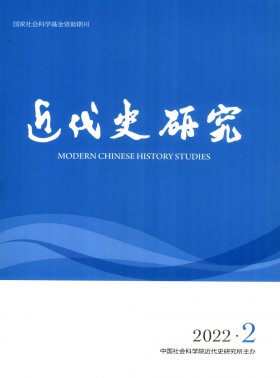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近代民法法典化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从近代法典编纂历史看,法典编纂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个社会内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导致法律的演化,二是外力的推动。国家是法律制定的主体,法典编纂和一国的政治状况也是密不可分的。谢怀栻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移植外国法律,必然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原因。纯粹的‘被迫’或纯粹的‘自觉’都是极少的。不过在有的情形,被迫的成分大一些;有的情形,自觉的成分多一些。”[1]而清末的民法法典化是“后生外发型”的,其变革也是内外原因综合的结果。 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在谈到法律和经济关系的时候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无论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的立法,都只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3]可见,法律作为经济的表现形式,离开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不可能得到生长和发展,特别同人们的经济生活更加密切的民法。中国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4],只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才开始逐渐解体,新型商品经济形式随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清末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5]可见,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6] 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末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已有阶级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要求构建一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环境,要求政府从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开始逐渐渗透到新式的工矿企业和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封建势力的阻挠,使得工商业者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集团与外国资本同台竞争,不仅得不到本国法律(因为中国封建法律规定的多是限制商业的发展的规范)的保护,而且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从而始终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民事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而与此同时,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社会大众,其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也拥有部分财产,也要求法律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益,赋予更多的、与资本家阶级一样的、平等的民事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也迫切希望通过变革法律使自己被赋予平等的民事权利。 所以说在整个社会,无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政府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清末旧有的法律《大清律例》无法调整这种新型的关系,惟有变革旧的法律,构建新型的民事法律规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二、政治上收回“治外法权”的策略需求 (一)“治外法权”的丧失和政府对变法的推动 “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是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后通过军事优势在中国攫取的司法管辖权,它使得中国政府丧失了对在中国的外国侨民的管理权利。从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始,英、美、法、俄、德、日本等20多个国家相继在中国取得了这样的特权。这种特权的取得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主权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现实政治制度反思。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则从法律制度的改革入手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摆脱民族危机。为此,清政府从丧失之日起就不断同西方国家交涉,希望能收回这一权力。但是西方列强却要求清朝政府“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并作出承诺:“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实,皆臻完善,英国即允弃其领事裁判权。”[7]随后日、美、葡三国先后作出类似允诺,这无疑给清政府内部改革派以希望,于是各封疆大吏纷纷上书条陈变法,最著名是以两疆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的“江楚会奏三折”,他们在第三折中写到“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转化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8]在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西方国家有条件地放弃“治外法权”的允诺,极大地鼓舞了清政府。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明确下诏指出了变法的理由,并表达了变法的决心和变法的宗旨,同时要求各地推荐变法人才、各住外使臣搜集各国律例,为变法作准备。谕旨称“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9]从谕旨内容来看只字未提民法,而对民法典编纂首次提及主要来自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三位清廷重臣在保举修律大臣的奏折中,在谈到修律应效仿日本时说:“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也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叹服。”[10]应该说这是清末修律前官方首次提及到对民法的注意。#p#分页标题#e# (二)社会精英对民法的关注 民法是近代西方法典编纂最重要的部门法,是西方社会张扬民权的重要载体,它为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马克思说“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清末的一批有识之士在主张变革旧律的同时也开始对西方的民法典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重视。最早对民法给予注意的是总理衙门附设的同文馆对《法国律例•民律》的翻译。1861年为培养翻译人才,清廷总理衙门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于翌年开学,1866年来自法国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化学教习毕利干将法国法翻译成汉文,时称《法国律例》,于1880年出版。其中的《民律》、《民律指掌》实质上就是《法国民法典》,共22册,占了近二分之一的比重。毕利干为何要将卷帙浩繁的《法国律例》翻译成册,我们从现有的史料中无法得到答案。但在《法国律例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同文馆化学毕利干教习,系法国好学深思之士。着有化学指南、阐原各书。翻译成帙,而于刑名,尤本诸家学。兹后因授课之暇,商同丁总教习,率化学馆诸生,译出法国律例共四十六卷。”由此可见,毕利干之所以翻译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测出民法在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地位是非常之高。《法国律例•民律》可以说是它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模式的法典。[11]在中国民法近代化史上的开启性的意义。这也可从梁启超和康有为对此书都曾作过评价和分析得以证明。正是在毕利干翻译的《法国律例》基础上,维新派人士开始注意到民法编纂的意义。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这样写到西方国家近代法典化运动:“外来人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行施定,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12] 尽管康有为并不能对民律和民法作出正确的区分,但是能注意到民事法律规范的重要性已是难能可贵。维新派的另一泰斗梁启超1904年撰写《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通过对日本民法学研究成果的研究,特别是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的《民法原理》和穗积陈重的《法典论》,提出了法律之种类可划分为“主法和助法。主法者,实体的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是也。助法者,施行法律之法律,如议院法、选举法、行政裁判法、民刑事诉讼法,乃至其他为一时一事所制定之特别法皆是也。”而“主法明大纲、助法明细目”,[13]二者在法律中的地位是有所区别的,民法是主法,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是不同于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也不同于民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而法典编纂的次序应是先实体法后程序法,民法作为重要的法律部门,理应是先行编纂,这是梁氏从法典编纂的角度提到的民法在法律部门体系中编纂的重要性。应该说维新派对民法编纂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进步人士对西方民法价值的认同,对《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清末的一些政治家在同西方制度接触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编纂民法典的必要性。早在变法开始之前,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三位总督在保举修律大臣的奏折中奏称“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也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叹服。”[14]这是指近代日本在民法典编纂上产生“新旧民法”的论争,强调中国在变法时也应该注意民法编纂问题。显然这是清末立法原则“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务期中外通行”的体现。清末思想家、政治家所从事的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在一定意义上为民法典编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德日民法典编纂的模范效应 清末法制变革是“后生外发型”的,而“后生外发型”的典型特征是其法律制度的变迁并不完全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而主要是外力催生的结果。清代末年这种外力就是收回“治外法权”和“富国强兵”的政治需要。所以沈家本在谈到清末修律的直接动因时说:“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15]从1901年提出变法开始,清政府就开始着手选择达到这一目的的“灵丹妙药”,一方面于1905年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他们的足迹遍及日、美、德、法、俄等15个国家。同时也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德国和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迅速强大的示范效应倍受清末统治者的青睐。 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反法同盟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国内共有300多个独立的邦国,1871年普鲁士邦宰相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武力统一了德国。从1871年开始到1897年德国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商法典等六部法典,标志德国法最终形成。特别是统一民法典的制定,经过了理性主义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蒂堡教授和实证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之间关于法典编纂的论战,这场争论最终使得德国统一民法典冲破了法国民法典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国式的“潘德克顿”体系。《德国民法典》以全新的风格确立了民法典编纂模式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民法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进来,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等,这无疑也使清政府感到一种新制度的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呼吁“仿照德制”。 [16]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主张“请远法德国”。[17]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也强调“以德为借镜”。[18]因此在选择民法典编纂模式时采纳了“远法德国”的原则。#p#分页标题#e# 近代日本更是创造了神话。近代日本也先后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日本也获得了“治外法权”。而日本通过变革传统法制,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民法的制定上经历了由具有民主主义革命特征的法国民法向具有封建保守特点的德国民法的转变。日本借此不仅收回了“治外法权”,而且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的东方成员。中日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了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举国大哗,方知国力不足恃,旧法不足尚。”[19]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重创了号称“北极熊”的沙俄,再次震惊了清朝统治者,“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20]这两起事件使清朝统治感到拥有类似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日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西方列强俱乐部成员是与其近代法律的法典化休戚相关。而日本法律法典化过程中,民法典的编纂引起的争论最大,它最终兼收了封建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的二方面的因素移植了德国民法典,清朝统治者从中看到了希望,决定“近采日本”。 三、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整体要求 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其法典上的表现是混合式法典,从战国时的《法经》到清末的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体现出这种混合式特征,虽然各种法律部门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其渊源。但是民法只是被看作是“田债、钱粮”等细故,且民事纠纷采取了科刑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随着清末《大清新刑律》的编纂、一些商事法律的颁布以及程序法的制定,民事纠纷的调整手段明显缺位,因而民法典的编纂尤为迫切。 诚然,法律体系的架构是各部门法律的有机结合,缺乏任何一个部门法,法律体系都是不完备的。清末随着法律改革的深入,民法典的制定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06年7月当时的《时报》刊登一篇题为《改良法律所应注意之事》,从法律体系构建的角度论及了民法典编纂之迫切性以及立法的次序问题:“法律分析多门是,然大别之,实民法,刑法两类,其余皆从此而生,而法律之精神,实也寄于此。盖专制国之法律,命令而已。其条文皆注重上与下之间。至于人民与人民之交涉,视之殆无轻重。自民法独立,别与刑法分驰,然后人民之权利,日益尊重。然民法又原于宪法,宪法未立,又几无民法可言。故必次第分明,然后下手不至错乱,得收相维之益。今者民法未立,而商法先颁,民事刑事诉讼法又相继出焉,学者常议其本末倒置。”[21]可见清末修律集中在刑律、商律和程序法的的修订上,而对“西方近代法律真正心脏—民法典”[22]的编纂却没有能够给以足够的重视。 1907年4月《南方日报》同样刊登了一篇题为《论中国急宜编订民法》的文章,该文也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论述了民法在当时的中国编纂的重要性。“今之所谓法治国者,大都合君臣上下而一出於法,法之范围非常宽泛,悉数之不能终。然究其大要,在上则为行政法,在下则为民法。”“我中国自预备立宪以来,朝廷之上亟亟注重於行政一方面,而于民间私法之一部分迄未议及。殆未知民法之关系於人民者重且大欤。”[23] 既然是以法治国,众多的法律部门是必不可少的,民法典的编纂涉及到人民之权利,其关系重大。同年针对民法立法的迟缓,新成立的民政部从自身的职责出发,通过对各国民事法律编纂的比较,在上奏的《请速定民律折》中,对西方法律分类、公法和私法关系、二者对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不同价值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速定民法。奏折中有言:“刑法所以纠匪僻于已然之后,民法所以防争伪于未然之先,治乎所关,尤为切要。”又言“临事有率由之准,判决无疑事之文,政通民和,职由于此。中国律例,民刑不分,……,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语焉不完……。仰体圣谟,深思职守,窃以为推行民政,彻究本源,尤必速定民律,而后良法美意,乃得以挈领提纲,不至无所措手。”[24]1907年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在《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奏折》中从民法和刑法的关系谈到了要编纂民法的意义。他说:“民法为刑措之原,小民争端多起于轻微细故,于此而得其平,则争端可息,不致酿为刑事。现今各国皆注重民法,谓民法之范围越大,则刑法之范围愈小,良以有也。”[25]应该说随着法律近代化的推进,立法者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使得民法的法典化显得尤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