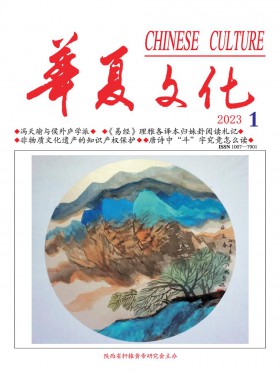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化研究中身份的语义危机,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族裔散居将个体与集体置于不同的文化、种族、民族中,同时将他们所面临的身份归属问题推至风口浪尖,从而引发了个体与集体的文化、种族与民族“身份危机”。费瑟斯通在论及全球化与身份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指出,[1](P166)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以前在社会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现在存在于社会内部。迁入者消极接受民族或地方的主流文化的无意愿性引出了文化多元主义与认同破碎化等问题”。此外,有关种族、民族、国家、大规模移民潮、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等问题的思考与论争,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对身份问题的研究。正因为“身份”处于“危机”的状态才促使它成为目前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那么究竟什么是“身份”(identity)?无论是国内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对“identity”的多种翻译方式,还是国外学界对“identity”一词的语义内涵界定的质疑,①都表明对“身份”的语义内涵有必要重新审视。本文从“身份”的语义内涵的变化与界定而引发的危机来分析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研究扩展为“认同”研究的重心转化过程,并指出这种变化源于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 一、“身份”的语义危机 国内文化研究语境中对“identity”有三种译法:一是身份;二是认同;三是身份认同。②其中第三种译法强调的是对身份的认同,重点在认同。因此,“identity”的译法实际上也就可以归纳为两种:身份、认同。从表面上看,一词两译意味着一词两意,但实际并非如此。基于对已有的使用或专门探讨“身份”和(或)“认同”的研究的梳理,有关“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两种观点:一种将身份与认同等同。例如,王宁在1999年对文化身份进行了定义,[2]他认为“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另一种认为身份与认同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闫嘉认为尽管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identity”,[3]但它们在含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一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在这种意义上是表示身份的意思。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 尽管二者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二者都认为“身份”与“认同”对应的是英文中“identity”一词。那么,为什么“identity”会被译成“身份”与“认同”呢?在《汉语大词典》中,身份(身分)有五种含义:(1)出身与社会地位;(2)模样,姿态;(3)手段,本领;(4)行为,勾当;(5)质地,质量。③这里并没有英文词“identity”所表达的含义。“identity”源自拉丁词根“idem”,本意是“同一、统一”,是指在任何条件下都保持同一与统一的本质属性。因此,“文化身份”是指与所属文化的本质属性保持同一性与统一性,这种同一性与统一性不因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中文原有的“身份”一词并不包含这层意思。那么,再看“identity”的几种中文译文:同一(性);一致;身份(分);本身;本体;个性;特性。这里的“身份”与《汉语大词典》中提到的“身份”的语义并不一致,它表示的是某人的本质属性。如在“identitycard”(身份证)这个词组中,“identity”被译作“身份”。这个译文保持了“identity”的原有意思,但也意味着在中文“身份”的定义中增加了英文词“identity”的含义。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一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源于“identity”的翻译。“认同”作为名词表示“同一”,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1984-04-18)中,“民族认同的浪潮,正在冲击着台湾海峡的人为藩篱”。③由此可见,最初对“identity”的翻译,无论是“身份”还是“认同”都确认了这个词所具有的同一与统一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身份”与“认同”所表达的都是“identity”的基本语义。文化研究语境中的“身份”与“认同”实衍生于“identi-ty”一词。从上述对“身份”与“认同”在中文中的语义分析,可见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它们在作名词时与英文词“identity”的语义内涵完全相同。 因此,王宁关于文化身份等同文化认同的论断是有理可循的。而闫嘉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进行区分时,既考虑到二者相同的一面,又意识到认同所表示的动态过程,这是“identity”一词所不具备的动态语义内涵。“认同”作为动词有三种基本含义:(1)认为一致、相同;(2)认为彼此是同类,具有亲近感或可归属的愿望;(3)赞同;④这意味着对“identity”语义内涵的理解增加了“认同”的动词属性。以上我们分析了关于“identity”的两种译法的来源、相同与相异的方面。“identity”一旦用来表示过程,那么这词的词义本身就分离出模糊、相悖的两种趋向。“identity”一词的根本属性是同一、核心与本质,一旦被解释为“过程”,此词的根本立足点就会发生变化。身份也便具有“建构性、流动性与多样性”的特征。[4]这不仅是翻译上的难题,而是对“identi-ty”的本质定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际上,“identity”一词所增加的动态属性,不能仅仅归于中文学界的翻译与理解问题,而是因为在西方学界“identity”一词的语义早已发生了重要转变。#p#分页标题#e# 二、“身份”的“认同”转向 针对究竟什么是“身份”的问题,Hall提出,[5](P287)“‘身份’与其说是一个完成的事物,不如将其看作是‘认同’,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尔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identification)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6](P212)这表明不但国内学界通过“认同”一词的动态语义扩展了“身份”一词的原有语义内涵,而且在国外学界,身份的概念也已经被转化为认同,增加了原来“身份”一词所不具备的动态意义。“identification”是心理学术语,通常被译成“认同”。它由动词“identify”变化而来,与“i-dentity”一词属于同根词,强调建立身份的过程。在中文中,“认同”一词既用来表示“identi-ty”,又表示“identification”,然而这两个英文词在含义上又有本质上的区别。于是,这便形成了国内文学、文化研究语境对“身份”与“认同”之间关系产生模糊界定的局面。这同时也说明国内与国外研究语境对身份研究都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将“身份”定义成“认同”⑤表明:首先,“身份”的核心语义发成了本质性的变化。认同强调的是“主体认同的过程,它并不表明认同了就必然会导致内在的同一性,特性,或是有界限的群体特征”。[4]认同实质上已经脱离了“身份”的内在语义。其次,西方学界对“i-dentity(身份)”的研究已经转化为对“identifi-cation(认同)”的研究。而我们在中文文化研究语境中在使用“认同”一词时,为避免模糊,应指出它所对应的到底是“identity”还是“iden-tification”。 这种转化并非偶然,原有心理学上的“认同”研究对理解身份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标志着“认同”由心理学上的术语逐渐转变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对象,并与身份研究发生了重叠。Gleason对认同由心理学方面的术语发展到社会学领域中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描述。[7]他指出“认同”的概念来自弗洛伊德,最初指婴儿同化外在的人或物的过程,是解释儿童社会化方面的关键术语。这个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只局限于心理分析领域,后被用于种族研究,再后来与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以及“参考群体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这里,“认同”的过程包含着个体对什么样的群体对自己意义重大,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是合适的等问题的思考,“认同”的最终形成则是“个体单方面对某一特定身份或是某一系列身份的占有与投身”。随后,对“认同”的研究就不仅局限在心理学、社会学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研究领域,最终与身份研究结合在一起。Ceru-lo指出目前对集体身份及其建立过程的研究使学者们的兴趣投向了“认同过程本身,以及促使认同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号的研究”,[8]他认为“认同”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连接点,包括身份生产、身份制度化、身份阐释三个阶段”。这时,对“认同”形成过程中经济、政治以及权力话语的影响的考察,使对“认同”的研究出现了多角度与逐渐深化的过程。 由“身份”研究转向“认同”研究,研究重心的转变不仅是语义内涵的扩展与变化,也意味着有关“身份”的理论认识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身份”的不同界定显示出不同身份观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身份观是促使研究重心转变的关键。 三、后现代主义“认同”观的建立 目前理论界存有几种身份观的不同分类:在文化研究领域,Hall首先将主体观的演变划分为启蒙主体身份观、社会主体身份观与后现代主体身份观;[5](P275)Kellner从历史分期上将身份观的发展划定为前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9](P141)社会学领域就“身份”的内在属性,将身份观概括为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⑥这几种划分的共通之处是他们将身份观的第三阶段都定义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可见,他们在借后现代的语境对之前的身份观进行观照与思考。后现代主义身份观既表明了身份发展的后现代阶段,也表明了身份的后现代主义性质。究竟身份的性质在后现代阶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将就后现代主义之前的身份观与后现代主义身份观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实质上是“认同”观,这种“认同”观是建立在反思之前的身份观基础之上的。 (一)后现代主义之前的身份观 首先,我们来看启蒙主体、本质主义与前现代身份观。启蒙主体身份观认为“个人作为有中心的、完整的个体,有理性、意识与行动的能力。个体的中心含有一个内核,伴随着主体诞生,这个本质内核开始存在、显现,同时将始终伴随个体存在,并保持始终不变”。[5](P275)本质主义认为:“个人具有一个本质的身份,这个身份与个人所属集体的本质特征相契合。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的建立需要个体经历长时间的自省,但是个人无法逃离自己的身份。它被更为本质性的东西固定下来———即人的天性。”[10](P381)Kellner认为在前现代时期,身份是固定的,稳定的。[9](P141)在前现代社会,身份不会被当作问题进行反思与讨论。个人不会经历身份危机,或者是极端地调整他们的身份。比较这三种身份观我们发现,它们所论述的核心是身份具有本质性、稳定性与前定性,这与身份的基本语义相符。 其次,再看现代主义、社会主体与建构主义身份观。现代主义身份观对身份的本质属性产生了疑问,但它坚信可以创造身份并保持它的坚固与稳定。因此如何去建造一种身份并保持它的坚固与稳定,成为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思索。社会身份认同与建构主义身份观非常相似,皆隶属于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它们认为身份是自我与他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强调对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上看,“自我不再是稳定的前定实体(asolid,givenentity),而是一个过程,在其所进入的社会情境中持续地创造与被创造”。[7]Erikson有关身份的理论为建构主义身份观在心理动力学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11](P19)他认为,尽管身份由于个体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与变更,但是,身份概念所具有的内在性与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身份无论是反映在主观意识中,还是处于动态运动过程中,都会保持它所具有的同一性与持续性”。他一方面肯定了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另一方面指明了身份的同一性,二者共同构成身份的本质。#p#分页标题#e# 总而言之,前现代身份观与启蒙主体身份观,只不过分别点明了历史阶段、所受理论思潮的影响,而二者所理解的身份观的内涵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是一致的。同样,社会主体身份观、现代主义身份观与建构主义的身份观对身份属性的理解相近。因此后现代主义之前的身份观,主要考察的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身份观。尽管建构主义身份观对本质主义身份观所强调的身份的“前定性”与“本质性”进行了挑战,指明了身份建立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但这两个阶段都肯定了身份所具有的同一性、稳定性与持续性。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之前的身份观对“身份”的基本语义内涵并没有质疑。 (二)后现代主义身份观 本质主义强调身份是给定的、赋予的,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份是建构出来的。总而言之,二者的共通之处是肯定了身份的存在。在前现代与现代社会,身份的存在是不被怀疑的,而在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下,身份的是否存在受到质疑。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身份是一个虚构的中心,对于一些事物的解释我们必须依赖它,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中的共同体》中所表明的现代民族身份的想象性特征,折射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6](P211)Eliot在《自我的概念》一书中对于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自我是灵活的、断裂的、片段的、去中心的与脆弱的……自我由人为创造的、经过个人的精心阐释,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形成。自我的形成受社会的影响,通过文化资源来维持身份……自我离不开所植根的社会、文化、政治与历史语境。所有形式的身份都是对私下与公共,个人与政治,个体与历史的想象性的构建。”[12](P2)后现代主义在肯定了身份的建构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身份的想象性、主观选择性与去中心性,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身份观否认身份的存在。对后现代主义身份观与之前的身份观的对比表明,后现代主义之前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具有内在性、固定性、持续性、建构性、本质性,等等;后现代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具有去中心性、想象性、破碎性、主观选择性、权力话语参与性,等等,总之,前者肯定身份的存在,而后者否认身份的存在。既然身份的存在已经被否定,“identity”的核心语义内涵也已经被驳倒,那么受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理论界将目光转向了认同的研究。 理论界从意识到“身份”内涵的模糊性,到最终界定它所增加的“认同”属性,从“身份”研究到“认同”研究的重心转移,都是以后现代主义身份观作为分水岭发生的重要改变。在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理论语境中,“身份”成为德里达提出的“超验的所指”。这就如同齐格蒙•鲍曼所言,“无论什么时候提到身份,在我们理念的背后都有一个和谐性、条理性和一致性的模糊的镜像,而当我们进行追寻之时,身份又处于永久流动的状态”。[13](P235)这意味着根本没有恒久不变的身份,或是根本找不到我们所谓的“身份”,“身份”存在的确定性被驳倒,这也便导致了今天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的语义危机与“认同”研究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