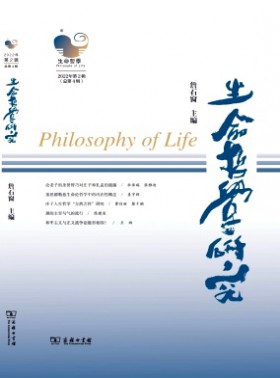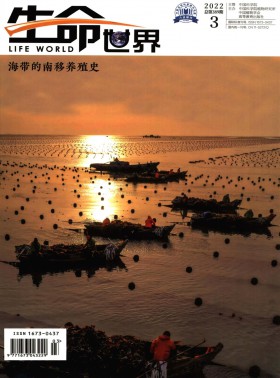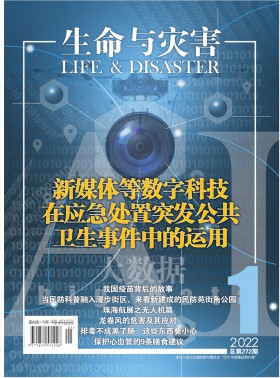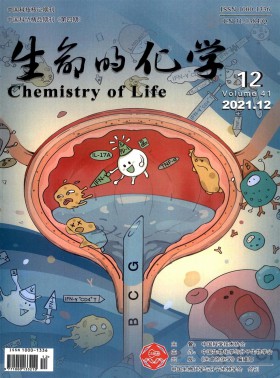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生命之爱作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1
扣下锅盖的一刹那,锅里所有的鳝鱼都痛苦地昂起头,如蛇般扭动着,天啊!我好残忍。
油烟升腾,模糊了我的视线。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看见其中一条鳝鱼,在极力弓着腰,像是怕烫着它那花白的圆肚皮。再瞧瞧其他几条,早已把身子蜷成一圈,尖尖的脑袋被层层地圈在正中间。
我愣住了。鳝鱼啊,你在仇恨我吗?在用一种极端的生命姿态发泄仇恨吗?
我小心地把它挑起。可怜的鱼,头和尾部因为支撑弯着的腰而被烧得焦黑,只有那圆肚皮没被烧到,发出刺眼的白光……仿佛有什么秘密。
我好奇地用刀小心将它剖开。霎那间,我惊呆了,热泪簌簌落下,因为,我发现了一种不平凡的爱:生命之爱,就在那鳝鱼的肚子里。原来,那鳝鱼的圆肚皮里有一团小小的卵!天啊,多可敬的生命!为了保护腹中的小生命,鳝鱼妈妈用一个弓着的姿势,为腹中的小生命撑起了一条生命的弧线。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2
我不去想,生命中的困难。
活着,一直活着,才可以远行,
我不去想,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
顽强的生命就是希望,
地上冒出来的小芽儿,
通过努力,长成参天大树,
人类又何尝不是这样?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会向那个方向出发,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3
盛行于世,而你们也深受其害,难道你们不知道的危害吗?不,你们应该还能记得当初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诫吧?诚如大人们所说,一切都是好奇心所导致的吧。
毒,就是对生物体有害的物质,难道不是吗?难道加一个字就对人体无害了吗?什么冰毒,什么海洛因,什么吗啡,不都是这样吗?一旦上瘾,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吗?不,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当你们看着身边一个个同伴因而死,是什么感受呢?恐惧?担心?我想,更多的,还是后悔吧?可是,为时已晚了。
当你们走上这条路时,最担心的人是谁?是你们的父母啊!他们含辛茹苦的把你们养大,你们却如此报答他们,他们能好受吗?父母把你们送进戒毒所,希望你们能够改头换面,可是,听到的却是你们因毒瘾发作而致死的消息,沉重的现实打击着他们,除了哭,他们还能干什么?我想,如果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你们的你的生命,他们必然会毫不犹豫就同意,所以,如果你还有良心,就请你们不要留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就像一把锋利的剑,伤害着你的身体,迫害着你的心理,控制着你的行为,多少人因嗜毒上瘾,却没钱支付,因此走上了不归路,有给自己的未来添了一滴墨。看到父母心力交瘁的样子,你就不曾有过一丝心酸与自责吗?
现在的社会如此美好,人们因此而感到骄傲,却也为你们——一群迷途的少年而寒心,醒醒吧!迷途知返吧!远离,珍爱生命,为自己的未来谱写更加华美的乐章吧!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4
——读《我爱祖国的蓝天》有感
今天,我读了《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本书,看着那触目惊心的数字,读者把那感人肺腑的事例,一页一页熟悉地摸着、翻着,都写满了世界的困惑,地球的危难,我不禁潸然泪下,感触颇多,但令我最烦恼的还是水——生命之源。
“如果把整个地球缩小,捧在掌心,地球非常漂亮,就像一颗美丽的蓝宝石,散发着耀眼的蓝色光彩。”确实,地球很美丽,是我们美丽的家园,但是,如果装扮地球最重要的水没了,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存活,因此,水是生命之源——成年人的身体里面有60%~70%是水分,而小孩子体内更是有80%以上都是水分。勤劳的水溶解和运送各种营养物质,是他们呢能顺利的被我们吸收,再把代谢废物排出体外。总之,“水”在我们的体内担当了很多项大工程,离开“水”这位万能超人,我们则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们需要水,但首先要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大家知道吗?虽然地球上被70%多的水资源包围着,但有许多的水资源我们都无法使用。比如我们常见的海水,看看海水湛蓝湛蓝的,一望无际,包围了大半个地球,其实海水又咸又苦,不能饮水,不能浇地,也很难用于工业。虽然现在的科技能够淡化海水,使海水变成可以饮用的水,但是费用却是相当的高。因此我们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26%!我们只有保护水资源,才能幸福地生活。
虽然现在许多人都开始注重使用水资源,但有些人却还是无节制地用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5
一、选材要“准”。选材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准确。如2012年苏州市中考佳作《心中有支欢乐的歌》一文,紧扣“欢乐”,选取三件事:小时候,“我”在寻觅春天中获得快乐;小学时,“我”笑对风雨其乐无穷;上中学,“我”在同学情深中其乐融融。每一个时期,都有一支欢乐的歌,在心中唱响。文章以时间为线索,选材处处紧扣文章的主旨,使得文章中心鲜明凸显。再如2012年东营市中考佳作《寻找之根,扎在心田》一文,文章以“寻找”为线索生动叙写——在家中寻找到妈妈之爱、在晒台边寻找到爷爷之爱、在教室里寻找到老师之爱、在冬日里寻找到社会之爱。此文精心选取,巧妙组合,使得文章主题深刻,意蕴无穷。由此可见:作文的选材,一定要紧扣中心,否则就会造成主题不集中,立意不鲜明。因而,在写作之前,我们一定要精心筛选,三思而作。
二、选材要“熟”。选取那些熟悉的有意义的事情作为材料。如2012年武汉市中考作文题《敬畏文字》,此题意在引导考生对语言文字要有敬畏之心,使用语言文字要有严肃恭敬的态度。有很多考生礼赞文字,抒写敬畏之情;还有很多考生阐述敬畏文字的意义与作用,号召世人提升素养,敬畏文字。这些文章由于考生积累不丰、认识尚浅,可谓浅尝辄止,空洞无物。可有位考生却从自己经常写错别字入手,叙写小学到初中其语文成绩的一波三折,在老师的引导下,纠正了自我经常写错字的习惯,其语文能力与水平与日俱增,传神地展现因敬畏文字而提升能力的历程。由于作者对所选材料熟悉,写起来得心应手,行文如行云流水,因此获得满分。
三、选材要“真”。只有真实的材料才能被读者接受和认可,才能使文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考生只有将那些融入自我体验和感悟的真人、真事、真情变成流淌于笔端的文字,文章才能成为心灵的舞蹈、灵魂的高歌。如2012年安徽省中考作文《幸福在其中》一文:
父亲载着我回家,一路上,风越刮越猛,都快把车子掀翻了。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一下子抱住父亲,依靠在他的背上,享受这一刻的温暖。父亲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他后面完全受不到前面吹来的风的袭击。靠在父亲的背上,我似乎能听到他的心跳,他的喘息,他的呼吸时而急促时而平稳,身体也由于寒冷而哆嗦起来。父亲竭力抑制,不让身体颤抖,但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我问:“爸,冷吗?”父亲说:“不冷,你坐好,冷的话就紧挨着我,快到家了。”
回到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刚动完手术没几天,顶着狂风来接我的。我的眼眶噙满了泪水,我这一路上是在向着怎样的后背索取温暖啊!幸福是父亲的后背,就像一道围墙,立而不倒,替我抵挡风霜雨雪,使我健康成长。
本文叙写我靠着父亲的背回家之事,以自我的体验作侧面烘托,细腻而传神地展现了父爱的伟大。如此独特的素材如不是自己体验怎能得到?考场作文就需要这样的素材,小作者正因为有了真切的生活体验与深刻的感悟,写起来才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由此可见:考场作文只有选材真实,才能打动人、感染人!
四、选材要“小”。切口小,以生动具体的小素材反映大主题。如2012年济南市中考作文《咀嚼生活的真味》一文就选择了四个小镜头,从而写出生活的真味——义务打扫卫生的老奶奶自豪地说:“打扫自己的家是我的责任”;影星张一山面对他人不解回应道:“没有努力,何来鲜花和掌声”;安第斯山上的普雅花生存之道告诉我们:生活在于坚持;孟佩杰以孝心行动告诉我们:直面困境,笑对生活。小作者细心咀嚼着生活中的这些人和事,从而悟出生活的大道理:“生活的真味不在于生活中的艰辛,而在于在艰辛中体观对生活的热爱。只有热爱生活,生活才会有滋有味;只有热爱生活,生命才会有声有色。生活的真味,就藏在我们奋斗的历程中,请你好好珍惜,细细品味……”
五、选材要“新”。选材出新可从如下方面突破:①选新人新事,只有富有时代气息的人和事,才能更贴切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征;②选与众不同的人和事,从个人生活中去选取别人无法获得的独特的素材,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奇”;③用新角度挖掘旧材料。有些材料,表面看来很旧,但如果站在新的角度上来挖掘,也很可能翻出新意来。可以说,材料不新鲜就不能感人,新颖生动的材料像带露的鲜花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更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如2012年荆州市中考作文《因为有爱》一文:
在这个初夏的季节里,北国最美的茉莉花,瞬间绽放。2012年5月8日,胜利路北侧第四中学门前挤满了刚刚放学的学生。原本停在路旁等待接学生的汽车突然向前蹿去。车旁的张丽莉向前一扑,一拉一撞,两名学生获得了新生。而她,永远失去了双腿。其实,她可以选择不动,后退。那样,客车会从她身边滑过。可她选择了向前,那样的毫不迟疑,那样义无反顾。因为有爱,她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以自己的柔弱身躯撑起一片生命的晴空,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赞歌。
此则素材关注现实,紧扣时代,新颖鲜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英雄壮举的由衷赞美之情。由于材料新、立意高,因此让阅卷老师爱不释手。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6
一、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挖掘生活素材
创设符合作文训练要求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生活体验。在课堂教学开始时,导入《世上只有妈妈好》的音乐情境,在音乐声中播放妈妈给在灯下读书的孩子端来一杯热牛奶、爸爸夸奖拆坏电话的孩子、父子一同游泳、妈妈陪同课外学习等一幅幅熟悉又亲切的画面。让学生在音乐中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关心爱护自己的事情一一说出来。丰富的情境使学生强烈地感受到父母的爱,爱的力量使学生心中涌起了一桩又一桩的往事。学生的思维活跃了,有的写出了“妈妈下岗了”“爸爸在医院的日子”“寒冷的深夜妈妈赶织毛衣”“爸爸撕作业”等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们教师要给学生创设真实的情境,调动学生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积累,唤醒写作欲,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学生有了对生活的强烈体验,自然而然地要表达出来。习作取材于生活,让作文成为学生传情达意的工具,让作文成为学生生活的需要。
二、借助教师范文点拨
包头的张苑莉教师曾执教“父母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声情并茂地朗读了自己的范文。她的文章真实感人,叙事清晰,内容生动深刻,感情细腻,语言文采飞扬。张老师这篇下水文的主要内容是:小时候,她与院子里的伙伴在除夕夜到郊外玩耍,由于没有告诉家人,父母连夜将她找回,面对着急而疲惫的父母,她内心充满了自责。如“世界上的父母是最伟大、最辛苦、最无私的。我从小到大,父母自己可以省吃俭用,却不让女儿受一点委屈。他们对我有操不完的心,着不完的急……然而,父母总是甘心情愿为之,不求任何回报!”“ 父母的爱,是我黑暗中的明灯,经常在身边照亮着我。父母的爱,是避风港,时时接纳我、包容我、鼓励我。父母的爱,是我生命中的加油站,让我有勇气面对生活。”张老师读完后,让学生评价她的文章哪里写得好,有的学生说:“好词佳句多,过渡句写得好。”有的学生说:“这篇文章叙事具体。”张老师引导:“为什么我能把这件事写具体?”最后张老师小结,这源于她留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习惯。张老师适时引导、引导得法,她让学生在范文中分析文章的思路和写得好的地方,让学生在互评中交流、领悟本次习作的写法。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写作的技巧。
要教好作文,教师应当成为一个善写的高手,留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这样才能做到指导有序、方法得当。
三、品读文本,突出教学重点,富于指导性
学生初次习作在叙事方面往往不具体、不生动,在人物语言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方面缺少细致的刻画。第六单元选入语文教材的文章,文质兼美,典范性强,是指导学生写作的最好范文。讲评学生的习作着重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可以充分利用《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课文,出示描写父亲奋不顾身挖掘废墟时的神态、外貌、动作的语句,如“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引导学生学习作者观察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通过与学生共同赏析课文片断,让学生反复朗读,说一说、议一议、评一评细节描写的妙处,引领学生感悟这些细节描写的作用。循序渐进地点拨,多次强化引导学生掌握这种写法,能有效地突破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四、注重教给学生修改习作的方法
在讲评习作时,出示修改习作的符号和修改方法,修改方法指导要细致:(1)改正错误:用错的标点、错别字、病句。(2)完善句子:改得通顺、具体、生动。(3)推敲内容:改得真实具体、合乎情理。(4)出示有毛病的片断,如“爸爸看到我没有完成作业,非常生气,把我教训了一顿”可指导学生从人物的神态、语言等方面去进行具体的描写。引导学生按评改要求,逐个“病例”进行剖析、诊断,找出“病症”,并对症下药,进行口头修改。最后让学生自改习作,交流写得最精彩的片断,在交流中互改,发表不同看法。指导学生修改习作有层次,使学生修改时做到思路清晰,明白要修改哪里和怎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