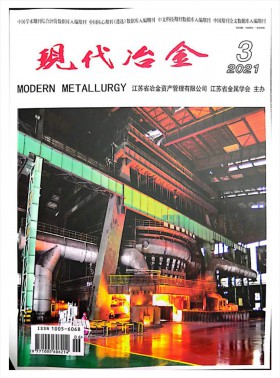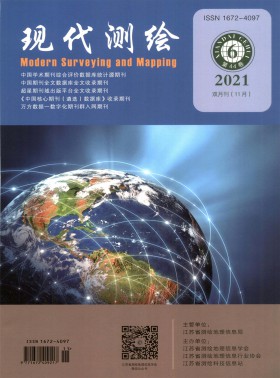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现代诗集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现代诗集范文1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现代诗集范文2
2.广电应对三网融合策略探讨励怡青
3.解析傲威系统在"豪门盛宴"节目中的应用夏力
4.索尼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3D世界现代电视技术 林亮辅
5.高质量高码率新介质——新一代高清摄录一体机HDC-1680李对峰
6.信息动态
7.三网融合内容集成播控平台规划与设计张大勇,吴正斌,蔡常军
8.走进《孔子》——后期特技管理与制作徐欣
9.电影《惊天动地》数字中间片工艺过程探析王淼
10.电影视觉特效的前期——全新电影视觉特效的前期拍摄理念和技巧刘松
11.数字电影影院管理系统(TMS)的设计杨雪培,张鑫
12.BIRTV2010嘉宾访谈录(三)
13.全新草谷更佳服务——访草谷公司亚太区副总裁AndrewSedek《现代电视技术》编辑部
14.面对三网融合与高标清同播的挑战——访东方盛行电子有限责任公司陈海卿
15.洞察3D叩问未来——记"索尼3D探源之旅"《现代电视技术》编辑部
16.中央电视台B-1高清转播车设计与实现(上)陈辰
17.摆脱传统脱机编辑手段——构建基于磁带采集和文件转码的混合脱机编辑工作流程刘羽
18.面向全台网环境的扬州电视台编播业务流程设计徐俭
19.泉州电视台卫星新闻采集系统设计林华淼
20.我国三网融合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丁颐,郑煊
21.荆门电视台3G新闻直播系统设计概述别业鹏,余彩云,贾云鑫
22.新形势下新媒体运营平台整合关键技术的探讨梁力强
23.响度技术在播出中的应用陈雨
24.电视节目声音制作的技术质量控制问题综述裘钰
25.如何布好演播室主持人出镜的效果光刘生远,韩奕伟
26.浅析基于条形码与计算机技术的电视台设备资产管理系统谢仁明,邓新力,邹娟娟
27.电视台技术项目管理实践与经验王洪涛,姜继伟
28.柳州电视台非编网络管理系统蒋婧,曹慧
29.网络电视流媒体监播系统设计陈敬添
30.DVCPRO录像机电路故障实例分析曾蓉,宋玮
31.佳能XF305在电影制作中的运用——著名摄影师刘勇宏谈应用袁旭稚
1.积极稳妥地发展IP电视《现代电视技术》编辑部
2.现代技术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朱虹
3.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推进三网融合——BIRTV2010主题报告王效杰
4.中央电视台"十二五"期间的技术支撑和实现丁文华
5.立体电视广播的整体解决方案——Quantel(宽泰)立体电视录编播网络系统乐永升
6.现代电视技术 Chyron图形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介绍GreyLennon
7.赢享三网——网络电视台建设之路毛烨
8.新草谷、新起点、新技术吴兵
9.浅析佳能全球首款便携式高清防抖镜头HJ15e×8.5BKRSE-V江口和哉
10.BIRTV2010嘉宾访谈录(二)
11.以严谨创新的专业精神为用户打造安全有效的应用系统——访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冯隽尧先生王兰岚
12.中央电视台南非世界杯转播前场收录制作系统应用徐妍
13.甘肃广电总台10讯道数字转播车系统设计与构建王昂,王华强,毛锦侠
14.构建基于服务器的高清电视制作系统陈克新
15.播总控系统各种服务器的软件部署和应用以及应急处理方法王树全
16.浅析临沂市广播电视台8+2讯道高清转播车的建设沈
17.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现场直播方案的探讨徐勇,张昕
18.IT网络技术制播系统的融合牛睿,侯少卿,宫鸣宪
19.浅析辽宁电视台网络字幕系统陈万军
20.可伸缩视频编码技术及其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中的应用王强,郭晓强,解伟
21.高清数字微波传输技术介绍宋智军
22.一种地面无线新闻节目传输系统的研究与设计董楠
23.广电传媒受众呼叫中心技术平台建立与应用陈浩
24.SMG数字广播业务系统建设中的问题探讨与分析徐征宇,张申伟,黎烨华
25.新媒体技术应用模式及其关键技术陈爽文
26.高清音频有你更精彩刘金
27.浅谈体育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中A1的自我修养徐慧明
28.新闻频道演播室的布光设计李奇
29.多频道、多品牌字幕机综合应用案例分析及病毒隔离创新机制邹宗华,蒋进,唐晓晖,顾茵莉,何雁,李彬
30.素材迁移转码技术在备播系统中的实现肖航
31.时间信息在屏幕上的显示顾云,吴永生HtTp://
32.网络化高标清同播制播系统质量评价及控制(下)鲍思明
1.三网融合、高清、3D影视,从BIRTV2010看广电发展之路《现代电视技术》编辑部
2.在新一代电视技术发展峰会上的致词宋宜纯
3.在新一代电视技术发展峰会上的讲话王联
4.从愿景到实现——浅论三网融合政策下的电视台新业务鲁泳
5.网络电视台建设实践与思考——面向全球部署的虚拟数据中心建设模型冯勤
6.面向三网融合的新媒体互动平台许斌
7.信息动态
8.数字播出领域的响度控制ThomasLund,曲向辉
9.进阶媒资系统设计现代电视技术 王杰中
10.BIRTV2010嘉宾访谈录(一)
11.浅析2010南非世界杯3D观摩实验陈力
12.2010年南非世界杯转播信号传输介绍张大立
13.中央电视台2010南非世界杯转播节目制作情况浅析王珮,伍旸
14.网络化制播系统安全设计与实践(下)徐济众,李泽强
15.多业务并存制作网的设计与实现许修环
16.广播级户外景观摄像机系统的实现王振,丁鑫锋,杨林明
17.利用矩阵实现字幕机的网络化同步播出李正坚
18.厦门电视台总控的数字化改造林珠凤
19.3G,折叠空间的新闻利器——3G在电视直播领域的应用探讨旷文彬,陈诚
20.小型电视传输网络前端系统的方案设计王亚杰,李然
21.电影全数学化演进技术系统及发展战略研究刘达
22.评奖标准问题思考——从节目年度评奖看对电视声音制作的影响与发展李宁
23.电视台综艺演播室音频系统的设计与实施王兰岚
24.合唱作品录音的解析孙长青
25.高清时代电视转播音频制作的变革张平
26.央视戏曲频道《青春戏苑》栏目包装创作心得赵衍雷,张宏涛
27.在基于DAB技术的交通诱导系统中实现车辆跟踪的设计韩忠,范成涛
28.由一起数字电视集播事故看前端机房用电安全杜申利,周宏
29.贵州电视台网络图书借阅系统的实现杨楠,黄学军
30.谈基层电视台的摄像机维修林宏
31.网络化高标清同播制播系统质量评价及控制(上)鲍思明
32.我谈电视李智勇
33.走进高清便携朝代——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影像信息消费产品市场企划部总经理山本敏彦专访高鸿
8.电视转播领域的网络音频发展趋势菲利普·朗沃
9.城市电视合建设网络电视的模式探讨傅峰春
10.当前广播电视技术业务发展及城市电视台的对策——在全国城市电视台技术协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报告徐国银
11.M-Live3G直播系统的实现和应用薛英军,荆错
12.中央电视温哥华冬奥会高清转播实战经验——移动外场网络制播系统的设计与应用陈欣
13.3D原理及3D拍摄实践村田秀夫
14.索尼3D现场制作系统设计——新理念新挑战杜卉
15.巴可大屏幕在电视直播中的应用秦军
16.背景墙显示系统应用总结李力胜
17.新闻演播室制作和包装讨论会实录
18.现代电视技术 网络化制播系统安全设计与实践(上)徐济众,李泽强
现代诗集范文3
1、iPod
iPod难道是在2001年发明的?其实,早在1979年,英国人凯恩・克拉默和好友詹姆斯・坎贝尔便提出发明一款烟盒大小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想法。他们的发明被叫做“IXI System”,可将数字格式的音乐存储在一个芯片上。此外,他们还为播放器准备了显示屏和导航按钮。他们本可以凭借这一发明成为百万富翁,但最终未能如愿。IXI自身存在一个很大缺陷,只能存储3分半钟音乐,很难让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几乎很少有人拥有电脑,下载音乐是个难题。
2、汽车
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在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发明的。而实际上,法国发明家尼古拉斯-约瑟夫・古诺特早在1769年便制造出一辆蒸汽机汽车。这辆汽车能够搭载4吨重物,时速可达4千米。1771年,古诺特在测试中失去控制,驾车撞到一面砖墙上。不可否认,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发明,但古诺特发明的汽车既慢又笨并且安全系数极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终结了古诺特改进汽车的希望,他在贫穷中了却一生。
3、热射线
2007年,美国军方公开了一项秘密武器,通过发射热射线使人产生火灼一般的感觉但不会造成致命伤害。早在公元前400年,磨光的表面便被用于聚焦光线。公元前212年,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制造热射线,烧毁来袭的敌方战舰。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传说,但希腊工程师伊欧尼斯・萨卡斯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的“死亡光线”具有可行性。实验中,他并没有使用巨大的镜子,而是选择50个真人大小的铜镜,将阳光反射到一艘小木船上,木船不久后便起火燃烧。
4、计算机
绝大多数人认为计算机是在20世纪40年明的,发明人是艾伦・图灵(也有说是康拉德・楚泽)。实际上,早在1833年前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就已初现雏形。1822年,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提出制造机械计算器的想法,用于计算多项式函数。后来,巴贝奇又计划研制一台能够编程处理所有数学问题的计算器,即所谓的“解析机”。最终版解析机能够读取穿孔卡上的程序和数据,可存储1000个数字,每个数字的小数位为50个,大约相当于20.7Kb。在1878年去世前,巴贝奇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设计趋于完美,但遗憾的是,他最终只完成部分原型。
5、潜艇
如果问潜艇是何时发明的,绝大多数人会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1870年,在这一年,儒勒・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预言了这项发明。而实际上,早在1580年,英国客栈老板威廉・伯恩就设计了一艘可潜入水下的船。1625年,世界上第一艘潜艇在荷兰人科尼利斯・德布雷手上诞生。这艘潜艇由12名桨手提供动力,可以潜水4.5米深。30年后,比利时人又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作战潜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也就是1776年,伊兹拉・李曾驾驶名为“海龟”的潜艇执行作战任务。“海龟”所携武器是一个钻孔机,用来在敌舰身上钻洞,而后将定时炸弹放入洞中。
6、视频游戏机
视频游戏机一般被认为是在1972年发明的。实际上,早在1948年,一名名叫小托马斯・戈德史密斯的大学物理学教授就为其“阴极射线管娱乐装置”这款原始的视频游戏机申请了专利。这个装置基于老式的军用雷达显示器,人们只能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个点。在将外星人或者别的图片贴在屏幕上之后,一个原始的视频游戏就诞生了。由于成本过高加之缺少趣味性,当时只制造了少量原型。
7、自动门
世界上第一道自动门是美国人德・霍顿和卢・海维特在1954年发明的。而实际上,古希腊时期的一名数学家、工程师兼发明家希罗就已发明了自动门。希罗一生发明无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早期蒸汽机――汽转球。当时的自动门被用于宗教仪式,相当于一种原始的特效。当时的自动门机关就像是一个捕鼠陷阱,但它的功能不是抓老鼠,而是让公众觉得是上帝的呼吸打开了他们面前的门。
8、火焰喷射器
火焰喷射器是1901年由德国人理查德・菲德勒发明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发明了。能够连续喷射的火焰喷射器。这种可怕而残忍的武器摧毁了德军的心理防线。实际上,古希腊人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发明了火焰喷射器。公元672年左右,一名叙利亚工匠发明了后来被称之为“希腊火”的烯烧剂,这种烯烧剂被用于海战和陆战,以烧毁敌船和烧杀敌方士兵。“希腊火”遇水不灭,能够在水面上燃烧,与凝固汽油有些类似。
9、电池
世界上第一块电池是由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在1800年发明的。在这一发明问世前9年,意大利解剖学家及物理学家鲁依吉・加尔瓦尼发现了“生物电”现象。实际上,世界上第一块电池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发明的。1938年,德国考古学家威廉・康尼格发现了著名的“巴格达电池”(黏土罐),其顶部有个沥青塞子,位于钢管内的一根铁棒从中间穿过。对“巴格达电池”复制品进行的测试显示,如果将醋等酸性物质放入罐中,便可产生0.8~2伏特电流。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人使用电流镀银,现在的伊拉克人仍沿用这种方法。
现代诗集范文4
1.1不同造型的线的重复构成营造出的光感效果
日本“美能达摄影机制造厂”标志,外形是一个椭圆形,中间的部分是由细到粗再到细的白色的五条线条整齐排列组成的,乍眼看去这中间的五条白色线条在黑底的正椭圆形内就像黑暗中的几束光。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标志,其外形是一个正圆形,在黑色正圆形为底的背景里,被白色的细线条均等分割,其中左上角部分至上而下白色线条先由粗转到细,一直往下推到了第九条白色线条,使得这款标志在左上角部位给观看者以突显光芒之感。
1.2粗细不等线条的排列营造出的运动感效果
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标志,主题图案为多个五角星的组合。在表现中运用粗细不等的13条横虚线对五星加以装饰,这些线同时又象征着美国独立时的13个州。中间的白色星星以虚拟填补,使得这五颗星给人炫目闪烁的视觉效果。又例如,“冬季奥运会项目——曲棍球”标志,由粗细不等的、倾斜的黑色曲线组成。线条的粗细变化使标志图形中隐约形成了一个打曲棍球的运动员向前滑动的效果。
1.3线条方向的改变营造出的波动感效果
日本“兹贺县琵琶湖研究所”标志,每条线条的方向发生了一定弧度的改变、上下方的黑色线条至上而下由粗到细和由细转粗,以及中间两条黑色线条由粗到细再到粗的变化,使得这款标志在整体视觉上呈现出波动感的效果。美国“克罗斯曼出版社”标志(图4),用横置S状的曲线为单元形重复横向排列,营造出了具有波动感的效果。
1.4线条排列方式的不同营造出的空间感效果
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标志,用螺旋线分割正圆形后,运用放射状线条的排列构成了整体标志,营造出了具有“深度”的空间感。匈牙利“国家美术馆”标志(图6),其整体形象是采纳美术馆的正面形态,用竖直的一条条黑色线条以及黑色线条间的白色空间表现了美术馆前柱子的形状。下部每一条黑色线条突然变为连续的折线形态,表现了美术馆台阶的形象。此标志是线条形态转变造成了空间视幻效果。
2图底关系的巧妙设计表现出图底反转效果
“PinkFlamingoFarm”标志,当你看标志中白色的部位时,你看到的是马头形象;当你看向标志中黑色的部位时,看到的是一只火烈鸟形象。“FranzBernard”标志,是字母“F”和“B”的巧妙组合。乍眼看去,观者看到的是中间的白色部分“B”,当你视觉一转,你又会看到负空间里的“F”。
3用线或用面的设计的特殊形象表现矛盾空间效果
3.1具有共用线的形象营造出的矛盾空间形象效果
美国“华琼森图书馆”标志,该标志是两张折叠后凹下去的纸形和另两张折叠后凸起来的纸形构成的,最终形成了同时具有凹凸感的效果。
3.2具有共用面的特殊形象营造出的矛盾空间形象效果
在标志设计中运用共用面矛盾空间表现法,可在二维空间内表现出三维空间的矛盾空间感。例如日本“本田设计事务所”标志,中间是水平放置的菱形,相对于左边垂直的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形象的底面;而对右边垂直的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形象的上面。
3.3视平线以上与以下立体的组合表现的矛盾空间效果
应用视平线以上与以下立体组合的原理,可设计矛盾空间效果的标志。如“海恩(建筑师)”,当我们同时看向字母H与左上方黑色形时,字母H是处在视平线以下的形象;相反,当我们同时看字母H与右下方黑色形时,字母H是处在视平线以上的形象。
现代诗集范文5
关键词:汉代服饰文化;现代艺术设计;指导意义
中国服饰源远流长,自从有了人类也便有了服饰。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汉代逐渐出现了麻、棉、可纺织的布、丝绸,以这些材料作为服装的面料。特别是到了汉代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服装面料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同时汉代的染织工艺、刺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服饰的变化和发展。
一、汉代服饰的艺术特点
众所周知,服装的色彩是服装设计的三大要素之一。人们对于服饰的最初印象与感受,首先是从色彩开始的。汉代的服饰总体来说是由历史性色彩图腾崇拜演进的。简单的说,一是红色,二是黑白二色,四是青红黑白四色,五是青红黑白黄五色。远古的先民崇尚红色。夏商二元对立,尚黑尚白。西周四方模式,青赤黑白褒贬分明,汉代沿用了秦以来的服装色彩。即五行五德五色说,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他杂色为间色。
图纹即十二章纹,“十二章”纹样在服饰上的应用开创了服饰标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先河,这也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服装从此不仅仅是遮羞蔽体、御寒保暖的物质品,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含义、标识意义、身份象征的更多文化内涵。成为社会文化、阶层等级的重要反映。十二章纹来自远古时代的传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些图纹都是抽象化的表现出来的,是抽象化的造型,但是能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一般而言,服饰图纹的基本特征是心灵世界的自然化体现。这图纹中,表面看来是自然的一个外壳,内核则是人的灵魂。
二、汉代服饰的文化内涵
从汉代服饰的色彩和图纹方面可以看出汉代服饰的象征性,这些纹饰的抽象寓意性表达,形成了汉代服饰清淡平易的风格特点。在造型上,紧身束裹的托地深衣,端庄典雅的服饰风格无不透散出一种含蓄美,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以儒道文化的引导为支撑的。这种含蓄的美学思想表现为情感的含蓄、朦胧与直觉的含蓄美的文化特征。要探究中国汉代服饰展示的这种含蓄美的根源即儒道互补这个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美与道家返朴归真的自然美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服饰美得哲学基础。
我们都熟知的大圣人孔子,他即反对着装不能过于简陋,又不能有过繁的装饰。注重恰到好处,这正是他在服饰中体现出来的中庸之美。他注重“文质彬彬,衣人合一”讲究一种和谐的美,他的这种服饰观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是有一定意义。设计注重内在因素,讲究与环境、场合相结合,设计不突兀,不做作,能够恰到好处的表达主题。这些理念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艺术设计中,
我们可以通过匠心独运的图案、色彩运用,达到一种和谐的美,使现代艺术设计能够体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建构起新的具有民族性的艺术设计语言。
韩墨的服饰文化观“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舒适性、自然性。注重人的精神、气韵和风度,追求人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自在,强调人的内在美质,反对外在的束缚,否定过分的外在美饰。这种服饰思想对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艺术设计也要讲究设计的本质,体现目的性,在此基础上尽量追求一种美观效果,不能本末倒置,只讲究装饰效果而忽略它内在要表达的东西。
总的来说,汉代服饰文化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服饰是渗透当时人们的情感意愿、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观念,一种反应社会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汉代服饰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充实的内涵。
三、汉代服饰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
21世纪的今天,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现代艺术设计离不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滋养。汉代服饰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代表,我们应设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设计。
现代艺术设计运用汉代服饰文化不能只是将传统纹饰进行简单的拼凑,这样不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在他们作品中只有简单的外形躯壳。真正的有造诣的设计师,应该试图发现一种既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本土文化,从中提炼总结出新的设计语言,从而让汉代服饰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呈现出新的活力。通过对汉代服饰文化的理解、继承和发扬,找到我们现代艺术设计可以传承利用的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
(1)追求一种自然设计的表达
老子和庄子的服饰观,即追求一种自由洒脱的着装风格,讲究人内在的品质,而忽略外在的装饰。这一服饰观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艺术设计也要讲究一种自然不做作的设计风格,同时也要注重设计的品质,讲究作品要有一定的内在质感。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科技时代与历史上的手工时代、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儒雅飘逸的深衣长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所以,在现代艺术设计上我们要找寻符号时代背景的设计。可以运用自然元素来进行抽象化的设计,也要讲究舒适性,可以借鉴仿生学的理论,来完善设计作品,能够体现出内在的本质。这种设计风格往往更能够得到大多数人们的欢迎。现代艺术设计也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自然的设计,一种符合人类需求的设计。
(2)图纹的抽象化,设计注重时代性
现代设计一定要在民族统中融入现代意识并再创造的一种设计。传统汉代服饰它是历史,是民族文化的代表,现代设计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事物,它的本质是运动不是静止。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服饰上有很多已经抽象化了的图形,这些图案代表了我们祖先的知识和智慧。现代设计可以吸收这种方式,把具象的事物进行抽象化的设计。但是,这种抽象一定要有代表性,要能够反应主题精神。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找寻设计语言和设计方法,关键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重新至于当代文化之中,切合时代所要表达的主题,同时结合现代人的思考理解,把传统文化语言与时代相合使富有时代特色。
汉代服饰,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秉承了华夏服饰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具有悠远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现代设计中的合理表达设计理念对设计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服饰的文化对现代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必须重视汉代服饰的考察研究从而总结出有利于现代艺术设计的方法和经验,进一步提升设计的水平,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现代艺术设计的民族性、时代性的展现。
参考文献:
[1]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08.
[2]岳伟、夏祺.浅谈现代艺术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成功2009.3.
作者简介:
现代诗集范文6
韩长赋指出,都市农业是伴随现代都市的发展而发育成长起来的新型农业形态,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开始起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为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城市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功能拓展、科技应用和管理水平提高,逐步培育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都市农业,为支持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为探索“三化同步”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年积极实践,我国都市现代农业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展示了广阔前景,初步成为以服务城市、繁荣农村为导向,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载体,以现代科学技术、物质装备、人才队伍、经营方式为保障,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为目标的新型农业形态,并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先行者”、“排头兵”。
韩长赋强调,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历史时期,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农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城市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是保障大中城市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改善城市生态人居环境的客观需要,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三化同步”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都市现代农业在服务城市、繁荣农村、富裕农民、保护生态、传承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韩长赋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发展都市农业,要按照《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要求,遵循现代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都市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基本方略,把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把聚集先进生产要素作为重要手段,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强大动力,不断优化布局结构,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争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十二五”总体目标是,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把都市农业建设成为城市“菜篮子”产品重要供给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农业先进生产要素聚集区、农业多功能开发样板区、农村改革先行区,大幅提升城市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基础好、产能高的大城市,要稳定面积、提高单产,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粮食优势区域的中等城市,要发挥资源优势,加快新技术推广,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一些特大型城市,要加大投入力度,保护优质高标准粮田,稳定粮食产能。大中城市发展粮食生产,要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上下功夫。二是大力抓好“菜篮子”建设。确保主要“菜篮子”产品供应数量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合理,关键是要认真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好“菜园子”,管好“菜摊子”。要稳定提高自给能力、加快健全市场体系、不断改善市场调控。三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是都市农业的基本要求。要大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提高本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强外埠调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四是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种功能,是都市农业发展的潜力所在。要根据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需要,加快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率先实现优质产品、优良生态、优美景观一体运行。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五是持续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带动周边现代农业发展,是都市农业的功能所在、使命所系。要发挥展销平台的辐射作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农业园区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