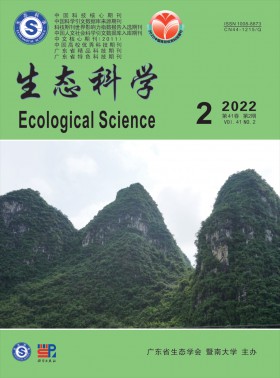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视域下解读狄金森的诗歌,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ckinson1830一1886)是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她一生离群索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她的诗主要涉及到自然、生命、死亡、时间等。多年来,批评家从许多方面对其诗歌进行了研究。有的探索其诗歌中的意象,有的从超验主义的视角研究其诗歌,一些批评家还从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来研究其诗歌……这些批评使得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解读视角丰富多彩。 近年来,生态批评理论的出现,为解读其诗歌又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总体上,生态批评集中于描述自然环境的文学作品,努力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意义,如自然的自在价值、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对其他生命的敬畏等等。细读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我们发现其诗歌具有丰富的生态意义,首先其自然诗歌体现了诗人融入自然之乐,感受自然的无私和慷慨,以及生命平等的有机自然观,并对自然中的动物充满了深切的生态关怀。同时,本文关注生态批评视角的转移,如从自然转向人类自身。诗人不仅试图从自然诗歌还从其他诗歌对于现代科技和智慧进行反思,指出人类的机械自然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诗人还反思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物质观念,强调努力保持心灵纯净的必要性。这些生态智慧无疑对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 我们注意到迪金森创作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的诗歌,这些诗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诗人长期隐居,没有世俗的羁绊,诗人有足够的时间专注于自然和自己的内心。而自然的灵动和美丽,如随风摇曳的小草、瞬间掠过的飞鸟、晚风中的花香等,无疑也触动了诗人的灵魂,激发其诗歌创作的灵感。细读这些以独特视角描写自然,用心灵与自然进行交流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对于自然敏锐的感悟和深切的生态关怀。 诗人喜欢自然的美丽,经常在其诗歌中描述自己用心感受的自然,即使是自然中的寻常景象也能使诗人的心情激动不已。如在《我掠夺过树林》一诗中,诗人描述了自然给她带来的瞬间的快乐:“我掠夺过树林—/那信任一切的树林。/那些不知怀疑的树/捧出苔藓和刺果,/供我欣赏,使我快乐。/我打量他们珍奇的首饰—/我伸手抓,我带了回去—/那庄严的铁衫会怎么说—/那橡树会怎么说?”[1] 当然,诗人并没有仅仅停滞于自然之乐。除了陶醉于融入自然的快乐之外,诗人还进一步看到自然的无私和慷慨。如在《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一诗中,诗人写道:“这些是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她慷慨邀请/一切饿汉,品尝她/神秘的芳醇—/这些是自然之家的礼仪—/对乞丐,对蜜蜂/敞开胸怀/同样殷勤。”,这无疑使得诗人对于自然的感恩和谦卑之心跃然于纸上,也会更加使人对于自然产生敬畏之心。 生态批评主张有机的自然观,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将地球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河流就像是人体的动脉,将生命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河流必须保持自然顺畅,并能够流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在河上筑堤坝是对自然的粗暴干扰。湿地是地球的再生中心,就像人类的肝和肾。在湿地中的物种处于食物链的底层,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一方面制造和储存营养,一方面清除自然系统所产生的废物。”[2]这使得一些生态批评学者认为自然就像人类的个体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系统。对此,诗人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诗人在《地球有许多曲调》中写道:“地球有许多曲调。/没有旋律的地方/是未知的半岛。/美是自然的真相。/但是为她的陆地作证,/为她的海洋作证,/我以为,蛩鸣/是她最动人的哀乐声。”作者认为自然就像音乐一样相互作用和联系,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旋律和曲调。细读该诗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有机的生态自然观异曲同工。 生态学者保罗•泰勒认为:(1)人类是地球生物圈中的成员。(2)所有生物都在一个相互依靠的体系中相互联系的。(3)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每一个有机体都是生命的中心。”[3]这种生命平等的思想正是生态批评的基本思想之一。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对生活于自然中的动物也充满了关怀,在《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一诗中,诗人饱含深情的写道:“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她美丽的翠绿—/已经两次,冬季在河面留下/银色的裂隙—/为松鼠,你准备了整整两个/丰盛的秋季—/自然啊,就不能给你漂泊的小鸟/一颗,草莓?”诗人的感受是细腻的,诗人关注自然中的动物,认为所有生命应平等的栖居在自然之中。 读迪金森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诗人对各种动物充满了好奇和关切:“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有时奔驰—/……当我还是孩子,赤着脚—/不止一次,在中午/相遇,曾以为是鞭梢/散落在阳光里—/我弯下腰去拾取,/它却扭曲着,离去—/不少自然的居民我都熟识,/他们对我,也不认生—/我常为他们感受到一种/亲切的喜悦激情—……”(《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 诗人宣称对于许多“自然的居民”是“熟识”的,与它们是亲近的。同时,自然中的动物对于诗人也是亲切的:“蜜蜂对我毫不畏惧。/我熟识那些蝴蝶。/丛林中美丽的居民/待我都十分亲切—……”(《蜜蜂对我毫不畏惧》)由此,我们发现诗中的自然万物和诗人是平等的、和睦的。这正如生态学者汤姆•里根所说的:“大致说来,我的立场可以总结如下。一些非人类的动物在相关道义上和一般的人类是一样的。”[4]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在进一步感悟自然万物时,自然觉得人应该承担起对其他生命关怀的责任,包括漂泊的小鸟、松树、蜜蜂等这无疑是生态思想的直接体现。 二 生态批评的视角广泛,除了关注自然,生态批评还将视线从自然转向人类自身。首先是关于科技的思考,关于这一点,生态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指出:“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5]#p#分页标题#e# 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不断的开发自然,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也空前膨胀,但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问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困境,这也是生态批评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早期科技应用于开发自然的成功,人类对于科技也过度的依赖和迷信,有人甚至乐观的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是技术问题,只要科技发展了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并不那样简单。 “19世纪的文学,尤其是英国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冲突”。[6]同时代的美国诗人迪金森的诗歌也不例外。诗歌中的自然是如此美丽,诗人和自然中的“居民”相处是如此愉快,但是诗人并没有拘泥于这种美丽和惬意之中,而是进一步把目光也转向了人自身,并深刻的思考了人们所引以为豪的科技和智慧和人的感性的自然审美之间的关系。 首先,诗人肯定科技对人类的贡献,歌颂科技的伟大成就:“我爱看它跑过一哩又一哩/掠过一条条山谷—/停在水塔下把自己灌足—/然后,放开惊人的大步/绕过成堆的山峦—/趾高气昂,睥睨着/道路两侧,简陋的房舍—/然后,爬过/依照它的身材/开凿的石槽/以可怕的,啸叫声/不住地抱怨—/然后,冲下山岭—/像嗓音洪亮的传教士一样嘶吼—/然后,像星辰一样准时/停下,驯顺而又威武/停在自己的厩棚门口—”(《我爱看它跑过一哩又一哩》)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一辆火车,对科技充满了热爱和敬佩。 但是,诗人认为科技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大角”是他另一个名称》中,诗人写道:“大角”是他另一个名称—/我宁愿叫他“星星”。/科学也太讨厌/竟干涉这类事情!/有一天,我踩死一条小虫—/一位“学者”恰巧路过—/咕哝了一声“百足”,“蜈蚣”!/“哦,上帝,我们多么脆弱”!/我从林中采来一朵花—/一位戴眼镜的怪物/一口气数清了雌蕊的数目/给她分“科”归“属”!……”在这首诗里,诗人认为科技是不能代替直觉感受自然之美的。 其次,作者还认为科技也无法代替人类心灵的感悟:“知道怎样忘却!/但是能否教我?/据说是最容易的艺术/只要知道怎样做/在求知的过程中/迟钝的心灵死去/为科学献出牺牲/如今已是寻常之举/我上学校上学/却未见聪明一些/地球仪不能教我/对数不能解决/“怎样才能忘却?”/哪位,哲学家,请说!/啊,掌握这门学问/必须学问渊博!/学识在书本里么?/我就可以买到/是像一颗行星么?/可向望远镜请教/如果是一项发明/必定有了专利。/智慧之书的博士,/你,是否知道?”(《知道怎样忘却》)智慧并不能解决人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心灵方面的问题,如怎样忘记,如何使得心灵不“为科学献出牺牲”等等。 此外,诗人还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人类科技知识的局限性的一些思考:“自然,是我们所见—/午后的光景,山峦—/松鼠,野蜂,阴影—/自然,甚至,是乐园—/“自然”,是我们所闻—/大海的喧嚣,雷霆—/食米鸟叫,蛩鸣—/自然,甚至,是和声—/“自然”,是我们所知—/我们却无法说明—/要道出她的淳朴—/我们的智慧无能—”(《自然,是我们所见》)这里,诗人指出了智慧的局限性,自然的淳朴和美丽是远非我们的知识能够揭示的,更不用说用手中所掌握的科技去征服一切,那样有可能会由此打开所谓的“地狱之门”,招致严重的后果。 因此,诗人既看到了科技的巨大力量,同时也认为科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掌握了科技的人类,应该更多的时候将自然看做是审美对象,而不应仅仅将自然看作是征服对象,从而失去敬畏和谦卑之心。 三 除了对科技的思考之外,生态批评还进一步关注人的心灵。对此,生态学者鲁枢元先生提出“精神生态学”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系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系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7]并认为“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地向着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蔓延。”[7] 随着人类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也越来越多,自然理所当然的被人们视为是财富的来源而并非是生活的家园。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人们不断的掠夺自然,自然沦为人类暴力开发的牺牲品。生态问题更加严重:污染、疾病、土地沙化等。同时,在利益面前,人性变得更加的贪婪、丑恶和卑鄙,这也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态进一步失衡。 “美国学者查尔斯•哈珀曾经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主导社会范式”做出如下归纳:1.经济增长压倒一切,自然环境(当然包括天和地)只不过是理应受人支配的生产产品的资源。2.关注个人的、当下的需求与幸福。3.对科学和高技术的信念是有利可图;以市场调节生产;为追求财富最大化敢冒最大风险。……”[7]这种过分强调物质标准的思想与诗人所描述的纯粹的自然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社会必须变得更加俭朴并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人类必须将自己从物质的贪婪中解救出来”,[2]从而由此达到精神上的纯净。细读爱米莉•迪金森的诗,我们同样看到诗人重视精神生态,不断向内探索,倡导和歌颂人类精神净化,并希望用这种精神力量制衡着人性在物质诱惑面前的丑恶,努力达到精神生态的平衡。 首先,诗人也强调俭朴:“我有一枚金几尼—/被我失落在沙滩上—/尽管数额并不大—/尽管我还有许多镑—/在我节俭的心目中—/仍然不能不介意———/以至为了找不见/坐在地上长叹息。”(《我有一枚金几尼》)从这里我们看到,尽管诗人并不贫穷,但还是倡导节俭,以至于不小心失落很少的钱仍然感到惋惜。需要指出的是诗人的节俭并非是吝啬,而是减少不必要的自然资源的使用,并把对自然资源的占用降低至最低水平。#p#分页标题#e# 其次,诗人生活平淡,不为名利而写作,宁可贫困也希望保持灵魂的纯净而不愿受到物质的玷污:“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贫困,批准/这种腐败行径/也许,只有我们,宁愿/从我们阁楼的斗室/一身洁白,去见洁白的上帝—/也不用我们的“白雪”投资—/思想属于/给予思想的人—/就向他,体现思想的灵魂—/出售高贵的歌声—/经营,应该做/神圣美德的商贾—/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发表,是拍卖》) 诗人还认为诗歌对于人类的灵魂的承载和触动要远胜于物质财富:“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这渠道最穷的人也能走/不必为通行税伤神—/这是何等节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虽然精神上的失衡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生态恶化引起的,但是诗人还是希望努力通过对于精神净化的倡导和歌颂,以改善人的精神生态,进而反作用于社会和自然生态,促使掌握了现代科技、对物质标准过分迷恋的人们具有反思自己的动力。也许这种精神力量是柔弱的和有限的,但是诗人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小石头多么快活/独自在路上滚着,/从不介意荣辱沉浮/从不畏惧危机发生—/它朴素的褐黄衣裳/为过路的宇宙所穿上,/象太阳一样独立/成群或单独,都发光,/以不拘礼的礼节的淳朴/履行绝对的义务—”(《小石头多么快活》) 尽管爱米莉•迪金森的时代还没有出现生态批评,但是诗人对于自然的深刻认识、对科技和智慧的反思,倡导人的精神的净化等无疑是生态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竟与现代生态批评家们如此接近,具有强烈的前瞻性。 现在,我们再次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迪金森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诗歌中的自然纯净、美丽和慷慨,生活在其中是如此的快乐,诗人的心灵是多么的清澈、纯洁,诗中深刻的生态智慧是如此的灵动,犹如穿越心灵的清风,纯净、悠远、引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