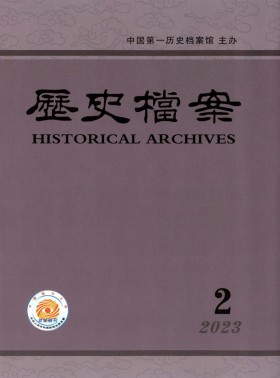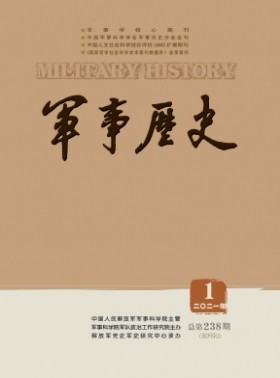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与盛世情结阐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盛世”的本义是对中国封建王朝盛衰、治乱过程中一种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概括,引申为对“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时期”①的价值指认。近年来,“盛世叙事”、“盛世情结”等提法在历史题材影视剧领域甚为流行。实际上,以历史学判断的“盛世”为题材的“盛世叙事”类作品并不多见,当前的历史文学作品所显示的,主要是一种“盛世”、“乱世”、“末世”的审美思维视角和开国治国、开创“盛世”的执政文化价值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才是整个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并由此构成了一种“盛世情结”。长篇历史小说则是其中的主导者。本文即拟对这种精神文化现象及其历史生成,进行必要的辨析与探讨。
一“盛世情结”在建国初十七年的历史文学创作中就已经存在。对应于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思维和人民革命的时代特征,反映王朝“乱世”、“末世”状态的历史文学作品在当时成为创作的主流。电影《宋景诗》、长篇小说《李自成》以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为己任,电影《林则徐》、《甲午风云》等着重表现内忧外患的末世状态中民族英雄的情操与品格,作品普遍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革命文化立场,自然缺乏“盛世情结”的精神意蕴。但与此同时,不少现代文学史上即名满天下的老作家,却应和新中国的开国气象,表现出关注开元治世、呼唤升平“盛世”降临的创作心态。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就浓墨重彩地歌颂“了不起的历史人物”②开创新时代的“政治才干”、“文治武功”及其所向无敌、“天下归心”的人格魅力。曹禺的《胆剑篇》注目于弱小国家同心同德、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而战胜强敌、开创伟业的精神。田汉的《文成公主》,则表现了唐蕃团结、民族亲好的盛世期待。在小说领域,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等,着意抒发“盛世遗才”的落寞、挑剔、愤激与自矜,而“盛世”思维的审美视野和精神路线,实际上也曲折地隐含其中。
结束、拨乱反正时期,历史文学作家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题材,从刘亚洲的《陈胜》、杨书案的《九月菊》、蒋和森的《风萧萧》和《黄梅雨》,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顾汶光的《大渡河》、李晴的《天国兴亡录》,等等,一时蔚为壮观。此外还有徐兴业的《金瓯缺》、冯骥才与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和《神灯》、鲍昌的《庚子风云》等抗御外侮题材作品,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周熙的《一百零三天》等题材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表现中国封建王朝“末世”、“乱世”的各种社会抗争及其失败,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盛世”向往之情则相对匮乏。但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转入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轨道,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风光不再,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文学创作逐渐淡出,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等力作巨制,逐步将审美重心转移到了对帝王将相和王朝历史盛衰本身的思考上来。这类长篇小说大量涌现,而且大多以篇幅浩繁的多卷本形式出现,力图形成一种史诗的风范与气势,再加上电视剧改编的巨大影响和一些同类题材电影的出现,一种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盛世情结”,就以相当成熟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成为了长久持续的文学创作热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不过,因为普通百姓和媒介评论更多地关注影视大众文化性质的作品,结果长篇历史小说更为丰富深刻的“盛世情结”表现,则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遮蔽。
二具体说来,当代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以盛世主宰者为叙事核心,全面展开封建王朝的某个辉煌、鼎盛时期,正面描写其改革和兴盛、繁荣与富强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类作品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代表作当属二月河“落霞”系列长篇小说和孙皓辉的《大秦帝国》。二月河《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创作始于1985年而延续到1999年,在90年代中期后形成了一股“二月河热”。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更将着眼点由“皇帝”转为“帝国”,体现出更为自觉的“盛世叙事”意识。小说和电视剧相互呼应、推波助澜,使历史文学的“盛世叙事”达到了高潮。孙皓辉煌煌五大卷的《大秦帝国》,则以其辽阔的历史画卷、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对中华文化之根的深刻挖掘,在新世纪文坛令人刮目相看、由衷钦佩。
二、以历史上某位著名的改革、变法人物为主人公,着力描写其开创盛世、中兴王朝的变革过程,探究盛世形成的基础、条件和前因后果。前十七年的《蔡文姬》、《武则天》、《胆剑篇》、《文成公主》等话剧作品,就属于这一类;新时期以来的代表性作品,则有凌力“百年辉煌”系列的《少年天子》、《晨钟暮鼓》,熊召政的《张居正》和颜廷瑞的《汴京风骚》等。其中建国初十七年的作品着力表现生机勃勃的开国气象,新时期以来的这类作品,则着力发掘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和辉煌时期壮观表象背后的隐曲与艰难,着力展示杰出历史人物艰窘的生存状态和坚韧的人生品质,由此揭示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邃、复杂和盛世开创的艰难、崇高。《暮鼓晨钟》和《少年天子》以历史进程、文明样态契合美好人情人性为盛世形成条件的思想路线,《张居正》对权谋合理性及相关体制所依据的民族文化血缘根基的体认,颜廷瑞的《庄妃》和《汴京风骚》对于专制文化氛围扭曲高尚人格的慨叹,等等……实际上都是在深刻地思考民族腾飞、盛世来临的艰难与复杂。
三、作品描写封建王朝的乱世或末世,却以挽救危局、力图王朝中兴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并表现出高度认同和赞赏的价值倾向,从中体现出创作主体强烈的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向往和对于传统“升平盛世”的认同感。代表性作品有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曾国藩》和《张之洞》描述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末世的朝廷重臣,虽然他们费尽心力创建的辉煌功业最后都化为乌有,曾国藩为自己“吏治和自强之梦的破灭”痛苦不已,张之洞临终前慨叹“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但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始终不渝地追求王朝振兴、国家强盛的文化人格,显然取赞赏、讴歌的态度,对于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历史洪流中为建功立业真诚、悲苦却迭遭坎坷挫折的生命形态,则表现出深切的体谅与同情,一种深沉的向往和追求民族“盛世”的精神心理和创作立场,也就贯穿于其中。#p#分页标题#e#
三“栽什么树儿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探究作家的精神建构及其文化生成,可从根本性的层面,发掘出文学作品精神文化内涵的形成原因。对于历史文学“盛世情结”的探讨也是如此。我们不妨从“情结”概念的内涵谈起。作为荣格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情结”主要是指由社会的、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创伤性体验及其心理积淀,这种体验和积淀往往构成一种“典型情境”,作为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③,生成种种“原型”,从而成为“联想的凝聚”。“就象磁石一样,这种情绪具有巨大的引力,它从无意识、从那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王国吸取内容;它也从外部世界吸取各种印象,当这些印象进入自我并与自我发生联系,它们就成为意识”④,从而形成精神心理的兴奋点和思维的定势;而且,它还构成一种价值预设,一种“观念的天赋可能性。这种可能甚至限制了最大胆的幻想,它把我们的幻想活动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⑤。一旦进入审美活动,围绕“情结”形成的精神兴奋点和审美思维定势,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当代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正是这样一种民族记忆及其心理情感的积淀与转化。
经过中华民族历朝历代追求和向往的长久积淀,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境界,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心理与情感体验的“原型”和“典型情境”。近现代中国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坎坷命运、奋斗历程和一百多年殷切期待而始终难以实现的创伤性体验,则深化和强化了广大民众对民族盛世状态的诉求,以至凝结成了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痛点”与“情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清新明朗的开国气象,使中国作家和广大民众自然萌发出“时间开始了”、升平盛世即将来临的心理预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氛围,更将这种心理感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在50年代末的经济困难时期,历史文学“盛世开创”“颂歌”的创作倾向反而强势登场,出现了《蔡文姬》、《胆剑篇》之类的作品。但由于指导思想失误等诸多的复杂因素,社会主义建设历经坎坷与挫折,甚至形成了这样全局性的动乱,以至在拨乱反正、痛定思痛时期,民族的盛世境界还难以预期,也来不及被向往和憧憬,历史文学作家们只能忙于抒发愤懑、总结教训,“盛世情结”则被暂时搁置起来。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状态逐渐丰富而充分地展开,中华民族的振兴又显示出切切实实的可能性。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触发,使人们对于“盛世中国”的期盼再度迸发出来,于是,对中华民族盛世历史的眷恋与反顾,对民族“盛世”这种“典型情境”的领悟与传达,就在历史文学创作中构成了“联想的凝聚”、思维的定势和价值的预设,形成了“盛世情结”的集中爆发和全面表现。
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叙事形成热潮,还存在着深刻的现实原因。首先,近30年来中国国家文化由革命文化向执政文化的转变,以及国家治理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民族复兴、“盛世”来临的美好前景显得可望可期,于是,回顾和讴歌民族历史上的“盛世”来作为时代现实的映衬和参照,就成为各方面均能认同和欢迎的文化行为。但是,当今中国由于社会的深刻转型,又处于一个问题复杂、矛盾尖锐、弊端丛生的历史状态,当公众对各种现实弊端心怀愤懑而又不便言说和缺乏应对之策时,以托古鉴今的方式,借历史类似图景的重构来形成一种替代性的宣泄与满足,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又使“盛世情结”叙事对于传统“盛世”内在复杂性的揭示,获得了广泛的接受空间。再次,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也加深了民族自我体认的精神需求。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要学习先进国家、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人类历史文化状态,就必须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理解和认识民族的自我特征,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文明理念,只有这样,学习、融入和超越才有可能沿着正确、快捷的路径进行。而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话语霸权,往往会压抑或掩盖后发达国家及其人民的真实处境,偷换乃至取消他们面临的真实问题,中国同样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的盛世,则为加强民族自我认同、增强对话语霸权的有效抵抗,提供了可靠的精神资源。时代心理的深厚基础和有力铺垫,使得历史文学创作的“盛世情结”,达成了由心理积淀向理性自觉的转化。于是,从《少年天子》呼唤体制改革、文明进化以使国家走向强盛开始,到二月河的“落霞系列”作品直接探讨盛世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曾国藩》深沉反思国家中兴的复杂与艰难,直到新世纪的《大秦帝国》等作品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强盛之世的史诗性画卷,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叙事就随时势的发展一步步走向高潮,终于蔚为壮观。
总的看来,近现代中国的“盛世情结”堪称一种“因痛苦而追寻而探求而行动而激扬而积极运转”的“积极的痛苦”,这种“积极的痛苦”能够凝聚并表达出来的基础和触发点,则是中国政治情势由革命文化向执政文化、建设文化转换的客观现实。“盛世情结”类历史文学的创作,则是全社会“盛世情结”的审美反映和审美实现。相关作品所表现的民族盛世的辉煌景观、王朝改革图治的历史画卷、盛世的来龙去脉与规律得失,以及由此显示的民族文化的正负面特征、对于建设文化和执政文化的历史反思,既使这种“积极的痛苦”得到了“仅仅从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全部得到的满足”⑥,又使时代的认知需求获得了可雅俗共赏的文化资源,还使现实社会的进程获得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具体参照。
四历史文学作家之所以热衷于传达理解和传达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存在这种“盛世情结”,关键则在于,创作主体普遍存在一种依托民族历史及其主流文化,来感悟和映衬当代中国历史情势的“代言人”意识。
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与原则确立之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创造,就一直强调一种“载道”、“代言”的传统,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做“圣贤”思想的代言人。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创造,实际上也存在具体内涵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代言”与“立言”两种精神立场。“立言”者往往以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为基础,挑战和反抗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和传达其个体的“现代意识”与生命感悟;“代言”则往往以当今时代和民族历史的主流文化作为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基础。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所体现的,显然是后一种精神文化立场。具体说来,建国初十七年的创作者主要体现的,是“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精神姿态。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胆剑篇》等作品,都明显地表现出将当代政治文化视野和时代价值取向附着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迎合“时代精神”的“代言”性审美倾向。《蔡文姬》对曹操的“翻案”,就与类似的历史兴趣和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观点密不可分,曹操形象也有明显的“理想化”、“现代化”色彩。《胆剑篇》将过多的优点集中于小百姓苦成的身上,力图使他成为人民群众智慧、胆略和力量的化身,目的也在于体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观点。《关汉卿》依据极少的历史资料,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进行创作,本身自然无可厚非,但作品中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框架的情节建构,正面主人公充满战斗激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形象定位,则显然是当代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艺术化。90年代后“盛世情结”叙事的主体精神站位,则体现出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向中国传统的国家文化立场和主流历史观转换、挪移的倾向。作家们力图摒弃阶级分析思想观念的遮蔽,从历史文化事实出发,客观地、全方位地还原历史真相,相对于当代政治文化当属“立言”姿态;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类作品虽然也蕴涵着某些超越性、现代性的历史认知与生命体验,但文本依托中国传统官方史学的价值立场与思想架构的特征,却表现得相当明显,其中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代言者”的精神姿态。#p#分页标题#e#
从中国审美文化的角度看,这种“代言人”姿态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创作“雅”、“颂”传统的继承。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诗经》,建构了“风、雅、颂”的审美传统。《毛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注释《周礼》则指出“: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近人钱穆《读诗经》着重从时代变迁角度来加以阐述“:窃谓诗之正变,若就诗体言,则美者其正而刺者其变,……诗之先起,本为颂美先德,故美者诗之正也。及其后,时移世易,诗之所为作者变,而刺多于颂,故曰诗之变。”⑦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的“盛世情结”,正是“雅、颂”审美原则的精神传承。这种审美原则是许多历史文学创作者的思想自觉。熊召政谈到《张居正》的创作时也说:“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跟着市场走,而是出于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⑧。唐浩明甚至把历史人物的事业和自我的人生追求融为了一体:“我在自己四十岁写曾国藩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心态,所以写曾国藩写得酣畅淋漓。”⑨甚至连建国初受到严厉批判的电影《武训传》,解放后继续摄制的动因,也在于主人公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⑩、有助于“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诸多表述之中,一种或者“美盛德之形容”、或者“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以为后世法”的精神姿态表露无遗。创作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大力渲染天下初定、生机蓬勃的氛围,讴歌主人公开创新时代的“文治武功”,和一个时代“天下归心”、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目的就是要和建国初的时代气象相映衬,从而“美盛德之形容”。二月河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紧紧围绕帝王主人公,表现他们政治活动及其文化、心理基础,叙事策略已接近国家神话的性质,甚至显示出一种代帝王言的叙事效果,实际上就是希望既能“美盛德之形容”,又能“言王政之所由兴废”。唐浩明的《张之洞》择取中国在民族患难中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历程的枢纽型、代表性人物,表现他们为民族历史进程劳心劳力的所作所为和崇高人格,目的也在于“以为后世法”。一种“颂”或“大雅正声”的审美品格,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相当鲜明地显示出来。
“盛世情结”叙事以“雅”、“颂”的审美精神,正面表现国家强弱、兴衰的客观情势,着重剖析和赞颂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的丰富性格、复杂命运和价值状态,并努力揭示其中的历史文化内在机缘和演变特征,这就使创作主体文化代言者的精神站位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五创作主体的“雅、颂”意识与民族集体心理的“盛世”诉求有效地对接,就是历史文学“盛世情结”叙事产生强烈创作激情和巨大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很多历史文学作家都注重自我创作与时代氛围的对接。建国初期的历史文学创作强调“翻案”、“古为今用”意识,甚至过度强化“今”,导致了《新天河配》、《新牛郎织女》等庸俗化的创作倾向。90年代以来的“盛世情结”类叙事也有这种自觉的对接意识。唐浩明就是如此:“我选择的人物都是中国近代史人物,我不想选择那么久远的年代,那样共振共鸣会差一些;我选择的历史背景和我们现在的历史背景也有某些相近——‘洋务运动’本身也是试图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其中心目的是富国富民,与当今的改革开放也有类似之处。”
刘和平谈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改编时表示:“把历史题材当现代题材写,把现代题材当历史题材写,这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创作原则”,他希望“现代人看这部戏能感觉到强烈的现实感,但又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历史剧,即是发生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的人和事”
。胡玫导演《雍正皇帝》和《汉武大帝》时,甚至对于与时代精神需求进行“对接”的细微之处,都把握得相当准确:“当年的‘雍正’只是对于强者力量的呼唤,对秩序和盛世的企盼,而今天的‘汉武大帝’,则直接展现强者的力量和盛世现实。我们以此来呼唤现代中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
特定的时代形势往往会产生特定的精神状态,进而形成对文学艺术的相应需求;历史对于现实而言,体现为一种被储蓄的文化资本,一旦时代需求有效而成功地对接,就能构成巨大的现实影响和启示力量。从5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到90年代的“盛世情结”叙事所形成的良好接受效应,根源均在于此。80年代也出现过长篇小说《唐宫八部》和电视连续剧《唐明皇》等“盛世叙事”文本,却没有产生社会或文化思潮性质的巨大影响,至关重要的客观原因,就在于时代心理基础尚不够充分,因而无法形成适时、有效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