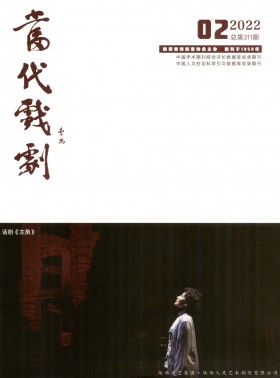人水关系的伦理价值观的反思,日益凸现于学界中心论域,“现代水伦理价值观”与“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则成为当代西方反思人水关系中提出的的两大代表性理论主张。对于正处于工业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面对日益严峻的水危机挑战,如何回应国际学界对水伦理价值观的现代性反思,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发展实践反思后作出的理论解答,也是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 一、现代水伦理价值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价值观 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以自然的主宰者自居,凭借理性和科技的力量,坚定“人定胜天”的信念,移山填海、围湖造田、拦河筑坝、乱排污水、乱采水资源、践踏水环境行为越演越烈。人水关系由农业文明时代的依赖关系转向了统治关系,被演绎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画卷。其中,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的环境哲学,工具主义成为人们对待和处理人与水关系的主导价值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主要有五方面内涵:第一,信仰笛卡尔“主客二分”式的哲学观。在人与水的价值关系中,抽象、单一和普遍的“人”被视为唯一的价值主体,水环境只能是价值的客体;第二,在人与水主客关系中,人是水环境的改造者和征服者,而水环境则是被人任意主宰与征服的对象;第三,水价值取决于人这一主体对水的需要程度,取决于人对水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人是水环境价值的惟一尺度;第四,人与水的关系始终是目的和工具的关系,人自身具有的内在价值决定了人是水环境的目的,而水环境是人实现其自身需要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第五,爱水、护水、治水和管水不是为了水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类利益和幸福的最大化,为了人类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主张工具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无疑是导致全球水环境危机的深刻根源,正是这种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使人把水当作任意处置的对象,使水成为个人或人类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工具。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人类对水环境的态度逐渐地由“敬畏”走向了“无畏”,由“顺从”转向了“征服”。现代水伦理价值观引发的这场深刻的水危机,正把人类推向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97年发表了《关于环境伦理的汉城宣言》,明确指出了人类反思和改变传统价值观的紧迫性:“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全球环境危机,是由于我们的贪婪、过度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造成的,换一句话,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导致了这一场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进行反思,其结果将是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甚至最终导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1]36正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中,在对工具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的批判中,后现代的水伦理价值观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极具影响力的水伦理思想。 二、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 后现代主义水伦理价值观即“生态中心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性解构,主张深生态的水伦理价值观,即强调包括水在内的自然环境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而且自然的这种“内在价值”是先于人类而存在,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因此,人类应当善待水等一切非人类存在物。 “自然价值论”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构建深生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当今各种形式的生态危机,都是因为人类长期以来坚守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致。由于人类否认自然的价值,使得人们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占有和征服自然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价值在人类道德共同体价值体系中的地位缺失,是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直至不断走向冲突的深层根源。为此,批判和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自然具有客观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破解包括水危机在内的生态危机的迫切选择。 生态中心主义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倡导“大地伦理学”,其中蕴涵的有机整体主义的大地价值论,是水伦理的重要理据。他在《沙乡的沉思》最后一章“大地伦理”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大地伦理”就是要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大地上每一个成员,即人和非人类存在物都纳入到道德关怀的共同体之中,“土地道德①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他们概括起来:土地”[2]201。作为大地生态共同体成员的水的价值,必然随着大地价值的认同而得到确立,水价值同样是水伦理得以构建的理论前提。大地伦理蕴含的整体主义的大地价值论,可以说是开启了后现代的自然价值论,初步构建起了后现代的水伦理价值观,从而为保护包括水生态系统在内的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道德义务,提供了理论支撑。 深生态学者纳斯倡导“生物圈平等主义”,主张生物圈内包括人和水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休戚相关,而且都是价值主体,均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是“一种直觉上明晰的价值公理”,无须逻辑证明。纳斯提出的“自我实现论”认为,西方传统中的“自我”是人类社会中原子式的分散孤立的“小我”,而“自我实现论”中的“自我”是自然界由无数的“小我”和“大我”(包含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组成的有机整体——“生态自我”。如果“小我”有内在价值,那么“大我”同样具有内在价值。“自我实现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生态共同体及其成员的价值认同,达到“活着,让他人也活着”(他人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3]的人与万物平等相待、和谐共生的道德境界。“自我实现论”进一步从有机整体主义的角度论证了生态共同体中自然万物内在价值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从而为自然万物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p#分页标题#e# 罗尔斯顿则明确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理论。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价值看作是人拥有道德权利的根据。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人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工具价值,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把人看作是唯一的道德关怀对象。因此,确认大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成为环境伦理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罗尔斯顿认为,内在价值同样存在与自然界中,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物,都具有像人一样的内在价值。“从狭隘的主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大自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创造并维持人的生命,因而它只有工具价值。但是,从长远客观的角度看,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都是有价值的”;因而,“惟一负责的做法是以一种感激的心情看待这个生养了我们的自然环境,正是它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价值”。[4]269在罗尔斯顿看来,这种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仅是客观的,不能以人的主观偏好为转移,而且在人类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人类这一价值评价者本身也是大自然价值演化和创造的结果。因此,倡导尊重、热爱和善待自然的环境伦理学,成为人类对大自然创造性的恰当回应,对地球的整体性伦理关照,是人类应有的道德选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无疑包含了对“水”等一切自然物内在价值的确认,为把“水”纳入道德共同体提供了伦理辩护,从而为水伦理的构建奠定了哲学基础。因此,随着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水具有内在价值的水伦理价值观应运而生,成为水伦理得以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 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尽管观点各异,却依然有着如下几点共识:第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水伦理价值观是导致全球水危机的深层根源。解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确立新型的“生态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是人类破解水危机并重建人水和谐关系的首要选择。第二,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有价值。自然价值不仅有其外在的工具性价值,而且更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第三,人与水是平等的价值主体,都拥有道德权利,人与水之间不是主客体的两极对立关系,而是主体间平等的和谐共生关系。第四,人是自然界中的普通公民,在生态共同体中,相对于人的价值而言水生态的自然价值具有客观独立性和先在性,而且水生态的整体性价值高于人类这一部分价值,具有优先性。这种以自然价值论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由此构成了“生态中心主义”水伦理学的理论基点。 上述现代与后现代的水伦理价值观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就现代水伦理价值观而言,其局限性主要有:其一,它是单一主体中心论,这种“主体(人)-客体(水)”两极对立的思维框架,极易导致人对水的征服意识,把水仅仅当作是面向单一主体的被动客体而随意对待。其二,它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同质性主体论。当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抽象为一个同质的类主体时,实际上被当成了个体的简单放大。其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中的“人类”因被“抽象”成为虚幻的“类主体”,使得“人类整体利益”难以纳入一个个具体的功利主义者的视野。[5]实际上正是西方普遍认同的个人所奉行的工具主义水伦理价值观,才造成了当下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因此,正是上述种种局限,使得现代水伦理价值观难以构建起倡导人水和谐的水伦理体系。 从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来看,表面上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但从其论证逻辑来看,依然没有摆脱他们批判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人因具有“内在价值”而获得道德资格,水等自然物具有与人相同的“内在价值”,因而它们具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资格。在此,“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思路依然清晰可见。因此,想要彻底消解掉“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其“主体(人)-主体(水)”的主体际哲学框架,具有后现代哲学所普遍具有的“泛主体”、“泛价值”和“泛道德化”倾向,从而极易使人们走向“万物有灵论”或“神秘主义”。他们主张的大自然中水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的先在性和系统价值的最高性观点,极易导致人类价值和个体价值的自我贬低,使人们在人与水的交往实践中难以真正贯彻水伦理,水生态保护的原动力难以持久。[5]46因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和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都无法使人类真正走出水危机,无法将人类最终导向人与水相和谐共生的伦理境界。只有整合并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水伦理价值观,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水伦理价值观,才能和解人水矛盾,使人与水生态环境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6]26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也是构建新型人水关系的水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所在,是指导中国建设人与水和谐关系的总体性水伦理价值观。所谓“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就是在处理人与水的关系中,一切以提升人的幸福度为根本旨归,一切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动力,一切以全面发展的人为价值尺度,一切的人与水的交往行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用水权和赏水权,善待水环境,保护水系统,优化水生态,促进人与水的和谐共生与协调共进,实现人与水的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是以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交往实践观为理论依据的。所谓交往实践,是指“诸主体间通过改造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活动”。[7]55交往实践观具有以往实践观所没有的新特点:一是交往实践超越了单一的主体性,成为多极主体性的物质交往活动,交往实践中的主体际关系既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二是交往实践是“主体-客体-主体”多重关系的统一体。从静态的结构看,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发生主客关系;从动态运行的结构看,交往实践发生着多极主体间的双向变换、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三是“主体-客体-主体”的相关性模式。传统的“主体-客体”相关性框架是以各主体社会交往关系相分离为特征的,而“主体-客体-主体”框架是以主体间社会交往关系的统一为标志的。交往实践中,任何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所构成的主客关系,都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片段或环节,主体作用于客体时,都将关涉和制约到由客体中介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四是双向建构、双重整合。交往实践既建构交往关系结构,又建构参与交往的主体;既交往整合各级主体的形态,又交往整合各级主体共同体。五是交往实践具有系统性,六是交往实践具有历史性。[7]60#p#分页标题#e# 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正是建立在上述交往实践观基础之上的。首先,“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包含了“主体-客体-主体”这一新的哲学构架。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坚持的是“主体-客体”二分关系,“生态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主张的是“主体-主体”的主体际关系,而“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在此强调的是“人(主体)-水(客体)-人(主体)”的多级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关系。当“人”面对“水”环境客体时,一方面,“人与水”的“主-客”关系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以水环境客体为中介生成了一极主体与其它多极主体的“人(单个人)与人(多个他者)”的“主-主”关系,从而使水环境客体始终处在人类主体间的认识和实践关系之中。因此,“人与水”的“主-客”关系在“主-客-主”关系结构中仅仅是一个片断,一极的主体(个人或组织)通过水环境客体的中介,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与多极主体(同代或后代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从而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人与人”的“主-主”关系。可见,作为中介的水环境,其价值总是对人而言的,总是处在主体际的利益关系之中的,进而在它相关的多极主体间获得价值认同和道德关怀。 其次,“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重新确立了水环境的价值主体。水环境问题不在于坚持水环境要以人的价值为根本,人是水环境的唯一价值主体,这一点并无修正的必要。破解水危机问题也不在于要确证水等自然物的内在价值,从而把价值主体范围扩展到自然界。人水关系能否和谐的关键,在于我们确立以什么样的人为水环境价值主体。“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中的价值主体在此得到了新的规定,即不仅仅是指原来的“单个人”和“当代人”,也不再是“单面人”和“少数人”,而规定为“全面发展的人”、“当代人与后代人”、“最大多数人”或“全人类”,从而有助于避免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那种自私自利式的水态度和水行为,或者有助于矫正当代人急功近利式的治水与管水模式,进而促使人们从更全面、更长远的视角,以更谨慎和更尊重的态度与水和谐相处。 再次,“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倡导新的价值尺度。在坚持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尺度的前提下,对这一价值尺度予以重新修正:人与水的交往关系首先应当确立共时态价值尺度,即以“全面发展的人”和“最大多数人”的多样化利益需要为价值尺度。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往往会兼顾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经济需要与审美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等多方面和多层次需求的满足,从而在与水环境的交往实践中,会注重保护水的多样性、长远性和整体性价值,自觉尊重水环境和保护水生态的安全性。人与水的交往关系也应当确立历时态尺度,即以“当代人与后代人”同等的可持续健康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水伦理价值尺度。任何改造水环境的行为,都必须兼顾同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当代人的幸福指数提升以不影响后人的幸福追求为价值尺度。 最后,“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蕴含了水危机风险防范机制。以往的水伦理价值观,由于“主-客”框架和“主-主”框架的局限性,使得水环境的价值评价只来自单一的主体。这种单一向度的评价往往带有主观偏好,难以避免水生态和水环境遭受破坏与污染的风险。而“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由于内含“主体-客体-主体”的完整结构,使得水环境价值及水伦理形成了三重评价向度:即“自我评价、对中介客体即环境的评价,以及主体际互评”。[8]309这三种向度的评价,犹如三道水环境风险的防范网,水环境价值由此将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认同,人与水的交往行为将更加趋于理性,利用、改造和开发水环境的决策将更加科学,人与水的交往实践将置于更加广泛的监督之下,原来那种单一向度和片面评价所造成的生态风险将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是历经反思现代与后现代水伦理价值观基础上构建的一个新型的价值观,它克服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大水伦理价值观的局限性,在批判整合前两者中实现了水伦理价值观的理论超越,进而为水伦理学奠定了建构的理论基础,同时为坚定可持续发展信念,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我国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实践中,“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保护水生态环境运动提供了内在动力,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节水型社会,构建人水和谐的水伦理,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