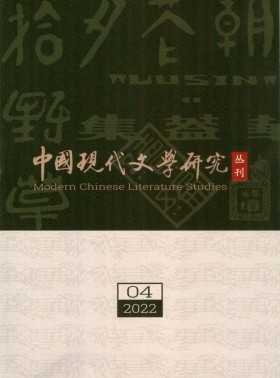现代文学三十年,“理想”可以说是个关键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下,随着诸种现代性的诉求,对理想的表述不仅成为知识分子个体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流露,也逐渐成为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社会理想不是凭空虚构的,其形成和表达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观。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表征现代性的线性历史观已普遍植入社会各界。这种线性历史观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使人们认为“时间是向前进步的、有意义的,是从过去、经过现在而走向将来的时间观念”[1]32。这样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观念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两个基础层面:一方面是对未来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未来理想的对照面———因为当时的危亡时局而形成的落后的焦虑。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交织,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主要结构。对未来理想的表述尽管晚清就已初现端倪,这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对将来中国的想象中就可以看到,但现代文学理想表述形式的突起与分化实际上还是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们共同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理想表述的激烈分化和急剧意识形态化。对未来理想的激情表述是对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的以革命为指向的激进主义的。而与激进的现代性诉求者们的理想取向相比,倾向于温和和保守现代性诉求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热衷于对理想的激进表述和乌托邦承诺,因而他们对社会理想的表述就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在后两类学人中,多数知识分子以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求实态度回避或淡化了对未来理想的表述,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诉求中,自觉不自觉表现出了理想表述的线性时间观,形成对激进现代性的反思,并对未来理想的表述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综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大家,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就属于这种另类。
通观其人其作,不难发现,两位作家都执着于自己所经验社会的理想表述形态,两位作家从创作之初其作品就与革命理想的线性时间观不相融。线性时间观是通过与过去或传统的对立和分离来理解自己,它不断地趋新和追求“进步”。而老舍和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理想表述,排斥了线性时间观所带来的“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老舍在创作中表述其社会理想受传统民间社会的循环时间观的影响,而沈从文则采用的是湘西世界的神话时间观。
一从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来看,老舍是来源于民间底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此的作家,他在创作中致力于启蒙,也致力于使自己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这决定了其小说尽管具有浓厚的文化启蒙色彩,但着力表现的还是民间普通大众的生活情感,是民间平民社会对社会生活的种种理想,这样一种理想与革命文学对未来理想的表述无疑会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老舍在其小说中是这样来构造人们所期盼的社会图景的: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人们对婚姻、爱情最本分的要求是有个安稳的家,就像《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所热望的和小福子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子里,“像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或者像《我这一辈子》中的小糊裱匠,凭自己的手艺挣饭吃,加上个人的小小计划,活着有奔头、有劲儿。显然这种社会理想的表现形式建立在老舍对线性时间观的怀疑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舍较为认同的是民间带有循环倾向的时间观念,其小说表现的理想着重点在于对“现在”时间段的叙述,希望在现实的基础上能有安定的生活出现。正由于此,老舍对现代社会走马灯似的种种思潮持怀疑态度,抱着极大的不信任乃至反感。老舍指出:“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2]184他认为当大多数人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都不可得的时候,小布尔乔亚的精神诉求实在近于无病呻吟。在老舍的心中,有着自己改造社会的模式。它首先出现在《赵子曰》里的李景纯身上。他对赵子曰说:“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作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3]373
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有志向的人往往从这两条路择其一,作为自己崇高的奋斗理想。《二马》里的李子荣、《铁牛与病鸭》中的铁牛,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形象;《猫城记》里的大鹰、《离婚》里的丁二乃至《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都是富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形象,这种改造社会的模式特点也是与民间底层社会特点紧密相联的。即其社会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性就如老舍所提供的两种改造社会的模式一样,并存于民间底层,两者此消彼长,构成其社会理想的相关组成部分。这是建立在现实经验实用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显然它并不寄希望于用任何理想彼岸的东西来修补这个世界的不足,在这个底层的世界里,现代以来的线性进化史观对民众已失去了蛊惑力,对动乱之苦的趋避,对安定的渴望成为整个民间底层社会超越一切的需求。其实若纵观老舍整个一生的创作,即使建国后他对未来时间段的表现也总是较为笨拙。比如在《龙须沟》、《茶馆》等话剧中,一到表现新社会,老舍所擅长的人物刻画就往往陷入概念化和模式化,他自己对此也直认不讳。从时间观念契入,我们或许还能发现老舍研究中一些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比如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话语里总认为老舍是在新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受到英国文学的启发才走上创作道路的。而从老舍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时间观念来看,实际情况应该是:老舍能成为一个作家,除了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外,他的个人底层生活境遇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其实老舍在谈到创作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老舍说他的写作是“借着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国家和个人”[4]115。
从本文的论述看,老舍是那种在传统与现代悖论间陷入极深的作家,他受到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但是他又怀疑线性时间观,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常常是传统循环倾向的时间观念决定了其创作中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
二相较于老舍,沈从文对线性时间观的怀疑更甚,他干脆彻底否定并摒弃了线性时间观,用“返回过去”和记忆来构筑自己的理想世界。在沈从文的记忆中,革命属于“砍头”和“杀戮”一类,为他所特别反感。他在回忆中叙述,在他的家乡,辛亥“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捉来的人只问问一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后来衙门又说‘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对此,沈从文总结道:“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怀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5]270-272从所谓的线性历史中,沈从文“读”到的是“愚蠢残酷的杀戮”,而不是当时众多人士所许诺的未来愿景。显然,过往经历和经验使他不认可革命作家们忙于唤起民众去参与革命,更不认可知识分子们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之相反,他认为需要改造和反省的不是民众,而是知识分子自身。与老舍一样,他同样要在作品中替底层民众说话,但选用了不同的时间轴线,采用了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话语策略。#p#分页标题#e#
不同于老舍质朴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沈从文试图用语言营造回忆性情境,诗意地再现底层民众的纯朴、善良、自尊、自重、自爱、诚信。这种创作目的决定了他肯定不会追循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这一潮流,而是将远离现代的传统或非现代性的东西确立为其理想的来源和出处。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里,沈从文选择了神话时间观,以神话充当了寻求社会理想的一个工具,从而放逐了线性时间观。因此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6]2“造庙”无疑就带有“宗教”意识形态和“神性”取向,取了“神话”的视角和神话的思维方式。普通人的生活,在他笔下就具有了“神性”的阐释维度。神话时间和历史线性时间的不同在于,历史线性时间是直线式向前发展的,它依此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一三段式的发展序列,存在越是靠拢时间前端的,越具有肯定性价值。相反,神话时间则是一种历史之外的时间,不是一种时间的前后延展,而是一种接近静止和共时性质的时间形态。“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活的方法与排泄情感娱乐上来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7]278沈从文向往和赞颂的湘西,是一个静谧、缓慢、恒永的世界,在近乎“静止”的时间形态中,湘西以其自在而本真的方式存在着。线性时间观无疑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如黑格尔把历史和时间视为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过程。与之相反,神话时间观就会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在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叙事话语表现了神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表现出对生命迷幻和神秘体验的热衷,这是对线性时间观核心理念———理性的消解。沈从文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来消解理性。一是梦魅书写。《边城》中翠翠与兄弟俩的爱情是通过唱歌发生的,而这唱歌又是翠翠通过梦境来感受的,各种生活都在其梦中以变形的形式出现,醒来后朦朦胧胧的她不知道自己的爱情究竟属于兄弟中的哪一个。三三、萧萧、凤子、夭夭无一不是美丽的造梦者,且她们完全不在意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而跨越了时间的线性所指。最典型的是《神巫之爱》中神巫的感受,在小说的结尾,神巫总算找到了他寻觅的哑女,却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还有更使他吃惊的事,在把帐门打开以后,原来这里的姊妹两个,并在一头,神巫疑心今夜的事完全是梦”[8]427,神巫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其实沈从文所描写的整个湘西世界,何尝不能作为一个个梦境去看呢?梦魅化使得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巫术般的神秘气氛,同时也消解了线性时间轴的前后逻辑,使过去的带有原始性的传统能不可思议的去而复返。再就是身体叙事。肉身无疑是消解理性的最好武器,带原始性的身体崇拜和在沈从文小说中无处不在,并被赋予神性。湘西的男子壮烈如山,女子柔美如水,两性的自然结合是湘西最美的诗意存在,对应于以自在自然方式存在的湘西山水和风俗。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原始性的描写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应和,他小说中的苗族想象和中国想象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族想象之间存在着荒原———拯救的同构、呼应关系。”[9]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不论能否直接对应于西方现代主义,但其确以独特的神话时间观念,诗意地表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两位对政治意识形态比较排斥的作家,在革命文学方兴未艾的年代,写出了意识形态格外强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和《猫城记》(1932年)。这两部作品均急于介入现实政治意识形态,都对现实政治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与他们创作的一贯风格格格不入。这说明两人也都受到与革命作家相同的落后焦虑的影响,但两人化解焦虑的态度和方式不同于革命文学。两位作家的化解方式都不是求诸于彼岸世界,老舍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而沈从文是求解于记忆之中。对于现在他们都表现出忧虑,对于未来,他们更表现出深深的焦虑。就老舍而言,一方面,他从启蒙的现代性角度对民间文化中的落后面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坚守民间最核心道德观和做人准则的底层人民生活却不断走向毁灭,这带给老舍面对未来时极深的痛苦。在《猫城记》的后半部分,老舍突破了自己在前半部分较为克制的叙述,控制不住地把自己的悲观、失望、痛苦、无奈,借“我”之口一股脑地倾诉而出:“……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10]490对于沈从文而言,他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写了都市与乡村两个世界。第一卷是对都市现实的无情批判,到第二卷他对现在的都市已彻底失望,他把笔墨荡回到湘西。他在序中写道:“我应当告读者的,是这书与第一卷稍稍不同,因为生活影响于心情,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又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11]147这“力量”便来自湘西故土,而他又明明感觉到这种力量在未来已不可能出现,只能来自记忆中的过去,只能表现出一种美丽的忧伤,从而以不被大多数时人理解的“返回过去”来化解焦虑。
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社会理想,尽管与革命文学比起来颇为另类,但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代表了受传统较深影响的底层社会对理想的理解和表达,是现代文学关于社会理想的多元化表述。从“救亡”的角度看来,由于放逐了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他们的理想表述在当时失去了一种能够凝聚中国社会人心的精神力量。这在一个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时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样一种理想表述在当时是对革命文学理想表述的一种补充和制约,而在激进的现代性诉求常常由于种种错误而进入歧途并最终耗尽激情之后,它又是对未来理想表述的一种反思性力量。当然,它自身也是作为应该反思的对象而存在的。可以说,正是不同理想叙述形式的相互交织与作用,才形成了现代文学上世纪三十年理想叙述的经典性、复杂性和反思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