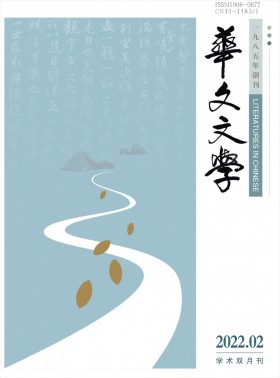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史上的渔父形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给所论之渔父(一般还有诸如渔夫、渔翁等称呼)特意加个引号,是因为讨论所及,不完全限于那种以打渔(包括钓鱼、捕鱼等活动)为生的人,而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在水上讨生活的人群。但就整个中国文学史(指的是从古代拉通到现当代。以下如非特别指出,文中所说文学史即此意义)来看,由对打渔为生的渔父到更广泛一类人物的观照,是经历了一个前后不同的视角变化过程的,且由此而有本文所指陈的“渔父”形象的古今演变。 一一般认为,姜尚是出现在历史上的第一个渔父。关于姜尚(又叫吕尚、太公望)之事,文献多有记载。《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谢曰:“……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①《史记•齐太公世家》亦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適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②《韩诗外传》卷八对姜尚事迹记得更为详细: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于棘津,钓于’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 ③此外,《吕氏春秋》、《说苑》、《水经注》等典籍对此也有记载。但问题是,这个叫姜尚的渔父,乃历史人物;上引文献材料,也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去进行记载的。不过,虽然这与我们要讨论的作为文学形象的渔父还有很大距离,但作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人物原型,它却不无启示,并由此与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了文学描写对象的“渔父”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文学史上,“渔父”被当做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首见于《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④ 在这段文字以下,作者充分展开而叙写了孔子见到渔父以及和渔父对话的过程。首先是渔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的谈话,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接着写孔子见到渔父,受到渔父的直接批评,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应该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进一步写渔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谓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最后又描写了孔子对渔父谦恭、崇敬的态度。 虽然,在渔父与孔子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展开的活动中,作者真正的创作动机是要凸现隐藏在渔父形象背后的那个“道”,并以此来批驳“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的儒家价值观———这跟《庄子•秋水》篇中虽然也有“庄子钓于濮水”⑤的描写,但仅仅是作为一个叙事背景出现,重心乃在“宁生而曳尾涂中”的价值表现是同样的逻辑。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明显地,《庄子•渔父》篇中渔父形象的塑造至少较之前面关于姜尚的记载,不仅记叙更为充分,而且最大不同的是,这个渔父显然是个虚构的人物,故在客观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文学性。 进一步来看,这种文学性,既体现在通过渔父那番洋洋洒洒的言论所表达的关于“慎守其真”、“法天贵真”而反对“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道家思想的阐说当中,还清晰地见于各种文学手法的综合运用上:诸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以及心理、细节刻画,场面、神态描绘和对比、映衬等成熟的叙事文学所具备的种种艺术手法,在这段文字中都可以找到。由此,一个超然物外,潇洒自如的文学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而作为陪衬人物的孔子,其惶然劳形、恭敬谦卑的形象同样也十分生动。 屈原也有《渔父》涉及到了渔父形象的描写:“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⑥关于此文作者归属问题,尚存有争议;此处我们且从王逸“《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⑦之说,而将之归于屈原名下。较之《庄子•渔父》,屈原此篇虽然就文学手法的运用来讲,不如前者繁复多变,但本篇剔除了《庄子•渔父》那里多少于文学性表现有所妨碍之嫌的大段对话,而采用更为简练省净的笔墨,聊聊数语,即把无论是屈原,还是渔父的形象,都刻画得生动传神,却是颇为成功的一点:“忧愁叹吟,仪容变易”的屈原、“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⑧的渔父,无不对比鲜明而如在目前;尤其是渔父在其说屈原不得后,莞尔而笑,鼓+自歌,不复与言而去的那种超然物外风格,更被传达得淋漓尽致。 自此以后,文学史上开始渐渐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渔父”形象系列。且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渔与耕、樵、读并有的重大文化意义;单就文学领域而言,渔父形象和主题,不管是在艰难无道之代,还是昌明繁荣之世,亦不论是下层不遇文人,还是得意之士,甚或帝王将相等,都有纷纭众多之表现。 如《南史•隐逸列传》中就记载了一位标为“渔父”的隐士,其形象的表现同屈原那里的“渔父”可说是完全一致的: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陵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河水--。相忘为乐,贪饵吞钩。#p#分页标题#e# 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⑨ 在这则故事中,更进一步地强化和凸显了渔父的隐逸形象特征和作品所要传达的隐逸主题:在《庄子•渔父》篇中,主要的写作动机是有关“道”的阐发,故渔父的“说教”面孔还颇为突出;而到屈原那里,渔父其实又更多地是作为主人公的陪衬人物出场的,要凸显的仍是屈原这个主要人物及其坚守的“道”。但到《南史•隐逸列传》这里,虽一样也有“道”的阐发,却是作为人物描写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出现于篇中的(传达人物形象的隐逸特征的必要内容),而且,渔父自始至终都是作品刻写的中心和主要人物。 后来的《宋史•隐逸列传》⑩中,写到一个松江渔翁,其出处选择及形象表现,跟《南史》里的渔父可说是大同小异。兹不再赘述。 至于在作为抒情文体的诗、词、曲等中,有关渔父的形象描绘,更是纷纭众多;尤其是唐代以后,作为审美意象的渔父在抒情体文学领域愈发常见。但这种渔父形象或意象的表现,却又有很大的分别。对此,宋代王令有一首《不愿渔》写道:“终焉可百为,不愿为渔子。当时渭阳人,自是直钓耳。今非结网身,岂有得鱼喜。试身风波间,特用豢妻子。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瑏瑡?虽然看似同为“渔”,但实质上却有迥然的不同。至于到底如何不同,王令之前唐代白居易的《渭上偶钓》一诗,就已说得非常清楚:“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偶持一竿竹,悬钓至其傍。微风吹钓丝,..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在这里,白居易明确地把“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的钓者具体分别为三类:“钓鱼”者,“钓人”者以及“对鱼坐”而“心在无何乡”者———这其实也正是现实生活中那种以打渔为生的渔父,在进入文学领域后分化出的三种不同类型。 “钓鱼”者一类,指的自然就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渔父原型(为区别起见,这类人本文统以“渔夫”相称)。在文学史上,对这类形象的关注和描写,并不多见。如清代郑板桥的《渔家》即为其中一例,它对渔父生活的现实情景进行了如实描绘:“卖得鲜鱼百二钱,籴粮炊饭放归船。拔来湿苇烧难著,晒在垂杨古岸边。”瑏瑣?而“钓人”者,指的就是类似姜尚那种借钓鱼以引起政治系统关注,进而干求功名,亦即志不在物质层面上的鱼,而在仕途、爵禄这样的“鱼”者。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躬行此事,还是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如此愿望者,实为不少,唐代李白《行路难》“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即其典型。而宋代王安石《浪淘沙令》一词同样对“钓人”的价值选择作了高度肯定:“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至于最后一类,其实即所谓“避世而隐于渔者也”瑏瑦?,也就是名为渔父,实为隐士。这种人虽然在生活内容、存在方式上看似与现实中那种完全以打渔为生计之业和全部社会内容的渔夫有相同处,但二者实有本质的分别:我们以为,隐逸之所以能够成为话题,正在于其中包含有值得我们探讨、深究的文化史的因子;就其主体来说,他不是樵者之类的普通人,而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重大的士人———我们认为,区别普通人与士人的,无它,仅在一“道”字而已。对此,王夫之明确地说道,“隐之为言,藏道自居,而非无可藏者也”。有知识的主观凭藉,有知识而来的自己的思想和尊严等,即是这个“道”所应含之义瑏瑧?。也就是说,与渔夫“无可藏者也”不同的是,可称之为渔隐的这类人乃所谓“藏道”者,即他们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方式、生存意义等等都有着渔夫那里完全没有的那种主动、自觉和理性的价值思考、判断与选择。 相较之下,中国古代文人关注的从来就以渔隐为主;亦即,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实际成为了种种隐士的表现形式之一。换句话说就是,由最早的渔父原型人物姜尚发展到后来,凸显的主要是其超越现实层面之上的精神特质与内涵的表达,从而使“渔父”在实际上成为了表现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至于“渔父”一语所指陈的物质生活,即真正打渔部分的内容,在这种表达中自然被尽可能地省略和虚化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则越发突出。 通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种“渔父”,就其形象特征来看,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内容:连人物起码的姓名、出处(《宋史》那里只多加了“松江”这个地名而已)等情况也没有交代,以打渔为业,以远离世俗(主要是指传统主流价值观所一直认同的政治体制)的隐逸为主要的存在方式,人生态度上表现为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洒落自得;而从思想渊源来看,则又主要是道家任真全性,与自然(道)为一的思想在起作用。关于后者,即隐逸思想源流问题,笔者曾在拙文《先秦儒道隐逸观及其形象表现之不同》中简要论及了影响最大的儒、道隐逸思想之分别问题。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仅从这句话看来,似“有道”之世,士人方可求仕、入世,而“无道”之际,则大可隐去。但从孔子及其他儒家的行为来看,其实大不然。有道还是无道,儒家从不曾脱离“世”的系统。所以,孔子在说“无道则隐”的同时,还谈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显然,此“隐”仍是行义的一种方式,仍是要求参与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去。#p#分页标题#e# 而道家的隐逸观呢,则是庄子一方面看到了“处江海而闲”之“隐”,但另一方面,他更要崇尚“无江海而闲”的“隐”———如果说,“处江海而闲”之“隐”是以山林皋壤来超越尘俗生活的话,那么,“无江海而闲”的“隐”则更是连山林皋壤也一并超越,而达到一种纯然精神上的、实现了个体生命自由的逍遥游境界。这样,隐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实现“生”之逍遥。不过,由于道家无论怎样强调主观上个体精神的超越,而他终究不能须臾脱离现实,因此,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山林皋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道家之“隐”往往同林泉岩穴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也是为什么与此同时有些隐逸(他们往往被视为是具有道家倾向的)并不重视、甚至看轻林泉岩穴的缘故。 这种分别,显然可进一步从前述的无论是《庄子•渔父》篇,还是屈原那里的“渔父”,《南史》里的“渔父”,《宋史》中的松江渔翁等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上得到充分说明。 二但这种情况,在发展到现当代文学后则发生了迥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照:首先是表现对象上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古代文人从种种水上讨生活的那类人群中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了渔父(又主要是作为隐士的渔父)身上的话,那么到了现当代作家这里,他们的视角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相对狭隘的渔父,而大大扩展到了整个与渔父处于类似生活情境中的其他人群,诸如“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 渡船夫(船家)、纤夫等等,由此,在古代文人那里作为中心和主要表现对象的渔父,如今仅仅是表现对象之一种,从而体现出对象的扩大化或曰泛化。这方面的作品很多,例如:“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我心中一惊,这才知道船家竟是个老太太!一头银丝,满脸皱纹,褂袖与裤子都高绾着,腿和胳膊都形同朽木,身上不着丝毫雨具,任凭风吹雨打,眼里的光芒却不肯熄灭。”瑐瑢?“……初回来时,年纪较轻的本地人全不认识,只四十岁以上的人提起时才记得起。对于这个人,老同乡一望而知这十余年来在外面生活是不甚得意的。头发业已花白,一只手似乎扭坏了,转动不怎么灵便,面貌萎悴,衣服有点拖拖沓沓,背上的包袱小小的,分量也轻轻的。回到乡下来的意思,原来是想向同乡告个帮,做一个会,集五百吊钱,再打一只船,来水上和二三十岁小伙子挣饭吃。” 自然也有渔父,如孙犁笔下出入于白洋淀里那个“自信和自尊”的老头子:“撑船的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子,船是一只尖尖的小船。老头子只穿一件蓝色的破旧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篙。……” 李杭育那里葛川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他精壮得像一只硬梆梆的老甲鱼,五十岁了,却还有小伙子们那种荒唐劲头,还能凭这点劲头搞上个把不大规矩的婆娘。 他的赭红色的宽得像一扇橱门似的背脊,暴起一棱棱筋肉,像是木匠没把门板刨平;在他的右边肩胛骨下,那块暗红色的疤痕又恰似这橱门的拉手。这块伤疤是早先跟人家抢网打起架来,被对方用篙子上的矛头戳的。”瑐瑥?张炜那里的老筋头:“老头子弓着腰才能从窝棚里钻出来,直起腰,就显出瘦干干的高个子。他恼怒地向一边吆喝什么,没有回应,也就坐下来。好像他在吆喝自己的老伴或者孩子。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是真正的光棍一条。” 再如聂鑫森笔下死湖边的垂钓者:“湖东的几株垂柳下,颤颤地伸出三支钓竿。一支是三节竿、可伸可缩,手柄是有机玻璃雕制的,透明如水晶,看得出是从渔具店买来的。浮标呢,是一截又粗又短的软木,白白嫩嫩,像一截小藕。……”瑐瑧?徐岩那里所描写的那个瘸腿的捕鱼汉子:“男人瘸着一条腿,走起路来极吃力的样子,有些像江岸深处红柳丛中穿梭往来的跳鼠。男人瘦削的肩上扛着两挂网,网穗上结着的一些铅疙瘩在他的胸前哗啷啷直响。” 由以上所引还可看到表现对象变迁的其他一些内容,诸如渔父由古代的基本上是知识精英阶层而变化为现当代的广大社会下层百姓,也由古代文学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老年人而扩大到中青年,由男性而至于女性;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由江河湖泊而扩大到大海(古代文学中也偶有把渔父的活动地点设置在海滨的,但总的来看比较少见)。 此外,这种对象的变迁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原来在古代文学中主要是作为背景出现于作品中的关于江河湖泊等的环境描写,到现当代文学中,其本身就是作家要着力描写和表现的一个对象,如:“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p#分页标题#e# 显然,这里描写的,也是沈从文“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 而必需的表现对象,也是作者“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对象之一。 这种情况,同样也体现于李杭育的笔下。他关于葛川江的描写,显然也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材料,而是被作者当做葛川江上诸如福奎、大黑、四婶、阿林、阿环、阿村们一样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充满了坚韧顽强辛酸爱恨情仇等丰富、复杂人性内容的一个必须的观照对象:“在这里,中游向下游的过渡,葛川大岭到头了。南岸断断续续的群山的余脉,也自灵山逐渐收势。葛川江跃出葱茏,挣脱了两岸大山的夹持,面前忽向它敞开了下游平原,一个坦坦荡荡的世界。一时间,它有些茫然,何去何从游移不定,无数的选择机会反叫它见异思迁,乱了章法。这里拱拱,缩回来又去那边逛逛,便在三里渚一带不负责任地瞎流一气,兜出七汊八湾,把古安县仅有的一小块平原撕成一片一片,破破碎碎地勉强拼凑。……你看葛川江从容流去的样子,就像它坚信会有流回来的一天。”瑑瑢?所以,王蒙为此曾说:“葛川江像是一个古老、威严、暴烈而又多变的精灵……”其话语背后的将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对象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其次是描写内容和主题上的变化。较之古代文学,现当代作家们没有再刻意去表现古代文人那里的隐逸文化内容及主题(至于“钓人”主题,在现当代作家这里更是消泯无迹了),而是以描写“渔父”的现实生活为主;或者说,在现当代文学中,“渔父”不再只是一个隐逸文化的象征符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生生,有种种喜怒哀乐世俗情感内容的现实人物,是这个人物跟水,跟“渔”有关的全部现实生活。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当代作家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不管其创作动机如何,总之在客观上,李杭育全面、淋漓地向人们展现了葛川江上一系列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喜或悲,或苦或乐,或美或丑的现实生活状态。如有论者在谈到《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福奎这个主人公时就曾指出,作者笔下的人物是现实的而非象征的,福奎作为“葛川江人”一出现,便带着他特有的复杂性教人陷入沉思。他同样追求着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全部本分的需求,矛盾在于,当同村人生活潜在地起着变化,走向富裕的同时,福奎作为昔日葛川江上的强者,非但没改变他光棍汉的处境,反而日渐潦倒。这是小说的焦点,也是主人公心理矛盾、纠结、跌宕的触发点。 这种“现实性”在这个系列的其他人物那里同样得到了鲜明体现,如《葛川江上人家》中的四婶,作者写道:“四婶倒不是秦寨老祖宗的种。她十六岁从龙阳山那边嫁过来,一口气养了五个女儿,二十八九岁就徐娘半老了。丈夫老四死后,纤板归她了,靠这条修修补补凑合着用的破船养家活口,钱挣得倒也不少。这会儿,她扶着舵把,让船头稍稍偏斜一些,避开那些被洪水卷来的树枝。江上漂满了杂物,地上长的、岸上搁的、人家用的,但凡能漂起来的,什么都有,像是百货展销。四婶的脸紧紧绷着,像一张灰白的光板羊皮。她虽说还沉得住气,也心知大祸临头了。当然,她和秋子都有好水性,万不得已就弃船下水,兴许能捞回命来。叫她为难的是,丢了船,即使她娘俩能侥幸活命,日后又指望啥呢?秋子还没出嫁,秋妹才念初中,三姐儿还不会挑花,四丫头只会玩鸡逗狗,五妞还拖鼻涕……”瑑瑥?一个混杂于一群在葛川江上吃弄船饭的汉子中的坚韧得令人心酸又不无敬佩的女性形象,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下层妇女的生活情形,如此地跃然纸上。 徐岩《杀生鱼》中的瘸腿男人和他的女人的生活也一样充满了这种强烈的现实性:“稍后,两人都夸到了瘸腿男人的女人。瘸腿男人说的话让老赵惊讶不已。两人竟是后到一起的一对夫妻,女人走了两户人家,吃了两家井水。女人原来的丈夫是个赌徒,动辄就酗酒打骂她们娘俩,女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过日子。对于那个恶徒来说终于有了报应,在一次酒后聚赌时因赌资纠纷动刀子杀了人被判了极刑。女人解脱了,但日子过得却苦,经人介绍便又走了一家,也就是嫁给了打鱼的光棍汉瘸腿男人。孩子带过来时就十三岁了,瘸腿男人出钱把她送到镇上念了书。老赵说原来老哥竟是个有情有义的捕鱼汉子呀。瘸腿男人呷了一大口酒然后神采飞扬地说,咱说不上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却也应该有一颗拍得响的良心。” 由此可见,现当代作家们关注的不再是“藏道”的“渔父”形象,不是他们那种远离,乃至于超越现实生活之上淡泊、超然的得道之境,而是普普通通的世俗中人,且大都是那种社会底层人物,是他们的令人动容的喜怒哀乐,是他们在油盐柴米中的折腾和挣扎,幸福和不幸,有情和无情……当然,现当代作家们也描写和传达了他们面对这种时代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等所作出的深切思考与反省,或者说,这种思考与反省同样成为现当代作家的一个重要描写内容。如张炜在《古船》中隋不召手指众人说:“老船摆在省城,连外国人都去看它。它老家倒无人去看。二十多年了,负责看守的人告诉,老船半夜里就呜噜呜噜哭,它想家。二十多年了没去一个人看它,真是对它不起。我给老船跪下了。给它磕头。我说服了看守的人,用手去摸了它,这是二十多年里第一次有人摸它。我的手指刚刚挨上,它就抖起来。我摸着,它抖着,后来我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说老船呀你想开些,洼狸镇人都是些不忠不孝的人;再说二十多年里也不得空闲。先是忙着革新和炼钢,后来饿坏了又不能远行;刚能吃饱了走路,红卫兵又兴起来了,镇城墙上有机枪……我哭啊说啊,参观老船的人都跟着我流泪了。连外国人也流了泪。外国人的眼泪是绿颜色的。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洼狸镇今天松和一点,俺这就接你回老家去。郑和大叔不在了,我这个小兵伺候你吧;我死了,再让知常接替我。看守的人说,‘这不能够。’我哭着离开了。”瑑瑧?这段极具象征和隐喻特色的描写,显然是作家面对当代种种变化所作出的深沉思考与反省。#p#分页标题#e# 再次是审美倾向的变化。因对象的变迁,描写内容、主题的变化,由此导致这种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在审美倾向上,自然也呈现出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极大不同。古代文学的这类作品,审美倾向上表现为省净、简约、阴柔,予人以超然淡泊、自然宁静的审美之趣,到了现当代作家笔下,因其强烈而突出的现实主义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则体现为相应的凝重、悲怆、刚健的审美倾向。同时,这种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遵循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递进式地发生的。就现代到当代来看,如果说,在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这样的跨越现当代的老作家那里,一定程度上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古代同类题材的审美风尚的话,那么到当代作家如李杭育,如张炜等这里,则几乎是将之前那种优雅、从容的审美趣尚荡然一空了。 如王蒙谈到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时就指出:“他客观上直觉地意识到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巨大威胁,他的洒饵喂鱼颇有一种孤独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壮美呢。”瑑瑨?后毅则说:“从文学对人的审美观照来看,他们又都展示了人性中力的强度与美感,在精神上涂上了昂扬向上的宗教色彩。”瑑瑩?耿立、军磊论及张炜的《古船》时也着重谈道,在《古船》中,张炜却把艺术触角伸进了农民文化意识的底层,把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群体与个体进行全面关照。作品中既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人物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像《你好本林同志》那样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而是把笔墨集注到了人类的苦难与耻辱、痛苦与焦灼。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总体来看,最为突出的则是浪漫主义的写意手法为现实主义的写实所取代。由于古代“渔父”题材的重心,是要通过“渔父”与非“渔父”、出世与入世态度等的对比(后来的这类作品虽一般是径直描写“渔父”,但潜在地还是存在着这层对比),传达一个逍遥自在、从容自得、洒脱自如的人生境界,“渔父”本身的行事并不是重点,故往往简略写之;加上这种人生境界,本就带有强烈的超现实的浪漫成分,也决定了它的表现手法是写意的。 但到了现当代文学阶段,作家的目光和心思基本上都放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自然使得他们在创作时,要采用一种写实的手法,既具体如绘地描写江河湖泊大海,更要历历描写生、长、死在这江、这河、这湖、这海上的男女老少的全面、丰富乃至细琐的油盐柴米生活,和喜怒哀乐的生存状态。由此,一方面,传统题材那里已有的一些手法,如人物形象的塑造、对话描写、心理刻画、细节描写等到现当代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叙事手法也更趋丰富和复杂多样,诸如典型的运用,顺叙、倒叙、插叙、平叙的安排,常规线性与多线性、环线性叙事等的结合,等等。 如李杭育《珊瑚沙上的弄潮儿》描写康达这个人物,康达很担心自己的体力是否吃得消。这两年,他明显地开始发胖,腹部凸出来了,胸脯上一堆肥肉,胳膊圆滚滚的像条打足了气的车胎,摸上去光溜溜的。他脸色看上去不错,苍白中透点红润,额头、眼角都还没起一丝皱纹,丰腴、光洁的面颊上一笑便漾开两个酒涡,愈发显得年轻、活泼。但这全是假象。他自己有数,苍白是真的,那点红润却是由于血压偏高的缘故。照宾州人的习惯说法,他是只“空心萝卜”。 他天天吃减肥茶,做俯卧撑,却总不见效。 这里对康达的外貌、身体状况等都作了异常充分细致的写实,这显然与古代涉及此类人物时那种寥寥几笔的简略刻画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更能表现出作家植根现实,描写现实的创作动机。 三当然,上述的从古代到现当代“渔父”题材所出现的这些变化,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从文学创作领域自身来说,也可从外部环境———精神的,文化的环境,客观的物质环境———来看。限于篇幅,本文只打算从以下两个方面简略谈谈:一是客观物质环境,这里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的变化。现当代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涉及到了这一点,如李杭育写道:“可惜呀,如今鲥鱼稀罕得很,几乎在葛川江里绝迹了。这条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这也许就是葛川江里最后一条鲥鱼了,就像他本人是这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渔佬儿享受最后一条鲥鱼,这倒是天经地义的。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口福。这条鲥鱼他要留着自己独个儿吃……”瑒瑢?至于评论家们也纷纷注意到了作家们对这种变化的深切关注:“她是古老的,在日新月异的现世界现时代,葛川江的古朴风习简直像活的文物。渔佬和画师爹也许像上一代的遗民。时代似乎已经抛弃了他们,但他们仍然如此地执着,如此地忠于自己的已经过了时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瑒瑣?作者以一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诚挚的同情心描写了他们的不幸遭遇。无论是那位一辈子在葛川江打鱼谋生的渔佬儿福奎(《最后一个渔佬儿》),或是那位手艺高超、久享盛名的画屋师爹耀鑫(《沙灶遗风》),还是那位乐观豁达、深谙水性的弄潮老头(《珊瑚沙上的弄潮儿》),他们都曾是各自所操行当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在祖祖辈辈赖以滋养生息的葛川江及其两岸,辛勤地劳作,默默地生活。然而蓬勃发展的农村经济,搅乱了他们平稳迟缓的生活节奏,甚至威胁到他们古老的谋生手段……瑒瑤?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备尝由此而来的适应或不适应,及其或欢欣或痛苦,或幸或不幸,作为其中一员的作家们自也要如实地描绘和表现这种巨大变化,并以此传达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反省。 其次,“渔父”题材的这种古今演变,还跟文学的价值追求,及其所要表现的人性(自由本质)的发展有关。关于文学的价值问题,骆玉明先生曾这样谈道:“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质、创造其自身生活一种特殊方式。文学固然根源于并反映了现实生活,但它绝不会成为后者的镜像;它总是更多地表现了意欲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而这种意欲和想象如果是合理的,便会改变现实生活的内容乃至人自身。进一步说,文学的所谓‘合理’又是具有特殊性的。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或证明现存秩序的正当性并维护它的继续存在,或意图用另一种预设的秩序来代替前者,文学却是直接从感性、从生命本真的欲求出发,所以优秀的作品总是能深刻地揭示人性的困境,人性欲求与社会规制的矛盾……”瑒瑥?至于具体到中国社会,这种人性因历史而有的丰富复杂的变化发展,骆玉明先生也有论及,他说:“我们可以把古代文学后期人本主义精神的成长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变异’现象,因为它以个人为本位,重视人的情感与欲望,肯定人的自由意志的态度,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个体自我克制,要求其服从群体意志和尊长威权的态度存在着直接地矛盾与冲突。”瑒?瑦具体言之,这种“变异”,愈到后来———按传统说法,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则愈突出;由此,无论是价值观、对人的个体欲望、情感、个性等的认同与展示,在现当代文学当中,自然也相应地愈发丰富复杂,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历史变化要求文学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展变化,而促使文学创作进行相应的调整。#p#分页标题#e# 这种调整,就“渔父”题材来看,就是要求现当代作家不能再像古代文人那样,只把目光集中在仅仅作为整个社会极少数的、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渔隐身上,而必须扩大了去关注,去表现占据社会更大多数的社会下层百姓的现实人生百态和喜怒哀乐的情感欲望等。故,一以言之就是,“渔父”题材之所以出现上述的古今演变问题,正是社会历史及文学发展变化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