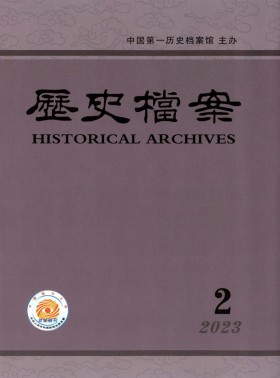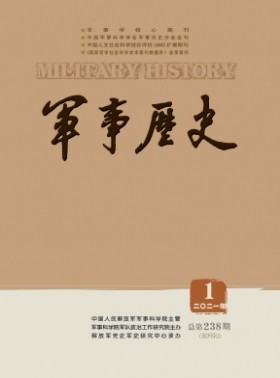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看捻军文学创作,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当下,随着历史题材影视剧、红色经典剧的热播,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又重新崛起在中国的文坛上,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概念模糊的现象,诸如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历史文学创作应坚持怎样的原则,等等。
历史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也是过往事实足印的记载。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艺术结晶。历史与文学是两个概念,两种体系,前者要求史料翔实,考证精确,客观叙述,绝无粉饰;后者要求富有想象,大胆创造;前者是铁板一块,后者是鲜花一丛。如此看来,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对历史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就出现了许多不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作品。但不管怎样,最终人们还是从无数的创作实践和认识经验中获得了共识,归纳出一条历史文学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坚持历史框架、历史精神、历史走向不变的大前提下,作家按照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展现、发挥各自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塑造人物形象,谱写自己的作品。郭沫若先生的创作方法,笔者以为是可取的。他在从事历史研究中,严格遵循四个字,即实事求是。他在进行历史文学写作中,也坚持四个字,即失事求似,意思是失去历史表面上形式上的事实,追求精神上本质上的相似。也就是讲,在时代背景、人物活动的场景和事件发生的地理环境、历史的走向、历史的精神上要“实事求是”,而在具体到人物塑造、场景描绘、情节安排、气氛烘托上要“失事求似”,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艺术虚构①。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艺术审美规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还历史原貌,让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借鉴;作家的任务是让读者从历史境界中获得美感,获得心灵的震撼。因此,历史文学的作家既要戴着镣铐跳舞,又要戴着镣铐飞翔,确实要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硬功夫。张笑天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文学作家,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但历史小说什么可以虚构,什么不可以虚构?我遵循的原则是,重要的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年代都必须真实,写项羽爱上吕后、刘邦与虞姬有染不能叫历史真实……写历史小说,包括那个时代的服饰、语言、官职、称呼、生活习惯等等看似细微末节之处,都必须有考证,细节失真会导致通篇失败”[1]。张笑天在《重庆谈判》里就虚构了与的一场重头戏。他根据毛、蒋同住宿林园,且二人都有早起的习惯,早晨他们在林中散步不期而遇,并在石桌旁小坐交谈半小时的史实虚构了一场戏。但他是依据当时的社会斗争焦点,毛、蒋两位领袖人物的知识素养、语言风格、性格特点以及所思所想虚构的,所以得到了史家和观众的认可。所以我们说,历史文学的虚构部分,只要合理,合乎人物身份,合乎逻辑,能使读者认为可信并在无形中受到感染,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所虚构的情节与历史真实应达到一脉相承、音律和谐、化为一体。
著名学者蒋星煜先生的历史小说在国内外颇受读者欢迎。他的历史小说《李世民与魏徵》改编成京剧《兴唐鉴》,他的《南包公海瑞》改编成《海瑞上疏》,他的《包拯》、《海瑞》被一次又一次印刷出版。他的所有历史小说都力求严格按照时空的逻辑顺序推进演绎,他笔下赖以衍发的环境、衣着、用具都做到唐宋不同,明清各异,一一都有质的定性的东西。他正是严格遵循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创作的。
捻军起义是19世纪中叶爆发在黄淮平原上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运动,它掀起的反清斗争无论从时间跨度、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仅仅次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捻军比太平天国产生时间要早,延续的时间比太平天国还长。捻军前后坚持抗清斗争18年,最高潮时期总兵力有数十万人,先后转战于安徽、河南、湖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直隶等十省区。它不仅是太平天国的盟友和北方的屏障,还是太平天国败亡后的继承者,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特别是在后期,它几乎成了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强大后盾。捻军运动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不仅从政治上动摇了其在黄河流域的政治体系,还使得清室财政危机加重,更在军事上摧毁了它的政治支柱,前后消灭数十万清军及地方团练武装。捻军运动在18年的浴血斗争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超群领袖人物,像盟主张乐行、军师龚得树、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等等。在这些将领的统率下,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战法战术,如装旗战、圩寨战、流动战、步骑联合战、圈圈战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捻军是伟大的农民运动,捻军是近代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捻军在反抗清王朝统治和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出生入死的战斗精神和辉煌业绩对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就曾着力宣传颂扬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斗争精神,借以鼓动会员和民众的抗清意志。安徽督军柏文蔚曾派员专门调查捻军历史予以张扬。已故的著名捻军史专家郭豫明先生在他的专著《捻军史》里写道:“捻军这支纵横中原的劲旅,以自己的顽强战斗和卓著业绩,在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2]609。学者徐松荣也在他的专著《捻军史稿》里写道:“捻军起义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跳出苦海,反抗剥削压迫,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农民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他们的抗清业绩和英勇无畏精神将永垂史册,光照人间。”[3]541-542可以说捻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文艺紧密联系。捻军将士和他们的乡亲们创作了数以百计的歌谣、故事,形象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当时就曾为鼓舞他们抗清斗争的豪情发挥过作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捻军故乡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又不辞辛苦地搜集、整理、发表了大量的捻军歌谣和传说故事,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捻军颂》、电影文学剧本《捻军》、《乾坤剑》和小说《雉河集起义》等。80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星星草》、《紫尘三杰》、《军殇》和《捻军》,这些作品在国内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笔者认为,历史剧《捻军颂》、电影文学剧本《捻军》、长篇小说《星星草》(凌力)和《捻军》(史清禄)是称得上优秀之作的,是符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的,是实现了作家所追求的“文学应当使人向上,应当激励人们挞伐假、恶、丑,鼓舞人们实现灵魂和操行的真、善、美,应当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最美好、最高尚的东西开掘出来,奉献给人民和世界文明”[4]的宏伟目标的。#p#分页标题#e#
但也毋庸讳言,有些作品显然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蓄意编造历史情节,展示低级趣味的性描写,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语言、性格、行动更是空穴来风地“胡写”,既背离了历史真实,又玷污了文学的美学性原则,这一切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捻军研究学会为了进一步活跃捻军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出精品力作,专门召开“捻军暨捻军文学创作研讨会”,这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目前我国的文学事业正呈现出一个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人才辈出,新作不断。捻军是近代农民运动的正义之师,是历史文学创作的重大题材,作家应该勇于担当歌颂捻军英雄的重任,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那么,怎样的作家才称得上经典作家,怎样的作品才堪称经典呢?与雨果同时代的理论家圣伯夫认为:“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是一位丰富人类精神的作者。它确实增添了人类精神的宝藏,他推动了人类精神向前一步的发展,他发现了某些不容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对那些似乎人人皆知,早已被探讨过的永恒激情作一番全新的考查。”[5]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天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都具有独立的艺术个性和写作特色,因而对同一题材的理解、感受的程度和对人生现实意义观照的程度也不相同,写出的作品必然千差万别。平心而论,我们当前出版的一些历史文学、影视作品,有的“观照现实”过度,有的“硬贴”、“硬靠”,有的“戏说”,有的“胡说”,更有一些“胡写”、“漫扯”的低俗作品。难怪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期仍在批评我们中国的作家少有自己的观点,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笔者认为,能够丰富人类精神,推动人类精神向前发展的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志,就是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探索。像雨果的《悲惨世界》是通过主人公冉•阿让灵魂的挣扎展开对社会的批判;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是通过那位含泪举枪打死白军情人的女红军战士马柳特迦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其人性与阶级性的情感纠结。像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忠诚对奸诈的不懈斗争,《水浒传》中除暴安良的英雄血性的展现等,在这些中外文学经典中,无不寄寓着人类的理想,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而脱离了对人性的探索,为迎合市场去津津有味地表现血腥搏杀、怪力乱神、畸形情欲等等这样一些内容,不仅不会引导读者向真向善向美,相反倒会引人堕落。同样,历史题材、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的前提下,既要对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再现历史和战争的真实场面,又要表现敌对双方的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的人性的挣扎。作家应秉持悲悯情怀,穿越两军对垒的屏障,穿越残酷的现实,淋漓尽致地表达人性的善恶交织、情感的复杂纠结。只要我们的作家认真地对19世纪中期的“捻军运动”的这段辉煌历史“作一番全新的考查”,不仅仅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陈述和对简单的善恶是非的二值判断,而是赋予人物深重的悲剧性历史涵量,更多的历史文学的精品力作将会出现,新时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将会得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