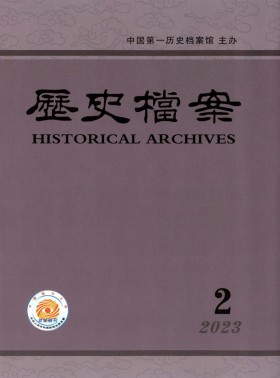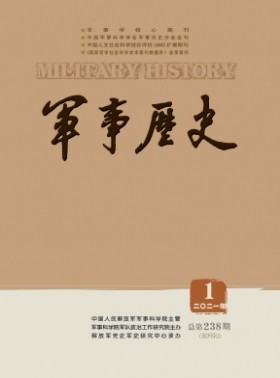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的特质和创作原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历史文学,顾名思义,是历史与文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互相接缘与相互渗透,即运用文学艺术手段形象地表现历史生活,让读者或观众在感受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同时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历史文学与现实题材的文学不同,它取材于一定的历史故实,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的联系,是一种有限度的文学——必须体现一定的历史质感和实感。因此,对于历史文学作品,在强调它的思想性的前提下强调真实性是十分必要的。从历来论者在评论时较为一致的观点看,关于历史文学的真实性标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历史的真实与历史文学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属于历史文学中的杂文、随笔一类样式。在这里,征引史料要精确,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属于历史文学中的小说、戏剧一类样式,要遵守的是历史文学的真实。所谓遵守历史文学的真实,就是在不违反历史的本质真实(即不超越历史的经济、政治、思想诸条件)的前提下根据文学创作的规律进行虚构,塑造出典型性格来。
诚然,历史文学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将历史真实、历史文学真实与艺术虚构科学地结合起来,即在表现历史本来面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但不管怎样虚构,历史文学所写的内容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和历史常识,更不能凭借主观臆测写一些在当时不可能有或张冠李戴的事。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注重艺术而疏忽历史、为了艺术而忘了历史的现象在当今的历史文学中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屡见不鲜。这类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形式也颇为多样。有的是时代环境错乱颠倒;有的是在古人身上赋予了现代人的思想、行为、语言;有的是对历史上有定评的、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进行随心所欲的改写;有的“高明”的作者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回避,结果写成的作品时代难辨,环境不明;也有的是细节描写失真,忽视了对历史面貌的真实描绘。凡此种种,在各种题材、各类作家中均有存在,甚至诸如唐敏那样的成熟的中年女作家和功力高深的已故老作家田汉,也出现过失真的败笔或创作的疵点。其中,关于吸烟的细节描写就是一例。
据有关史料记载,烟草在明朝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才陆续由国外传入我国。其传入的途径大约有三种:一种是由葡萄牙人在明朝万历年间经海路带来,所以它得以首先在中国的福建等沿海地区种植。大约与此同时,烟草也由中国的商人和华侨从吕宋国(今菲律宾)贩运入广东一带,这是第二种途径。对此,明末名医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四十八》中记载道:“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1]那时烟草的传播可能要晚于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不然他不会在这部收录了多种药用植物的巨著里只字不提。明末的著名科学家方以智在所著《物理小识》卷九中,对烟草的来源和在我国传播情况,亦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证。他在该书中也说烟草是明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后又向北传到长城一带。与方以智同时代的姚旅在所著的《露书》中,则把烟草叫作“淡芭菰”。“淡芭菰”即“tobac-co”的音译。该词原系美洲阿瓦克族印第安人用以称呼鼻吸卷烟的,以后为各种欧洲语言所借用。我国关于“烟”这一名称是从日本传来的,黎士宏《仁恕堂笔记》:“烟之名始于日本。”由于人们享用烟草的主要方式是将其点燃后吸其烟雾,故烟草之名迅速代替了“淡芭菰”之类的译名。至于今天最普遍的机制纸卷烟,即所谓香烟,则是在清末光绪年间才从国外传入的(据有的学者研究,首次传入我国的时间是1890年)。第三种途径是北路,即先由日本传入朝鲜,又由朝鲜传入我国的辽东,时间也是在明万历年间。朝鲜称烟草为“南灵草”或“南草”。《李朝仁宗实录》中说,“南灵草”虽号称能治痰消食,但实际上损害健康,“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世称妖草”。明朝末年,烟草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蒙古族等已经比较流行。清人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写道,烟草“关外人相传本出高丽国(朝鲜)”。其实日本、菲律宾的烟草也并非土产,而是由欧洲人的远东海上贸易引进的。
由以上史实,我们可以断言,宋朝根本就不可能有烟草,更遑论那时吸烟几成风气。但在唐敏同志创作的有关李清照的长篇历史小说《红瘦》一书中,却数次写到与烟草有关的事。如“老张蹲在李格非面前,抽着旱烟,闷了半天,说:‘李先生,我听衙门的书记说,大学士苏东坡大人真的犯了事,要杀头啦,牍文都下来了,是这样的吧?”再如“……清益(李清照的妹妹——引者注)从小筐子里拿出一个烟袋来,给父亲看……李格非不禁喝彩道:‘好个绣工,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是清照姐姐绣的。她说要送给父亲您的,是我借来做样子的。我怎么也绣不好,就搁在这儿了”。
请看,当时不仅有了烟草,而且还有“旱烟”。既有“旱烟”,那当然也就有了“水烟”了?因为“旱烟”是相对于“水烟”而言的。另外,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当时想必也会吸烟了?不然李清照何以要花那么多功夫莫名其妙地为父亲绣上这样一个脚踏火球的的烟袋呢?历史小说是一定的历史社会生活的反映,《红瘦》当然也概莫能外。既然如此,那么通过这部小说,你就不仅可以看到在宋朝已有了烟草,而且好像朝野上下已有不少人学会了吸烟,似乎当时吸烟已形成了风气。这能符合历史事实吗?长篇历史小说《红瘦》是如此,而被誉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之一的历史话剧《关汉卿》也有类似问题。历史话剧《关汉卿》是我国著名现代剧作家田汉先生“为纪念大戏剧家关汉卿而作,可称为田汉戏剧压卷之作,也是新中国剧坛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2]。该剧中也有关于吸烟习尚的细节,如:刘大爷:咳,去年大旱,今年水又太多了,回头再淹一下,怎么过日子啊?周老汉:你总算城里还有爿小店,亲家母又能干。刘大爷:她们在城里我总是提心吊胆的怕出事,还不是果然就出事了?周老汉:这年头乡下就不出事了?崔村胡老汉的大姑娘不是照样给秃鲁浑抢去了?刘大爷:可也是。城乡都一样,不知哪一年能过太平日子啊。
周老汉:(卸下锄)真有点累不起了。在这里抽一袋烟再走吧,亲家。刘大爷:(放下犁)好。歇一会儿吧。(他们用燧石击火抽烟。)倘说宋朝没有吸烟的习尚,那么元朝是不是就会有呢?若认为上述史料可靠的话,则元朝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3世纪,离烟草陆续由域外传入国内的明万历年间,要相差三、四百年。然则田汉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也许是田汉先生认为上述史料有误,而他依据的则是其他史料?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恰如田汉先生1958年5月8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所言,创作这一剧本时“为了赶六月下旬纪念关汉卿的任务”,“不能不写得快”。大概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以此来排遣下层人物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闷情怀就这样写上了,属于误笔。不过,这一误笔与整个剧本创作的成功比起来,确实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是枝节问题。但即令是枝节问题,我们认为也不应该忽视。若被忽视了,就会多少也要影响到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p#分页标题#e#
依据某种特质和创作原理,历史文学(包括历史小说、历史剧本等)可以进行大胆地想象和虚构,但不管怎样“大胆”都必须合理。所谓“合理”即“必须是会有的实情”[3],尤其对牵涉到有关时代的典章制度、风俗文物、生活习尚、衣冠服饰等,则不能失真。这也是历史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而写历史剧本则要“失事求似”。这“失事求似”的确道出了历史剧本创作的真谛。试想,若历史上没有这种事物又怎能谈得上“失”,又怎能去“求似”呢?如果让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或不可能发生的事也可以写,那还叫“历史文学”么?如果这样写也可以,那么有位中学生在改写杜甫的《石壕吏》时说,那天夜里,唐朝的官吏最后不仅带走了老妇人,还顺手牵羊把人家的彩电和录音机也抢走了,不是可以照样成立吗?然而,事实上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常理和历史常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
总之,我们认为,历史文学不同于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它除了也要进行一般的艺术创作外,还有个应怎样求得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否则就会令人有胡编乱造、违背或歪曲历史之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茅盾同志认为,“艺术真实”这个用语并不确切,改为“艺术虚构”较易理解,即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这样也突出了艺术虚构在历史题材中的重要性。但是,艺术虚构并不是凭空捏造、主观杜撰的。诚如茅盾同志所说,在进行艺术虚构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即不损害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换言之,假人假事固然应当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产生的人和事,而真人真事也应当是符合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不是强加于他的思想或行动。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够做到这样的虚构,可以说它完成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4]。人民欢迎并热切地需要历史文学的创作者们更多地拿出这样的完美的堪称不朽的作品、越千百年也无法打倒的作品、给予现在和将来以力量和启迪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