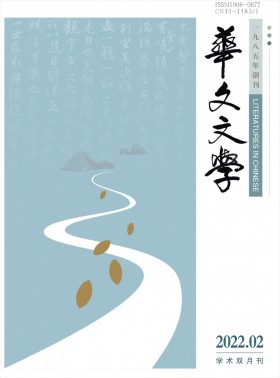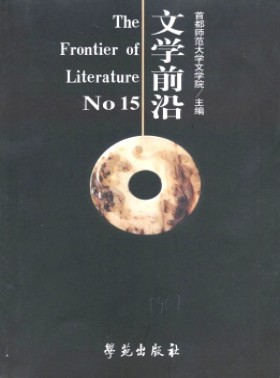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与道德之间的论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文学与道德的概念界定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往往通过具体生动感人的形象,而不是像哲学、社会科学那样用抽象的概念去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不仅是人们学习语言的载体,同时也成为熏陶人们心灵、健全人们精神的手段。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作家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从生活中得到的大量感性材料熔铸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其次,始终离不开想象(幻想、联想)和虚构;第三,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道德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道德具有历史性、阶级性和继承性。道德规范与法律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两者都是行为规范,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第一,作用途径及约束力不同。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而道德是一种心灵的契约,只能靠人们自觉遵守,所以约束力比法律弱很多,靠舆论来实现道德的力量;第二,形成方式不同。道德是在生活中逐步确立的风俗规则,法律则是有国家制定的;第三,代表的利益不同。法律一般是当权者管理的有力工具,而道德是群众在生活中的利益体现,有一定差距,特别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往往分别代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利益,处于对立的地位。 二、文学与道德之间的论争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服务于道德是主流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艺为道德服务的主张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1]———就已经察觉到文学的道德教育作用。荀子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2]当然这里的“声乐”,是指附上音乐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说荀子已经认识到文学以情感人的特点和文学的道德教育作用。但是,古人对文学的文艺性多持轻视态度。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扬雄以文章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国语》、《离骚》、《孙子兵法》、《史记》以及许多诗文名著,据说都是不得志的“贤者”的“发愤之作”。[3]两汉以后出现了一些纯文学的文论。如陆机的《文赋》,“因为他纯粹地从文学观点去讨论文学”。齐梁时有两部重要的批评著作,恰好代表当时文学上两种相反的观点。一部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代表传统的“文必明道”的思想,另外一部是锺嵘的《诗品》代表重纯文学的倾向。到了唐朝,白居易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极力主张文学应起褒贬善恶、补察得失的作用,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读群《学仙》诗,可讽放佚群;诗群《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群《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群《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宋以后,文学完全从属于道德,为道德服务的地位。石介说:“道德,文之本也”。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理学家周敦颐认为“文所以载道也”。他们这里所说的‘道’包括道德,但不单指道德,而是指封建统治阶级提倡那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清末的革新派梁启超等人,认为文学决定着道德的变化,所以断言改革道德必先从改革文学开始。[4]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尚未具备独立性,大部分时期服务于道德,到后来甚至成了道德的附庸。并且可以说,在中国方面,从周秦一直到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输入,文艺都被认为是道德的附庸。这种思想是国民性的表现。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喜欢把文艺和实用分开,也犹如他们不喜欢离开人事实用而去讲求玄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论史上甚至近现代,文艺为道德服务的主张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二)西方文论史:两种观点并存 西方文论对于文学与道德的论争的焦点是文学与道德是否具有一致性。有论者认为,文学与道德存在一致性。他们很重视文学净感情、劝善惩恶的作用,但是和中国古代文论不同的是,一些西方美学家试图弄清文学与道德关系的本质,从思辨哲学的角度探讨美与善的内在联系。”[4]柏拉图主张美与善的统一,尤其强调文学的美善结合,但他认为,引人向善是一件不易的事,须借助于形式灵活的文学作品。“让她们用故事来形成儿童的心灵,比起用手来形成他们的身体,还要费更多的心血。”[5]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在《为诗一辩》中认为“表现美德、恶性或其他内容并能够寓教于乐的虚构形象是诗人的根本标志。”雪莱认为:“诗歌遵循道德行事,因而具有道德效益”。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文艺在意象之后隐寓一种宗教理想或道德教训。作家如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都相信文艺和道德是密切相关的。而认为“为文艺而文艺”典型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与老师柏拉图持有相反的意见,“评诗的标准和政治及其他技艺的标准绝不相同。”政治标准并不能评价文学,文学有其自身的标准与特点。克罗齐认为:“艺术活动不是一种道德活动,直觉即艺术,一个审美的意象显现出一个道德上可褒可贬的行为,但是这个意象本身在道德上是无所谓褒贬的。[6]雨果提出:“为文艺而文艺”的口号,他坚持文学的纯文学性,不能因为道德的介入而消去文学的艺术性。可见看出,西方文论史上关于文学与道德的论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两种观点并存。 三、辩证看待文学与德育的关系 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文学与道德的论争,比如《人民文学》举办的首届论坛上就文学最高目标是道德伦理还是艺术品质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各自观点。有论者认为把文学的最高目标定为道德是狭隘的,文学不等于道德,趣味也不等于尺度。有论者认为,文学伦理同时两种意义,一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作家的道德伦理,也就是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怀,另一种是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文学自身特征,是指合乎文学逻辑的形式与技巧的追求,而这两种存在并不矛盾,都是作家对文学负责的精神。[7]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儒家的“传教”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古罗马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等,都把文学视为对人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一种途径,文学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群体发展的需要。[8]朱光潜认为,文艺对人的影响深广是因为文艺是情感的自由发展区域,情感的势力比理智更强大。他强调在美感经验发生之前,文艺与道德关系是紧密的。并用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作为标准,将作品分为三类:“一有道德目的者;二一般人所认为不道德者;三有道德影响者。”有道德目的者,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训。一般人认为不道德的作品通常指材料或内容中有不道德的事迹。有道德影响是指读者读过一种艺术作品之后在气质或思想方面发生较好的变化。还有学者从文学的内涵和特征来分析文学与道德存在的一致性。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潜在道德内质的精神活动。道德倾向同其他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分一样,是一种决定文学作品优劣成败的因素。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人物的思想内涵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以这种道德情操来感染读者,这是文学优秀品格的显著标志,是文学道德价值的基本轮廓。文学活动中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历史尺度、历史逻辑和道德逻辑、历史价值和道德价值、审美因素和道德因素,本来应当是和谐的、统一的,人为地割裂势必造成创作的畸形。有论者认为,文学有诸多功能,其中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德育功能,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围绕某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呢喃与人性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学者们对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多角度的剖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文学与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文学的德育功能仍是当下的主流思想。#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