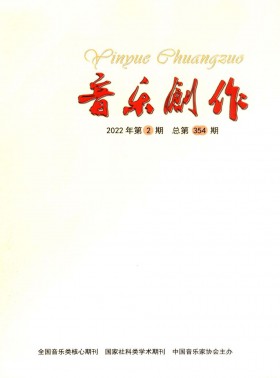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音乐与古诗歌兴衰的联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说:“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这个所谓的“音乐文学”就是“代胜”(即“一代之所胜”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之诗歌,潇涤非先生说:“一种声调(音乐)之改变,恒足以影响诗歌之全部。”即是说音乐的代胜促成了音乐文学(即诗歌)的代胜。鄢化志先生补充道:“既云影响诗歌之全部,则不惟形式,内容之改变自然亦在其中。”虽然诗与乐之孰“本”孰“用”(诗乐本用之争)尚有争议,然诗乐互补,携手并进共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诗乐一家,源远流长。古人言之不足,故嗟叹(诗)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为什么呢?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为何仁声之入人深于人言?《乐记》答曰:“凡音者,生人心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于是,自然有声入人深于言入人。即如巴尔扎克所说:“音乐易打动人心。”恐怕谁都有过被音乐叩响心扉的经验。一曲在耳,或轻灵、或沉郁、或欢欣、或悲怆,但凡有情有心者即能有所感悟,有所体会。而乐感之敏锐、心灵之纤巧者,则更易于旋律中如见高山、如闻流水、如临瀚海碧波、如当大漠风沙。音乐史家罗曼•罗兰说:“音乐如果能假文字则更易打动人心,曲而有词往往比空灵幽独的乐曲更易为人理解,从而深入人心。”而诗歌之动人心处,恰在于其与乐音声相和!《乐府》篇释诗歌说:“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毛诗•郑风•青衿》说:“古者教诗以乐,颂之,歌之,弦之,舞之。”钟嵘《诗品》说:“古之诗颂,皆被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由此得见,诗乐委实是一路携手,相濡以沫。为什么会如此?鄢化志先生说:“就表现功能而言,语言长于描述形象事物及拿捏理性思维,音乐则长于传达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于是,诗乐双剑合壁,自然能响浃肌骨,发人内自省。王灼《碧鸡漫志》说“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殆源出于此。 一、诗、骚、乐府、唐诗与音乐 纵观中国音乐史实不鲜见“涵养其心,乐助诗者为多”(《乐记》)之理,民族音乐从雅乐(先秦时期)、清乐(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燕乐(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俗乐(元明清时期),一路走来,衣被诗辞,首屈之功,诚不可没。无论是雅乐时代的“三代之时,以声依咏,以律和声,乐乃为诗而作”(《文献通考》)的余韵无歇,“诗三五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的“洋洋乎盈于耳”(《论语》)。乃至南方根植于湘沅神秘巫音从而产生丰富想象力的《楚辞》,“第一等好处在他的音乐,第二在他所和的乐,第三在他演唱的姿势,最后才是他的文词”(谢无量《楚辞新论》)。还是清乐时代的“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而有匹夫庶妇,呕吟土风,知识分子诗唱“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汉书•艺文志》),及至“御军三十余年”的魏武帝也“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无不是诗乐相和。而音乐之雅乐而清乐地演进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诗之四言而五言地发展。众所周知,雅乐是比于国风而成,清乐是吴声、西曲在相和歌(相和歌乃汉民歌承国风,楚声而来)之基础上兴起。相较而言,清乐比雅乐更丰繁,自然要求有与之适应的诗体与之齐头并进,钟嵘《诗品•序》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也”。于是,汉乐府以降终于五言腾踊,流行传唱起来。游本《中国文学史》说“至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成为我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而唐代音乐文学唐诗的春秋鼎盛,又恰在燕乐的丰满,成熟。燕乐是中土音乐兼收并蓄北朝、隋以来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印度、朝鲜等外国音乐,合发展而来的汉魏晋之清商乐,熔一炉而成。王凤山先生说:“音乐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诗歌为音乐注入鲜活的灵魂,使诗与乐共同发展。”唐诗的空前正印证了斯言。唐诗合乐而歌绝非虚言,《全唐诗附录》中说:“唐人乐府用律绝等,杂和声歌之。”王骥德《曲律•三十九》云:“唐人绝句,唐之曲也。”王世懋《艺圃撷余•论诗》说:“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汪师涵《诗学纂闻》中说:“七言律诗,即乐府也。”王圻《诗文献通考论歌曲》云:“凡七言近体皆可歌。”[1]这不过是文献史料,说理略显干瘪苍白,从唐人诗歌中管窥一斑则生动得多。刘禹锡《竹枝词》的“人来人去唱歌行(歌行体诗)”;白居易《杨柳词》的“《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若缘辞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歌行体诗)”等等,不胜枚举。[2]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王维之《渭城曲》(即:《送元二使安西》),以其清丽真挚的芳萋动人被作为送别之曲广为传唱,又经乐工手成《阳关曲》(而或称《阳关三叠》)余韵至而今。其实,诗乐合而双馨在唐诗家的逸事中也可窥见二三: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旗亭画壁”的风雅已令人叹为观止;而王摩诘抚琵琶,唱自己的诗作打动权贵而高中头名更是令人心慕不已;最是让人拍案称奇“我是胡家儿,不解汉儿歌”的偏北之地竟然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李忱)之壮景。 妙哉,妙哉!乐为诗传添双翼。其实,唐诗家还要么也通音律,与李龟年,刘采春等乐家过从甚密;要么本身就是大音乐家,如常建善弹筝、王维善琵琶(曾官大乐丞)、李白游历挟古筝行,等等,而白居易更是“本性好丝竹,趁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的音乐鉴赏评论家,他的诗中乐音响不断(如《琵琶行》)。而诗家为了自己的诗文广传四海,不惜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音乐史•概述》就提到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的广度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唐诗家精益求精地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使诗人与乐、诗歌与乐的鱼水情深不仅体现在唐诗本身极具音乐性,节奏感,从而平仄错落,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而且,在音乐的羽翼下,诗举足千里,韵游天外,真正做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了。#p#分页标题#e# 二、宋词、元曲与音乐 燕乐之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二十八调,音律变化繁多,而各调还独具各调的特殊形象和情感(如黄钟宫宜富贵缠绵,正宫宜惆怯雄壮,大石调宜风流蕴藉,小石调宜旖旎妩媚等等),又弦乐音域广阔,演奏速度自由,故“极尽哀乐之情”。而五言七言的固定诗体与其配合演唱自然不易,于是长短句(即:词)便应运而生(或者说应乐而生)了。《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间,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这个“胡夷里巷之曲”中“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少年学子的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序录》),而“访云寻雨,醉眼芳草”的怡悦和征夫思妇,离愁别恨的伤感比重最甚。正是燕乐的新鲜活泼,曲调繁多,与词本身的市民阶层之娱乐性质结合,很快风靡与市井了。 词大盛于宋,恰在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窥一般)。但,也正源于此,词在“宋初承晚唐余绪,词风艳冶欹靡,词体沦为歌楼酒筵娱宾谴兴的工具”,“连倡导诗新运动的欧阳修也未能超乎其外”[3]。然而,燕乐小石调宜旖旎妩媚,正宫宜惆怯雄壮等,就要求词这种“音乐文学”必须与音乐的代胜适应之。于是,柳永,苏轼应乐“生二变”[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词至晚唐五代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柳永一变,主要运用俚语,反应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使词从贵族官僚的华筵走向城市的旅邸歌馆,艳情旅愁色彩浓郁。苏轼一变,于婉约之外另树一帜,把词体从歌馆酒筵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一扫脂粉之气,任情抒写旅况、友谊、爱情、政治、农村等等,终于为词这一音乐文学表现社会铺开了通衢。[5] 词与乐之关系更加密切,词之大家者无论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柳永,还是“笔底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东坡,虽才高八斗却命途多舛,恰是这般,这些优秀的文人知识分子与真实的生活,现实的人民距离近了心贴近了,以鲜活的感情挥洒笔墨,词唱自然“入人深也”。于是便有了婉约派的风靡市井,少年学词“十又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碧鸡漫志》),妓女“不愿君王叫,愿得柳七叫”,盛况空前至于西夏归朝官叶梦得作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描述。而豪放宗东坡也毫不逊色,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载:“东坡守涂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市井,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逻卒)对曰:某稍识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曲,记而传之。”妙哉,词方成即传唱于市井!更叹一逻卒也深通音律,宋词之兴,可知也!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胡寅《酒边词序》里说:“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于是,宋词在婉约宗柳三变,豪放宗苏东坡两面大旗之下,继起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张元干等等各显神通,把宋词唱响到了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风行天下。 而此时以工整五言七言为代表的律绝,虽以“筋骨肌理”(钱钟书《谈艺录》)著世,却也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宋代文人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重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源泉,构不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激动读者。”(游本《中国文学史》)宋初以御用文人杨亿为首的西昆体及继之而起数十年的西昆派承晚唐五代浮靡文风,“或咏前代帝王,宫廷故事,如《汉武》、《宣曲》;或咏男女爱情,如《代意》、《无题》”(同上)。由于缺乏真实感受,所以内容单薄,感情空虚,“写来写去,无非几个陈腐典故”。然由其辞藻华丽,声律偕和,更由于统治者的偏爱,竟达到“杨刘采风,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局面。于是欧阳修遂以韩柳古文运动自承,反对西昆体。 而继西昆坍塌而后起的“险怪奇涩”诗“说理成分多,缺乏生动形象,不免乏味”[6]。王安石更是要求诗“以适用为本”,政治实用色彩极为浓郁。江西诗派虽引领一时风骚(“宋代影响最大”),但新旧党争使黄庭坚一系愈来愈脱离现实,而用故则“务求争新创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却又走上新的形式主义”[7],即黄庭坚自己所谓“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谈》),却致使诗文生硬槎桠。诗至南宋有杨、范、陆、尤“中兴四诗人”,法自然、重现实,不乏佳句,却是昙花一现,转瞬遗踪不再。而教人学诗要“妙悟”的严羽,恰在“悟”上让人“迷离恍惚”[8],终惟恍惟惚。宋诗之败,败在脱离群众、生活,空欲以理取胜,教条之物终难以动人。于是乎也就难以谱之成曲,即使强为之,也是曲高和寡,自然难以传唱开来。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途羹,故远不如唐人。”于是,宋诗难免百年孤独了。 宋词的婉约、豪放随风入化,衣被一代!然而,随着词的纵深发展,继之者却自缚手脚,大晟府词人便是如此。他们的代表周邦彦脱离现实,单纯为配合音律而大讲平仄,严守四声,这就与郑樵《通志•乐略第一》所谓“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之旨相去甚远,不免下矣。而南宋词家步周邦彦后尘,又师法姜夔,把词按周,姜遗法“一字一句地来死填死和”,用字词讲究到“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乎缠绵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失柔婉之意”[9]。于是,在片面追求文词的工丽和音乐的谐美之上,词又走上了不归路。#p#分页标题#e# 而此时民间的长短句歌词,却秉承着燕乐的余韵和新兴于民间的俗乐,又“吸收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当时流传于北方的散曲(也称北曲)。”散曲与音乐关系更加紧密,由其口语化,也就更易于传唱。曲大盛于元,而元曲之特色一言以蔽之:俗。作何解释?曲分小令、套数及介乎其间的带过曲,小令本是民间小曲、词调,自然不能免俗;套数虽延自诸宫调,但无论小令还是套数“皆传于市井”,被称为“街头小令”或“叶儿”,此其一俗也。元朝读书人地位骤降,元史开科取士不过区区三十六年之光景,八倡九儒十丐之卑位痛彻骨髓,因而也就有了“断肠人在天涯”道无尽的悲怆和迷惘。反过来,对诗歌或者说对“代胜”的音乐文学来说,这倒不见得坏。“士人难跻身朝列,便致力民间词曲、杂剧,一方面抒发胸中愤懑,一方面远灾避祸。”于是,身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不得不收拾起自命清高,与贩夫走卒为伍、与耕汉樵夫同道,喜其所喜,怒其所怒,刺其所疾,感其所遇。于是“喜笑怒骂皆文章”,而这些个浅显易懂的下里巴人很快就作为“民声”(或说“人风”)传唱到了市井之中,乡野之间,牛马走之口。“他们悠悠长长、拖拖昂昂地拉一嗓子”,在读书人鞭辟入里却又通俗易懂的文字里,在或喜或悲的唱腔中释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此其二俗也。文人的地位低了,却与生活与群众贴近了,于是笔调自然新鲜了。作品中当然就“有了市井市民气,青楼脂粉气,农田泥土芳草气;有了怨气,怒气;有了阳气,胆气!”(苟德培《诗殇》)也就自然为受剥削受压迫的黎民百姓喜闻乐见。而这一切,早已具有了通俗流行音乐的性质,反应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况。 三、明清的“代胜”诗与乐未能合 王肯堂先生说:“唐之歌(诗)失而有小词,则宋之小词,宋之真诗也;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之曲,元之真诗也;宋元之诗,吾不谓其诗,非不唐也,为其不歌也。”此言不虚。而明清之真诗呢?明清是俗乐大盛的时代。却未闻宏声,未见宏人。 俗乐的代胜音乐文学是什么呢?王肯堂先生说:“我朝之真诗,我朝之山歌(或者说民歌)也。”委实如此,山歌正是诗与俗乐合的“当时之体”,其怨刺有若诗经,有若乐府。然而,山歌作为黎民百姓之歌却由于没有或少有文人的介入,终未能成大器,而不免堕于下流矣。为何有如此这般凄凉呢?与元朝不同,明朝文人知识分子之地位此时已迅速回升了,读书人学优则仕,官民自然有别,而表达民声的山歌如“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却是官人老爷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因为皇帝们防民之口。其实,做惯了艰涩板滞的八股文的他们,即便有心也无力矣。纵观明清两朝,无论是明台阁体的“陈陈相因,极极平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还是前七子盲目复古,“一味以剽窃模拟为能,成为毫无灵性的古董”;再还是后七子“诗至天宝以下,俱无足观”的鼠目寸光,“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募帖’”;又还是公安派“心灵无涯,搜之欲出”的“找错创作源头”;以及竟陵派“独抒灵性,却乞灵于古人”,俱无代胜可言。而放眼清史,初有隐于山野,“不食周粟”的顾、黄、王三家诗,虽从律、绝上讲为正途,却终因不符“诗合乐代胜”发展之轨迹,而未能光大。而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派更是“从顾炎武到王士祯,得见清诗由现实主义向形式主义转变”[10],诗虽然有意有境,终不能流传于万口。正如任二北先生《唐声诗.总论》言:“作诗苟不为声,义虽止而不能远。”清诗恰脱离“诗合乐传万口”之轨道,即便有意有境也不能广为流传了。 朱谦之先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学,即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学。所以,音乐史与文学史是同一并进的,如果一个时代的音乐进步了,便文学也跟着进化,另发展为一种新文学,而前代的旧文学就不能普遍,只好供好古家赏玩,成为贵族文学。”而这时的律绝诗歌盛于士大夫间,俨然已是贵族文学,不再能万口流传。于是也就有了赵翼《论诗》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殇》评论说:“此间纵横着幽怨与无奈!”何解?律绝诗歌走到明清已然没落!怎能万口传?宋湘更是哀怨道“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他们不知道,这时候音乐早就与律绝诗歌越走越远,音乐正把戏曲里的腔调曲文送向寻常百姓家!他们只道是自己“工夫半未全”,只道是自己“诗尚不曾工”,却不知道诗歌随着音乐有代胜,不知道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是缺一不可的。 游国恩先生说,真正的诗歌是劳动人民(以民歌形式)创造出来的,而后文人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学习之,发展之,从而形成一代之所胜。“汉乐府,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说明了这一规律,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地转变,也说明了这一规律。”然而,诗歌走到明清,音乐的代胜———俗乐出现了,诗的代胜———山歌(民歌)也出现了,却由于没有或少有文人地参与,代胜的诗与乐最终没能充分地走到一起。于是,诗歌走到明清竟成为绝响。而这与“八股文”所束缚,“文字狱”的禁锢恐怕也不无干系。也由此有了“万马齐喑究可哀”时埋首故纸的乾嘉学派和朴学。而戏剧却在落魄文人和各地方俗乐结合下,“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昆曲盛行时流行语:“收拾起”出自李玉《千钟禄》中的唱词“收拾起大好山河一担装”;“不提防”出自洪?《长生殿》中的唱词“不提防余年值乱离”),于是,万口传。#p#分页标题#e# 结语: 万物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古诗歌正是由于与音乐珠联璧合,才有了古诗漫漫千年的一路清歌。也正是由于明清的诗歌与音乐的分道扬镳,或者说明清文人与代胜音乐文学的异径殊途,也才有了古诗歌一路下坡的颓势难收。“清韵悠扬飘千载”的诗歌正由于明清文人士大夫僵硬固步地邯郸学步,“学韩学杜学髯苏”(宋湘《说诗八首》)的亦步亦趋,却与本该参与进去而未能的代胜音乐文学山歌(民歌)越走越远,不仅使自己乏善可陈,且也使山歌(民歌)沉下潦,殊堪悲也。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自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鄢化志先生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则不仅不顾音乐,连语言的内在音乐—体制格律韵脚也未成型。”自然很难说是音乐文学。新诗要想长足发展,就需要自身有所突破:与音乐结合向音乐文学方向迈进。 时至而今的代胜音乐文学当为何物?盛行的流行音乐歌是不是就是而今的代胜音乐文学呢?我们的现代诗人词人是不是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呢?其实有目共睹,无论是从流传形式、传唱方式,还是流传广度、影响深度,而或是歌词内涵,肌理蕴藉等各方面讲,流行音乐都当之无愧为今天的音乐文学。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下流行音乐文学(歌词)中虽不乏上乘之作,却也充斥着太多的庸俗(而非通俗)。历览前代音乐文学,无论是诗骚包罗祭祀、农桑、燕飧、怨刺、战争、徭役、爱情、婚姻等之万象;还是诗词曲牢笼旅况、宦游、友谊、爱情、政治、浮沉、颠沛、怀古、咏史、说理、谈玄、感时伤事乃至农忙、洗浣、乡村田园、山水花鸟等之百态。都显见“一代之所胜”的音乐文学兼收并蓄社会生活各层次、各方面之态势。而音乐文学发展至而今,似乎对爱情一系“情”有独钟,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洗耳以听、拭目以对:当今之音乐文学是否真正意义在广泛反映社会生活?是否真正符合音乐文学之发展轨迹?应该说,这恰便是我们现代诗人词人应该改进的当务之急。我们再也不能沉湎在前代之所胜中玩弄古董、孤芳自赏,从而重蹈明清文人覆辙了!参与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让我们今天的代胜音乐文学———我们的诗歌随着音乐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