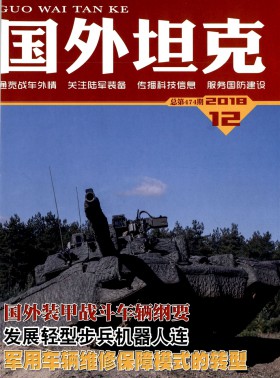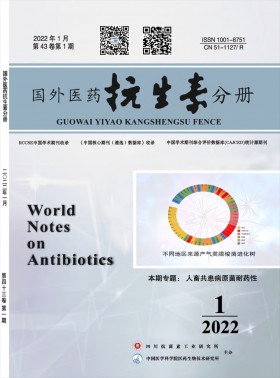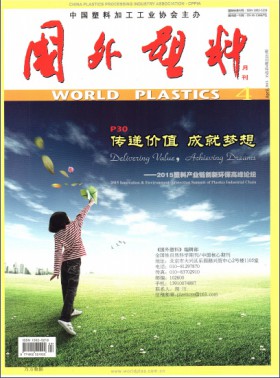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国外农业生态学启发,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骆世明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热带亚热带生态研究所 农业部华南热带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
对农业生态学使命的认识
农业生态学的兴起显然是受到农业发展遇到不可持续问题推动的。“国际农业发展知识、科学与技术评估组织”总结了2008年4月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南非会议成果,发表了《农业处于十字路口》[4]。报告清晰表明各国都认识到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源支撑不了未来社会对农业产出的要求。报告认为包括产品供应、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服务在内的农业多功能性是不可回避的,其中第7条结论指出:“通过进一步将农业知识与科技转到以农业生态科学为主,将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同时维持和提高生产率。”在国外“Agroecology”使用的范围不仅包括“农业生态”,也用到我国常用的“生态农业”表述方面。联合国食品权特别报告员DeSchutter[5]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纵览过去5年来发表的科学文献,特别报告员认定,生态农业(agroecology)作为农业发展的模式不仅展现出在概念上与食物权有很强的关联,而且证实生态农业可以在国情不同的各个国家中为众多弱势群体具体实现食品权这项人权取得明显的进步。此外,生态农业展现出的种种优势,与人们熟悉的常规方式,诸如培育各类高产改良品种的做法成为互相补充的一种农业方法。
生态农业能够有力地推动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他建议通过扩大生态农业的实践,以便能够在增加农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计的同时避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美国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举办的第13届国际农业生态培训班上,人们引用爱恩斯坦的名言:“我们不能够用产生问题的思路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们认为引导工业化农业发展的传统农业科研思维属于还原论(reductionism)。这种还原论方法已经不能够胜任未来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生态学要促进农业一系列观念变革,从而克服一系列传统工业化农业引起的严峻问题(表1)。美国农业部在2009年终于跟随众多欧洲国家在人力、物力和机构设置上大力支持有机农业发展。在这个基础上,Hooedes等[6]撰写的美国农业“国家有机行动计划”中,认为有机农业也应当采取农业生态学的综合、整体、多样的思路,甚至认为应当在传统农业研究机构以外成立独立的有机农业研究机构,以摆脱传统农业研究的还原论思维。显然国际上农业生态学被认为是一种对工业化农业方式和传统农业科研思维的深层次颠覆和革命,并赋予了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使命。
对农业生态学内涵的认识
丹麦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生态系的Dalgaard等[7]在综述农业生态学的时候根据不同研究人员的研究范围,提出了农业生态学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他们认为与农业生态系统的能物流、资金流有关的生态、农学与经济学结合的部分可以称为“硬农业生态学”(hardagroecology)部分,而与人类社会及其利益管理体系有关的则可以称为“软农业生态学”(softagroecology)。他们的文献搜索结果表明,使用了“agroecology”或者“agro-ecology”关键词的文献中66%属于自然科学,13%属于社会科学,5%属于经济学文献,16%属于自然与经济结合学科,2%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同时跨自然、社会、经济三大学科范畴的文献。法国农业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家Wezel等[8]在综述农业生态学文献时发现,农业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是趋向扩大。扩大方向之一是从农田层面向农业生态系统和地理景观层面拓展。扩大方向之二是从农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硬农业生态学”向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农村可持续发展、社会学与经济学等“软农业生态学”发展。美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Gliessman[910]索性把农业生态学描述为研究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体系的生态学。Wezel等[8]认为,目前“农业生态学”实际上指的既是一个学科,还是一类实践,甚至是一种运动。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种农业实践方式的认识
在中国农业生态学指导的实践被普遍称为生态农业,然而在国际上生态农业的术语应用并不广。利用“ecoagriculture”或“eco-agriculture”为题目或者关键词的文献到2010年仅有46篇,其中有34篇文献的作者还是中国学者。在中国1990—2010年“生态农业”为关键词或题目的文献却达到7986篇。在国际上大量使用“agroecology”来描述利用农业生态学指导的实践,实质等同于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践。联合国食品权特别报告员OlivierDeSchutter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也如此,以至在翻译中需要把“agroecology”翻译成“生态农业”才符合中国人的表述习惯。Altieri[11]认为应当重视循环体系建设和维护土壤有机组分,充分利用物种多样性与遗传多样性以便提高太阳能、水分和养分等自然资源利用率,还应当注意通过扩大物种间有利的相互关系,强化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DeSchutter[5]提出生态农业需要模拟和利用自然进程,通过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生物多样性构成、养分循环和能源流动关系构建来实现系统的多功能协调。报告中列举生态农业的实践模式有农林结合模式、农牧结合模式、流域集水模式、综合养分管理模式和综合有害生物防治模式(玉米地防治玉米螟的推拉体系、稻田养鸭体系)等。在美国加州覆盖作物和有害生物的陷阱作物也经常用到。
由于生态农业是智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而不是投入集约型生产方式[11],除了重视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外,国际上普遍重视来自广大农民的实践经验和经历长期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传统农业遗产。2004年以美国学者SaraScherr牵头在内罗毕成立了国际“生态农业伙伴”(ecoagriculturepartner)[12]。其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过景观层面的布局,协调生态、生产与生活关系。该组织的口号是“为了人民、食物和自然的景观”。在其内罗毕宣言中,除了强调景观分区布局和管理外,还强调结合乔灌草的农林体系(agroforestry)和实施有机与循环方法。Gliessman[10]认为,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实践转变可以分为4个水平。第1个水平为资源节约技术,推广节肥、节水、节能技术等。第2个水平是投入替代技术,化肥用有机肥替代,农药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替代。第3个水平是系统结构变化,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结构、循环体系结构和流域景观元素配置结构的变化都属于这个水平。第4个水平是食品供应体系的改革,食品供应体系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者、食品加工、产品运输、商品销售、食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调整。美国“国家有机行动计划”中也提出要避免把有机农业简单理解为允许和不允许投入什么的农业,有机农业是与农业所存在生态系统结为统一体的农业系统[6]。#p#分页标题#e#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个运动的趋势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生态农业建设逐步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目的在于发掘农民智慧、改善食品供应体系、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增加农民经济收益、保护珍贵农业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拉丁美洲的“农民对农民运动”(英文:farmertofarmermove-ment,西班牙文:movimientocampesinoacampesino,简称MCAC)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该组织成立已经36年了,目前遍布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如古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西等,参加运动的农户达到数十万。在20世纪60—70年代,依托良种,并依赖化肥、农药、灌溉等高投入为基础的“绿色革命”在拉美国家小农中推广失败。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接受缩减政府、出售国有企业、开放市场等措施,农产品市场被发达国家占领,土地被大公司占领,农业推广服务萎缩,农民被迫成为城市居民或者退守边缘区域。同期,在国际上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SARD)项目推动下,拉美国家的小农发现,生态农业方法不仅使其产量倍增,而且保护了环境。于是他们就在这些项目组织交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农民之间进行技术和经验交流的组织。目前该组织正试图凝聚力量,在交流生态农业技术的同时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管理体系和国家政策[1314]。
在武装叛乱麻烦不断的尼加拉瓜,全国农民与牧民联盟在1987年开始实施“农民对农民项目”(campesinotocampesinoprogram)并且取得成功,农村也得到了安宁。成功的原因总结为:农民自己的试验和评价,本土知识的交流,活跃的对话和创新,水平对话机制出现的乘法效应,有推介成果的积极分子出现,创新成为农民的风气,不断有地方领袖出现[15]。在古巴1999年正式成立农民对农民农业生态运动,农业生态运动成功解决了在禁运条件下通过利用当地资源与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保障供给中显示出了明显优势,2009年就有超过11万户农民参加[16]。在巴西,2001年召开全国农业生态学会议,2002年成立全国农业生态联盟,2003年在有机农业的法律框架内认可了农业生态,2004年成立巴西农业生态协会,2006年巴西农业研究组织正式把农业生态作为该研究机构的一个学科领域[8]。在生态农业推广过程中,各国特别注意避免过去农业推广那种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方式,重视农民的平等参与及横向交流。农业生态在美国也已经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形式存在。在美国加州,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有机农场为农民提供有机农业培训,校内建立了社区农业生态项目(programincommunityandagroecology)。加州还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与农业生态有关的民间组织。例如“社区农业生态网络”(CommunityAgroecol-ogyNetwork,CAN)、“农业和基于土地的培训联盟”(AgricultureandLandBasedTrainingAssiociation,ALBA)、“社区支撑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根本的改变”(RootofChange)、“食物共有”(FoodCommon)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从不同的侧面推动农业生态的发展。RootofChange致力于把被现代商业运作分割了的食品供应体系重新连接起来。FoodCommon计划建立有机食品供应体系,力争在2020年实现10%的本地消费食品为本地生产。
ALBA着力培训和培育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小型农民企业。他们不但提供技术培训,而且为起步农民提供廉租农田。CAN则通过与拉丁美洲咖啡生产者建立直接联系,增加生产者收益,减少消费者负担,建立起消费者对生产者和生产方式的了解。另外FarmerMarket为农民生产的有机食品提供了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渠道。“美国收获正义”(JustHarvestUSA)组织则为外国农民工提供保护,争取正当权益。美国有机农业运动也是从民间开始的。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成立了“加州有机认证农民”(Ca-liforniaCertifiedOrganicFarmers,CCOF)、“有机农民和园艺者联盟”(MaineOrganicFarmersandGar-denersAssociation)、“东北有机农业联盟”(NortheastOrganicFarmingAssociation,NOFA)等。民间的大量工作促使美国农业部在2000年制定了国家有机食品标准,并在农业部设立国家有机农业项目,2009年专门设立管理职位[6]。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认识
法国Wezel等[8]的分析表明,德国基本还是把农业生态学放在一个生态学分支学科的范畴看待。例如德国哥廷根大学作物科学学院农业生态系定义:“农业生态学集中研究在农业景观区和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群落、食物网关系和保护生物学”。德国马丁等[17]在2006年写的“农业生态学”中定义农业生态学为:“研究人类为某些作物的生态所塑造的环境中生物生存条件的科学”。这不同于美国以Gliessman[10]为代表的包括社会经济体系在内的定义,即“农业生态学是研究食物系统的生态学”。Dalgaard等[7]则利用社会学家RobertKingMerton(1973)提出,后来为JohnZiman(2000)再次论述的评判科学的4条规范来评判农业生态学。第1条评判标准是关于内容的社群性(communalism)方面,要求科学的内容能够向社会大众扩散。第2条规范是研究人员的包容性(universalism),即科学研究人员应当不分种族、肤色、信仰、性别等,有广泛的包容性。第3条规范是利益中立和谦逊(disin-terestedness,humility),研究结果能够超脱个人利益和研究人员个性是重要的。第4条规范是严格论证下的原创性(originality),要求研究结论能够经受得起怀疑和验证。文章作者认为第1和第2条规范对于农业生态学不成问题。第3条规范对于农业生态学一般也不会存在问题。但是,农业生态学研究涉及社会层面时,就不容易遵循利益超脱的规范。用第4条规范来衡量农业生态学的时候,文章作者认为一方面农业生态学有些研究仅仅进行半定量的调研和访谈,结论的重复性和严密性容易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农业生态学一些小规模的田间研究要上推(scalingup)到系统和景观层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太简单,容易出错。
对农业生态学在中国发展的启迪
根据各国对于农业生态学的理解和发展状况,反观我国的农业生态学发展,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学发展的优势和问题所在,以推动学科健康发展。“农业生态学”在我国指的就是一个学科,其指导的实践和社会运动在我国称为“生态农业”[18]。这样就避免了国外认为农业生态学既是学科,又是实践与运动的问题。在我国农业生态学理论框架中,农区生物与环境通过能物流整合起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是基本研究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硬农业生态学”部分。根据控制论原理,调节和控制这个体系的机制包括分散在自然体系中的非中心调控机制和受人类左右的中心式调控机制。中心式调控机制又可以分为经营者和操作者的直接调控,以及影响经营者和操作者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法规等间接调控。这部分调节控制机制就是所谓“软农业生态学”部分,其中包括了价值流和信息流。尽管我国在农业生态学体系的构建上比较完整和稳定,但是在与农业生态系统调控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法规的实际研究还是落后于需要,也落后于不少国外同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同行在认识农业生态学对还原论思维方式下的农业方式与农业研究的颠覆性意义方面(表1),还没有国外同行理解得那么深刻和紧迫。#p#分页标题#e#
在我国生态农业实践常被分为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实际上对应于Gliessman[10]所指的第1水平变革(资源节约型技术)和第2水平变革(投入替代技术)。生态农业模式则对应于他提出的第3水平变革(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我们在认识上还有3个优势。一是认识到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与生态农业模式相互联系,一定的模式对应一定的技术体系。二是认识到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是由多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技术组成的。三是在我国生态农业模式方面,农区景观生态规划、农业生态系统循环设计、农业生物多样性关系构建被认为是生态农业模式建设中最重要的3个方面[20]。这个归纳能够包容迄今为止国际上农业生态实践中有关的主要模式。不言而喻的是,世界各国丰富的农业生态实践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对于Gliessman食物系统变革的第4水平(从农田到餐桌的社会体系)而言,我们在农产品加工链方面偶尔涉及,也在生态农业政策方面加以研究,但是很少在生态农业研究中涉及生产组织、运输组织、供应链组织、市场组织层面。这种状况与国情应当有关。由于我国市场化处于起步和完善阶段,供应链的垄断问题和生产者与消费者被分割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然而,农业生态结构涉及的社会经济组织方面仍然值得今后加以重视。
我国生态农业实践在一开始就是通过有远见的专家提倡,并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就是“九五”和“十五”期间农业部等8个部委支持的全国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活动。由于有经费支持,有专家指导,发展快,势头猛,颇有些轰轰烈烈的味道。然而其持久性和传播效率却不如起源于基层的拉丁“农民对农民运动”。当国家部门的兴奋点一旦转移,全国性有组织的生态农业活动就陷于停滞。相比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在农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众多参与者的创新势头和农民横向知识传播的乘法效应等方面都望尘莫及。我国在省、市、县、镇、乡各级组织的生态农业建设一直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这反映了我国对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发育初期,有关农民自发组织开展生态农业的社会环境还有待成熟。然而,我国已经有支持农民技术协会和农业行业组织发展的政策,这为自下而上有组织的农民生态农业行动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环境。值得我们今后加以重视。在我国生态农业实践中非常重视农民经验和农业传统知识。中国农业大学李隆教授[21]有关间套作研究、浙江大学陈欣教授[22]的稻鱼共作研究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与闵庆文研究员领导的团队持续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23]。李文华院士[24]主编出版的《生态农业》中总结了大量农民创造的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目前仍有约6亿人口在农村。目前对农业遗产的挖掘和对农民经验的提升还远远不够。今后,不仅需要科研人员的继续努力,更需要广大推广人员和农民懂得这些经验和遗产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加以发掘、研究、保护和推广。
目前我国农业生态学研究多在农田和农田以下水平开展。在农田生态系统水平的水分平衡、养分平衡、能量平衡的研究已经从短期田间取样研究向长期定位试验站支撑的研究发展。作物间套作的养分、光照、水分、病虫关系,作物害虫天敌的化学相互作用,作物土壤微生物的复杂影响,农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等研究方向都相当深入,并且常常触及前沿[25]。然而在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景观层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与农业生态学相关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就更加少了。正如Dalgaard等[7]所指出的那样,在层次比较高的体系中开展研究有两个难点,一方面大系统受限于时间和资金,不少研究仅能够进行半定量的调研、访谈、取样,得到有关结论的重复性和严密性容易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小规模的田间和实验室研究要上推(scalingup)到系统和景观层面的方法还不十分成熟。因此利用模拟、模型和数学方法进行综合和上推成为必要。这需要在我国今后的农业生态学研究中加以强化。农业生态学的社会经济研究比较弱与我国农业生态学起源于农业高校的农学学科有关。只有通过现有农业生态学家进修有关社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或者通过与社会经济学家合作才能够克服农业生态学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