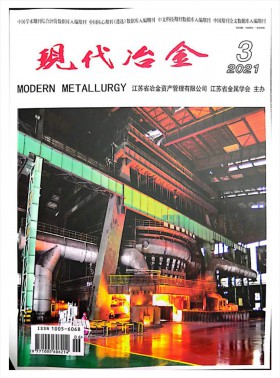诗性形态的显隐: 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中的“文体互渗”批评话语
第一,中国现代“日记体小说”的批评话语。在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体互渗”批评话语中,“日记”文体较早地受到批评者关注且引起重视。1902 年,时人在《< 鲁滨逊漂流记 > 译者识语》中评价原著说: “原书全为鲁滨逊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 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13]他强调现代“日记”文体中的“自叙”特征,读之有味,味即在于“日记”文体的言情性,且对日记文体化入小说颇为赞许。到了 1932 年,孙俍工在《小说做法讲义》中将小说体式分为四类,日记式位列其首,并对日记式小说定义为“是一种主观的抒情的小说。是一种以自叙作为表现的样式的小说,借主人公自己底笔意语气,叙述自己底阅历、思想、感情以及周围之物象等”[14]。可见“自叙的抒情”对日记体小说的关键性,而“感情”便是“诗性”的重要一极。然而,日记体小说的“抒情”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后两个十年迅速弱化,日记体形式本身也开始受到冷遇,失去了五四时期的热闹景象。20 世纪 30 年代,王任叔在对现代小说体式进行考察分析后指出: “第一人称的写法绝对减少。”[15]可见“自叙”文体已在凸显群体意识的革命时代面前显出自身的弱势。穆木天说的明确: “在现在的中国,写工农兵用自白与日记是不可以的。”[16]他举例丁玲小说《杨妈的日记》为证,认为“杨妈的生活是可以客观地描写的,可是叫杨妈写出那一段漂亮日记来,则是滑稽的了。”[17]这都进一步说明了以“抒情”见长的日记文体很难与 30 年代日益成为小说中主角的工人、农民形象达成统一。
第二,中国现代“童话体小说”的批评话语。“童话”也是现代文学发生期备受关注的一种文体。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的《童子世界》( 创刊于1903 年) 是刊发时人儿童观及儿童文学作品的刊物。由于对于童话的内涵外延及其幻想本质不甚确定,所以这一时期的现代学人似乎更热衷于探讨童话的文体特征。周作人认为: “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计自三岁至十岁止,其时,最富空想,童话内容正与相合,用以长养其想象,使即于繁富,感受之力亦渐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18]指出了童话的“情感”和“想象”特征。之后,郭沫若于 1922 年 1 月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童话、童谣、剧曲) ,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于 1922 年 7 月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指出: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冯国华于 1923 年 11 月在《儿歌底研究》中指出: “我以为儿童文学,就是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之堂奥; 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富有兴趣,一方面投儿童的心理所好,一方面儿童能够自己欣赏的,就是儿童文学。”这些认识与周作人的童话观异曲同工,皆强调童话文体“想象与情感”的“诗性”特征。实际上,从发生学角度来看,童话起源于人类的童年时代,“童话之源盖出于世说,惟世说载事,信如固有,时地人物,咸具定名,童话则漠然无所指尺,此其大别也生命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渐启,鉴于自然之神化,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征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18]童话的形式特征是由文学的母体———“神话的文体特征逐渐演变而来的”[19]。这与维科的“诗性智慧”观点甚为相和,即童话是人类童年时期“诗性逻辑”的呈现形式。于是,童话的文体特征融入现代小说,就自然使得现代小说获得了新鲜的“诗情”养料。到了 1918 年,儿童文学运动蓬勃开展,胡适在《晨报》上发表《儿童文学的价值》一文指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儿童文学运动为现代小说创作开辟了别样路径,童话体小说创作也产生了第一块丰碑———叶圣陶的童话小说。
第三,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批评话语。“诗歌”与现代小说的“文体互渗”最为普遍,因此,诗歌文体特征及其互渗现象也是批评家们论及最多的话题。早在 1904 年,平子在《新小说》中发表文章说: “盖小说( 传奇等皆在内) 与歌曲相辅而行者也。而歌曲者乃人情之自然流露,以表其思慕痛楚、悲欢爱憎,然闻悲歌则哀,闻欢歌则喜,是又最能更改人之性情,移易世之风俗。上古之小说、歌曲无论矣。然自周以来,其与小说、歌曲最相近者,则莫如三百诗。然则以《诗》为小说之祖可也。”[20]85平子认为从上古以来,歌曲、诗歌与小说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歌曲、诗歌的“性情”元素同样存在于小说之中,发生着同样的“易世”功能,他强调的是歌曲、诗歌和小说的抒情特征。时人说: “则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其言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形象而起。”“美的概念之要素,其三为形象性。”“美之第四特性,为理想化。理想化者,由感觉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之谓也。”[20]256这些都阐明了现代小说的价值在于其审美性,而审美性则来自于“具象”而非“抽象”,“具象”连缀着感情,是抒情而非叙事和议论。叶圣陶提出“散文诗的小说”,认为此种小说的基本条件是: “一、作品由诗的构思组成; 二、全篇情节挺简单; 三、形象化的诗的语言。”[21]赵景深甚至用一个公式来概括短篇小说的构成: “短篇小说 = 抒情文 + 叙事文 + 写景文。”[22]他们都是主张诗歌元素对现代小说的渗透。到了 1920 年,周作人正式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的“抒情诗的小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说: “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 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3]周作人强调了“抒情”之于现代小说的意义,“诗”是可以化入现代小说的,他的诗歌与小说文体互渗的批评话语也成为了“现代抒情小说”概念的最初定论。此后,周作人持续关注着诗歌与小说的文体互渗现象,尤其关注着有得其衣钵之称的废名小说创作,在评价废名小说《桃园》时认为意境的营造与散淡的叙事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具有“含蓄的古典趣味”。[24]评价废名小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25]。除了周作人,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批评家也是废名诗化小说的注目者。沈从文评价废名: “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并认为在与废名风格并列的小说家中,他自己就是“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26]。时人也如此认为: “以文章而论,新小说中废名与沈从文二君的最为我所喜欢,沈氏文章颇受佛经影响,也有融化唐诗的意境而得到可喜的成功的。”[27]至于朱光潜、李健吾关于废名诗化小说的文体批评则与周作人、沈从文有异,他们发现了诗化小说的异质元素,即从“诗情”到“理趣”的过渡与诉求,也就是废名小说哲理性和思辨性的理性追求。朱光潜先生认为《桥》“愈写到后面,人物愈老成,戏剧的成分愈减少,而抒情诗的成分愈增加,理趣也愈浓厚。”刘西渭也持相似的看法: “冯文炳先生徘徊在他记忆的王国,而废名先生,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同时,他所有艺术家的匠心,或者自觉,或者内心的喜悦,几乎全用来表现他所钟情的观念。这都是因为废名 30 年代小说中的“理趣”特征愈加浓烈,而诗意的抒情元素越来越少。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诗情诉求,到三四十年代的理趣诉求,废名足可以成为现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互渗所凸显的诗性形态起伏消长现象的典型代表。即使以“诗性”见长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在抗战期间就十分欣赏改行当记者的作家,于1947 年写给周定一的信中言之切切: “添一批生力军进来,产生百十部别具一格的现代史,这点希望对于一个兼具记者的作家,比寄身大都市纯职业作家尤有把握。因为生活接触范围比较广,且贴近大地人民。”[29]“贴近大地人民”也就意味着切近了鲜活的社会群体而非个体的生命价值,情感、想象、自然等诗性元素也就被放逐。#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诗性”的消长起伏是现代小说创作中的“文体互渗”批评话语的内质,它丰富了现代小说史的内容。然而,上世纪 20 年代小说批评话语的“诗意人生”并未维持太久,随着主体的成长以及时代的影响,步入 30 年代的现代小说及其批评话语越发显现出理趣的端倪。“30 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虽然在人生价值的认同方面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追求文学艺术的实用功利主义方面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左翼’作家还是‘京派’文人,在创作中都融入了理性的思考,情感一旦注入理性的引导,必然产生对艺术审美的自觉追求。”[30]这种嬗变也体现在现代小说文本的话语策略和表达方式层面,但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一言之,现代小说创作中“文体互渗”批评话语的诗性形态浮沉是与现代作家的个性人格、社会时代意识以及文化精神密切关联的。
本文作者:王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