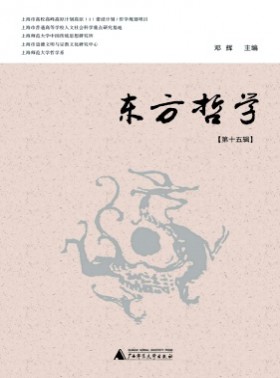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哲学视阈的档案与档案化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档案可以定义成记录过去的现在的一种有意义存在,是对过去式当前记忆的物质化。档案因实践而生,记录了实践的真实,真实是档案最一般的品格,档案总是留真、存真,而人们却能保真、用真。档案的从无到有是档案化,档案化是发展中的档案,具备延续性,档案亦能档案化,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不断地档案化实践中能指导新实践的能力逐渐减弱而消亡,二是因新实践的需要获得新的生命。
从事物发展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来看,厘清什么是档案,档案是怎么来的,档案能如何,以及档案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是认识和研究档案的基础。自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郎格鲁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科学以来[1],围绕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形成了众多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文件说、文献说、原始记录说、信息说、社会记忆说等,这些不同的论点和表述为辨识档案提供了多个方向和可能,显示出档案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但却鲜少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档案天然地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哲学是对一切学科都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高度的思维概括与凝结,运用哲学思维和方法对档案问题展开探讨,从而透过种种现象更深层次地认识档案。鉴于此,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档案以及发展中的档案(即档案化),以抛砖引玉,深化人们对档案本质的认识。
1档案的哲学意蕴
站在哲学层面来认知档案,理解档案的本质,关键是要抓住档案产生的根源和发展机制。亨利•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谈道:“身体是处于将来和过去之间不断运动的边界,就如一个突出的终点,我们的过去持续驶向我们的未来。鉴于我们身体在某一瞬间只是个导体,介于影响它的对象和它影响的对象之间,虽然如此,如果把它放到时间的流动中,总是处于我过去行为终止的那个点上。”[2]74-75人们总是带着过去随着运动持续入侵将来,被入侵的将来不断变成现在接着变成过去,又被身体带动占据接下来的将来,如此循环往复。这里笔者尚且不讨论将来,不论将来如何,总会成为现在,变成过去。怎么知晓过去?或者说过去是如何存活?“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抵达过去,除非我们坦诚地将自己放置到过去。”[3]146“过去应当始终在一种仅仅用另外的形式重复它的当前中呈现自身,并且一切事物都应当一去不复返。”[4]272立足当前,过去和将来因无法触及,是在现在维度的虚拟,唯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当下的行为动作决定了现在的所为,规定了过去的模样,又奠定了将来的格局,这也造就了人们总是立足现在,回眸过去,展望未来的处境。既然现在需要过去,需要过去发生的事实,必然是要将过去的现在呈现在当前。从经验上看,这种呈现最直接最节约的方式就是回忆,但事实证明回忆却不是最有效的。因为脑体的回忆是有缺陷的,受时空限制,且需要过去事实的主体不可能都是曾经参与过这“过去事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这意味着需求主体不清楚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能通过回忆让过去存活。当然,也可以寻找当时参与事件活动的主体来回忆,此种情形下,回忆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便直接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记忆和语言能力。然而,语言的功能再强大,记忆却是有限的,且两者在不同记忆主体之间存在着能力大小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与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对回忆的可信度造成影响:顺着有限的记忆表达,表达出的东西远远少于需要被理解的;而如果循着有限的记忆充分发挥语言的能力,则会引致对需要被理解的事实的偏差。况且人们不能遇事都去找参与主体回忆(需要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成本难以估量),此外,回忆的时限还受参与主体的自然生命的限制。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实践留存,它可以不受参与主体的记忆、语言以及自然生命力限制,通过对它的认识就能了解需要的东西。事实不变人在变,仅靠人的记忆与回忆不一定能准确抓住那发生了的实践事实,唯有那些经历了社会实践的有意义的留存,才能将过去带到现在。档案总是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在时间的长河中,依托人们身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在切实发生着的就是切实发生过的,而切实发生着的实践活动正在形成档案这一存在,切实发生过的实践活动已经形成了档案这一存在。因此,如果从哲学层面给档案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认为,档案是记录过去的现在(这里强调的是过去进行时)的一种有意义存在,是对过去式当前记忆的物质化。处在不同时间节点看同一事物,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多样的。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档案,这种伴随产生的状态说明档案的产生总是正在进行时,是当前的。笔者认为,档案的有与成和实践活动的始与终是遥相呼应的,实践活动未结束,档案还在形成中,正进行着对当前记忆的物质化。从档案成型或档案可用的时间节点看,人们利用档案是在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档案所记录的已经是过去的。任何东西只要是没有用处就变得毫无力量,那些随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就结束用处或者没有意义的存在不能成为档案,档案的意义就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事实的发生,档案有用的体现是后来的社会实践需要曾经的社会实践事实。人类实践活动无不受意识的支配,而实践活动中意识形态的当前记忆唯有通过人们的作为附着在载体之上才能变成物质存在,得益于这种物质化的存在,人们在后来的实践中才可以复活过去。档案的本质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真”与“实”的留存,这样档案才能直指实践事实本身,才可以为后人了解曾经事实提供直接真实的途径。诚然,因实践的复杂性,档案不可能将发生过的实践事实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并呈现在需求主体面前,但并不影响它带领人们窥探已发生过的事实情况。即使其记录下来的远远少于实践事实需要表达的,档案却没有主观记忆与回忆的缺陷,足以让需求主体了解实践事实原貌。“档案作为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它所记录下来的信息点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貌,但并不影响人们后来利用档案建构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性原貌。如学生入党审批文件,记录下的是入党学生的姓名以及时间信息,至于学生入党的过程无从体现,但在查阅时,某某学生在什么时间入党这一事实和当时的入党实践活动是一致的。”[5]档案可以将过去复活的力量来源于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致性,来自于档案的真材实料。
2档案的真实品格
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是对过去式当前记忆的物质化,记录着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生着的事实,它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真”与“实”的留存,保留着真实的社会事实,真实是档案最一般的品格。“档案是人们有意识保存起来的对已发生的某种人类实践活动的事实进行的记录,这种记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经验事实,即过去的可供验证的事实,具有‘一种可供了解和追溯历史事实的特殊意义’。”[6]档案的这一品格表现在档案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也是档案之所以是档案,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内在规定。人类世界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产生和使用工具的世界,人们总是借助于各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所需,在人、工具、工具对象三者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之间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且只有通过各类工具人们才能实现诸多需求。“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为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7]人们需要做或者等待做的事情起初都是意识形态的,在人们做事的过程中利用语言、文字、图像、物体等工具完成需做或待做之事,就将意识形态转换成了物质形态,成就了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人们据需做或待做事情的性质,考究要达到的目的与效果,然后利用语言、文字、图像、物体等工具,通过合理合法、规则有序组织后作用于对象,直到达到实践目的与效果。这一过程中,人们利用的工具被附上了烙印,得到充实与升华。一旦实践完成,意识形态的需做或待做之事消失,存在过的实践变成不再进行的行动,成为过去,只留下了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些随着实践活动的结束就完成使命,而有些则带着实践事实信息,能在将来带需要过去的人们回到过去直击实践事实,这些“真实”的留存就是档案。按照上述说法,人们定会怀疑笔者将档案的范围无限放大了,但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档案是社会实践的真实留存,它的形成以具体实践的结束为标志,无论是否将其收归档案馆(室)进行规范管理,一旦实践结束,形成的档案可以让有需要的人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了解实践事实这一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由此可见,档案价值的发挥与是否完成归档以及保管在何处都无关,并不是必须完成归档环节到档案馆(室)规范保存,又通过档案工作人员的提供得以利用的才能算为档案。那些经实践锤炼,能成为人们抵达过去了解过去的真实之存在都是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是人们抵达过去的直接途径,它是实践活动工具的直接留存,记录着实践的真实,后又成为人们了解过去的工具,其价值的发挥是以人们的需求为转移的。事实上,一定社会时期内,人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使用着通识的符号,流通的工具,通用的手段,这使档案以一种最质朴的状态记录着实践,承载着大家共通的信息,一旦被展示,所有人都能领悟与明白,而需要之人则可以使用它的质朴和直接来证明自己或者得到经验性认识,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支持。正因为如此,档案才有了保存在档案馆(室)的需要与必要,而不宜直接放在完成实践之人的手里。这既是档案真实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档案价值发挥规律的客观体现。作为在实践中使用的工具,档案因实践活动的不再执行就完成了帮助实现实践主体的利用目的,接下来的任务是帮助需求主体实现利用目的,这时候的需求主体可能是当初的实践主体,也可能是实践对象,或者与两者都无关。换言之,在档案价值发挥的轨道上,其利用者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形成范围内的参与者,凡是需要曾经事实的需求者都能利用。因而,唯有将这些资源放在一个公共的区域规范管理,才能不以保管之人的意志为转移,才能尽可能长久且公平公正地提供利用,造福社会———在公共的档案管理区域,档案工作人员遵循一定原则和方法,比如以全宗为基础,遵循来源原则,保持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的价值等,为方便保管、查找、利用而对档案去粗存精、进行标记以及进一步地有序化,通过各种方法对档案保真保实;再藉档案利用环节,即档案价值实现的环节,经需求主体提出之需求,“通过物质性媒介(档案信息载体与人体)将意识形态的档案信息内容与档案信息内容对应的空间对象连接”[8],使档案原样提供,发挥档案之所能够,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真、用真,维护着档案的真实性意义。
3档案化与档案的档案化
3.1从无到有的档案化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遵循着“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自然运动法则,从虚无到实在仅是差着实践的一步之遥,而从实在到虚无可能是实践的推手,也可能是历经时间洗礼的自然抉择。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都知道贝克街221B是福尔摩斯的住址,贝克街虽是真实存在于伦敦的一条街,但在小说连载时却没有221B,小说的成功使人们异常喜欢这个虚化的神探,为了纪念他,人们将贝克街239号按小说内容布置变成221B使其成为可用地址,现今该地址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而真正的贝克街221B每周都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福尔摩斯迷寄来的信件。可见,人们通过实践可以将有些虚无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随着这种物化实践不断进行,人们甚至会相信那是真的存在,忘记或忽略了起初是虚构的这一事实。无论实践是否弄虚作假,实践本身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实践中使用的工具才能在后来直指实践本身,让需要的人们了解。在目前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东西,都在环境的关系网中作用与反作用,经历着时间的改变与抉择,而人造之物一旦脱离人们的价值需求就会在实践中被抛弃,从实在走向虚无。德里达认为:“所有个人的、社会的、机构的以及技术上的信息交流过程(Communicationsprocess),实际上是一种档案化(Archiving)过程,或者即他所谓的‘档案化’(Archivization)。”[9]在实践结束之后,对于实践中的真实留存,人们会受现有的主流价值观支配进行选择性保存,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是结合当下社会需求以及将来的社会需求进行的一个预判,我们不能只将在这种环境下甄选出来的才称为档案,也不能将这样的选择作为档案化的开始。档案伴随实践而生,实践的开始就意味着档案化进程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的结束即档案的形成并不是档案化的完成,档案的成型待用到用,即档案价值创造到档案价值实现过程都是档案化的范畴。从档案的轨道上看,在实践的信息交流中因信息与载体的结合得以成型,开始信息交流就开启了档案化进程,实践的结束因档案的成型(也是档案价值的成型)以及人们现有价值观评判的介入似乎是个结点,但无论是否被人们选中放进档案馆(室)保管,只要它能直指实践本身,能带将来的人们回到过去,它的价值就一直存在。至于其价值能否实现,则在于人们需不需要。
3.2档案的档案化
档案化是具备延续性的,已经完成档案化的档案总会加入到新的实践,再一次进入到档案化行列。那如何看待档案的档案化?档案档案化后还是档案吗?在笔者看来,档案的档案化是档案,但是否仍能作为“档案”留存,则需要看它与新实践的贴切程度,即它能直指新实践事实本身的程度。档案的档案化仍然是档案,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实践事实的真实留存,能直指实践本身,即使加入新实践,这已具备的性质和能力是不会改变的。档案的价值实现出于人们实践需求,一旦价值实现意味着档案加入新的实践。档案被利用加入到新的实践是业界最为常见的档案的档案化现象,档案被利用加入新的实践,并不能改变档案对原本事实的记录,却因为加入了新的实践成为记录新的事实或与旧有事实结合的新的档案。不过业界更多的只关注到了提供利用环节,因为这是档案实践工作的一个节点,档案工作者使命的完结,人们甚少去想这些档案的归属。无论被利用的档案是证明事实还是提供经验性认识,它都会作为新实践中的一种支撑得到价值实现,那它是否仍能作为档案留存需要看它能直指新实践事实本身的程度。如在人们选择深造时得提供已取得的最高学位学历的成绩情况,这里的成绩(学籍档案)是深造的准入资格之一,面对的实际是当事人需要获得深造的学历学位,一旦当事人取得相应证书,作为准入资格之一的成绩并不能说明当事人完成深造取得相应证书这一事实,即使成绩本身是档案,但它却不会被作为当事人深造阶段的学籍档案留存。与之相反,如纪委监察部门在调查某问题人员时,取证到文字、照片、视频等各类记载问题人员的档案,这些是新实践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事件完结后就需要作为新实践的档案予以保留。另一种档案的档案化现象在档案管理部门是常见的,即为节约资源且更高效地提供利用或保护档案原始载体,或者是档案载体无法再继续留存而对档案信息进行新方式方法的保存,如对纸质档案的数字化。这可以对应到德里达的“技术上的信息交流过程”,这种档案的档案化仅仅只是将档案信息进行有效转移,信息转移之前是档案,信息转移后档案载体虽发生变化,但仍是信息与载体的结合,其内容并未发生变化,仍能直指当初的实践事实本身,得到的结果是档案。与上一种现象所不同的是,这里对档案信息转移的实践成为手段,实践前后的档案直指的实践事实是相同的。还有一种档案的档案化现象是曾经的实践未存在有效留存,却有参与人或知情人,通过向参与人或知情人了解曾经的实践而得到的记录,典型的如口述档案。这里人们会质疑,参与人或知情人又不是档案,通过向其了解曾经的实践不能算档案的档案化。从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实践是离不开人的,人是实践活动中能动的工具,参与实践或了解实践的人将实践事实掌握在脑中,通过回忆的读取方式能直指实践本身,这也算是承载实践真实信息的工具留存,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种活着的“特殊档案”,而通过向参与人或知情人了解曾经实践事实的实践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档案的档案化。可见,这里的档案化实践亦是一种手段,得到的档案所指的事实与参与人或知情人了解的事实是一致的。当然,诚如上文所述,人的记忆与语言表达存在着能力大小的差异,因此,通过向参与人或知情人了解曾经实践事实的这种档案化得到的档案结果,其直指实践事实本身的程度是需要考究和有待检验的。基于档案本身的演化规律,随着档案化的持续延伸,档案的最终命运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逐渐消亡,一种是逆向重生。前一种情况是指档案在不断的档案化进程中,与新实践的契合度出现渐弱的趋势,事后能指新实践事实本身的能力会越来越弱,被留存的几率也越来越小,最终逃不过淘汰灭亡的命运。后一种情况是指档案在档案化进程中因新实践的需要获得新的生命,有些档案对过去的真实记录,其价值本身就是无可替代值得永存的,也有档案在档案化中价值发生了转化,与新实践结合成为新的档案。档案因实践而生,记录了实践的真实,被利用是因为与实践的一致,淘汰灭亡是因为丧失直指新实践本身的能力,可见,档案的有无都需要实践的推手,由实践创造,可以在实践中重生,也可以在实践中灭亡。
作者:赵红艳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