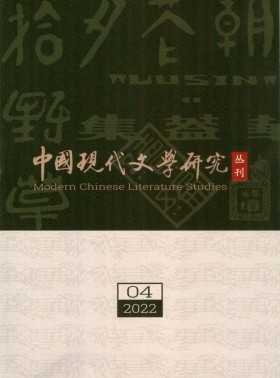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中留学生的作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为了新国新民、变法维新,纷纷提倡向西方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派遣留学生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政府自1872年选派了30名幼童赴美开始,便陆续向英、日、法、德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路矿、机械、军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留学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媒介”作用)。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郭沫若在1928年就曾不无自豪地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句话虽有浪漫夸张之处,但现代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确是曾经出过洋的留学生,他们对新文学的贡献、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因留学国家不同而导致的思想意识、文艺主张、审美情趣等的不同,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论述。那么,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全球化”语境下,在“后殖民大流散”(postcolonialdiaspora)中“出入于各种文化,不属于任何一种”的世界公民越来越多的当下,再回看现代文学中那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形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与那些土生土长的人物相比,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为作品及现代小说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质素?这便是本文兴趣的开始。
一、报国无门•随波逐流•努力自强
“以我这样的少年,回到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亲爱的父母姊妹!亲爱的祖国!我英士离着你们一天一天的近了。”[1](P37)这是冰心《去国》中主人公在回国船上的激越情怀,相信也是当时大多数归国游子的共同心声。然而主人公的满腔报国热情却被对现实的失望一点点熄灭了,最后,为了不愿在“饮博闲玩”中虚度光阴,为了避免“沾染这恶社会的习气”,不得不满怀悲愤地呼喊着:“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而离开了回来仅仅一年的祖国。英士的失望,相信同样也是当时大多数留学生回到祖国后所遭遇到的。如果说英士依靠父亲的声望尚能在衙门里谋到一个衣食无忧的闲职,而那些没有关系可以依靠的,便陷入了谋生的漂泊困顿之中。郭沫若颇具自传色彩的《漂流三部曲》中的爱牟自日本回国后,为着自己的兴趣以及“转移社会”的希望,弃医从文,但却无法摆脱历年来的贫苦生涯,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在生活的压迫下,他不得不与妻儿分离,送他们东归以另谋生路,一个人在上海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到了续篇《行路难》中,爱牟虽也重回日本,与妻儿团聚,却依然为生计所苦,最后只得避居乡野。
与英士、爱牟的无奈去国不同,多数的人还是留了下来,或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曾经有所作为;或者虽不满现状,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前者如《倪焕之》中的蒋冰如、《母亲》(丁玲)中的于云卿等,两人都曾留学东洋,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蒋冰如曾和倪焕之一起精心设计“理想教育”,于云卿则“讲民权”、“倡共和”,与留洋同学一起办女学堂,并支持在娘家孀居的姐姐进学堂读书。后者如英士在美国时的几个同学,刚回国时原想办一个工厂,既可以“振兴实业”,又可以“救济灾民”,只是无从筹措资金,只好作罢,渐渐安于做一名“闲员”,过着英士所深恶痛绝的随波逐流的生活。最让人失望的是,这种“恶社会的习气”不仅影响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连那些曾积极从事于改革的人,有的也被现实所屈服而逐渐同化了。如蒋冰如在理想教育受挫后,思想开始退缩,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在倪焕之为之热血沸腾的大革命前夕,他担心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受影响,特地赶去把他们叫回家中。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两类人思想虽日渐萎缩但却无须为生计担忧,有的甚至能够飞黄腾达,那些和爱牟一样谋生艰难的人,只能如《神的失落》(王西彦)中的那位沉默寡言的蔡仲民,在一个偏僻的山城中做一个生物教员,走着别人眼中的“末路”;或者像《围城》中那位既可爱又可怜的方鸿渐,从上海到内地再由内地到上海,为谋一个职位而四处奔波。在众多反映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愁苦穷困的生活状况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描写了归国的留学生。如靳以《生存》中的主人公李元瑜教授,是一位唯艺术至上的画家,在法国留学时,他曾清高地拒绝了别人用高价来购买他的作品,理由是不能“出卖我的艺术”,然而才华横溢的妻子因过度操劳而过早的憔悴、衰老,儿女因贫穷、饥饿而受到的欺侮和满眼的泪光,使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靠卖画来维持生计。
当然,在一些留学生身上也体现或寄托着某种光明与希望。蒋光慈《兄弟夜话》中的江霞,也是一位刚刚归国的热血青年,国内的黑暗使他常常怀念莫斯科的光明、自由,但种种失望与愁闷并未减弱他的革命激情,没有做“逃兵”,也没有放弃自己改造中国的主张。司马文森《天才的悲剧》中的尚仲衣教授是位留美博士,抗日战争中他放弃了自己在名校的教授位置和美国绅士式的生活,投笔从戎,艰苦的随军途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但认真耿介的性格使他招致流言与排挤,被免职后他依然留下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死在了去香港的途中。在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思想变迁、心路历程,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在作品中所承载的意义,并不因他们的留学生身份而有别于其他的同类形象(尽管他们或许有着各不相同的独特之处),如蒋冰如的由“新”变“旧”,正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总结或预见的那类停止不前或退步的知识分子形象:由“痛骂官吏的学生”变为“嫌恶学生的官吏”,由“家庭革命者”变为“压迫子女”者;英士、雷先生的学无所用、报国无门,英士同学的随波逐流,爱牟的“弃医从文”、李元瑜教授的“艺术至上”之在现实社会中的难以立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是从“留学生”这样一个角度继续或加重了对那个扼杀人才、令人窒息的黑暗社会的批判和控诉。如果说江霞的身上还有着革命文学中浪漫蒂克的气质,那么尚仲衣教授的遭遇(这两个人物都有着很大的纪实性),则是通过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悲剧命运来揭示了整个时代与民族的悲剧。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现代文学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与丰富。#p#分页标题#e#
二、个性解放•东西差异•回归传统
许地山《三博士》中的何小姐有这样一番“高见”:“留学生回国,有些是先找事情后找太太,有些是先找太太后谋差事的。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么都不找。”[2](P17)其实,“找事”与“找太太”无论先后,对于那些踌躇满志的归国留学生来讲,和所有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恋爱、结婚在他们的生活中无疑占有很大的分量。前面提到的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蒋光慈的《兄弟夜话》等作品中,在主人公的理想与抱负、失望与愁苦中,都还包含着一个个性解放的问题。爱牟在家乡有一位父母包办、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伤心而不能离婚的妻子,江霞在家乡则有父母帮他订的婚约,尽管两人都非常思念家乡与亲人,但为了不受旧式婚姻的束缚,爱牟拒绝了高薪聘他返乡行医的邀请,江霞则经过一夕长谈,说服了奉父母之命劝他回乡成婚的大哥。爱牟心灵上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但还是追求着自己爱情与婚姻的自由,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却完全被旧礼教所束缚,连面对心上人向自己表白爱情的勇气都没有,逃回到家乡,逃回到“良心的慰安”中,最后,在精神的痛苦中沉江自杀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激烈与不彻底同时俱在,即使是留过洋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现实或文学作品中),在那样一个新旧错杂的社会,无论勇敢还是懦弱,对某一方而言,悲剧都是难以避免的,这悲剧也许仍该归于社会或时代。
有些故事与个性解放没有多少关系,而与留学生阅历东西的生活经历相关,也涉及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曾喜欢过一位叫玫瑰的混血女孩,玫瑰活泼而随便的性格在他看来,对己是“天真”,对其他人则是“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3](P136)。这样,讲求实际的佟振保便放弃了自己的初恋,只留下一个“玫瑰”的名字来比喻自己的妻子与情人。然而在徐訏《吉布赛的诱惑》中,“我”在吉布赛女郎的怂恿下,认识并爱上了美若天仙的模特儿潘蕊,几经周折后两人终于结成美眷,并一起乘船回国。但是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差异,使这位异国女郎与“我”的家人难以相处;在内地大学,“我”又因忙于教务使热情外向的她受冷落而日渐憔悴,于是两人又回到马赛,潘蕊在自己的模特儿工作和社会交际中重放光彩,“我”却深感孤独与忌妒。当然,因文化差异在两人婚姻生活中所造成的影响,在作者浪漫诗意与暗含哲理的笔下很容易就得到了解决,因为可以战胜一切的爱情,也在吉布赛人的人生哲学的感召下,两人回归自然,一同漫游世界、阅历人生。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中,一度常将两类形象加以比较,一类是在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时代新女性,一类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东方女性。就人物本身而言,这两类形象并没有孰是孰非的对立,只是因作者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审美标准等的不同而蕴涵了不同的意义,拥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空间与情感方式,有时也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如许多研究者所谈到的茅盾笔下女性形象的转变,即由时代新女性转向对传统女性美德的发掘与肯定。那么在留学生的感情生活中,有像佟振保那样喜欢“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却娶了一个“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的“很乏味”的女人(前者是给外人看的,后者才是自己的感受),有的则的确是心仪于具有古中国情调的“传统”女性。
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被曹七巧“黄金的枷”劈杀的人中有她的女儿长安,也许在七巧“悲烈”的故事中长安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陪衬,所以在《怨女》中作者竟删去了长安那一部分,其实长安的故事在《金锁记》中是最为诗意感伤的,如同那句经典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童世舫从德国留学回来,他也曾为婚姻自由抵死反对家里定的亲事,但当他父母终于同意他解约时,他所爱的女同学却移情别恋了,由此,“他深信妻子还是旧式的好”。这样,多年没见过故国姑娘的他,长安的矜持与沉默、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话,使他觉得很有点楚楚可怜的韵致,是他所怀念的幽闲贞静的中国闺秀。以童世舫这样一个有过个性解放、长期在外留学经历的“新人物”,而对古中国产生怀念,也许是一种对传统的回归,然而这回归是有选择性的,如同“新”的不彻底一样,长安的抽鸦片、长白的姨奶奶,仍使他感到了“难堪的落寞”,最终断绝了在长安被迫与他退婚后两人继续的来往。
如果按现代文学中常用的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来看,如新与旧、东与西、现代与传统等,在留学生的婚恋故事中,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中西结合的差异、对传统情调的眷恋,都可以说是源于二者的对立冲突与相互交错,只是在现代文学的大叙事中,更为关注的是由二者所产生的先进与落后等大问题。个性解放在五四新文学中本来就占有重要的位置,描写留学生的作品中与此相关的,如前所提到的,并没有超出其他作品中所涉及和探讨的问题。中西结合的差异、对传统情调的眷恋或许能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要么并不是作者所感兴趣的、要么被作者轻巧地避开或解决了,都没有再继续下去;远离故土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则在当代台湾作家白先勇、於梨华等人的笔下有了深入的探讨与展示,这随同中西的文化差异与碰撞,一起成为面临全球化、跨文化语境下当代中国人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文学中描写留学生在国外求学的作品里,固然也有思乡情,但更多的则是弱国子民所受到的民族歧视与金钱势力的压迫,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民族尊严、情感与性的苦闷、追求个人享乐等。此外,以茅盾为代表的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再塑造与肯定,以童世舫为代表的对东方情调的“回归”,与新时期后对“五四”的反思、“国学热”等文化现象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复杂性,也是现在依然面临并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镀金的“学说”•中西的“合璧”
前面所论述的归国留学生的生活百态中,无论是喜还是悲,是崇高还是凡俗,都不失其人生的认真与庄重(或许是因为作者更多地将批判锋芒指向了那个社会与时代而非个人)。然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由于作者的叙述视角与讽刺嘲弄的语气,使一些做着看似同样事情的人物,却披上了一层滑稽可笑的外衣,尽管他们本人也不失努力和认真,但许多人显然并未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同情。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就像闭关自守的清政府终于决定向外派遣留学生一样,大多数人是抱着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出国留学的,但是,当和其他事情一样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之后(尽管在当时那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留学的目的也就慢慢“多元化”了,甚至也就没有什么目的了。方鸿渐曾就此发表过高论:“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4](P81)于是,方鸿渐由留学生变为“游学生”,在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课,最后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又随便买了个博士学位。尽管他耻于以此示人,但他三闾大学的同事韩学愈却拿着同样的文凭,得了教授又得了历史系主任的职务。#p#分页标题#e#
当然,像方鸿渐这样落拓潇洒、毫无“上进心”或功利心的毕竟是少数,许多人不论家境好坏,是非常“珍惜”这出国的机会的。文博士(老舍《文博士》)在留学期间,“有时候宁肯少读些书”,也不肯放弃在留学生间的种种交际与宣传,“为是给将来预备下帮手”,由于其他事情花费太多时间,他因交不上论文,延长了一年才毕业。张爱玲《相见欢》中的伍先生与文博士所见略同,“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对“会出个把要人太太”的女留学生和“国内名流的子弟”,极其热心周到,以此来扩大交游。连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的随员甄辅仁,在纽约住了些日子,回来后便到处对人讲“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尽管他的博士照“连帽子都不会戴,把穗子放在中间”,他还是把照片印在名片上四处送人(许地山《三博士》)。
既然留洋是少数人才有的机会,全中国又有多少个博士,况且得到博士学位又那么不容易,使人不能不特别地“自重”起来,哪管做的论文是《麻雀牌与中国文化》,还是《北京松花底成分》、《油炸脍与烧饼底成分》(《三博士》)。文博士回国半年,过去的朋友一个也没靠上,自己为适应国情而定下的并不过高的希望———“四五百块钱的事,和带过来几万陪送的夫人”———一个也没有实现,但一个美国博士,既不能从“下层社会拾个饭碗,抢点饭吃”———如果这样,何必去美国得博士?也不能“做倒了名誉”,在大学里做个“教员”而不是“教授”———《三博士》中的何小姐以为,一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
最后,在焦委员的指示下,去了济南。在焦委员看来,“这些无经验,难于安置,又没多大学问的新博士与硕士们,顶好是当新姑爷。他们至少是年轻,会穿洋服,有个学位;别的不容易,当女婿总够格儿了”[5](P242)。他派文博士到济南,因为那里的“振兴实业”(联络富商)和“到民间去”(联络富农)的工作都需要人,也就是为那些富商、富农“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从中选择新姑爷。这正好和文博士在美国时的宣传“当代的状元理应受富人们的供养与信托”不谋而合。不管是为了“增加免疫力”,还是为了日后的飞黄腾达,留过洋的人在大到择业择偶、小到饮食起居上,自然有着与众不同之处。除了那些一味要洋派的人外,如张爱玲《留情》中的杨先生,太太刚生了孩子,就逼着她吃水果、开窗户睡觉,为此还得罪了丈母娘,把自己的太太也俨然培养成了一位沙龙里活泼俏皮的主妇;多数人还是很注意中西“融合”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所谓的“中西融合”,只不过是从西洋文化中拾得一点表层的皮毛,在“没有希望的中国”便充当起西洋文化的代言人,在国外,自然又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只是他们所代表并用以融合的,要么是新文化运动早已批判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腐朽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要么如曹元朗只是将中西文学中的意象、典故生硬地拼凑在一起;这样融合的结果只能是一些不东不西、不伦不类、毫无意义的畸形儿。比如文博士一面时时不忘自己在美国住过5年,济南那难以下咽的西餐、没有沐浴设备的公众浴池等,使他愤怒地想到自己“不久就得变成个纯粹中国人”(这和英士的不愿同流合污相去甚远);一面又以“当代的状元”自居,杨家那慵懒淫逸、自成一体的大家族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甚至想如果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即使牺牲“理想”也无所不可。而他们进行“融合”的目的,如同他们的出国留学一样,是为了给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能力与条件,这本无可厚非,尽管在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文博士这样的人无疑是时代潮流中的渣滓,如同作者对他们毫不留情的嘲讽一样。只是他们还要时时处处用“做稳了奴隶”的优越感,来蔑视、指摘“你们中国人”,只能在脸上再涂些白粉的同时,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同情。就形象而言,他们是些“扁平”人物,远没有那些“由新而旧”的形象丰满,但是这类在现代文学中不起眼的形象,在当代中国及文学中还是能够找到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这或者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也许是因为留学生的确在近现代中国的各项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许是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主题的影响,才使我们(或许也应该包括作家)以一种先验的形象或目光来审视他们。那么他们即使不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应该心怀祖国与民众,即使他们的努力都以悲剧收场,即使他们最终同流合污,但毕竟抗争过毕竟推动过时代的巨轮;他们出国即使只是为了“镀金”,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些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的个案,比如生活习俗、婚恋观念等;如果他们连这些也没有,那么如张爱玲所言,他们就做这个时代广大的负荷者吧,尽管平凡、琐碎,但终究是一种“苍凉的人生启示”。如此等等。可能就是依照这样的逻辑,本文在现代文学中寻找着,似乎也都找到了,有的尽管并不彻底;而在“即使”之外的那些“畸形儿”,也并不是无法界说的“另类”,他们为时代悲剧中过于沉重的个人悲欢增添了滑稽却轻松的成分,谁知道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是最符合那个社会的口味,从而加速了它的腐败与瓦解,这或许是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反讽吧。
在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专门描写留学生或者涉及留学生的作品尽管不少,但大多是以他们归国后的生活为主。这从一方面说明现代作家更关注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那些人、发生着的那些事,也是现代作家社会感、时代感的一种表示。前面的分析中也曾谈到,在所涉及的同类题材或形象中,如知识分子、婚恋等,那些描写留学生的作品大多也并未脱离整个社会环境与创作潮流,如果与时代主潮有距离的,也只是作家个人风格的展现,并不因留学生形象而有所不同,如徐訏、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在当下所关注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等问题,在那些涉及的作品中,也大都是一带而过,或许是因为在民族生死存亡、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都还没有进入被忧患意识所包围的现代作家的视野,或者尚没有余暇去深入思考。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描写的形象,在当代社会及文学中的延续,使我们在继续的思考中有了一个可以反观的比照与回溯的原点。#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