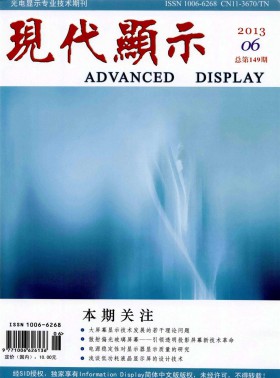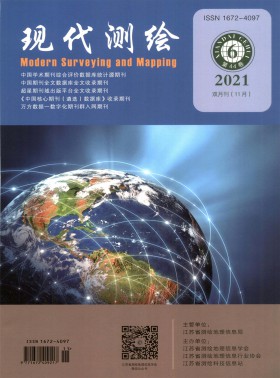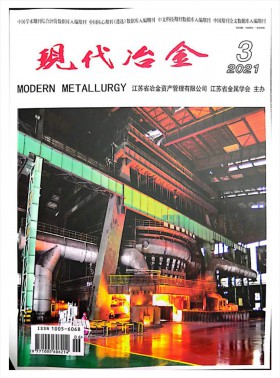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图书馆本体性危险,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20世纪中后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图书馆为主要叙述对象或故事发生背景的后现代小说。这批小说从图书馆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叙写人世百态,立足于批判立场,解构后现代处境下摇摇欲坠的现代性权威,同时也对图书馆这个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设施进行戏仿、反讽,从而表达出后现代作家对文明转型时期图书馆的尴尬境遇的嘲讽、反思及其特立独行的图书馆重构设想。博尔赫斯(JorgesLuisBorges)的《通天塔图书馆》(1941年)、戴卫•洛奇(DavidLodge)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年)、理查德•布罗提根(RichardBrautigan)的《堕胎》(1971年)是这批小说的突出代表。
将上述3部小说聚合到图书馆话题的视阈下就会发现,它们参与了一个基于共同命题的连续思考,即对后现代语境下图书馆的危机叙述及重构设想。《通天塔图书馆》以诙谐、调侃的笔调勾勒了一幅在符号狂欢下的知识迷乱景象,彰显出一个与宇宙同体、遮蔽人生、导向虚无的荒诞图书馆意象,传达的是图书馆的本体性危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则以一个图书馆使用者的个体生命的困境为切入点,体察性的冲动、宗教戒律与书斋制度的相互纠结,主人公窘迫处境的现实性生成与荒诞性化解构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在书名的导引下将阅读指向大英博物馆的价值性危机。与前两者比较,《堕胎》的蕴涵相对单纯,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未刊本”图书馆意象,直指现代性图书馆的制度性危机。尤堪玩味的是,布罗提根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图书馆设计竟然很快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生根开花,深刻地验证了后现代文学中的图书馆危机叙述并非文学的虚妄,也决非虚构空间的纸上谈兵。
从本体性的虚无与迷乱到价值性的荒诞与倒塌,再及制度性的批判与重构,3位作家围绕图书馆这个主题完成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后现代转型时期图书馆的危机叙事。认真研读这类小说,对于我们思考后现代语境下图书馆的本体再认识、价值转型与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
1博尔赫斯:文字、图书及图书馆的本体性追问
博尔赫斯是一位有强烈本体关怀的学者、诗人,他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的诗歌《天赐的诗》(1955年)以及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1941年)、《神的文字》(1949年)和《沙之书》(1970年)对文字、图书、图书馆进行了饱含哲思的诗性叙述。博尔赫斯以诗人的心、哲人的思想和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体验、拷问并解析着文字与图书、图书与图书馆、图书馆与人之间的神秘关联,同时将这一切容纳于他的后现代知识情境,是对图书馆本体的天才性勘探。
1.1《神的文字》:“我在说话”与“话在说我”
《神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囚徒的冥想,这个冥想有关文字与解放。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被西班牙人囚禁于石牢的印第安土著巫师,他叫齐那坎,连同他一起被囚禁的还有属于他民族历史和自然的美洲豹。黑暗的囚室中他回忆起石头、树、星辰、山河与帝国的纹理和形式,他坚信那都是“神的话语”。“神预见到天地终极时将会发生许多灾难和毁灭,于是他在混沌初开的第一天写下一句能够防止不幸的有魔力的句子。他之所以写下来是为了让它流传到最遥远的后代,不至泯灭”[1]172-176。“在神的语言里,任何一个词都阐述了一串无穷的事实”[1]172-176,“神说出的任何词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时间的总和。这个词等于一切语言和语言包含的一切,人们狂妄而又贫乏的词,诸如整体、世界、宇宙等等都是这个词的影子或表象”[1]172-176。“那是一个由十四组偶然(看来偶然)的字凑成的口诀,我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我只要念出来就能摧毁这座石牢,让白天进入我的黑夜,我就能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就能让老虎撕碎阿尔瓦拉多,就能用圣刀刺进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建帝国。四十个字母,十四组字,我,齐那坎,就能统治莫克特苏马统治过的国度”[1]172-176。对文字的终极性探询使他成为一个“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1]172-176,却同时又使他成为一个丧失自我的人。“我知道我永远念不出这些字,因为我记不起齐那坎了”[1]172-176。文字神奇般的魔力刹那间被消解了,他只能再次成为囚徒,成为历史磨难的殉道者,“躺在暗地里,让岁月把我忘记”[1]172-176。拨开《神的文字》玄妙叙述的迷雾,透彻地呈现出博尔赫斯对文字的两点认识,一是文字阐述了包孕“无穷事实”的宇宙,可以彰显宇宙的真谛和“鲜明意图”,因此文字是“神的文字”;二是人在借助文字阐述宇宙的同时又被文字阐述,也就是说,人在凭借文字说话的同时又被话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2]。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卓越代表阿尔蒂尔•兰波的这句话可作为博尔赫斯文字观的注脚。在这个“我在说话”与“话在说我”的悖论中,使用文字的人坠入了文字迷宫,丧失了自我,成为文字世界里的“缀网劳蛛”。对渴求解放的齐那坎来说,浩渺无限的文字世界已然成为一个比西班牙人的石牢更加密不透风的囚室。
1.2《沙之书》:解释的梦魇
《沙之书》叙述的是一本图书的故事。这是一本无限的图书,图书中的一个页码“大到九次幂”,“封面和手之间总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中冒出来的”[1]339-343。“我”满心欢喜地买下了这本沙之书,把它藏在书橱里,日夜研读,却永远也读不完。终于,“我领悟到那本书是个可怕的怪物……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我想烧掉它,又怕它烧起来也无穷无尽,于是把它偷偷地藏到有九十万册书的国立图书馆去,这才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1]339-343。“沙之书”的意象显然是荒诞的,却并不虚妄。它破解了图书在书籍世界中自我生成、不断扩张的秘密:解释与解释的循环。每一本图书都是对事物的描述、意义的表达与解释,同时又是对其他书的解释。在解释的循环中,书与书之间互相连结,成为一本“沙之书”,一种阅读者无法摆脱的梦魇。就像怀特海曾说过的,“西方的全部哲学仅仅是对柏拉图的注解。”[3]其实何止柏拉图的哲学,孔子的《论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几乎所有民族的文明、经典无不在士子们皓首穷经的阐释循环中,不断地冒出新的书页,成为一本烧不尽的“沙之书”。它们远离了图书曾经指认过的那些生动的现实,当然也在诋毁、败坏着现实。认真想来,博尔赫斯的这部看似耸人听闻的“沙之书”其实并非危言耸听。“知识就是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一系列现代性命题的提出及强化,彻底改变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符号、书籍的无限繁殖业已成为一个足以对抗第一现实的符码世界,身处第一现实、心置第二现实①已经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普遍宿命。这时,图书和人的关系经由现代知识体制的强化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反思和变革迫在眉睫。#p#分页标题#e#
1.3《通天塔图书馆》:重复的宇宙本体
“神的文字”汇聚成“沙之书”。“沙之书”簇拥在一个“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的无限时空中。这个时空名叫宇宙,又叫图书馆。《通天塔图书馆》讲述了发生在这个时空中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与传闻。故事和传闻的主角是“重复”,可怕的“重复”!图书馆与宇宙的结构重复,“宇宙(别人管它叫图书馆)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1]63-69,它“是个球体,它精确的中心是任何六角形,它的圆周是远不可及的”[1]63-69。“每个六角形的每一面墙有五个书架;每个书架有三十二册大小一律的书”[1]63-69。图书与图书重复,“每本图书有四百一十页,每面四十行,每行八十来个黑色的字母。每本图书的书脊上也有字母,但字母并不说明图书中内容”[1]63-69;“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个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重复后就变成了有序:宇宙秩序)”[1]63-69。字母在“翻来覆去的重复”,并使“书籍本身毫无意义”[1]63-69。“书写符号的数目是二十五。根据这一验证,早在三百年前就形成了图书馆的总的理论,并且顺利解决了任何猜测所没能解释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书都有不完整和混乱的性质”[1]63-69。“图书馆包含万象,书架里包括了二十几个书写符号所有的组合,或者是所有文字可能表现的一切”[1]63-69。在这个由“重复”主宰的时空中,“图书馆在发烧,里面的书惶惶不可终日,随时都有变成别的东西的危险,像谵妄的神一样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混淆一切”[1]63-69。人在其中,不断重复着各自“沉迷、期望、审查、愤怒、逃离、死亡”的荒诞人生,“独一无二的人类行将灭绝,而图书馆却会存在下去: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1]69。至此,博尔赫斯完成了他悲怆的图书馆危机叙事,其结论是:文字、图书、图书馆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强大的异己性存在。
2戴卫•洛奇:身置困境的图书馆价值重估
戴卫•洛奇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学者型作家、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他的小说《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在1965年一出版便成为轰动英国的畅销图书。其主人公亚当•爱坡比是一位25岁的文学批评专业博士生、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教规禁止采用人工避孕,他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因此家庭生活拮据而混乱。为了不再生育,他和妻子忍受性欲的折磨。同时,博士论文的进展也很不顺利。除了僵化、呆滞的学院体制,大英博物馆里朽木般干枯的学术生活也令人啼笑皆非。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前往大英博物馆读书的一天,诸事不顺的亚当早晨起来便感身体不适,此时孩子还生病,赶着去大英博物馆做论文的他却找不到一条干净的内裤。更可怕的是,妻子的月经没有按时出现。身置困境的亚当开始了小人物常会经历的那种情节——并不惊世骇俗,氛围却离奇诡异。一天里,他忐忑、幻想、觅职、寻书、经历年轻女孩的诱惑,最后总算化险为夷、平安返家。这显然是一个遭遇困境和寻求突围的故事。而大英博物馆,这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和图书馆,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更是亚当生命困境的形成和突围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的困境就是大英博物馆的困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就是亚当在倒塌。
2.1在伊甸园与图书馆之间痛苦地逡巡
主人公亚当•爱坡比的名字富于象征意义:亚当自然让人联想到《圣经》中人类的始祖,而爱坡比则有禁果之意。亚当的禁果正结在大英博物馆丰富藏书的枝头,他从此成为这里的常客,偷食此地的文明禁果,尝到了性欲与文明的苦涩味道。如果没有世俗的压力,如果没有图书馆,亚当•爱坡比夫妇会一直生活在他们的伊甸园里,自然而自由地生育、劳作、享受天伦之乐,而不违背宗教戒律,在这里践行上帝美好的规训:“生吾孩童之洁身者,保吾洁身至成年,让创造之美,变为善之源而非恶之陷阱”[4]152。可是,婚姻与求学却将他抛入了世俗生活与学术追求紧张、对立的困境中,上帝的规训因此变得狰狞起来。对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来说,由婚姻构成的世俗生活已是无法逃遁,要摆脱困境,他只能选择抛弃对上帝的信仰或者对图书馆的迷恋。有关二流作家梅里马什手稿的那封信,从亚当出门前往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刻起便埋伏在他一天的行程中,以希望的生动面孔诱惑着他对信仰和学术的背叛。亚当当然动摇过,性感女孩弗吉尼亚的出现将亚当对上帝与学术的信仰几乎逼进了绝境:他既可以在肉体的放纵中解放压抑的欲望,又可以换得桃色手稿获取名利,这样他就可以彻底抛弃上帝与学术,与甜蜜的世俗拥抱。但他注定是一个信仰的仆从,游移不定使他错失了弗吉尼亚性感的身体,摩托车的意外起火烧掉了桃色手稿,他只能再次在伊甸园与图书馆之间痛苦地逡巡。这真是一个当代大学图书馆的生动言说,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无处不在的学术背叛,偌大的图书馆,怎样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会有一些愉快的时刻,但是肉体却把他叫了回去”[4]1,图书馆的存在价值面临尖锐的拷问。
2.2宛如巨型子宫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亚当的邻居,只有一个孩子的寡妇格林夫人对他的谴责显然具有深刻的世俗逻辑,“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八九点钟离开家,不去工作,而去图书馆看书,这与犯罪没有什么两样。”[4]21亚当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读书的一天从世俗的谴责和妻子是否第4次怀孕的忐忑中开始,他会遭遇怎样一个阅览室?当亚当到达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这里“正逐步进入它冬日的角色——成为学者、研究生以及流浪汉与游手好闲者的避寒所”[4]38,“每天都来拜访这座蕴涵着丰富知识、历史与艺术成就的巨型宫殿似乎没有任何意义”[4]38。在办理阅览证续期手续后,他“走进了那个宛如巨型子宫的阅览室。地板上摆放着许多书桌,学者们蜷缩着身子,伏在书本上,就像一个个胎儿”[4]53。但是,等在外面的女人们对此深恶痛绝,她们在寒酸的公寓或者逼仄的住宅中,“站在窗前,观看着外部世界的生活、商店中的摩托车、广告牌与服装,发现它们非常好。她们痛恨子宫般的博物馆,因为是它给她们带来了贫困与孤独,是它每天占有了她们的男人,将他们的精力耗费殆尽……她们期盼着自己的男人最终从子宫中被驱逐出来的那一天……发誓绝不能让孩子们步父亲的后尘”[4]54。在这里,学术与生活分离,亚当意识到,“大多数文学作品讲的是做爱,很少讲生儿育女。而生活则正好相反”[4]240。要学术还是要生活?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夸张地呈现出学术对生活的剥夺,在一场有惊无险的火灾中,门卫堵着门不让里面的人出去,一位女博士生抱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塞到门卫手里说:“我死了没关系,但是我的博士论文一定要保存下来”[4]119。#p#分页标题#e#
2.3亚当和大英博物馆的希望
对于大英博物馆里形形色色的“亚当”们来说,出路当然不在成功谋得一份工作或者寄希望于妻子这个月没有怀孕,这个出路是侥幸的也是个别的,能解决一个“亚当”的一时之难,却无法帮助千千万万个“亚当”彻底摆脱生活与学术的困境。希望或许就在那个小说中语焉不详的美国胖子伯尔尼,他为在美国科罗拉多的一所大学建设一座真正一流的图书馆而来。他原本想买下整个大英博物馆,“然后把它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运往科罗拉多,把它彻底打扫一遍,然后重建”[4]218。可是,大英博物馆是不会出售的,他只能委托“亚当”们搜罗书籍与手稿,亚当因此会获得一份临时工作。高高的落基山上,一座新的图书馆正在筹建中。在这里,虽然不知道信仰、学术是否还会与生活冲突,但这毕竟是份希望。
3布罗提根:后现代语境下的图书馆制度设计
理查德•布罗提根是20世纪70年代活跃于美国文坛的“嬉皮士作家”。他的小说《堕胎》讲述了“我”在一家特殊图书馆的特殊见闻:这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有100年历史的“未刊本”图书馆,“我”无报酬并心甘情愿地供职其中。“我”的工作时间是自早9时至晚9时。“我”热爱这份工作,哪怕半夜凌晨,只要有作者送书来,“我”一视同仁,盛情接待,登记书名、作者,然后让作者自己选个书架放上。此图书馆不编目,“反正从无人来读书”[5]176-179。“我”接待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作者: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常年孤身一人住在无窗的旅馆小屋里,写了一本《靠烛光在房间里养花》的“专著”,她颤颤巍巍地把书送到图书馆时,“感到幸福极了,毕生的事业完成了”;另一位送来了他17岁时写的小说《爱总是美好的》,已退稿459次了,打破了世界纪录,现在他老了,满足于此数字;《他吻了整个晚上》的作者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看起来一辈子也没被人亲过,这女人的嘴生得奇特,好像给鼻子挡住了,甚至根本看不出她有嘴唇儿;另一位作者写了内布拉斯加州地方史7卷巨著,但他却从未去过该地;一个小姑娘写她的狗,“想让它名垂青史”;一位华人老者李广东,送来他写的西部盗马贼牛仔小说,系掌厨一生,偷空写成……小说结尾,又来了一个人,似曾相识,高个儿、金发、二绺长须,自报姓名理查德•布罗提根,送来的是他的第4本小说。“这本书写什么?”“我”问,他看起来想说两句[5]176-179。“不过是又一本书。”他说[5]176-179。看来“我”以为他想说两句是弄错了[5]176-179。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嬉皮士作家的异想天开,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未刊本”图书馆其实是一个极富后现代创意的天才设计,矛头直指现代性图书馆的制度性危机。现代性图书馆的制度危机来源于它顽冥不化的中心意识和权威情结。与之配套的现代出版制度通过编辑把关,出版经过权威许可的文明成果,并对思想进程进行日程控制。与此相适应,现代图书馆的图书采访、分类、编目、上架及看似严谨的借阅、阅览制度强化着自身的威严。被这个制度剔除在外的书稿成为“未刊本”,沦落为现代文明的看客。许可总是连结着驱逐,中心总是由边缘衬托,出版总是连带着“未刊”。嬉皮士布罗提根的创意正在于他以“未刊”来瓦解出版,以消弭“中心”的权威来恢复边缘的尊严,在话语权面前,人人平等。1990年,布罗提根针对图书馆的文学梦想终于成真,一位布罗提根的崇拜者在佛蒙特州的柏林根建立了“布罗提根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把不想出版或无法出版的图书送来。与布罗提根本人想法不同之处是来这里读未刊本的人还真不少。该图书馆藏书中,诗集特别丰富,奇奇怪怪的小说当然也不少,哲学体系林林总总,数量最大的却是自传[5]176-179。
4结语
这3位作家分别从本体层面、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图书馆进行了生动的危机叙事。他们的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后现作的调侃、戏仿、反讽甚至恶搞的色彩。或许他们有偏执,或许他们有时陷入空想,或许他们务虚多于务实,较少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但仔细品味他们的作品不难发现,针对图书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尖锐、严峻的,他们的反思是认真、睿智和深刻的。当前,文明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知识观、价值观在文明的变革中正处在一个重塑的阵痛期,人们对新制度的向往前所未有地迫切。图书馆在这个进程中显露出来的重重危机,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良所能够化解的。我们尤其需要对图书馆的根本性进行思考和战略性安排,上述3位作家的思考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