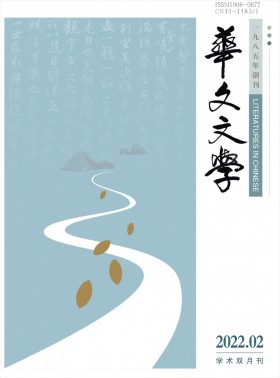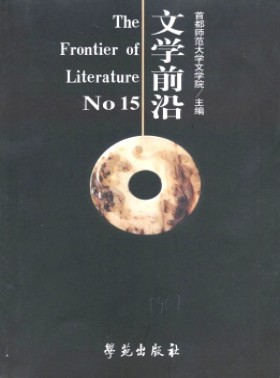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城市构建中的市民精神,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中国最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进入20世纪以来,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城市的精神意义确定尤为重要。关于上海,当代文学又是如何参与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学中的上海呢?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中王安忆以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为书写的对象,其间挖掘出了怎样的“文学上海”?这个“上海”与在历史情境中展开的城市经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长恨歌》为我们感知、理解或者言说“文学上海”提供了哪些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意义呢? 一、“文学上海”的集体建构 21世纪初期,上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城市代表,以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注目。 此间,上海城市身份的建构也成为世人所瞩目的焦点。 班纳迪克•安德森在论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特点时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自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的空间,都需要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公共领域”,以便所产生的意识、观念能够成为全体学员的共识。而文学作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也自然要担负起这种想象共同体的职能。[1] 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视角看,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书写对象,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的想象。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情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建构出来。[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我们认识“文学上海”提供了一个角度。20世纪90年代,当代上海文学写作试图挖掘“上海现代特性”,从程乃珊,到陈丹燕、王安忆。他们创作的动机是寻找与个体经验有关的老上海的历史记忆,以抵制当下有关上海想象的宏大叙事。这些状况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批评者认为历史中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只着眼于咖啡馆、跑马场、电影院,不免片面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虚妄的“建构”中,上海在被片面化的同时,还在刻意地制造着那种“历史怀旧感”。 杰姆逊于对怀旧电影的这样分析:“他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来龙去脉…而那些怀旧电影正是用色彩画面来表现历史,固定住某一个阶段,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来面目。”[3]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症候,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历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症状”。[4] 那么,关于上海繁华的描写,有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呢? 20世纪末期的上海正处于转型时期,不仅在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于文化和精神方面。在这种特殊时刻对上海老照片式的描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上海历史遗迹,而是借此对上海进行现代想象,通过老上海的回忆满足当下的虚妄。正是在这样一种(集体的构建)的思路下,上海曾经的现代性历史被众多的作家写成了一个城市不断地被想象的历史———现代都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城市的全面征服。事实上,从整个上海的发展史和文化的多元走向来看,上海以开埠以来特有的开放姿态,包容和接纳了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上海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整体状况证明这一点,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化写作呈现出丰富的状态。这其中,王安忆以一个上海定居者的视角,剥开城市富丽堂皇的外表下裹着的层层遮蔽,去竭力表现上海的方方面面,透视出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历史变迁中的上海市民的人生百态。 二、《长恨歌》———上海市民精神的书写 《长恨歌》发表后,评论界争论颇多。陈思和认为“王安忆在90年表长篇小说《长恨歌》,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事件,突出民间生活的自然状态,她通过上海市民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记忆”,[5]南帆的评论是:“种种都市意象所透露的种种女性生活对于这个世界的小感觉,毕竟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许多小感觉,小风波,小事件以及一批小人物,使小说具有了某中流言的性质。”[6] 笔者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以一个上海人的文化自觉性出发,试图还原真实的“上海”所做的探索与尝试。 《长恨歌》的开篇将视点集中在上海的弄堂,在弄堂中发掘上海精神。即使在高楼大厦拥挤如林的状况下,上海弄堂依旧平静的保持着自己的气度。 从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就是上海精神的负载者。 小说开篇,就通过城市鸽子的视角描写全城:黄昏时分,鸽群盘旋在上海的空中,寻找各自的巢……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东西南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撒播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死的。它们实在是及其美丽的景象。[7] 这幅上海的图景使我们联想到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所描绘的巴黎。王安忆在场景中看城的历史,从鸽子的视角对这座城市的描写占据了《长恨歌》的前几页,这可以看做是对上海市民精神阐释所做的一种文学准备。#p#分页标题#e# 《长恨歌》讲述了一位上海女性王琦瑶平凡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王琦瑶是一位典型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参加了一九四六“上海小姐”大赛,人称“三小姐”,由此做了上海军界某要人“李主任”的外室,搬进了“爱丽丝”公寓。“李主任”飞机失事,王琦瑶不得不从“爱丽丝”公寓中搬出来,逃避于外婆家———邬桥小镇。解放后她栖居站在上海的小弄堂,开了一间小小的注射室。后来,在与康明逊一段孽恋后,生下了私生女薇薇。80年代,女儿随丈夫去了美国,王琦瑶在各种舞会派对中聊度余生。56岁时,这个昔日风光一时的上海小姐与26岁的“老克腊”,两个人跨越三十年携起手来谈情说爱。王琦瑶从“爱丽丝”公寓回邬桥,再从邬桥回到上海,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孤独”境地。王琦瑶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作家赞扬的正是这种生命不息、进取不止的精神。 王琦瑶身上体现了“老上海”生活的雅致,对政治的淡漠态度,以及功利的婚恋观,不能不看作是老上海人,或者更确实说是上海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精神的反映。其它人物或多或少的都象征着上海的内容:程先生代表着老上海遗留下来的那点绅士派头;李主任,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他让王琦瑶成了“爱丽丝”公寓的女主人;康明逊代表着上海小资精神;薇薇代表着上海新时代摩登风气,盲目追求时髦,却一味的粗制滥造;老克腊代表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怀旧风”的一代,也可以说代表上海特定时期的病态。 三、“文学上海”的建构———诗意日常生活的书写 王安忆以一个上海人的视觉来观察一个现代城市历史进程中城市与人的关系。作家立足于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普遍的人生处境为载体,透视出在历史变迁中人性形态,对普通人与上海历史休戚相关的揭示,都蕴涵着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由此指向人的生存困境等内容。王安忆通过小说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一种强调诗意生活的世俗生活观是否能经住历史的巨大变迁,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与困境中保留下来?王安忆生于1954年,两岁时随母亲茹志鹃南下住进上海市典型的弄堂,附近就是淮海路和原震旦女子学院。对于童年时期的王安忆,弄堂道路既复杂又有序,生活也像弄堂一样既高尚、宁静又平凡朴实。住在同一弄堂的邻居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像她这样的南下干部家庭,也有上海普通的市民。复杂的居住环境使她从小就对人特别有兴趣,在所有人中,“市民阶层”又是她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开始的时候,王安忆只不过12岁,可从她描写少年成长孤独感受的小说《忧伤的时代》中可以看出,她拥有一颗早熟而敏感的心灵。在一个人性格成型最重要的12岁到22岁的青少年时期,她目睹了太多的孤独与无奈,但同时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坚韧。 上海呈现给我们的地域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在弄堂里生活的芸芸众生,也许一生都平淡无奇,但他们就是王安忆笔下“芯子里”的人,无疑,他们才是人生最美的一道风景。他们既有经营生活的能干务实,更有大难临头,处变不惊的勇气和执着。在《流逝》中,欧阳端丽在困顿落魄中,这个当年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奶奶,连马路都不敢过的小妇女,既能不辞辛劳的凌晨四点起床排队买鱼,也能为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在简单寒伧的作坊里工作八个小时。这些蛰居在狭小、浅陋的上海弄堂里的平民不问世事,只关注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他们更多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坦然,甚至在极苦的日子里“偷得浮生一日闲”。《长恨歌》里,尽管弄堂外的政治运动已是翻江倒海,一浪高过一浪,可王琦瑶们仍然守着炉火边上的小天地,做着可口的家常菜,翻新着每日的下午茶。 他们颇为精致的现代生活的芯子里是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鲜明特征和趋势。在审美、诗意的生活享受的激励下,柴米油盐之类的琐碎生活在这里经过了艺术加工,而富有独特的美感。 王安忆通过书写市民生活来展现了现代上海的城市精髓,上海人总是以艺术的态度来经营人生,他们享有的“是一种精雕细琢的人生快乐”。这种螺丝壳里的人生一颗菜一粒米都清清爽爽,市民在日常的起居中诗意化生活,这无疑是这个城市人们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热爱日常生活的市民与这座美丽的城市做到了惊人的协调。 在对上海全方位图景的展现中,在日常琐细生活的描述中,王安忆以知识分子的理性姿态为今天城市化写作中展现的现代上海神话揭开面纱,用她的小说以及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强化我们对上海的另一种记忆,一种更加真实、全面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