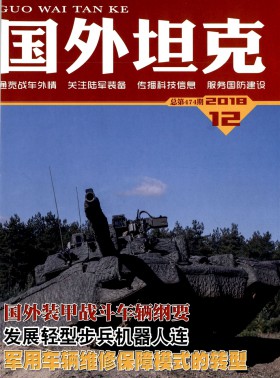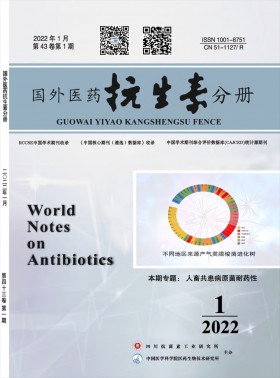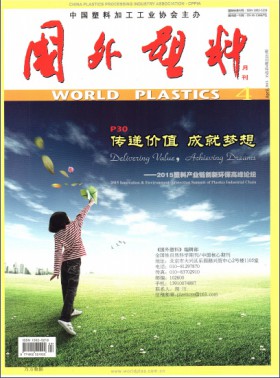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国外自然主义文学差异,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 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1]。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在富尔蒂埃尔詞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自称是描绘当代生活的小说家,乐于描写下层阶级,偏爱于病理学的特殊病例研究。在语言上,他们打乱句法的逻辑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胆的新词和有意的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来表达短暂的印象。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最高者是左拉。他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丰碑。这部巨著在于描写“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是描绘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部编年史式的历史画卷。其中优秀的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馆》、《萌芽》等。 左拉从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理论著述,系统阐述自然主义主张。除左拉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传至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纷纷涌入日本,以真实描写为目的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因其对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使得日本文学界迅速接受了以左拉为首的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并一度成为日本文坛主流。最早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森鸥外。1889年森鸥外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小说论》一文,对左拉以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详细、客观地介绍:“在这里,首次出现了‘实验小说’的字样,并说‘观察’与‘实验’是其理论基础”。除森鸥外的理论介绍之外,小杉天外是日本作家中最早受到左拉的影响且在文学创作中加以实践的作家。1898年,小杉天外在一家旧书店中偶遇左拉的《娜娜》,买来读后对左拉精确的客观描写大加赞赏并深受启发,从而写成小说《新姿》(1900年)。1902年,永井荷风发表小说《地狱之花》,不久,具有相同倾向的文学作品纷纷亮相。岛崎藤村的《破戒》与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发表正式宣告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之后藤村、花袋、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等先后发表一系列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后来他们两人被称为日本自然主义理论的双壁)等相继发表一系列重要评论,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兴盛开来并很快占据日本文坛的统治地位。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在写作技巧上很注重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借鉴和模仿,结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现代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大潮。然而,我们也看到,法国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和自然真实性,作品内容极力渲染人的生物属性、生理遗传和情欲,但细细品味起来,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由于其时代社会的变迁,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等,使得日本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自然主义相比有很大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更能体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鲜明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解。 二首先,在强调文学描写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冲动、人的生理情欲的方面,法国与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中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作为实验小说中人物命运变化发展的一条线索贯穿在作品中,作为一种因素、一种题材、内容表述的某个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种气质特征而表现出来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感兴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对生理情欲的描绘,客观地讲,理性的成分占主导地位,作家创作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层描写,更在于其包含的内在的、深层的意蕴。作品或预示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意指社会的堕落罪恶,或启迪人生生活,常常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意义和审美倾向。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体现了自然主义深邃的理性主义和严肃的价值取向。左拉说:“以生理学为依据,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处理的是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的人的最高级行为”。 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与其说是生理情欲、生物遗传的实验展示,不如说是自然主义作家以生理学、遗传学观点解释社会现象,研究人的思想行为的作品。他将生理情欲看作是人物精神解剖的记录,指出:“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造成种种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种种不同的人态,或为自然的或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们则以善德或罪恶相称”。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肉欲描写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隐私描写、女性肉欲、爱和性主题表现一拍即合,也迎合了日本的好色审美理念。因此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生理情欲的描写不仅仅只是被作为一种题材和一种因素,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对人物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取代了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非理性地渲染人的动物性与肉欲本能,过分强调和张扬人的本能野性,即动物属性的一面。岩野泡鸣据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神秘的半兽主义”自然主义理论,认为作为人性“灵”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追求,只能导向人的痛苦和死亡。 只有作为“肉”的非理性的兽性体验,才能获得人的快乐和生存。在他的《耽溺》和自传体“五部曲”中,有着大量赤裸裸的肉欲场面。 虽然这是一种对人的感觉追求“真”的体现,但是这种不作任何价值判断的肉欲的赤裸真实描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也招致了政府的查禁和评论家的诟病。永井荷风在他的小说《地狱之花》前言中这样写道:“人类的确难免有野性的一面。此乃是因为构成其组织的肉体上、生理上的诱发所至。是有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在许多事情上,这种黑暗的动物性依然存在,如果要塑造完全理想的人生,就要对这种黑暗面进行研究———因此,我想毫无顾忌地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的黑暗的情欲、斗殴和暴行。”也就是说,通过对肉欲的描写,暴露自己最丑恶的部分,发现自己真实的自我才是符合人性的文学表现。田山花袋提出了对生理情欲的自然主义“露骨描写论”。#p#分页标题#e# 自然主义文学从生物学、生理学角度,扩大和深化文学对人的认识和描写,使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属性,而且要表现人的躯体和情欲的各种功能”。 法国自然主义在对生物遗传、生理情欲予以表现的同时,十分注重外部环境作用。他们认为,人作为具有生理物质机能的生命体存在,决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原生态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左拉说,在《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作品里就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莫泊桑凭借《戴家楼》妓女生活的描写,揭露的是造成人物悲剧的资产阶级道貌岸然的淫乐生活环境。在他“最轻佻、最浅薄的短篇小说中,这位艺术家感兴趣的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则明显忽视环境与社会的因素,一味强调只要个人,不要环境,文学内容远离社会生活,渲染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的严重脱节,张扬人物内心丑陋的“公开告白”,对个人道德堕落的“忏悔”。田山花袋《棉被》中,淡化社会环境因素,一味地沉溺于时雄对女弟子畸形爱欲的个人内心心理的赤裸裸的暴露;《乡村教师》中,林清三压抑苦闷的内心、挫折失意的生活;岛崎藤村的《家》在描写封建家族没落的历程中,社会的作用、环境的因素都被淡化和隐退了,作品只是叙述生活中的细微琐碎之事,不厌其烦地描写达雄、正太与艺妓的关系,人物细腻而苦痛的心境,甚至人物的几种发型等,都被重复加以细致描写。在这里,人物内心的心理感受、情感情绪的变化与社会背景、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的,互不相干的。 三其次,日本的自然主义同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主张一样,都强调文学要“真实自然”、“客观展示”,要求作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以科学实验的态度原原本本地再现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自然与社会。左拉说:“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全部内涵。”[2]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两者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真实论的大旗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提出了“无理想”、“无解决”和对自然进行“平面描写”的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放弃一切目的和理想追求,这样才能达到对生活的自然真实的感悟。他们认为,“理想妨碍了对生活现实真实的把握”,文学创作要达到“破理显实”。但是,由于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真实论表现又有极大差异。法国的自然主义真实描写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的真实,展示的是广阔而宏富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幅。他们认为,真实的人除了生理遗传的因素外,还是社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人受到社会关系和生活境遇的制约,形成截然不同的人生。客观冷静的真实描写“成为对一个终结了的朝代的写照,对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时代的写照”[3]。左拉的创作中既有《卢贡家的发迹》、《欲的追逐》、《金钱》、《人兽》等中的那个特定时代上流社会人士“追求金钱和肉欲的记录”,也有如《小酒店》、《萌芽》、《土地》、《劳动》中下层人民苦难不幸、堕落毁灭的人生挣扎,作品揭示的是“第二帝国的整个历史时代”[3]。 而当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东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国,家庭、家族始终是国民生活的中心,社会的主要基础部分。一切对国家、政治及对生活、人生的观念与思想,都会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日本自然主义试图摆脱精神压抑和束缚,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实展示,来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袭观念,从而体现出日本知识分子在集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向往。岛崎藤村在《旧东家》中,以女佣人阿定所见的一系列女东家与医生的猥亵卑劣丑行,形象地诠释了天皇制下的传统道德观念沦丧和旧家族的衰败,揭露出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空虚腐朽的一面。田山花袋以家族为中心的自传体三部曲《生》、《妻》、《缘》中,作者忍受着“剥皮般的痛苦”,将家庭中的母子、婆媳、兄弟间的家丑外扬,逼真地暴露出沉闷压抑、琐屑畸形的封建家庭内部的生活真相,将家庭中“自己所历、所听的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诚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也写家族的兴衰变迁,但和日本自然主义创作中的“家”小说相比较,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品则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社会特征与时代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可以说是“世纪末社会生态的镜子”[4]。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个庞大家族体系所透视的,是法国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以来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和罪人,勾勒出了1851—1871年间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品中所展示的是社会的大“家”,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性。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家,只仅仅局限于家的内部,不再拓展到家之外,作品津津乐道的是个人的小“家”。时代的专制生活氛围,使得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观察社会、希望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我的时候,只看到束缚自我个性发展的封建羁绊及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家”。他们往往一味地专致于家庭内的琐屑事务与个人情感纠葛,把生活的视野收缩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 四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都十分强调作家应该隐藏自己的思想观点,让倾向和意图从作品的事实内容表述中自然流露出来。福楼拜说:“说到底,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是不应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应该在生活里露面一样”。左拉也说:“我们不必从我们的作品中去抽取结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作品本身就包含着结论” 然而,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所“自然流露”的作家思想感情倾向,却有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是积极的参与和入世的思想:莫泊桑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龚古尔兄弟的“文献小说”则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倾向,在予以自然真实地描绘的同时,还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但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无理想”、“无解决”、“平面描写”的后面,实际上放弃了暴露丑恶后的积极态度,明显流露出消极颓废、堕落放纵、自我分裂和虚无主义的世界观,给人一种没有希望和出路的窒息感受,从整体上传达出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黯淡人生观的思想倾向。他们提出“不要对任何理想下判断,不要作任何解决,如实地凝视现实就够了。这就是自然主义”,认为文学要表现的就是人类的“悲哀精神”或“觉醒者的悲哀”。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普遍认为,“暴露现实的悲哀,才是真正近代文学的生命”。《破戒》中的丑松,就是一个沉浸在“觉醒者的悲哀”中的人物。#p#分页标题#e# 《家》中的三吉、正太无法冲破婚姻、家庭的束缚,激烈的内心冲突,导致人物的抑郁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自暴自弃、耽溺肉欲,堕落沉沦;或消极厌世、孤独绝望、忧郁死亡,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无论是岛崎藤村笔下在家庭婚姻桎梏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田山花袋小说中彷徨消沉、挫折失意的“乡村教师”,还是岩野泡鸣作品里在放浪形骸、沉溺肉欲之中寻求精神安慰的有为作家,无不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消极颓废的倾向,读来令人压抑和窒息。 五1908年岛村抱月在《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描写方法、态度角度将日本文坛上的自然主义分为两类:一是纯客观的———写实的———本来的自然主义;二是主观写人的———解释的———印象派自然主义。前者是由西方输入的左拉式自然主义,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经过日本化了的自然主义。这种在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形成的自然主义,最终走上了私小说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在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最终却脱离自然主义文学之轨走向私小说之路,究其原因,是由于国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 明治维新在造就日本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不断冲击着封建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与日本的家族主义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在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最大障碍”[5]。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结合对个人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愈发突出。对于作家来说,“家族制度与个人主义的问题,家庭和个人的对立与矛盾问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也成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新文学的中心内容。”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自我的确立问题。 此外,当时日本政府对个人主义不断的压制,并且对文学作品也进行监视和控制。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受到挫折,因而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统治下,日本自然主义也不可避免得由反映外部社会的真实转为揭露自身。从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自然主义作家执着于“自我”而忘记了“全体”,即与社会和政治完全隔绝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毫无顾忌地暴露“现实”的丑恶,迫近人生的真实,但是这里的“现实”指的不是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国家的现实,而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并且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社会的历史性的把握,个人的现实追求的结果只能走向怀疑和虚无主义。这样的背景限制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主题和选材,同时也决定了日本自然主义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和宿命论,追求肉欲官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