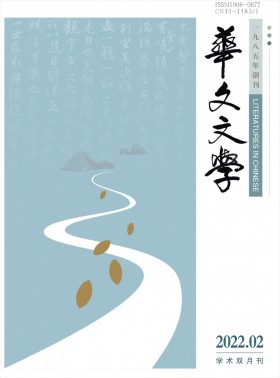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形象翻译创新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机械的、一对一形式的转换,需要译者细致入微的思维活动,以便体察到原文的深层结构所体现的概念意义,把原作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风格特征等尽可能忠实地传达给读者。原作语言与其民族语整体语境及文化社会语境和谐、融洽,而且原作者的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都是原语读者所默认的,但这在陌生的目的语语境中显得突兀而且异类。因此,译者作为在原语语境与译语语境中来往穿梭的使者,他(她)必须对原作的语言和所依附的文化信息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译作便是译者在原语与规范的译语之间不断调和、妥协以竭力弥补认知语境差异的创造性成果。虽然现代翻译研究着重强调“以译文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但无论翻译研究兜多么大的圈子,“等值”问题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所在。事实上,翻译研究的任务并不只是对比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应量,关键是“其实现的过程,即每个译者实现等值阈的内在因素,与其在不断而无奈地规范翻译等值,倒不如探索等值阈实现的过程”(姜秋霞2001:50)。因而,本文试图从译者角度,就关于影响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中“等值阈”的认知语境差异作一些分析和探讨,以供商榷。 二、文学形象语言“第二自然”创造与翻译中的“等值阈” 文学形象语言是以具体形象为手段,来描绘事物的特征、本质规律或抽象的哲理,为读者的思维提供一个形、色、声俱备的意象。正如刘熙载先生在《艺概》(1978)中所做的精辟论述:“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换句话说,作者将自己的情感与思绪恰如其分地融入物象中去,选取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来描绘景物,使作品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原文作者凭借语言作为媒介,对原自然进行了真实的写照,塑造出一系列可感性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物的内心感受,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如临其境的艺术氛围。文学作品中形象的塑造就是指能够真实反映原自然的“第一自然”创造,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在全面分析、研究“第一自然”的基础上,将原语所体现的语言、文化、艺术、历史及美学等方面的色彩最大程度地摄入到译语中,使译文能够真实而自然地反映“第一自然”的全貌,帮助译文读者能够产生像读原作时一样的启示、感动和审美经验。因此,文学形象翻译的“第二自然”创造则是指译者以原文为制约标准,从作品的意义、形式、风格和审美等方面入手,使译文以最自然而完整的方式重组再现原文的形象信息。 郑海凌(2000)曾将译者对“第二自然”的创造分为“离形得似”、“笔补造化”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个层次。意思是说,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及相关图式知识,将原作中提供的语言符号体系在自己的大脑中重新转换为同原文作者脑海中原来的审美形象基本一致的审美形象,也就是将译者的审美经验与作者的审美经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使原作中的艺术意境转化到译文中,并通过译文的语言加以再现。 因此,文学翻译首先要按照一定的美学原理进行再创造活动以展现原作的审美意象和美学价值,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实现的关键是在“再创造”过程中下功夫。许渊冲先生(2003:339)认为文学翻译不但要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译意,还要"译味"。所谓文学形象翻译的创造过程就是指“译味”的过程,译者忠实于原文却又不拘泥于原文,从众多的表达手段中选取一个最恰当的去再现原文的内容、风格、审美思想和意境。正如奥泽洛夫对翻译中存在的这一辩证法的概括“接近原著有时反脱离原著,脱离原著有时却是接近原著”(刘宓庆,1999:220)。在保持言内之意不失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译出言外之意,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审美经验。所谓审美经验(aestheticexperience)就是指“审美主体在体验艺术美时所产生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反映和反应,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以特殊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彭立勋,1999:36)。可以说,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之桥,对作为审美主体的译文读者产生审美的愉快,使审美主体不仅为之吸引,而且为之动情,从而在内心引发强烈的审美经验。 因此,译者必须把握原语深层结构中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特质并加以综合,以求再现这些特质的和谐美。如林语堂先生将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译文巧妙采用七个双声词,并重复使用so,强化了一种萧索悲切的气氛,表达出词人在黄昏细雨之后无奈而孤单的心境。可见,审美主体(读者)对审美对象(译文)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有助于原作创作意图的延展,使译文焕发出新的情趣和意味。也就是说,文学形象翻译的“第二自然”追求的应是神似而非形似,中国的水墨画在数峰清苦与一叶扁舟之间只不过是一片空白,却给人烟波浩渺之感,所谓不落一笔,尽得神韵。译者若能传达原文中“笔墨之外”的东西,必能得其韵致,传其意境。 可以说,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以形象思维为主。具体语言符号通过对具体描写的对象在译者中引发联想,间接作用于人的感观,唤起知觉表象,诉诸人的情感体验,激发人的道德评介和哲理思考,使人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而译者只有善于利用这一特点,才能使笔端的形象鲜明而富有个性,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各种信息,因此,这里涉及一个“等值”的问题。 何谓等值?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1964;1969)通过研究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中心,译文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失去了交际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奈达提出了“等效翻译”的理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因而必须调整信息量以适应信息道,从而克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此,奈达又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即原语和译语之间形成最贴切、自然的对等。翻译和创作一样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奈达的“等效”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对提高翻译活动的社会效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翻译界对此已有定论,即“等效”论的局限性是理论上言之有理,实践上未必处处行得通。#p#分页标题#e# 因此,等值似乎成了一个表达不断追求完美翻译的模糊概念,但这并不能否认翻译的等值性,也不等于完全肯定翻译全靠译者发挥创造。既然不同译者笔下的不同译作无法确定何为绝对意义上的等值,因此只能寻求某个或某些层面上的对等,如语言结构某些部分的对等;或语言意义某个(些)层面的对等;或审美效果某种程度的对等。也就是说,每种译作都是处于达到“等值”理想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位置,即处于某种等值阈。而所谓实现等值阈的过程,其实就是翻译的过程。影响最大等值阈实现过程的因素有很多,从译者认知角度看,归结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翻译涉及双语语言文化的冲突和制约,译者会受各种语言‘准则’的制约和要求;二是译者的主体语言能力、文化结构、审美方式等都会对解读(decoding)和重建(recoding)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各种不同的作用”(姜秋霞2001:50)。笔者以为,以上两个方面都可以纳入到认知语用学中关于译者认知语境的研究框架中。 三、译者认知语境与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中最大等值阈的实现 认知语用学认为,个人的知识结构是其大脑对外部世界的概括和抽象,因此,认知语境就是具体语境通过语用者的经验进行内在化和结构化的结果,是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在具体场合不明的情况下,语用者能够依赖认知语境运用语用知识对语义进行推理和判断。认知语境包括语用者涉及的情景知识、上下文、知识结构以及社会团体成员所共有的集体意识。在语用推理过程中,这几个语用范畴共同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认知语境这一概念的提出给文学翻译以重要启示。语言学领域内的语用认知和认知语境是针对交际会话来说的,而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但是阅读目的语文学作品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蕴涵无数的超交际因素,要获得这一活动的成功,必须对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有相应的认知。从译者的角度看,认知语境包含两部分内容。首先,对译语语言的熟练掌握和精湛运用是实现对原语文化认知化的根本条件,唯有如此,译者才能敏感捕捉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细微的语义差别,同时还将原文所附的文化信息最大程度地传递给译文读者。因此,文化认知语境是组成译者认知语境的重要部分。其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不断解读使原作的上下文知识逐步在译者头脑中得以内在化和结构化,即译者所阅读到的上下文知识不断被内在化为译者的认知语境。随着阅读的深入,认知语境也不断丰富。当阅读结束时,译者对原作的语境认知也相应变得完整和清晰,从而使译者对原作的把握更准确,使译文更贴近原作。 因而,从译者认知角度看,文学形象翻译中“第二自然”创造就其本质来说,是译者对作品空白和模糊点进行充实、发现和延展的过程,译者认知语境的差异会产生不同风格的译文。以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译文为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所包含的文学隐喻生动地表现了其主题思想,有效传达了意境信息,使含义的抒发情绪化、形象化、审美化。 翁显良(顾延龄,1993:47)本着侧重于意境传达的原则,采用散文释义的方法,既不拘泥于词语的完全对应,也不考虑原诗的韵律,在译文中附加了“hovering”、“sparkling”、“pretty”、“moan-ing”、“groaning”、“trudging”等词语,发掘原作可能潜藏的深层意义。但是“,thedayisaboutdone”、“onthefarbank”、“fartherandfartherawayfromhome”等句子和短语的使用显然是译者个人主观意见的反映,也给原作中的诸多景物关系和人物心理做了定型处理。Schlepp(文殊,1989:331,转引自黄国文,2003:22)的译文则是用名词及其附饰语,疏散地勾勒出一幅秋日伤感画面,与原作在形式上是完全对等的。对此,黄国文(2003)认为Schlepp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更能传递原诗委婉含蓄的意境,留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张春柏(2003:16)也说,“在文学翻译中,如果译者的交际意图是让读者全面享受原文的美学特点,而不仅仅是基本意义,就应该努力保留原有的交际线索,再现原文的风格特征。”而许渊冲认为,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保留原语表达形式,而是要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形式,更好地传达原作内容,以保留原作的艺术审美效果。许译将原文中“枯藤”、“老树”“昏鸦”等多个相对独立的意象巧妙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画面,形式齐整,音韵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外化了原作者的心理,使译文读者更容易领略到其中的主旨韵味,又不失原作委婉朦胧的意境美。 可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认知语境成为决定译文风貌的根本性因素,在客观上使得译文的艺术审美感染力成为译者的审美经验与原作的审美基调相结合的结果,译者的文化背景、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其再创造中皆有所体现,即“第二自然”的创造与主体认知的审美倾向密切相关,使文学翻译往往会带有译者个人的主观倾向。然而,尽管文学形象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创造性心理过程,但是如果完全脱离了文本的内在客观性,译文中“第二自然”创造中的意象信息或被增加,或被删减,亦或可能引起译作的韵味和形象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 Ingarden(1973)认为,翻译的创造性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有两种体现方式,一种是寻求对艺术作品最忠实的具体化,另一种是寻求放任自由幻想直到作品按照个人的奇思怪想来具体化。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各种形式的解读与创造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从译者角度看,为了使译文实现尽可能大的等值阈,则必须遵循第一种方式,即“最忠实的具体化”。结合丰富的文学译例,本文拟从挖掘深层结构的概念意义以再创原语的神韵美、突破表层结构的束缚以重现原语的意境美和结合原语表层结构意义以展示异域文化色彩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调节和控制译者认知语境差异,以实现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中最大程度的等值阈。 3.1挖掘深层结构的概念意义再创原语的神韵美 #p#分页标题#e# 文学形象中往往存在着深层结构所表达的语义内涵与表层结构形式不十分吻合的语言现象。这就要求译者在“第二自然”创作过程中能够透过表层结构,对深层结构进行艺术分析,发现语言深层结构之下的概念意义差别,力求将原文的思想、人物情感、风格及审美经验等予以忠实的再现。例如,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贾宝玉乍见黛玉时的印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对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文中划线处为本文作者所加, 下同) 杨宪益先生对三个“娇”字的译 文与原文的表层结构有很大不同: Her dusky eyebrows were knitted and yet not frowning; her speaking eyes held both merriment and sorrow; her very frailty had charm. Her eyes sparkled with tears. Her breath was soft and faint. In repose, she was like a lovely flower mirror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a pliant willow swaying in the wind.译者将这三个字视为同一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充分考虑到它们隐藏在深层结构之下的概念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娇袭一身之病”的“娇”乃是白居易《长恨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娇”;“娇喘微微”的“娇”乃是李清照《浪淘沙》“歌巧动朱唇,字字娇嗔”的“娇”;“娇花照水”的“娇”与李清照《念奴娇》“宠柳娇花寒食近”中“娇”字意义相当。因此,译者将三个“娇”字分别译为"charm","soft"和"lovely",正是因为概念意义不同,它们在译语中具有不同的表层结构。透过三个“娇”字,曹雪芹描绘出贾宝玉眼中的“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似乎使读者看到了她那泪尽而逝的坎坷命运。该译文成功地传达了原作的语言艺术效果,也充分展示了译者深厚的文化底蕴。 3.2突破表层结构的束缚重现原语的意境美 不同的语言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这在译者的认知语境中皆有所体现。例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世界文坛上的绮丽瑰宝,其炉火纯青的境界不但显示了莎翁的惊人创作天赋,同时也表明了英语语言的无限魅力。与汉语律诗一样,除了平仄韵律,莎翁采用了隐喻等艺术而天才的笔触,使作品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神韵,一种气质,一种灵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语这种语言是适宜将音韵附着于其上的,而汉语适宜于表意。因此,用汉语完全传达莎诗的精髓,难度自然可想而知。汉语读者习惯于平平仄仄,对于韵式为abbacdcdefefgg的音步自然感到陌生。汉语一韵到底,酣畅淋漓,而英语却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充满彼此镶嵌的抱韵或换韵。也就是说,汉语表述比较讲究含蓄,特别是诗词的语言,拥有丰富的诗意盎然的词语,带着各种感情和韵味,译成英文时很难与原文高度统一。翻译这些时,就更要求译者有创新立异的艺术,使译语以最自然、最贴切、最完整的方式重组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神韵。以《登鹳雀楼》的几种英译为例(转引自许渊冲,2005:43):许渊冲的译文采用“glow(发微光)”一字,扩展了“白日”的内涵,勾勒出一幅日落西山时的暮景而曲达其意。而WitterByneer采用简洁、凝练的写实手法,对原文中的画面进行直观的描摹。 JohnTurner将原文中的“白日”(thesun)间接地译为daylight(日光),借助于词汇意义联想,亦能传达原文的意境。 事实上,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等值阈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原文的风格和内容的再创造,使读者在此基础上感受到译文中那些变化莫测、复杂微妙的艺术氛围。译者不但要复现出原作的信息和内容,还要进一步重塑原文的艺术有机体,使原作者从译文里呼之欲出,与异域的读者对话。所以,译文可在保持原作意境美的前提下,突破表层结构而重新组合原文形象信息。例如,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一文以其语言精练、隽永含蓄的特点而享誉文坛: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而朱纯深的译文在传达原文信息方面,可谓恰到好处,不露刀斧之痕: The moon sheds her liquid silently over the leaves and flowers, which, in the floating transparency of a bluish haze from the pond, look as if they had just been bathed in milk, or like a dream wrapped in a gauzy hood. 译者没有机械地对译,而是摆脱了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采用简化法,用which引导的关系从句,将原文中的三个句子合而为一,使译文句意显豁且文采顿生。 3.3结合原语文化语境意义展示异域文化色彩美 译者作为一个不同于普通单语读者的特殊审美主体在进行审美客体表象内容的内在化过程中,会受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制约,在对文本意象进行转换时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各种表象、形象地比附和移植(姜秋霞2001)。因此,译者必须能够揭示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信息差异,避免由于译语与原语的文化先决条件发生冲突,妨碍了原语文化语境意义的传达。不可否认,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中也会有一些契合现象,如《旧约•传道书》第一章里写道:Alltheriversrunintothesea,yetseaisnotfull和《淮南子•泛论训》中“百川归海而海不盈”如出一辙。然而,译语与原语的文化之间毕竟存在着“真空”地带,此时译者的审美经验需要在两种文化的同与异中做出选择,因此,译者必须在彻底领会原文艺术境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克服与其认知语境上的差异,使译者的审美经验与原作的审美基调相结合,方可真正体现原文的文化艺术感染力。如英国现代作家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有这样一段评论:Forthylifeshallfallasaleafandbeshedastherain.张谷若将其译为:你的生命如秋雨一样地淅沥,像秋叶一样地飘零(张谷若1984)。着一“秋”字,译文描绘出一幅秋雨绵绵、黄叶飘零的萧瑟画面,表现出译者对原作语言和其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底蕴的高度把握和细微体察。#p#分页标题#e# 四、结束语 总之,文学形象的翻译是译者对原语的重新组合和再度创造,是译者在原语制约下运用自己在语言、文化、艺术及审美等各方面的底蕴和修养实现文学形象的“第二自然”创造的过程。为了避免由于认知语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语义转移和文学形象的变异现象,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学形象语言“第二自然”创造中的等值阈,译者必须在彻底领会原文艺术境界的基础上,在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思维状态中,灵活变通地选择语言来表达原作中形象语言的神韵之美、意境之美和文化之美。但是,在文本客体与主体心理相互作用过程中,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终究不能摆脱客观逻辑性,“如果原作是一朵莲花,译作也应是一朵莲花。诚然,世界上没有两朵完全相同的莲花,但莲花与莲花的共性是多于异性的。如果译作不是莲花而是水莲花则不同了。固然水莲花也是美的,但它却是不同的物种了”(赵彦春199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