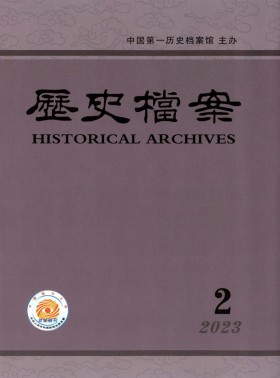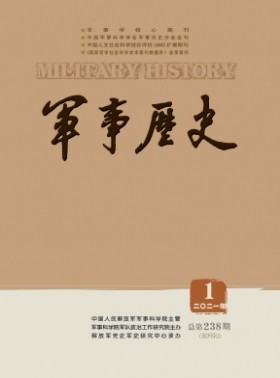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与文献关联论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刘宝楠说:“文谓典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刘师培的《文献解》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由此可知,“文献”是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说,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等,一言一语,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这里,“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直到今天仍然适用。本文所说的“文献”即指一切历史性的文字材料。我国的文献丰富而浩瀚,有如历史文献中的正史,正史之外的诸史,如别史,杂史,野史,又有如文学文献中的群书,如诸子,诸诗集,文集,词选,曲选,传奇,笔记小说等,都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人情风俗等做了或正面或侧面,或直接或间接,或主观或客观的反映,中国历史的点点滴滴和中华精神的方方面面都深深蕴含其中。历史文学家要感知历史的脉动,把握历史的精神,就不能不凭借文献的支撑。
六十年代初期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中曾出现过这么一种观点:“历史剧要求可以无需凭借历史记载、历史根据,而是借助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去综合生活,塑造出符合历史发展可能性的人物形象来,这样达到历史真实”,[1]“历史剧完全是古代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从剧作家的立场观点出发,根据历史真实性和可能性的法则,经过分析、研究,发掘了历史发展规律,创造出比实在人物、事件更完备的典型。”[1]对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吴晗曾尖锐地指出:“既然不根据历史记载、历史根据,那你又为什么一定要把所创作的东西叫历史剧呢?……既然不要历史记载、历史根据了,这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可能性和人物形象从哪里来呢?如何借助呢?借助什么呢?……既然历史记载,历史根据都不要了,那么,分析、研究一些什么呢?还有单凭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否就可以发掘历史发展规律呢?”[2]又有人说,过去的历史记载“就其实质来说,是不真实的、被歪曲了的。”[3]针对这种观点,吴晗说,“如果没有这些史料,我们今天连黄巾、赤眉、黄巢、李自成……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了,所以尽管是反面的史料,也还是无价的史料”。[2]“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多少年工夫,读了一千几百种史料,这些史料很少是人民写的,大都是封建史家写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伪造’而不去利用它。”[2]所以,尽管我国古代官修史书中不乏变乱是非、曲笔阿时之作,但它仍然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反映,是历史文学家认识历史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因此,我们只有充分掌握和消化了丰富的史料,才能在史料的总和中,看出历史的大势;在史料分析中,明察历史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感知历史的发展法则,才能使历史文学创作表现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才可塑造出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形象。
二、文献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原料宝库
历史文学如果不借助于文献记载,那么对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的判断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会无所凭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作出的作品就不可能或难以达到历史真实,更难成为上乘的、传世的佳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有关历史材料和历史记载进行广泛地占有,细致的研究、筛选、分析,有效的利用、加工的结果。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不仅考诸陈寿《三国志》、朱熹《通鉴纲目》、习凿齿《汉晋春秋》,更吸纳了三倍于陈寿《三国志》的南朝裴松之注,搜辑旧闻,甄别史实,增广异闻,矫枉补正,还博采了北宋的“说三分”和南宋及元代的说书、杂剧,同时,亦充分借鉴了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正是他熟谙历史,精于传说戏曲的搜求,加上他天才的再创造,才成就了不朽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文献不仅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间接反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世界的真实流露,也同样是历史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宝库。《隋唐演义》即是杂采唐五代乃至于宋人的笔记小说而成书的。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指出有关隋炀帝的事见于《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这些文学文献;又说“其叙唐宫事,皆杂采刘饣束《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柳珥呈《常侍言旨》、郑綮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鸿之《长恨歌传》,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再有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杀仓官王后土以息众怒和斩杀近侍,刘备骑“的卢”跃檀溪,关羽刮骨疗伤都取袭于唐传奇《独异志》。
传诵不衰的《长生殿》更是对文学文献进行了充分、有效的利用,诚如洪升自己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说:“史载贵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实际上,他不仅参阅了《长恨歌》、《长恨歌传》、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等诗文小说及说唱材料,而且还借鉴了元白朴《梧桐雨》、明屠隆《彩毫记》、吴世美《惊鸿记》等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进行了新的艺术处理,使作品的主题发展了,李、杨两个艺术形象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舞台上。举例来说,陈鸿在《长恨歌传》中采用“不饰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直言唐玄宗“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的丑闻,并且提出自己的劝惩主张:“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可以看出陈鸿是将杨贵妃当作祸国的“尤物”看待的。白朴《梧桐雨》对于杨贵妃的批判更加严厉。剧中,她既贪图享乐,行为放荡,又矫情虚饰,邀宠固宠。特意设置的马践杨贵妃的情节,足以表示白朴对杨贵妃的批判、鞭挞之情。白居易《长恨歌》,对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杨贵妃的恃宠致乱的批判则次于对李杨恩爱缠绵、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痛的渲染,表达了作者深深的惋惜和爱怜之情。……所有这些都被洪升熔于一炉,可以说,《长恨歌传》、《梧桐雨》的批判主旨被吸收了,《长恨歌》的爱情主旨更被取纳了,批判和同情、讽谕和惋惜、政治和爱情两个主题并行不悖,既表现“乐极哀来,垂戒来世”之寓意,又极写“钗合情缘”之缠绵。对于杨贵妃“一洗太真之秽”,把杨贵妃塑造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具有鲜明性格的形象,把《长恨歌》所渲染的“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魂追魄寻的爱情推向极致。其成功,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文献。#p#分页标题#e#
三、历史文学拓展了文献的功用
历史文学对文献的运用,是对文献价值的肯定,同时,又是对文献功用的拓展。首先,历史文学对历史文献的精慎选择,创造性的运用,使历史文献就不仅仅只是历史史事的记录和撰述,不仅仅只是对历代君王的歌功颂德,也不仅仅只是贵族士大夫的言行记注。其中的一条条史料,一个个细节,在历史文学中复活起来,充满情感,富于生命,服务于“我的”观念中的、符合那个时代社会背景、人情风俗的典型人物形象,发挥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作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大都就原型利用文献进行铺张敷衍,简略的充实,分散的集中,使忠者更忠,奸者更奸,善者越善,恶者越恶,小胜成大胜,大败成小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刻骨铭心的艺术典型。历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志吞四海的、值得肯定的政治家,在《三国演义》中他成了“奸雄”的典型。关羽,历史上是一个勇武人物,《三国志》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中的关羽只有一千字,写了他五六件战事。演义中关羽则被修饰了。首先,他作战勇猛,善于对阵厮杀,如: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三鼓杀蔡阳,斩颜良、诛文丑等。其次,他忠义无比,如:桃园结义、千里送嫂、居曹思汉、华容道义释曹操等。因此,关羽就不仅是一个武艺绝纶的勇将,而且还是一个忠义的典范。与此同时,对他的刚愎自用、自负骄人,则写得含蓄委婉。正因有了作者的文献重组,刻意创造,才有了白脸曹操,红脸关羽,且妇孺皆知,爱憎分明。
在情节冲突上,合理选择文献,构成了张驰有致、高潮迭起的矛盾冲突。《桃花扇》可谓典型矣。此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4]从第一出《听稗》到第八出《闹榭》,在侯、李爱情风和日丽中,写出复社文人的神采飞扬,阉党余孽阮大铖的穷途末路。自《却奁》始,以侯、李的分离及李香君的坚贞不屈,构成《拒媒》、《守楼》、《寄扇》、《骂筵》重场戏,揭示了昏君奸臣的饮宴作乐,从宫殿之内的弦歌四起反衬南明飘摇欲坠。以侯方域的行迹为线索,包括反对拥立福王,调和“四镇”冲突,劝谏高杰不成,高杰被许定国谋杀等情节,从宫廷之外写了将军大臣的鸡争狗斗,揭示了南明的大势已尽。从《逢舟》到栖霞山重逢,浓缩了南明王朝覆灭的必然与定势。正如孔尚任所宣称:“《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5]以“珠”串联起南明兴废事。
在塑造人物、提炼情节方面往往是表现作者创造力和想象力最多的地方,上举两例即可说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创作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有所图的。郭沫若在谈历史剧的创作动机时,指出动机有三种:“一种是再现历史的事实,次是以历史比较现实,再其次是历史的兴趣而已”[6]。因为动机的先导,作者在塑造人物、提炼情节、集中冲突上就必须围绕其动机而选择文献。其次,史料的残缺、错讹,古人的精神面貌、性格气质等,因史书的缺而不传,就又为作者想象力的表现提供了可能。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对此作了十分精当的论述。其一,他认为,“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7]所谓“造”,就是虚构和创造。由于史料的残缺,使这类作品有进行虚构、创造的余地。其二,他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7]一个是只好“搁笔”,一个却因此而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所以,历史文学作者或实录史书,摘抄章节,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或铺排敷衍、添枝加叶,既为其创作目的服务,又有意无意地丰富了文献的内容,拓升了文献的价值。
其次,历史文献的广泛系统运用,也使得广博的、只有硕儒博学才能通读的历史通俗了、普及了,从而达到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吴沃饶《历史小说总序》:“秦汉以来,史册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论士子购求匪易,即藏书之家,未必卒业,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蠹腹,古代精华,祝等覆瓿,良可哀也。……下走学植谫陋,每思补救而苦无善法。隐几假寂,闻窗外喁喁,窃听之,舆夫二人对谈三国史事也,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大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编者矣”。三国历史知识广为群众熟知,《三国演义》功不可没。可以说,中国百姓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多从历史演义和历史剧中来。关于隋唐知识,是从《隋唐演义》、《说唐》两书中得来。对宋代抵御外敌的了解,是从《杨家府演义》和《说岳全传》中来的。从《东周列国志》到《洪秀全演义》,连编贯通,汇成了一部老百姓的历史教科书。应该说,历史演义较之历史剧更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优势。因为戏剧受时间、空间、人物的限制,不便搬演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历史知识。象东周列国这样上下五百年的历史,以剧的形式出现只能一个个片断进行,例如,《浣溪纱》只表现吴越争霸中西子沼吴的一个侧面,《赵氏孤儿》只表现了《列国志》中的一二回。《桃花扇》只侧重了1644年至1645年一年间的旋立旋灭的南明历史。演义没有这如许的限制。几百个人物,数千里地域,千百年历史,都可自由驰骋,兼容并蓄。有了好的历史演义和历史剧,盲瞽村妇对祖国上下几千年能娓娓而谈。袁宏道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了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8]可观道66新列国志叙》中也说,有了历史演义,“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诫,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以上所述,无不对历史文学俗化历史、普及历史知识作了肯定。
四、历史文学丰富了文献宝藏
中华文献典籍之丰富是举世闻名的,它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载体,受到世人的称誉。有人将文献典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创性文献,一类是演绎性文献。原创性文献是不依任何文献为依傍的全新创作,如《论》,《孟》,《诗经》,《楚辞》之类。演绎性文献又分为两种,一是诠释体,一是演义体。二者均是以一定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的再创作。历史文学自然是演义体文献,它在中华文献史中占据相当大的位置,特别是自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产生以后,它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的宝藏。首先,它增加了文献的数量。就历史演义而言,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肇始,延至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历史文学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迎来了它的首次高潮,产生了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熊大木的《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宋志传》,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徐谓的《英烈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钟惺的《有商志传》、《有夏志传》,无名氏的《承运传》等等。至于历史剧,仅《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中涉及到的就有201种之多。[9]三国戏亦有40种之富。至清代,传奇兴盛,又有《长生殿》、《桃花扇》这类享誉千古的鸿篇巨制。正如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所说:“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其可称为历史剧者,居过半。”数量之富,不言自明。其次,丰富了文献的种类。从现存历史文学看,其本身就包括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电影,历史电视,史诗,咏史诗等多种体裁。#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