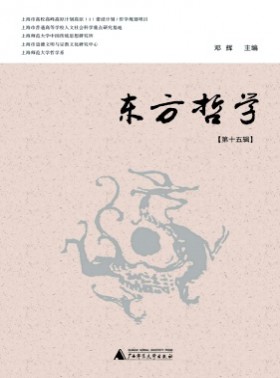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1
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学科划分,理论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实践哲学的目的在于行动。最高的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being as being)的知识,而实践哲学研究的则是何为最高的人类之善即幸福以及如何求得幸福。按照这种划分,似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不论在对象上还是概念上都没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以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成了无可置疑的前提。既然理论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存在”(being,或“是”),实践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善”(good),那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根本区分就在于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分。近代以来的实践哲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大相径庭,但在区分“是”与“善”的问题上,元不遵循亚里士多德,将“是”与“应该”、知识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截然分开。
事实真的如此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分科体系中真的只能分而不能合吗?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结合点,使得理论哲学能够为实践哲学提供一个可靠的规范性基础呢?实际上,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划分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被划分开的双方的确存在着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这个结合工作并非由亚里士多德自己而是由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托马斯·阿奎那完成的。那么,阿奎那是如何论述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在分别作为两者核心概念的“是”(存在)与“善”上存在着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呢?
一、亚里士多德区分“是”与“善”的理由及其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是”与“善”的区分主要是基于对柏拉图的批判。他认为,实践哲学所考虑的“善”,应该只是“属人的善”(human good),是人类可实践的善,而非那超越一切的善的理念。
柏拉图提出,善的理念高于一切可知的事物,也就是高于“是”。事物之所以能够以“是”相称,也是由于善。只有理解了善本身,才能理解诸事物之“是”,然后才能按照事物各自的“是”安排其次序,以成就实践中的正义。“作为最高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原则——同时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真的事物——善的相允诺了对哲学家统治的确证。那些把握了寻求现象后面最一般的原则的哲学家实践的人,最终会达到这个实质,这个实质能够解释每个事物的善是由什么构成的。没有关于这个相的知识,人们就不能连贯一致地思考道德问题,当然也不能为人生设计一种道德样式。”由于善的理念决定了诸事物的“是”,把握善的理念及其下属诸理念的知识,作为哲学家所特有的知识,就涵盖了对事物的实践的知识。如果有所谓的实践知识,它必然从属于对理念的理论知识。这样,实际上不存在一门专门的实践哲学,因为它跟认识理念的理论哲学别无二致。
因此,要想论述一门特殊的实践哲学,首先必须清除掉善的理念对于实践知识的优先性。实践哲学研究的善,不是那个产生诸“是”的善的理念,而是在诸“是”中所包含着的“诸善”,或者说是诸善中那个“最高的(或最重要的)善”。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念论的批判在于看到善的理念所隐含的一与多的矛盾。首先,如果善的理念是一,但按照范畴论,“善”可以述说所有范畴,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其次,如果善的理念是唯一的自在的善,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自在的善的事物,如荣誉、智慧、快乐,因此善的理念也不是那个唯一的善。这样,不论在范畴关系上还是在价值关系上,善的理念都不能作为普遍的、唯一的善。相反,与人的实践相关的善是多种多样的,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个可以实行的最高的善,即作为所有实践之目的的、完善的和自足的幸福。由于理论哲学所研究的“是”的问题与实践哲学研究的“善”的问题不可统一,实践哲学就独立地作为一门学科与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否认了存在一个单一的善的理念,但并没有否认善的普遍性。善并不局限于任何范畴,而是超越于所有范畴,如“是”一样具有类比意义上的同一性。但他并没有说这个类比的意义是什么,只说这个问题是另一门哲学即形而上学研究的东西,而他又明确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区分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说明善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述说所有的善的事物,那么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属人的善如何可以与其他类型的善相比较。因为他在讨论何为属人的善时,明确地运用了类比的方法,一方面将各种技师的善类比于人本身的善,另一方面又将其他生物的特殊的善类比于人的特殊的善。那么,如果不事先说明“普遍的善”的话,这些类比的依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要说明何为“普遍的善”,就离不开“是”的问题。要说明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就离不开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托马斯·阿奎那明确地完成了这个说明,并且按照“普遍的善”与“属人的善”的关系,以关于善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引出了关于善的实践哲学即伦理学。
二、普遍的善:阿奎那“是与善的可互换性”论证
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相衔接之处,有一点必须明确:形而上学中所谈的善必须是可实践的,即既要保证普遍善的优先性与超越性,又要保证它在人的行为中的可行性。面对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两大传统,阿奎那一方面虽然承认善在范畴上的多义性,但更强调善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承认善的超越公共性(transcendental commonness)的同时,否认善具有单一的形式或本质。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评注》中,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如同存在一样拥有多义性”解释为,善与存在两者可以互换(bonum eumente convertitur),即二者具有同义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在范畴上的多义性使得对善的研究应该分为不同的科学,作为实践科学的伦理学只能研究对人而言的善。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人认为,万物均以善为目的”,强调尽管万物所欲之善不是同一个善,但就善的本质在于其为万物本性之所欲而言,善就不能再被还原为其他实在,它本身必须是第一实在(the primary entity)。由此,善就是超越性的,它超越了一切范畴或种属的差别,成为万物共有的超越属性,这样就出现了“普遍的善”(thegood in general)。对这个超越性的普遍善,与“是”一样,只能用一般的科学,即其对象为“是之为是”的科学——形而上学来研究。这一步是阿奎那改造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观念走出的关键一步,使得他的伦理学出发点不再是对流行意见进行辩证探究,而是关于善的形而上学。
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首先讨论了善与存在的可互换性的问题。他的论证可以简单分为这几个步骤:(1)以可欲性(desirability)来定义善的概念;(2)将可欲性等同于完善性,因为完善是事物的目的之所在;(3)事物之完善在于使其存在实现(actual),因为其潜能尚未实现的事物是不完善的;(4)由此,善与是在实在中同一,因为是(to be,esse)就是事物的实现(actual-ity,actualitas)。这样,阿奎那完成对“是即善”这个命题的论述,下面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阿奎那抛弃了柏拉图把善作为万物模仿的唯一理念的说法,但也没有陷入亚里士多德只研究属人之善的狭隘范围。尽管万物各有其善,但这些善有着超越的共同性。与“是”一样,善本身是类比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分门别类地研究善的问题,阿奎那通过“善——可欲性——完善性——实现——存在”这样的链条将善与是串在一起。善表现为是的超越属性,就是可以在意义上与是互换的存在论之善(ontological good-rleSS)。但存在论之善必须是可实现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超越性的原则。关于这一点,阿奎那论证,存在与善尽管在实在中为一,但在概念上不同(善表现的是存在的可欲性方面),所以在表述一个独立事物时有所不同。存在有一个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一事物作为“某种”东西而单纯地存在(t0 have being simply),当它的个体特质获得进一步的实现,使其成为相对地存在(to have be,ing relatively),即获得其本质的完满。善也是如此,但其表述恰好相反:单纯的善指的是事物的终极完满状态,而相对的善则指事物的最初存在,即单纯拥有某种存在的状态。用两个等式来表示:单纯存在=相对善;相对存在=单纯善。在经院哲学中,事物之实现分为两个层次:一物所赖以形成的特殊的形式(the specific form)为它的第一实现(the first act)或初级实现(initial actualiza-tion);该物之特殊能力或禀赋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实现自身的完善,此之谓第二实现(the secoHdact)或完整实现(complete actualization),第一实现以第二实现为目标。也就是说,单纯存在(即相对善)作为第一实现,为第二实现提供了基础,有待进一步发展为相对存在(即单纯善)。这样,一事物的善就内在于其自身存在与实现之中。
这样,阿奎那完成了存在与善的可互换性的说明。作为形式和本质之实现的存在,并不是理念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具体事物的自身完善。而且,这个实现和完善是在从单纯存在到相对存在、从相对善到单纯善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这个说明一方面坚持了柏拉图主义中善与存在的关系,树立起善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到存在的实现过程,体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善的问题上的实践性原则,这可以说是对善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一个完美的解决。这是阿奎那的元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但是,确立起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元伦理学并不意味着伦理学的完成,关于人的实践之善的问题还有待说明。
三、阿奎那论普遍的善到人之善的过渡
阿奎那在讨论属人的善时,一开始就把人的善涵括在事物的善之中。他说:我们必须像讨论事物的善恶那样来讨论行为(ac-tions)的善恶,因为事物之所是,也就是它所产生的行为(act,实现)。因此,人的存在就在于人的本质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人只有在行为中实现自身的完善。由于存在与善的可互换性,人之善就在于获得其存在。必须注意,阿奎那已经区分了人的行为(acts of a humanbeing)与人(human acts),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属人的行为,才是伦理学讨论的对象。
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集中讨论了人的善恶问题。在这里,“存在与善可以互换”这个形而上学和元伦理学中的核心命题,被拿来作为将人与事物的存在、人的善与事物的善相比拟的依据。以下简要说明阿奎那如何将存在论上对善的讨论应用到伦理学上来。
(1)除了上帝,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善都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任何事物若拥有其应有的存在之完满即善,否则即为缺乏善,也就是恶,尽管它拥有某一方面的存在。由于存在与善的可互换性,任何行为就其实在性而言都拥有存在,就意味着拥有某种善,但是由于它尚未尽有其应有的存在之完满,即为缺乏某种善,即是恶的或有缺陷的。可见,行为的善恶,同自然事物的善恶一样,都在于是否拥有其应有的存在。这是对行为之善恶的存在论上的说明。
(2)关于行为善恶的源头,阿奎那同样运用存在论的结论作为论证行为善恶的依据。如同自然事物的善就是它所欲求的对象,人的行为的善也在于其对象。事物存在之完满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其“种”(species),即事物的形式,而行为的种则来自于其对象;正如自然事物的善来自形式,行为的善就来自它的适当对象;正如自然事物首要恶在于没有实现它的特殊形式(specific form,种的形式),那么,行为的首要恶也来自其不适当的对象,这种恶被称为“属上的恶”(evil in its genus)。
(3)既然自然事物的整体完善不只在于其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也在于那些必要的附属偶性,正如人的完善与其形体、能力等相关,这些偶性如果不成比例,也会产生恶,行为也是如此。行为的善不仅仅在于它的种即对象,还在于个别行为所涉及的特定的附加物,即行为的适当环境,缺乏其所要求的适当环境的行为就是恶的。这一步对于善的可实践性至关重要,因为它考虑了个别行为所发生的具体境遇,而不仅仅抽象谈论行为的类型。
(4)对于非独立存在的事物,它的存在有赖于动力因和形式因,而它的善则有赖于目的因(final cause)。人的行为,与其他事物一样,它的善依赖于他物,判断其善的标准则来自行为者有意的目的(the end intended)。
阿奎那总结了人之善的要素:(1)就行为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言,即具备了属的(ge-nerlc)善;(2)行为的适当对象,即行为的种的(specific)善的来源;(3)行为的环境,是它的偶性;(4)行为的目的,即其善的目的因。这里所列举的要素中,首要的是作为存在的行为。根据存在与善可以互换的原理,任何行为,只要是个“存在”,就具有某种善,这种善是存在论上的而非实践上的善。因为实践行为是意愿的行为(voluntary act),它的首要因素应该是行为的对象,所以实践的善由行为的种(species)所确定,这种善不同于存在论上的善,也不能还原为后者。很明显,在论证实践行为的善恶问题时,阿奎那根据人与自然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运用了类比的方法,正如在Q.18,A.1开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像谈论事物中的善恶那样来谈论行为中的善恶,因为人的实践行为也是一种存在。他根据两者共有的属、种、偶性与目的来同样界定事物与行为的善恶。可见,这里关于人善恶的伦理学论证,是关于存在论上的善即超越性的善的说明和存在与善的可互换性论证的应用。
至此,在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善”的问题上,阿奎那铺设了将形而上学命题应用到伦理学之上的道路。一般认为,阿奎那关于善的理论为道德理论提供了基础,而他的道德理论通过对自然的属人的善(natural human good)的说明为道德规范提供了基石。所以,只要我们知道了人性(humanity)的特殊结构,就可以通过洞悉何种行为符合或者不符合它,而对实践行为做出评判。理论思考与道德实践所共有的超越性基础(即存在)表明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联,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建基于关于道德实践的实际经验,它要求对实践基础进行哲学的反思。这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根本原理在“是”与“善”这两个概念的结合中沟通起来。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哲学教育;实践本质观;实践人本观;结合
一、的实践本质观和的实践人本观
(一)的实践本质观
1旧哲学本质观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本质观有客观主义本质观、主观主义本质观和人本主义本质观。
旧唯物论哲学的客观主义本质观从客体、客观性方面探寻事物的本质。唯心论哲学的主观主义本质观从主体、主观性方面探求事物的“自为”本质。人本主义本质观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起源于洛克,中经爱尔维修,到费尔巴哈达到典型形态。洛克认为人们关于物体的第二性质(色、声、味)的观念是凭借物体的第一性质(大小、形相、数目)的能力在人的心灵中引起的观念。爱尔维修以人为中心,用对社会是否有利衡量个人行为本质的善与恶。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典型,他认为人和自然一样是第一性的东西。
2的实践本质观
马克思的实践本质观是指哲学的本质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在实践思维逻辑中,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事物的实践本质的不断展开过程。实践本质说明“事物”是社会历史的存在,是在实践关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本质观确立了实践对于本质生成、发展、认识的重要作用,找到了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又反作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使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事物实践本质的方法论。
(二)的实践人本观
1旧哲学人本观
之前的旧哲学人本观脱离人的实践本性,不从人的实践本质去思考和理解人,主要有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和人本思维方式人本观。
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是把人和世界万物都看作是上帝创造的或自然生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用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的存在和本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于自然本性或理性。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认为人不是上帝和自然创造,其本质在于人是“自我意识”或“理性”的产物,甚至认为人本质就是思维或者精神。
2的实践人本观
哲学的人本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人本观,从实践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考察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指出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整个历史决定性,必须从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去说明人的本质。实践人本观不但肯定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还注重在社会关系中考察、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
二、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
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产生是同一过程,实践本质观的最终形成依赖于实践人本观的形成。哲学的属人世界观理论必然承认属人事物的发展,属人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属人事物“本质”的变化,人的发展也必然是人本质的发展,要遵循属人事物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在哲学教育中,要做到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相结合。
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是指在哲学教育中要把握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在实践本质观教育中体现实践人本观,在实践人本观教育中体现实践本质观,从而使受教育者懂得实践本质观是实践人本观的内在要求,实践人本观是实践本质观的深化和在“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做到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首先是在实践本质观中体现实践人本观,人所认识和改造的事物是实践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所以在实践本质观中肯定事物的本质必须肯定人及其实践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实践人本观教育中还要体现实践本质观。要真正理解实践人本观,必须找到形成实践人本观的基本方法和途径,这就须对实践本质观有正确而准确的把握。
三、运用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背离实践理解本质观的问题
实践思维方式是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在“本质”问题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实践本质观是哲学关于属人事物及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也是科学的方法,所以要把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哲学教育要坚持实践人本观,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实践本质观的重大意义,向学生讲清实践本质观的内涵和创新价值,使学生理解、接受实践本质观的理论和方法。
2不从实践理解人本观的问题
目前哲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还未能解决教育层面的偏差问题,主要是强调哲学教育的工作价值,用统一的教学模式束缚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不能主动地得到发展,反而变得因循守旧,盲目排斥这种哲学教育,结果适得其反,这种教育偏差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不了解人的实践本质。
3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脱离的问题
实施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统一的教育方法,就是在正确传授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基础上,把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的结合。既要用实践人本观作为坚持实践本质观的一个范例,使学生理解实践本质观的方法和原则,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事物,去分析、解决各种问题,又要用实践本质观的科学内涵,帮助学生理解实践人本观,自觉认识人的本质的形成、发展,进而科学理解人生实践、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等相关问题。
在哲学教育中的方法和问题还有很多,在进行哲学教育中,要遵循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哲学的教育活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克服传统旧哲学的缺陷,从实践进行哲学教育。
参考文献
[1]倪志安等哲学原理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 高三学生 焦虑 自信心 归因方式
1.引言
焦虑是一种“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困难,致使自尊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强,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1]。适当的焦虑能使人们调动一切防御器官应付刺激,超常发挥潜能[2]。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断过程[3]。乔建中和朱晓红等人研究表明学习焦虑水平对归因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不同学习焦虑水平的学生对于成功或失败的学习结果有着不同的归因倾向,而且这些不同的归因倾向有着与学习焦虑水平相关联的激励后效[4]。高三生将要面临着人生中第一次做出重要抉择的压力,必然会产生焦虑情绪,他们努力拼搏,并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作出整体的判断,预期自己考取理想学校的可能性,即考取理想学校的百分数,而自信心很大地影响他们追求这一目标过程当中的坚韧性、意志力和自身潜能的发挥。
高三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焦虑水平、自信心与成败归因方式总体状况如何,焦虑水平、自信心不同的个体是否具有不同的成败归因方式,从而启发我们如何通过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激发适中的焦虑水平,提高自信心和心理健康水平,为处于关键时期高考生的教育提供指导。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宿州市的两所高中的高三学生进行了调查,为了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选择的是一所重点高中和一所普通高中。本次调查共发放290份问卷,回收261份,有效问卷251份,回收率是90%,有效率是96.6%。被试的人口学特征如表1。
2.1.1采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游洁编制的《归因风格量表》[5],它包含8个题目,4个纬度,分别是能力归因、努力归因、运气归因、任务难度归因,采用七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计1分到非常符合计7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偏向该方面。本次调查中,努力归因因子a=0.752、运气归因因子a=0.810、任务难度归因因子a=0.801。
2.1.2采用的是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本量表有20个项目,采用四级评分,该量表有很好的信效度,并对所得量表分数从低到高划分成三种水平,前28%的为低焦虑,后28%的为高焦虑,中间的则为中焦虑。
2.1.3学生自评考取理想学校的百分数,0%为完全没有信心,100%为非常有信心。并对所得信心百分数从低到高划分成三种水平,前28%的为低自信,后28%为高自信,中间的则为中自信。
2.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3.结果分析
3.1高三学生的归因方式、焦虑和自信心的总体情况与差异比较分析。
注:能力(IS)、努力(IU)、任务难度(OS)、运气(OU),*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由表1得出,高三学生归因方式中努力归因显著大于能力归因,能力归因显著大于任务难度归因,任务难度归因和运气归因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我们发现高三生焦虑量表的标准分的均值为40.26,考取理想学校的自信心均值为75.47%,两者在是否在重点班、应历届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3.2不同应历届的高三学生在归因方式上的差异比较。
分析得到,成功时,应届生、历届生在努力、任务难度、运气归因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p<0.05,p<0.05),且历届生比应届生做更多的付出努力和运气好的归因,应届生比应届生做更多的任务难度低的归因。另外,我们也发现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努力归因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4.732,p=0.031<0.05),且文科比理科做更多的努力方面的归因;在性别、是否为重点班因子上归因方式无显著差异。
3.3不同焦虑水平与归因方式的方差分析。
由表3得出,成功时,不同焦虑水平的学生的任务难度归因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失败时,任务难度和运气归因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而且低焦虑者比高焦虑者更倾向于作出任务难度、运气的外部方面的归因。
3.4不同自信心水平与归因方式的方差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不同自信心水平的学生在成功时在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归因方面存在显著或非常显著的差异(p<0.05,p<0.05,p<0.001),失败时的运气归因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1)。
4.讨论
从高三生总体归因方式可以看出,高三生的归因方式已较为成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倾向于做努力方面的归因,而很少做运气和任务难度方面的归因,而大部分的研究也都表明个体在初中阶段,归因模式就逐渐趋向成熟,例如,王敬欣的一项研究表明,初中学生已认为努力和能力是影响学业成败的重要因素[6]。高三生总体的焦虑水平处于适中水平,自信心较高;但也有少数同学自信心很低,焦虑水平也很低,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学生几乎是自暴自弃,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追求,家长和学校要及时地发现并加以引导。另外,是否在重点班、应历届并没有对焦虑水平、自信心水平的高低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重点班的学生所制订的目标较高,而非重点班的学生相对较低,所以他们所感受到的焦虑水平和对理想学校的自信心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历届生虽然经历了一次或几次的失败,但他们相信凭借以前的基础和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应届生没有经历高考的失败,他们相信自己能取得成功。
成功时,历届生做更多的努力和运气好的归因,应届生做更多的任务难度低的归因,文科比理科做更多的努力归因。我们认为历届生一方面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运气,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文理科学生之间的差异则源于文科涉及面广,注重知识的长期积累,强调形象思维和感性认识;而理科知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强,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认识;形象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基础,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升华。所以文科生要想取得成功,就要长时期不断地努力,而理科生则更重视逻辑思维能力。
不同焦虑水平的学生在成功时的任务难度归因存在显著差异,失败时任务难度和运气归因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乔建中、朱晓红等人在学习焦虑水平与成败归因倾向关系的研究中有很大的差异[4]。总体来说,低焦虑者比高焦虑者更多地寻求外部归因,同样邹敏在针对初中生的考试焦虑研究中也发现了低焦虑者更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能力、任务难度[7]。正是个体更多地做出外部归因,而导致感知的压力较小,并体验为低焦虑,这也是个体保护自尊的方法。外部归因是不成熟的归因方式,不利于激发高焦虑者的积极主动性,所以高焦虑者要有意识地多做努力方面的归因,一方面可以培养正确的归因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焦虑水平,提高学习效率。
不同自信心水平的学生在成功时的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归因存在显著差异,即高自信者比低自信者做更多的能力高、付出的努力多的归因,低自信者比高自信者做更多的任务难度低、运气好的归因;失败时,低自信心者比高自信者做更多的运气差的归因。即高自信心者做更多的内部归因,低自信者做更多的外部归因。所以教师和家长要积极地引导学生做努力和能力,特别是努力方面的归因,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为高考的发挥和今后的人生奠定良好的心理素质。
5.结论
5.1总体上,高三初期的学生焦虑水平适中、自信心较高,总体归因方式比较成熟。
5.2成功时,文科比理科做更多的付出的努力多的归因;历届生做更多的付出的努力多和运气好的归因,应届生做更多的任务难度低的归因;失败时两者无明显差异。
5.3焦虑水平影响高三学生的成败归因方式,而且在成功与失败时表现不同。具体表现为:成功时,高焦虑者做更多的任务难度低的归因;失败时,低焦虑者做更多的任务难度难和运气差的归因。
5.4自信心水平影响高三学生的成败归因方式,而且在成功与失败时表现不同。具体表现为:成功时,高自信心者做更多的能力高、付出的努力多的归因,低自信心者做更多的运气好的归因;失败时,低自信心者做更多的运气差的归因。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
[2]赵云红.生命与焦虑.硕士论文.开封:河南大学,2003:12.
[3]章志光,金盛华.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53.
[4]乔建中,朱晓红.学习焦虑水平与成败归因倾向关系的研究.南京:南京师大学报,1997.1.
[5]游洁.大学生归因风格、价值观和寻求社会支持与帮助的关系研究.硕士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6]王敬欣,张阔.初中学生的学业归因、自我效能、考试焦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心理研究,20081,(1):89-91.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4
【摘要】 目的 对比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简称血灌)、血液透析(简称血透)两种治疗方式对维持性透析患者事件相关电位P300(简称P300)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选条件的64例须行维持性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衰竭(ESRD)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血灌组30例,血透组34例,分别测定两组治疗开始前、6个月后P300的潜伏期、波幅,并与45例健康体检者进行对照。结果 治疗前ESRD患者的P300潜伏期显著长于对照组,波幅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治疗6个月后两组指标均显著改善(P
【关键词】 血液灌流;血液透析;终末期肾衰竭;事件相关电位
终末期肾衰竭(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是较为严重的一组临床综合征,须行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等替代治疗手段来维持生命。ESRD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发病率很高,可达65%以上,常存在记忆力减退等认知能力下降。既往的研究表明事件相关电位P300(简称P300)可作为评价ESRD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变的指标[1],但不同的血液透析方式对维持性透析患者P300的影响如何国内未见报道,对此我们进行了初步研究,现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选择2003年10月~2008年12月我院肾内科新诊断的ESRD须行维持性透析患者,符合诊断标准[2],其中男42例,女22例,年龄18~45岁,平均年龄(27±7.8)岁,病程1~5年,所有患者听力良好,无神经精神病疾患史,锥体束征阴性。将64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血灌组30例,其中男20例,女10例;年龄18岁~49岁,平均年龄(27±7.4)岁;原发病为慢性肾炎15例,IgA肾病8例,多囊肾3例,梗阻性肾病4例。血透组34例,其中男22例,女12例;年龄21岁~45岁,平均年龄(28±6.9)岁;原发病为慢性肾炎21例,IgA肾病8例,多囊肾1例,梗阻性肾病4例。另取45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28例,女13例,年龄20~43岁,平均年龄(28±6.5)岁,所有志愿者听力良好,既往无神经精神病疾患史,内科及神经系统检查正常。各组间的年龄、性别及文化程度等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2.方法
(1)治疗方法 ①血灌组:费森尤思4008S血透机(德国Fresnius公司)、F6聚砜膜血液透析器(德国Fresnius公司,表面积1.3 m2,超滤系数5.5 ml·mmHg-1·h-1) ,丽珠HA130中性大孔树脂血液灌流器,碳酸氢盐透析,血液流速200 ml/min,透析液流速500 ml/min,双反渗水透析水,每周行2次血液透析(4.5小时),1次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树脂灌流器串联于透析器之前,待灌流器2.5~3.0 h饱和后,去掉灌流器继续血液透析1.5~2.0 h,低分子肝素抗凝(苏可诺2500单位/次)。②血透组:费森尤思4008S血透机(德国Fresnius公司)、F6聚砜膜血液透析器(德国Fresnius公司,表面积1.3 m2,超滤系数5.5 ml·mmHg-1·h-1)进行碳酸氢盐透析,血液流速200 ml/min,透析液流速500 ml/min,双反渗水透析水,每周透析3次,每次4.5小时,低分子肝素抗凝(苏可诺2500单位/次)。
(2)P300检测 ①检测指标:检测对照组及ESRD组P300的潜伏期、波幅。检测血灌组和血透组治疗前、后6个月P300的潜伏期、波幅。②检测方法:在屏蔽隔音室中进行,受试者保持觉醒状态及注意力集中,采用德国耶格公司生产的Neauroscrean Plus型肌电/诱发电位仪,按国际10/20统一电极安置法,记录电极置于Fz点,参考电极置于一侧耳垂,前额接地,电极与皮肤间阻抗10%则作废。最后取4次P300波的潜伏期(PL)及波幅(Amp)平均值,PL及Amp测定按杨文俊介绍的方法进行[3]。计算机自动分析P300波的潜伏期及波幅。P300的异常判断参考目前所选用的标准,以正常组的+2 s为潜伏期上限,以正常组的-2s为波幅下限,任一项超出正常范围均为异常。
3.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应用SPSS 11.0统计软件处理,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结 果
1.ESRD组与对照组P300的比较 ESRD组P300的潜伏期、波幅与对照组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讨 论
终末期肾衰竭患者临床上除有严重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外,可有多脏器功能损害,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发病率很高,可达65%以上,近年的研究表明,此类患者中亦存在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工作效率降低及思维不灵活等认知能力下降。事件相关电位P300主要反映人脑的高级心理活动(包括感知、理解、记忆、判断、情感等)[4],是诱发电位中潜伏期在300 ms左右的正相诱发电位,临床上主要用于各种原因引起认知障碍的病人,既往的研究表明血透可改善维持性透析患者的P300。本研究结果表明ESRD行血透治疗后P300的潜伏期、波幅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参考文献
[1]林洪全,李文华,韦武合,等.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事件相关电位P300的研究[J].临床神经电生理杂志,2003,12(2):78-80.
[2]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549.
[3]杨文俊.事件相关电位[J].新医学,1999,30(5):298-301.
[4]张 卓.事件相关电位在神经精神科的临床应用进展[J].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杂志,2005,14(1):48-52.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5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超级秘书网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