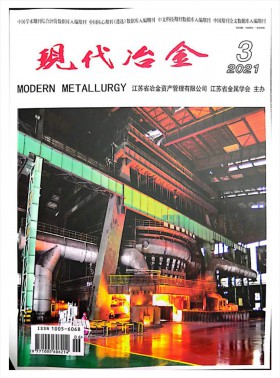作者:宋先红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历史作为精神活动的产物,较好地阐释了历史叙述与人对历史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历史小说采取的话语方式的最好的注脚。我们认为中国短篇历史小说话语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现代白话和短篇小说的呈现方式。这三个方面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得出来的。作为现代文学重要一支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外部形式上讲,它与历史文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是语体———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演变而言,就存在着由文言的史传文!半文半白的长篇历史演义!现代白话的现代历史小说的转变过程。而由“五四”白话文运动而引起的“文学革命”本身就是集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一身的思想启蒙运动。所以,从语体选择的角度来关注现代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文学语言的选择永远是一种政治事件,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观念外化”[1],但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书面语言与白话两种语体的区分,且这两种语体在使用者、使用者的历史认知、使用场合和功用等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区别。
1文言与正史书写
文言所代表的书面语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不为社会的全民所用,只有少数有特权和身份的人才能学习和使用它,而由它记录下来的典籍毫无疑问是它的使用者的思想产物并对后来的学习者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史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官修史书的传统,所以文言、历史、史官的封建正统历史认知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特殊局面。因此,探讨文言与正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分析封建正统的思想意识如何通过文言这种书写工具渗透到它的使用者──史官头脑中并通过正史的书写表现出来。
1.1仓颉造书的暗示:史官与书面语
《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初造书契。”后人由此断定:一,仓颉的身份是黄帝时的史官,二,汉字为仓颉所造。姑且不论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但是这则引文透露这样的一个信息:在中国古代,史官和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还可以说,只有掌握了文字才能作史官、记录后人所称的“历史”。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掌握文字并成为史官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状况看到:学习文字其实是少数人的特权。《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在叙诸子十家时,皆谓出于某官,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2]其实这里的某官,就是周代王官之所掌。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阐发道: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又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于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3]由此可见古代的文化要典都由百司之史掌握,所以有“百家之学,悉在官府”的说法,而能够接近要典并向百史之官学习者,也只有公卿子弟,所谓庶民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周代衰亡之际,王官失守,散为诸子百家,民间才得以师弟子的形式传授知识。私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但是他们授课的内容———也就是课本仍旧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六艺和诸子百家的典籍,而不是私塾老师自己的著作,孔子的“述而不作”应该是这个方面的有力证明。也就是说无论是官学和私学的授课内容都来源于以史官为代表的人所做的著述中。据此可以得出书面语的如下特点。书面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创造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书面语言的使用几乎成了一种特权和身份的象征。它之所以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与书面语言的以下特点有关:1)书面语言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与口语相比,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够获得,所以在人类物质水平不发达的一段时间内,它的获得和受教育机会一样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少数人几乎就是特权阶层和统治阶级的代表。2)书面语言可以通过媒介得以保存的特点使人类社会活动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流传下来,而人类社会活动如何书写就只能由上述少数懂得书面文字的人所决定。如果将文字书写当作声音的另外一种形式,那么后世听到的声音只有特权阶层或统治阶级的声音,而只会使用口语交流的大多数人的声音早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荡然无存。在这种意义上,书写能力就意味话语机会和话语能力,也意味着被历史记忆的可能性。3)书面文献作为后来教育所使用的资源,它所承载的少数人的思想同时被传达到受教育者那里,对受教育者起到一种浸润和同化作用,所以,书面语作为语言被受教育者学习的同时,它所承载的思想和意识也被接纳和吸收,并作为一种身份资本而一再得到尊奉和宣扬。在这种层面上说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就是某种思想的遵循者并不过分。从而,语体的不同选择就昭示着使用者不同的社会身份和不同的使用目的以及对事物的不同认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说“智力和语言只允许和要求有相互适应的形式”,虽然指的是不同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但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讨论同一种语言中不同的语体与使用者思想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文言只能为以史官为代表的少数人使用,这些使用者所受的教育乃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正统思想。这一点,可以从史家修史的原则和观点中得以明证。
1.2历史、文言与史官的封建正统历史认知
我国史书的写作滥觞于孔子删定的《春秋》和传为左丘明著作的《春秋左氏传》。经过后人阐发,“孔子删定《春秋》”是孔子“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礼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委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4]11可见孔子所撰《春秋》并不完全是鲁国历史的原貌,而是根据孔子“劝恶扬善”、“提倡王霸、王道”、“强调以封建等级次序为核心的‘礼’”的目的对原有历史进行重新编订的。《春秋》为后世史书的做法开了先例,同时孔子连同其他先秦的贤士用自己的学说“奠定了整个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论晚近历史》)。从先秦诸子大多“不用于世”的遭遇来看,他们的话语并没有在现实层面得到实现,这就有待于后世帝王用自己的权力来产生实际效应。官修史书就是实现这种话语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司马迁《史记》虽然是私家著作,表达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但它之所以获得正史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史记》在叙事、记载等方面的成就有关,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史记》从撰述目的到实践都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从他推崇孔子的话来看,他的“古今之变”还是以王道为依据的。从各下面史家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之废,王道之大者。”[5]荀悦《汉纪》:“夫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开辟草昧,岁纪绵绵,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原乎载籍制作业,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予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6]刘知己《史通•直书第二十四》:“况史之为务也,申以劝诫,树之风声。”[4]249刘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制第一》:“用使之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为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4]389司马光《资治通鉴序》:“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本,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7]官修史书作为各个朝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它的理想宗旨就是将这个“道”通过“撰述”的方式在历史中得以表达、并幻想帝王能借鉴学习历史成为“道”的完美体现者。中国各朝各代的明臣贤士也无一例外的都是“忠君”、“重道”的表率。几千年过去了,他们所遵的“道”还是“先王之道”,而且始终坚信有那么一个“道”可以贯穿历史,经天纬地。这样,文言、史书、儒家正统观念三位一体的局面也得以形成。文言的简洁、古奥、庄重、正式等特点也在经典的一再重复、历史的一再撰写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和确认。#p#分页标题#e#
2半文半白与中国传统长篇历史演义
文言与白话作为语体不仅存在使用场合的不同,也跟使用对象的知识层次和接受范围、接受程度有关。文言是书面语言,是和智识阶层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是老百姓的语言,是日常生活语言。要和老百姓沟通并要他们接受某一特定的观点或信仰,就必须用他们的语言。有人曾经讲过,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存在上下层、表里、雅俗分离的现象。在统治阶级上层、社会思想的表层和广大知识阶层,他们奉行的是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在普通老百姓、社会思想的里层,他们奉行的是一套功利的、世俗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着文言与白话两大不同的语言系统。所以,要想从上至下地推行某种思想或者获取更多的受众,推行者在迎合百姓口味的同时,还得调整所使用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世俗变文中以中国古代历史为内容的有:《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捉季布传文一卷》、《前汉刘家太子传》、《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舜子变》、《董永变文》、《秋胡变文》、《韩朋赋一卷》等。历史变文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它基于史实又不为史实所限,这种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笔法,使历史传说人物以有血有肉的面目呈现在变文中。这无疑影响了后世历史演义的写法。
宋代“讲史”在语言上对历史作民间倾向的改造,更多的是出于娱乐、商业利益的考虑并充分注意到受众的文化层次特点。“讲史”作为宋代民间说唱艺术“说话”的四家之一,和“小说”是最受听众欢迎的形式。它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城市里聚居的商人、小业主、手工业者、工匠、军士、吏员、伙计仆役等等构成的一个市民阶层。说书人在瓦肆里面对上述观众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如《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都是有文献根据的。如果说书人只是照搬史书,自然显得严肃、呆板,不受听众欢迎。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斗,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欲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他在这里说的是小说,但是面对相同的受众,其所论的“通俗”标准同样适用于“讲史”的说法。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大器(肖愚子)序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今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8]这里“言辞鄙谬”就是“讲史”的语言特点,虽然“士君子多厌之”,可是仍不妨碍普通市民对之青睐。历史演义是在“平话”的基础上,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修改创造,最后由文人编纂而成的。它一方面继承了“平话”民间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文人个人的创造而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它与史书和“平话”相比更具文学品格,也打下了作家个人在时代特点、世界观、历史观上的很多印记。可以说,历史演义是历史资源、民间文化、文人创作三者统一的结果,其叙事语言的半文半白是这三方面糅合的最好证明。
最早对《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作出说明的是明人蒋大器。他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来总括《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高儒《百川书志》则把《三国演义》的语言概括为“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是介于纯文言和口语之间的一种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它既与说话的产物有关、加工者的文人身份有关,也与“历史演义”这一文体有关。作为说话的产物,它的诞生地点是在热闹集市的瓦肆勾栏,所以它必须是口语的,是通俗易懂的。但演义的内容是历史的、而非现代的,与话本小说相比,为了造成一种“历史感”,使读者感到作品的语言“时态”和历史内容相一致,给读者一种“真实”的假象,必然离口语较远。生活在当时的文人将这两种语言进行了调控、折衷,创造出一种既适宜大众接受、又有适当历史距离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具体说来,演义中的表章、信柬、诏旨、正式应对等内容多引用原有历史文献,如《三国演义》“定三分亮出茅庐”、“诸葛亮智激孙权”、“白帝城先主托孤”、“孔明挥泪斩马谡”等章节中诸葛亮的语言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引用了陈寿《三国志•蜀国•诸葛亮传》中的有关章节。而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和渲染,则吸收了口语中通俗、极尽铺张和夸饰的特点。例如在《三国演义》第五回吕布大战刘关张一节中和第四十一回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上述两则文中,“了”、“抖擞精神”、“把马一拍”、“丁字儿”、“战不到”、“转灯儿”、“当时”、“只顾”、“不想”、“夺了”等都不是正统文言,而是当时的白话。那是不是历史演义的语言作了朝通俗化方向的改变,就意味着它的主题跟帝王将相无关呢,或是思想离百姓更近一层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演义着重演述的还是《三国志》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卓越事功,而且作者运用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对书中人物如曹操的奸雄、刘备的仁德、诸葛亮的智慧等等进行了大肆的夸张和渲染,以致“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状刘备多仁而近伪”,使普通老百姓以一种仰望的角度看待这些已经逝去、但曾经左右历史的人物,而进一步拉开自己和统治者的距离。其次,《三国志演义》的诸多主题中,儒家仁政思想是它的主导思想,不仅贯穿全部情节,而且贯通着对所有人物的评价。罗贯中就是用这个思想来处理千头万绪的三国历史人物的,他反复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基于此,《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摒弃了平话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使这段历史成为一个悲剧,但德却是全部情节的轴心。刘备集团广施仁义,其行为充分体现作者出作者仁义高于成败的观点。如在刘备败走江陵时,出现了十万民众随部队撤退、日行十余里的壮观场面。面对曹操精兵的追杀,诸葛亮劝刘备暂弃百姓,轻装前进,刘备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又如当关羽战死麦城,刘备不顾赵云等的劝说,感情用事,兴师报仇,其理由是:“朕不与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书中种种渲染、改动都是为了宣扬、赞颂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思想,不出《资治通鉴》等正史阐发的义理之外。#p#分页标题#e#
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在长篇历史演义的创作中虽然沿袭了“说话人”的口吻对叙事语言作了口语化的调整,使历史演义获得了娱乐性,但是创作主体———封建文人的正统儒家价值观念和他们对历史文本的固守,使他们不可能换一种眼光和一个角度打量历史。从语言的角度说,白话在他们眼里只是获取读者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象文言那样成为某种意识的承载者,或者说长篇历史演义的作者根本无意赋予白话某种区别于正统儒家观念的思想内涵。所以,半文半白的文学依旧是旧文学,白话再怎么向书面渗透,它始终是为通俗和娱乐的,而其中的思想意识始终是封建正统的和教化的。白话与现代意识的紧密结合还需要在现代短篇历史小说里得到真正实现。
3现代白话与现代短篇历史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集文学、语言、政治、文化于一身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名称上有“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不同的说法,但它实际上是以西方“民主与科学”观念为基础,以语言变革为切入点,最终表现在文学上取得极大成就的一次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的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自创刊之日起就通过译述和介绍大量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陈独秀、、易白沙等人先后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晨钟”之使命》、《孔子平议》等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礼教、旧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肯定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自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的解放运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语言为切入点,将语言变革和思想变革融为一体。文中胡适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之中,“一曰,须言之有物”和“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是内容方面的,而“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五曰,务去陈词滥调”、“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都是关乎语言方面的。而他在“不摹仿古人”这一项中,引人注意地提出了“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以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9]胡适在这里单单拈出“白话小说”作为“非摹仿之作”,一方面是他的文学进化论的思想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他在以后用文言/白话的语言形式区别死的文学和活的文学以及撰写《白话文学史》张目。一个月后,陈独秀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以更为激进的态度举起“文学革命”的大纛,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其中“雕琢的阿谀的”、“迂晦的艰涩的”、“明了的通俗的”是指文学的语言特点,而“贵族”、“国民”、“古典”、“写实”、“山林”、“社会”乃是就文学的思想内容而言,所以,他的“三大主义”就将文学、语言、思想的变革裹挟在一起。继而,钱玄同《寄陈独秀》(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傅斯年《文学革命申义》(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怎样做白话文》(1919年二月一日《新潮》1卷2号)、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平民文学》(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对此做出积极的响应,对新文学在语言建设和思想观念两方面发出了倡议。在现代文学语言改革的浩大声势中,鲁迅于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上成功的开山之作,表示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性就体现在新的语言形式、结构形式、思想特点上。同样是鲁迅以《补天》开始了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作。现代历史小说就是在现代短篇小说对体式和语言革新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有别于史传文体和传统长篇历史演义的创作之旅。现代白话本身的特点也许更能说明现代短篇历史小说与长篇历史小说的不同点和现代历史小说由白话形式带来的内在思想上的现代性。高玉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说:“新白话在形式上的确从古代白话而来,但它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它已经融进了大量的欧化的术语、概念、范畴,是一种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话语方式。”[11]用这样的白话写历史小说,带给我们的必定是建立在新的语言形式之上的新思想和新视野。现代汉语是口语、西方语言和文言等多种语言资源综合融会的结果,下面我们主要看现代汉语的口语化、欧化和文言的保留对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
3.1现代汉语的欧化与现代历史小说中“人”的情绪的表达
现代汉语的欧化主要表现在大量欧化词汇的运用,人物现代情绪的表达主要是指小说人物的各种情绪如欲望的觉醒、个性的抒发等的感知和表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人”的情绪和欲望几乎全部来自对西方的译述和介绍,所以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同构的关系。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说:“我们的语言,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我们拿几种西文演说集看,说得真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若是把他移成中国得话,文字得妙用全失了,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总而言之,词不达意了。”[12]说到底,欧化就是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在思维结构、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上感到古代汉语的不够用而向西方看齐的一种结果。要想准确地表达从西方借来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最简单、最直接、最贴切的办法就是“直用西洋词法”。于是,双音词及复音词剧增,音译词加入到现代汉语中,“汉语句子的附加成分,像定语、状语、补语明显加长,”[13]词汇传达的思想欧化了,旧有词汇使之具有新的意义等新的语法、词汇特点出现在现代汉语中。这不仅使古人能够说着今人的语言,而且形成语言在修辞上的多重效果,从而加强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在鲁迅、郭沫若、廖沫沙等人的历史小说中得到很强的体现(在后文中我们将要详细论述),而且对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技巧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在现代历史小说如施蛰存、茅盾、李拓之等的作品中得到尤为鲜明的体现。例如在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的第一段中,小说以鸠摩罗什视点出发,写他和他的妻子骑着骆驼走在往秦国去的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叙事语言中夹杂着大段的景物和心理描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非常少见,但是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却很常见。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在叙事中已经非常娴熟地用着“欧化”色彩很浓的长句。句子变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方面的变化,①双音节、多音节词汇取代单音节词汇。②数量词的出现。③大量连接词的出现。二是语法方面:①主语前面有长长的定语。②状语前置。③频繁使用被动句。④多用复句,如并列复句、转折复句等。这几种特点在以上这个三百多字的段落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使用古代汉语,上面这段文字就会变成:“大智鸠摩罗什携妻过凉州,前往秦国。时吕氏凉州既遭秦兵,国破城亡,满目荒凉”。肯定不会出现诸如“给侵晓的沙漠风吹拂着,宽大的襟袖和腰带飘扬在金色的太阳光里”这样细致、渲染的描写,也不会出现“有几所给那直到前几天停止的猛烈的战争毁了的堡垒的废墟上,还缕缕地升上白色和黑色地于今矗起在半天里地烽火台上”这样前置的、冗长的状语。书面的“欧化”句式无疑会减缓叙事的节奏,而更加适合细致、精确的景物、心理描写,为后来鸠摩罗什性欲和道义的冲突作了良好的铺垫。#p#分页标题#e#
3.2口语化与向大众传递现代情绪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以文学运动为突破口的启蒙运动,现代启蒙家试图通过对文学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品质的革新达到宣传西方现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目的,那么,为了更好的言说这个来自西方的“现代”,达到为大众所理解和认可的效果,大众口语也是欧化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选择。现代文学通过大众所熟知的语言形式———口语将现代精神传达给被启蒙者,从而将置身于蒙昧状态的“祥林嫂”、“闰土”们引向现代,所以,现代文学的口语运用表达的就是启蒙者对大众的一种言说欲望和言说方式。晚清时期,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已经开了将口语引入文学的先声,“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诸位启蒙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谈论用口语写作的重要性。胡适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从“八事入手”,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大致方向,接着又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以上“八事”做出了“肯定的口气”的修改,实际上就是一则做“国语的文学”的宣言,他提出“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说我自己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实际上还是继续抨击文言的“死文学”,提倡用“口语”写出活的文学。傅斯年在《如何做白话文》中就将“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作为做好白话文的两条资源中的第一条,他说:“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想把这层办到,唯有凭藉说话里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手段。”[12]鲁迅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讲上发表了以《无声的中国》为题的演讲,更是讲出了文言导致中国民众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害处———“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象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久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所以“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讲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4]在这里,“口语”的运用已经清楚地和交流、和国家民众的思想状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启蒙者们想通过“口语”启蒙大众的目的也呼之而出了。
用历史为教材,用口语的方式引导大家用民主和科学的观念重新看待历史,看到中国坏的根子究竟在哪里,这不失为启蒙大众最实在的办法。鲁迅说他用白话写历史小说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没有把历史小说的创作用意说得比这更直白的话了。郑振铎在《玄武门之变•序》中就指出:“中国的历史一向是蒙着一层厚幕或戴着一具假面具的”,所以有必要“在多方面的剥落他们的假面具,而显示出他们的真面目来”,并“揭发帝王们的丑相”,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是如此,茅盾的历史小说《石碣》是如此,郑振铎自己的《汤祷篇》也是如此。所以,历史小说用口语进行写作,其作用不是象“历史故事”那样普及历史知识,而是担负了更多启蒙大众的责任,所以其写法不能只是白话翻译文言历史,而是有更多的思想内涵。现以鲁迅的《奔月》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奔月》中,鲁迅不仅虚构了射日之后的后羿在打猎生涯中的窘境和因为猎绩不佳遭到嫦娥冷遇的的日常细节。文中大量“生活化”的白话口语完全打破了人们对一个英姿挺拔、连射九日的英雄的想象,其言语之中的无奈和俯就完全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无力照顾妻子的男子心声。因为人物语言和现实语言的一致,就让读者不只是坐在戏棚中听到或是在书中“隔岸观火”地读到、而是站在当下、进入人物处境中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末路英雄的无奈和悲哀。在那样的社会,英雄的命运尚且如此,常人的生活更何以堪?美丽神话中的女子尚且如此世俗而且背信弃义,俗人的道德更值得我们几许信任?作品用大众能听懂的语言将正史中的人物放置在日常生活中,说出了大众在日常中感受到却说不出的情绪。
4结束语
从文言正史到半文半白的历史演义再到现代白话的现代短篇历史小说,历史材料并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写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变化主要是通过叙述方式的变化表现出来的,而语体的选择又是叙述方式中最显著的特点。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历代正史中的封建意志和文言书写方式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书写者们正是利用文言的特殊地位很好地实现了历代帝王的统治话语权力;而传统长篇历史演义对叙事语言所作的口语化的调整,使历史获得了娱乐性,有迎合中下层老百姓趣味的倾向,但封建文人的正统儒家观念使他们选择了对正史观念的固守,半文半白的语体运用只是获取读者的手段,并不代表着思想观念的转变;现代短篇历史小说所使用的现代白话却既是思想的又是艺术的,它既表示了创作者们在新思想的影响下重新打量历史的一种姿态,同时也赋予历史文本另一种艺术诠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书写是和历史认知、语体选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历史认知必须从语言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