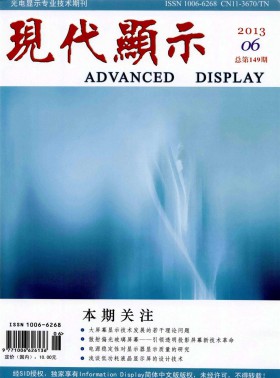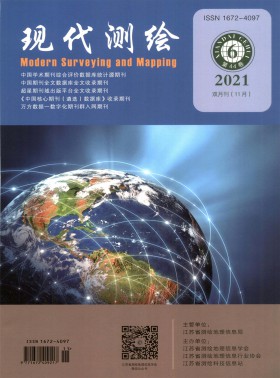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教学的反科学趋向及成因,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知识与教学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知识就不会存在独立形态的学校教育。知识的种类有很多,如科学知识、人文知识、艺术知识、宗教知识等。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知识,然而,科学知识却在一片质疑、拷问、批判乃至否定之声中被教学理论逐出“教门”了。目前,在众多呼吁“教学转型”的理论重建中,科学知识已经不再是教学内容中的合法成员,而是与“教育”“人性”“道德”等相违背的“异教徒”。审慎地分析当代教学理论对科学知识的偏见及根源,回归现代教学的本色,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一、狭隘理解教育的人文性,拒绝承认科学知识的教育价值 我国当代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关注“心灵”“个性”“自由”等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从脉络上看,当代教育的人文倾向既是我国教育理论对“人本主义”的“补课”,也迎合了当代世界教育理论发展的潮流。这股思潮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都认为科学知识缺乏人文关怀和道德价值,社会种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科技的困境。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总是意味着两面性———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并存、巨大的能量与毁灭性的破坏并存。显而易见,科学知识有利的一面在教育领域完全是反动的,科学所带来的利益仿佛只是单纯的、实用的、物质的方面,这与关注内在精神价值的教育活动格格不入。对科学知识的这种理解实际上完全抹掉了科学的教育价值,它只有训练价值,培养的只是“现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工人”,它对应的是“理性人”“经济人”“空心人”。 现代教育以人文关怀的名义将科学知识传唤到庭,要求它为自己进入学校的正当性作出辩护。这本身说明教育在进步,但是却在曲曲折折的理论思考中迷失了方向,以致“因噎废食”,丢掉了现代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科学知识。最激进的旧人文主义者要求停止科学研究,回到古代去。多数人不会如此极端,但大都倾向于认为科学带来的只是物质上的好处,伤害的却是高贵的“灵魂”。这种偏见移植到教学中,学习科学知识就好像在强迫儿童吞下一口不可口的食物,学习它最根本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儿童认识到现代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和有害性。 对教育人文性的狭隘理解和科学两面性问题的错误归因是导致科学知识被拒绝的主要原因。萨顿(G.Sarton)批评旧人文主义的狭隘时说:“他们只有一种被歪曲了的科学知识,并且只会从最坏的角度,把它只看作是一种单纯实用的和物质的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它,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抹杀科学的进步,揭露科学的害处。”[1]15实际上,科学知识原本就是从人文精神中生长出来的,“科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教育……不能简单地把科技教育和人文精神对立或分离开来”[2]。杜威认为:“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作出了贡献。任何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义的,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就连教育意义都没有。”[3]在杜威看来,科学之所以带来破坏和灾难,不是因为科学太发达了,而是因为人类对社会的研究太不科学了。我国教育家任鸿隽也认为,科学的两面性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科学发明只是一种原理、一种方法,它如何被利用是由社会组织决定的。防止科学发明被滥用,不是要停止科学研究,而是要改良社会组织。[4]618 正是因为意识到旧人文主义的狭隘性,萨顿呼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人文主义:“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1]133 二、以教条主义态度照搬照抄后现代思想,要求放弃科学知识的教学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现代主义的新范式,它形成于20世纪末,至今尚不清晰。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学说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智力生活的领地免受自然科学的霸权。近代科学自诞生以来,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效益和福利使得普通大众对科学知识产生崇拜心理,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科学是唯一真理。如果按照科学知识的标准———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来衡量,人文艺术类知识只能勉强算是“准知识”“非知识”,成为科学的附庸或从属。后现代主义通过解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来说明这些标准并不存在,科学知识并不比人文知识更优越,它不是唯一真理。 站在知识教学的立场,后现代主义的启示是不仅要重视科学知识的教学,而且要重视人文知识的学习,因为它们对于知识与人格完善具有同等价值。后现代主义的提醒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因为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但是在当代社会,包括教育领域,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偏见,人文学科被视为没有专业性、可替代性强的学科,人文研究被嘲笑是“崇尚空谈”“百无一用”“吃饱了撑的”。在英国,《迪尔林报告》(TheDearingRe-port)甚至建议:“在14岁以上学生的国家必修课程中,不再包括人文和艺术。”[5] 对待后现代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导致教学理论在汲取它的“营养”时却误入歧途,产生了错觉。错觉之一就是以为科学知识的教学过时了,现代教学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就得从科学知识转到后现代知识的教学。当前,一些被冠以“后现代”的教学主张对科学知识要么绝口不提,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否定科学知识的教学,认为它的客观化倾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往,容易导致集权化的“负交往”教学。相应地,反对的观点则从科学教育的作用和价值出发,要求抛弃后现代知识观。#p#分页标题#e# 如果认为教学理论汲取后现代思想就是吸收它的反科学性,那么这不仅葬送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而且会给知识教学带来巨大的混乱。“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线性地理解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系列关系……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过是对于现代性的缺陷加以弥补而已。”[6]后现代思想不是对现代主义的替代,而是补充。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哪种知识是后现代主义专门创造出来用以对抗科学的“知识”,知识的种类和总量并不因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有所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J.Habermas)说,即使现代主义灭亡了,但现代性的事业仍然主要依靠来自科学的专业知识为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7] 后现代主义在教学领域产生的第二种错觉是科学的确定性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之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这种错误散见在许多提倡现代教学要从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的学说中。所谓“不确定性”,就是不能有标准答案,不能有任何定论,必须将“知识”当作一个话题来探讨。他们把科学等同于小说,把“雪融化之后是水”和“雪融化之后是春天”看作是同一类型、具有同等效力的科学知识,把对科学知识系统性的破坏看作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教学。 虽然后现代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和小说之间就没有了区别。目力所及,这里只谈科学知识独有的系统性特征。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缘自于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给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提供合理、统一的解释,科学通过寻求自然现象背后的机制(又称为自然规律或因果律)来达到这一目的。人文、艺术和宗教等都不具有系统性,因为它们不能够也不需要对某一现象形成统一的、一致的解释。通常人们也说,哲学或教育学等形成了某某系统,但是站在科学知识的立场,哲学即使有系统那也不是只有一个系统,而是有无数个系统。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核心概念的内涵、研究问题的视角、得出的结论等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类却只有一个物理学系统、一个几何学系统。所有的科学家都共享着同一个系统,共享同样的知识标准和信念,都遵循着同样的研究范式,都将数理逻辑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此处所说的系统性正是指这种性质。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系统性,系统知识其实是科学知识的别称。系统知识意味着任何人想获得科学知识,就必须接受系统内部的基本规则。拒绝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就拒绝了科学知识的教学。所以,人们的确可以自由讨论“雪融化之后除了是水还可以是春天”“1+1不仅可以等于2还可以大于2”,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1+1=2是数学知识,而1+1>2只是个人观点;雪融化之后变成水是自然知识,而雪融化之后变成春天是文学。文学不是科学,更不是对科学确定性的挑战,它们是智力思维的另一种方式,是要保护智力领域不完全落入科学知识的霸权,让儿童知道在另一块生活的领地雪融化之后还可以是春天或其他。如果教师没有这种明确的意识和区分,那么他只能使儿童形成一个混乱的知识结构。 三、对建构主义的过度诠释,否定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可能性 建构主义发展至今成了一个庞杂的理论思潮,涉及到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皮亚杰(J.Piage)t和维果茨基(LevVygotsky)作为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核心思想是:知识是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建构起来的。相比较而言,皮亚杰侧重个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维果茨基侧重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建构主义揭示了学习过程中,意义的获得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传递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主体已有的经验(维果茨基称之为“自下而上的知识”,皮亚杰称之为“图式”)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站在知识教学的立场,建构主义的启发就在于提醒教师在知识教学过程中要留意学生由于背景经验的差异可能存在的理解盲区或歧义性理解,不要误以为同一种讲解对所有的学生都同样有效;避免它们的有效途径就是充分了解学生已有的背景经验,选择最好的教学方式。 但是建构主义心理学在教学领域被过度诠释,有人认为,既然意义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差异性,那么任何追求对科学知识的一致性理解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后现代主义已经证明了科学知识本身也是“不确定的”,这正好契合了建构主义的个体差异性原则。所以,对科学知识的歧义性理解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仿佛它才真正体现了主体的建构性,体现了科学的创造精神。这样一来,“建构”就从原来的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被扭曲为主体独断的创造与发明。这种观点是激进建构主义代表人物冯•格拉塞斯费尔德(V.Glasersfeld)和强纲领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拉图尔(B.Latour)最常见的套路。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是建构的,就意味着科学理论是科学家通过密谋协商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神话故事。 对建构主义的过度诠释,再加上错误理解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套匪夷所思的歪理。它认为一切面向已有知识的教学都是面向确定性知识的教学,都是在“灌输”,即使采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或布鲁纳式的发现法也还是在“灌输”,因为学生只是发现别人的知识,而没有建构或创造自己的知识。这种学习只是为了“获取存在于外部的和先前已知的真理,并不具备真正的开放性和进步性”[8]。“建构主义”的教学应该面向知识的不确定性,应该是一个同“知识的专制主义”做斗争的解放过程,学生物的学生不应该被希望相信进化论,学物理的不应该被希望相信牛顿定律,学数学的不应该被希望相信1+1=2。 四、失去科学知识的教学不是现代教学,更不是后现代教学,而是改良的古代教学 “知识转型”“教学转向”“概念重建”等是当下知识教学领域使用频率很高的新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反映了教学理论寻求发展的努力和进步,但是却在混乱不堪的理论话语中经过层层转手逐渐迷失了方向,形成一股汹涌的“反科学”“反智”思潮。#p#分页标题#e# 当代教学理论的反科学倾向是由于其对现代学校教育功能认识模糊,没有坚持学校教育的立场导致的。学校教育应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学校教育却不能包揽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校是他们形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生活场所之一,但学校却是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唯一场所。离开了学校系统的教学,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只能积累经验常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日本学者?原千?说:“在学校里,孩子们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只是知识的话,自己就可以学。可是人际交往、集体目标的实现等,是自己一个人所无法学习的。”[9]?原千?曲解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功能,刚好颠倒了知识学习与其他学习的关系。如果知识教学只是学校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学校的存在,因为游乐园、交际场、俱乐部等对人际交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更有效的、更直接的作用。 众所周知,科学教育始终是现代教育的核心,这是它区别于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现代社会,人们接受科学教育不仅是因为要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是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基础。任鸿隽先生认为,科学知识所产生的影响属于理论的要比属于应用的更深远,“人们只知道飞机与无线电怎样改变了社会组织,但不要忘了地动说与天演论怎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没有后者的改变,由中世纪进入近世纪是不可能的事”[4]618。可以肯定,失去了科学知识的教学不会是现代教学,更不会是后现代教学,而是改良的古代教学:只是从古代私塾搬到了现代教学楼,用鼓励和微笑代替了藤条和戒尺,用现代朦胧诗代替了古代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