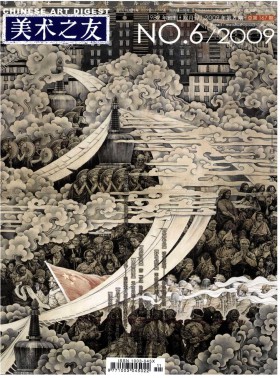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美术传播的历程及展望,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早在1986年前后就有学者指出“艺术传播是一个专门的领域”,“用传播学的视野和方法去研究艺术传播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美术院校的教学体系仍沿袭老一套,美术传播学方面更是鲜有学科意义上的建树。 在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已经从以往比较宏观、单一的话题,开始分化、细化和深化的今天,美术传播研究还停留在这种有名无实的状态,这一现象实在耐人寻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许与“美术”这个术语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游移性有关。汉语“美术”一词译自英文“art”,而实际上在西方“美术”的表达形式是“finearts”。 finearts译自法语“beaux-arts”,这一术语出现于18世纪中叶,“指非功利主义的视觉艺术,或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艺术,一般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有时也包括诗歌、音乐和舞蹈”。[1]据一些学者研究,蔡元培先生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时,也包括诗歌和音乐,后来以“艺术”作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则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视觉艺术。有学者指出这是“美术”对“art”的误读,其实还可以说这也是对“finearts”的误读。 的确,如果连“美术”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有理论清楚,要进一步对“美术”展开传播学方面的研究看来确实有些困难。 笔者在比较了各种美术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目前仍宜采用大家已经熟悉并普遍接受的美术定义,即,美术是指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在内的、非功利主义的、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视觉艺术。之所以采用这一定义,一是在一般情况下,西方也是这样来理解“finearts”这个概念的,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把“美术”单独与“视觉艺术”联系起来。 既然要用传播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美术,就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下“传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人们通过普通的符号系统交换彼此的意图。把美术视为人们交换彼此意图的信息载体是不成问题的,有争议的是,美术所采用的“符号”似乎不属于“普通的符号系统”。苏姗朗格、卡西尔、伽答默尔等人在运用符号学理论解释艺术现象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因为它与一般语言一样,承担着“表现”的作用。但他也强调了艺术符号的特殊性,他说:“一种在激发美感的形式媒介中的表现,是大不相同于一种言语的或概念的表现的”。苏姗朗格也认为,“按符号的一般定义,一件艺术品就不能被称之为符号”。 伽答默尔承认绘画是一种“表现”,但他认为“绘画并不是符号”,他说“符号无非只是其功能所要求的东西”,除去其功能(指示和指代)它就什么也不是,而绘画的“表现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指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替代。正是这种与绘画相适应的中间位置使绘画提升到一个完全属其自身的存在等级上”。[2] 美术的这种有着“自身实在性”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符号”或“超符号”的,这就意味着美术很可能难以被纳入人类的传播系统。因为按通常的理解,传播之所以为传播,就在于它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来进行的信息交流,传播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符号应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了美术的符号属性岂不是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它的传播属性。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详细的探讨。 美术究竟能不能被纳入传播系统之内呢?我们不妨对人类传播史作一简短的回顾:人类的传播行为最初是不分化不发达的,原始人同时重用所有5种感觉———嗅、触、听、视、味觉,这是一种传播的“自在方式”,跟动物差不多。接下来,在“距今四到九万年前,现代人类获得了说话的身体能力”。 口头语言固然是“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但“在穿越时空时却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仍然未能突破人体的限制。再往后,人类逐渐学会了利用人体以外的物质材料来传播信息,这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工具”。这种“传播工具”的发明使人类传播行为从“自在方式”转向“异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书面语言即第二次媒介形态大变化。 早期绘画、雕塑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开端。从目前已获得的考古发现来看,图画的发生肯定早于文字,如果说文字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图画就是文字的基础。一切古老的文字在其始创阶段跟绘画一样总是不同程度地模拟着“自然本身”,以后文字与图画分离,文字成为与口语相连专司概念表达的纯粹符号,而图画则与视觉意象结合朝形象化方向演进,成为一种能激发美感、且具有“自身实在性”的“表现性形式”(为避免与一般符号相混,苏姗朗格认为可以用“表现性形式”来替换“艺术符号”)。这样,就有了人类传播的两种基本方式:运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传播,运用绘画、雕塑之类“表现性形式”的非语言传播。[3] 美术作为非语言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传播现象之一。我们知道,美术的起源起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当时的美术遗存(洞穴壁画、小型雕像之类)来看,原始美术可以说全都是一种“特殊媒介”———沟通人与神或具备巫术交感作用的媒介。即便是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美术仍继续扮演这种“特殊媒介”的角色,绘画、雕塑和建筑一直是当时的“传播载体”中最神圣也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部分,这一点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美术遗产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光直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这样说:“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就是巫师的法器”,“据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人就握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政权的工具”。[4]#p#分页标题#e# 不仅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美术都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作用: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的基督教美术是“文盲的圣经”,“是向人们的意识灌输宗教的最强有力的、也许是唯一的有效方法,是信徒和神的直接心理联系的手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同文学相类似,“画家也和作家一样描绘基督……对于教堂他们所创造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只是福音书的编著者用词语来讲述(描写),”而画家则用形象来表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油画因其“能够更细腻和生动地表现出被描绘的事物,更鲜明、逼真地揭示出其所有的性质,所以,它超越了其他那些样式,因而更常用于教堂之中”。列奥那多达芬奇因之而自豪地宣称“绘画既全面优越于诗歌,也全面优越于音乐”。[5] 在中国历史上,绘画、雕塑之类也一直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这在若干古代文献里边说得明白,如“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丘明《左传》);“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古画品录》);“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从传播史的角度看,非语言传播早于语言传播,借助于普通符号系统的信息交流并非传播的唯一方式,广义的传播包括人类一切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二是美术传播现象自古就有,且贯穿整个人类历史。 人类传播虽由来已久,传播学却是20世纪30年代才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所以有学者说:人类虽然有着极为悠久的传播历史,却只有一个为时甚短的传播学史。传播学的正式形成虽属晚近的事情,但其萌芽却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美术现象也并非始自今日。据莫卡冈的研究,18世纪的杜博在对画与诗进行对比分析时就“出人意料地把问题转向了一个新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方面,即我们今天称之为符号学的方面。”杜博认为绘画所使用的是“自然符号”,其特点是“把自然本身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诗所使用的是“人造符号”,他说,词是“思维的随意符号”,而字母是词的随意符号。[6]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杜博的研究已初步涉及非语言传播与语言传播的区别。 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美术传播问题,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表现性形式”。“符号”(symbol)的一般定义是:“用以简单地表示或象征人物、集团或概念等复杂事物的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7]即伽达默尔所说的那种“无非只是其功能所要求的东西”。而美术形式则具有“完全属其自身”的实在性。实际上,凡称得上是艺术的事物都具有这种“自身实在性”。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读诗是不能“得意而忘言”的。[8]在这里,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形式”有悖于一般的符号,也就使它有悖于一般的传播定义。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呢?苏姗朗格的意见是或者修改符号定义,或者把美术的“形式”视为一种“特殊符号”(表现性形式)。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一般的传播定义,就不难看出这种“形式”上的特殊性对美术传播功能而言只是“限定”而非“取消”,易言之,它不仅不妨碍美术实现其传播功能,反而使得美术在传播领域中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地。 我们说美术的“表现性形式”有着“完全属其自身”的实在性,那么,它的这种实在性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美术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 美术形态的发生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黎明时期的器物制造。制造器物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实用,作为美术形态源头的器物造型本身,不过是某种使用功能的物质变现。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器物在被当作“特殊媒介”之前,它自身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有着自身形式意味的物质实体。器物如果一直被使用着也就是器物而已,但它也有不“在手”而被闲置的时候,这时,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实践终止之时便是精神活动开始之际。于是,器物成了心灵所观照的对象,人从器物那里直观到形式的意味和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器物本质上是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伸,原始人在观照这些“延伸的肢体和器官”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夸张它的作用和力量,并在交感巫术的氛围中产生许多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联想———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人们仍常常情不自禁地神化一些曾经发挥过非凡作用的器物,只是不自觉而已。在这种情境中,观念形态的东西与器物的造型形式结成种种神秘而复杂的联系,器物于是成为符号化的器物。器物一旦成为符号化器物,它的形式就不仅有了诡谲的意味,而且还往往具有神奇的作用———如沟通人、神,天、地的作用等等。当器物的形式与此类意义或功能的联系已到了牢不可分的时候,一些纯粹形式化或符号化的器物便出现了,如原始社会后期的玉琮之类。这类符号化器物与普通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凸显了“表现”功能,但它毕竟不同于纯粹符号,它的“意义”是从它原有的物质形态和形式形态生发出来的,在这里,意义与其特定的物质形态和视觉形式之间有着先在的牢固联系。拿著名的“良渚玉琮”来说吧,能不能随便更改它的材料和改变它的形状呢?显然不能。之所以不能,就在于它的材料(玉)是有意味的材料,它的形式(外方内圆)是有意味的形式。由此可见,美术的“表现性形式”之所以有着“完全属其自身”的实在性,乃是因为其“母体”即器物造型原本就是“完全属其自身”的东西。 美术形态的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来源是“摹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手印”和那些相当写实的洞穴壁画是最早的实物证据。至于同时期的一些非写实的造型形式,如装饰品、文身以及一些神秘怪诞的绘画和雕塑等等,其性质已经非常接近于今日之所谓“表现”。写实的以及表现的造型与器物造型不同,可以被视为“纯粹造型”。纯粹造型不再是某种实用功能的物质变现形式,而是某种“内容”或“对象”的“感性显现形式”。但它们和器物造型一样,总是要诉诸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感性形式,所谓造型就是把各种物质材料变成一些有用途或有意味的物质实体。这种物质实在性使美术具有所谓“实物语言”的性质。其次,美术作为视觉艺术必须具有可视性。绘画可以不描绘任何现成之物的形状,但它必须描绘可视的形状。比如,按几何学的定义,“线”是没有宽度和体积的,但画上的“线”要让人看得见就不能不赋予它一定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术也具有“视觉语言”的性质。#p#分页标题#e# 黑格尔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美学思想,他认为“艺术类型不过是内容和形象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是区分艺术类型的“真正的基础”。[9]用今天的眼光看,所谓“形象”其实就是广义的“符号”或“表现形式”。黑格尔按内容和形象之间的关系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认为其中的“古典型”艺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形象与内容互相渗透、融为一体。现成的例子便是古希腊雕塑。就古希腊雕塑而言,它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是“人”;它用来表现这一“内容”的“形象”(形式)是什么?也是“人”。在这里,人在现实中是怎样显现自身的,在艺术中也怎样显现自身,区别只在前者乃血肉之躯,后者乃青铜或云石。实际上,存在着并感性地显现着的并非只是人类,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世界一直以其诗意的光辉向人类发出会心的微笑,可见大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信息发出者。因而,在美术的“表现性形式”中,不仅“人”,大而言之一切能被我们感知的具体事物都如其本然地显现自身。所以,杜博把美术的这种“表现性形式”称之为“自然符号”。 综上所述,可见美术的“表现性形式”具有“完全属其自身”的存在本质,并呈现出实物语言、视觉语言和自然符号等形式特质。对美术而言,材料因素和手工技艺因素是它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凭借这些因素美术才得以成为人感性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美术领域难以见出“符号”与“媒介”的分离,格林伯格说“艺术即媒介”,这是对美术媒介形态特质的最直截了当的表述。 作为“符号”与“媒介”的统一体,美术作品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综合体验源”,面对一幅绘画或一尊雕像,人们可以去感受、辨认、联想、移情……甚至推理、阐释;它刺激感官、挑逗想象、激发美感,也唤醒心智,总而言之,它经得起我们全身心的体验;美术作品是传播的中介,凭借这一“中介”,传播得以突破身体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这一“中介”还具有穿越时间的稳定性和耐久性,诉诸缣帛、金石的绘画、雕塑使信息有了牢靠而坚实的承担者和跨越时间的传递者,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获知前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储存着丰富信息的缣帛或金石;最后,它作为一种“激发美感的形式媒介”,其视觉形象性以及寓于其中的审美愉悦大大降低了信息读取的困难程度,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易读性和感染力。当然,美术也有自己的局限,如作为静态媒介它完全不具备传播速度上的优势等等,接下来就会说到这个问题。 人们习惯于把人类传播史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媒介阶段;电子媒介阶段。实际上,在所谓口传文化阶段,借助于手工技术制作的媒介(如书写文字、绘画、雕塑等)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传播作用。在此期间,美术所发挥的作用好多时候甚至超过了文字。美术的力量之所以能够超过文字,就在于它的形式能直观形象地显示其内容,而语词符号与其所示意义之间的联系不存在这种直观性,要掌握一套文字系统的含义需要先学习了解其约定俗成的底层系统,否则,便不知道文字的所指。印刷术发明之前要普及识字教育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必须借重形象直观的美术。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美术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传播作用绝不是我们今天所想像的那么单纯。“艺术”意味着“用技巧和想像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审美对象、环境或经验”,这只是现代人对艺术的定义,如果我们照此去想象历史上的艺术,那就无法解释中世纪为什么把艺术称之为“文盲的圣经”,也无法理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这些话的意思。历史上,自有美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偏重于纯审美目的的、纯粹意义上的美术传播,但更多的是以美术的形式来达致其他目的(如政治目的、宗教目的、伦理目的等)的传播。美术之所以在历史上一再辉煌,被我们的前人誉之为“鸿宝”“纪纲”,被列奥那多达芬奇称之为“既全面优越于诗歌,也全面优越于音乐”的最高级的艺术形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之于诸如政治、宗教等领域的垂青。 美术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时至今日,它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却不无道理的答案:“美术在今天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这个答案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并阐释,当然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 麦克卢汉说:“媒介的内容就像破门而入的盗贼携带的一块多汁的肉,它的目的是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10]麦克卢汉这段名言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过去对美术传播的分析恐怕是过分注重它的内容了,却往往忽略了它本身的媒介形态。其实,只要我们撇开那块“多汁的肉”而把注意力转向媒介本身的性质,就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媒介形态的美术,其长处之所在往往也就是其短处之所在。绘画、雕塑都是静态媒介,建筑就更不用说了,它们不具备传播速度上的优势,尽管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卷轴画,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也有了架上绘画之类,但事情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改观。 媒介的静止属性还把美术传播限制在单向、定点的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切断了作者与观众双向交流的渠道,许多作品因易于损伤或价值昂贵等原因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难得与观众见面,这当然会进一步缩小其传播范围。其次,美术对物质材料和制作技艺往往有着相当苛刻的要求,好处是可以长久地保存信息,但毕竟成本昂贵、制作难度太高。据张光直先生研究,中国古代为了制造“特殊媒介”青铜礼器,常常导致国家迁移首都,代价之昂贵由此可见。[11]还有,美术固然形象直观、富于美感,但这也限制了它承载、传达某些难以诉诸视觉形象,而更适宜于诉诸文字或其它媒介形式的内容。是的,谁都知道美术很早就具有传播宗教———政治文化内容的作用,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美术作品的这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依存于当时的口传文化和现实生活情境的(如青铜礼器就总是伴随着宗教仪式活动),一旦丢失或脱离了这些附加因素和话语环境,仅凭美术形式,这些“意义”是难以传达,也难以保存、流传的。举例来说,在拿破仑的士兵找到那块著名的石碑之前,尽管金字塔前的法老一直在朝着人们微笑,古埃及的历史仍然是个无法破解的斯芬克司之谜。所以,一个民族如果仅仅只有美术,哪怕它相当辉煌相当杰出,如果没有文字也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如果美术过分发达,它还可能压制文字之类符号系统的产生和发展。#p#分页标题#e# 在机械动力应用于传播领域之前,美术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仍然可以大放光芒而雄踞一切媒介之首。今天,“美术为什么会变得不再重要了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三类:自然环境、社会体制环境、符号环境。不言而喻,当今世界这三类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尤以符号环境的改变为最,并对美术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使美术不再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早在印刷技术带来书籍的普及的时代,美术就开始受到影响并逐步从一些自己曾经扮演主角的传播领域撤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人们的感觉中美术变得不象过去那么重要了。在西方,这个过程大致开始于雨果说出“书籍杀死教堂”这句话的时候,在中国则恐怕还要早得多。 目前,人类已进入网络传播的时代。按“美术”这一术语所指涉的媒介形态而言,它无疑是依存于手工方式的传统媒介,如果从传播媒介“能说什么”和“能怎样说”的角度看,它不仅不可能跟网络比,也无法跟“传统的”摄影、电影、电视之类媒介抗衡。有人曾经把美术放在20世纪以来的媒介环境中予以全面考察,结论是它丧失了自己以前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功能。实际上,美术的这些功能并没有消失,甚至也没有减退,严格说来,美术所失去的是它以前在形态学意义上的独立性和在社会功能上的优越性。如果按照以往历史形态的美术传播功能来考察当代美术,它无疑是失去了这种相对独立的传播功能,但这仅仅是一种形态上的消解或一种形态上的转化。美术在当代传播语境中无处不在,相较既往,他弱化了形态的独立性但却与其他现代传播媒介结合,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传播能量。如,美术曾经作为“文盲的圣经”发挥过重要的宗教传播作用,但随着文盲的减少和《圣经》印刷读本的普及,教会自然也就无须再劳烦艺术家们兴师动众地制作“文盲的圣经”了。所以说,美术失去的不是功能,而是教会之类的“顾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为美术另辟蹊径,但在笔者看来,此前的许多“实验”或“创新”似乎找错了路径,一部分人忙于去改进美术的功能,那情形类似于把骏马的腿锯掉换上四个车轱辘,另一部分人在“说什么”上打主意,试图寻找一些为其它表现形式所无法表达的或疏漏的“内容”。大家知道,这些“实验”或“创新”在折腾一番之后,却大多以宣布“美术已经终极”而告终。 罗杰菲德勒说:“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12]至于在媒介形态已经发生革命性演变的情况下,美术这样一种传统形式将如何继续演进和适应,这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