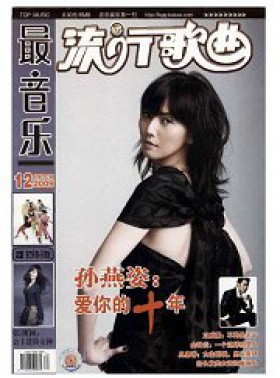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流行歌曲与文化政治的关联,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胡理丽
1927年,当时的先锋派作曲家,音乐开拓者黎锦辉创作的歌曲《毛毛雨》,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始,鲁迅将《毛毛雨》的歌声鄙夷为“绞死猫似地”[1]P201,然而无论如何《毛毛雨》风靡上海,黎锦辉自此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得不提到的大师级人物。1930年代流行歌曲和电影交相辉映,成为一种世俗流行文化的迅猛潮流。一直到解放前为止,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股以流行音乐、电影插曲和电影为载体的通俗文化热潮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压迫而消失,反而一直曲折前进,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左右着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某些走向,成为一个可以持续研究的文化事件,反过来我们深入检索这些曲目,他们曾在不同年代被标上“靡靡之音”、“汉奸歌曲”、“港台歌曲”,也成为思考都市文化环境很好的切入点。
一、西方音乐的侵入以及本土流行音乐的形成
20世纪初,圆片唱片和唱机传入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洋行开始销售唱机,唱片。它们作为一种新的,划时代的音乐传播媒介,介入到音乐传播模式中。[2]P60伴随着国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在上海租界里,水兵和船员带来了爵士乐,为的是看酒吧中的舞女和陪酒女郎。唱机和酒吧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东渡,不管我们如何咬牙切齿的反对列强,一种文化交融开始形成。如果进一步考虑都市文化语境的问题,唱机和电影改变了原本本土舞台剧、戏剧的即时性,新式娱乐方式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空间和时间感觉,而时空关系的重新定位无疑是都市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3]P3以此引发的对都市生活的体会在1920到19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那里达到非常高的水平。①有意思的是唱盘机和上海1930年代的流行歌曲(比如《夜来香》)在49年后的中国大陆电影中往往被平板化为亲美派国民党走狗汉奸的陪衬符号,原有的文化生态“场域”空间被强势的左翼意识形态遮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政治的“失语者”和“边缘表达。”[4]P10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南京路与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一起“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宏大图景,与大陆本土比较,它所包含的超前性是不言而喻的”。[5]P14超前性的娱乐文化代表着上海的都市生活越来越西化。而这时候黎锦辉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文人,黎锦辉可以说是在五四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他五四的时候加入北大文学研究社,组建乐团,办训练班,但是不同于左翼倾向的音乐家赵元任、黄自、王光祈,他的路子却是“提倡大众文艺,反对全盘西化,”试图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音乐神韵,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方音乐的本土化才逐渐完成。[6]P6黎锦辉的伟大贡献主要在于发扬“拿来主义”精神,把爵士乐,民间歌谣,中西混合乐队合并起来,创造出了所谓的“老上海的摩登时新调”,②“不论古今中外的各家诗词、夕阳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以及南洋一带唱的夕阳小曲、爱情歌等,一股脑搬来作为我的创作素材。”[7]P28,以《毛毛雨》为开端,黎锦辉的创作路子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鼎鼎大名的“时代曲”,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流行曲时代,而随之而来的国外音乐机构如英国百代(ElectricalandMusicalIndustries,简称EMI),胜利唱片(日商与英商于一九三二年合并)④对这些歌曲的盛业运作以及跟风者的伺机而动,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并和唱片、乐谱出版、电台、歌星、电影、歌舞厅、酒吧、澡堂、杂志和八卦小报一同杂糅进上海的都市文化语境中,而如果我们把思考的范围扩大到复杂变幻的1930到194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电影和音乐作为最重要的表达载体,则更加集中突出了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暧昧。其中的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都市流行音乐VS左翼音乐
1927年,黎锦晖创办“中华歌舞团”,开始系统训练歌唱和舞蹈艺术人才,期间,他提拔了两个人,一个原名叫做周小红,后来经他改名为周旋,另一个是云南的聂守信,后来以聂耳为名,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而言,黎锦晖的音乐和他对这两个学生的提拔可以说是极具象征意味,黎锦辉以时代曲成名,最终却被“黄色歌曲”的指责尘封至今;周旋以“金嗓子”的称号成为歌唱和表演的“两栖明星”,红遍大江南北,但最终命运坎坷,在1950年凄惨死去,对她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至少在主流话语的表达体系内她也只是一个“边缘者”;而聂耳则因为左翼的革命气质最终以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后世膜拜的对象,师徒三人在历史上不同的境遇可见政治的鬼魅。
“五四”以后以赵元任、王光祈、贺绿汀等人走上了左翼的“新音乐运动”⑤的道路,以民歌改造的形式宣传革命,这和黎锦辉的路子大相径庭。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黎锦辉所追求的“平民音乐”,“通俗文艺”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代必然是被质疑的。所谓的“通俗”无法和“士大夫加农民”的革命节拍相吻合,李锦晖的通俗歌曲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境遇,娜拉出走之后只有回家或者堕落,没有左右摇摆的暧昧。1937年底日军攻占上海,对本土流行音乐的苛责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漩涡则更加复杂。《何日君再来》恐怕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1936年7月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一次毕业茶话会上,同窗好友相约作曲留念,每人演奏一首歌曲,于是,年仅31岁的刘雪庵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以表达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1936年底,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开拍《三星半月》,找来刘雪庵的舞曲,并随后由黄嘉谟填词,影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是周旋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却成为一代经典。随后百代唱片公司灌录这首歌,依旧大卖。[8]P48刘雪庵是在黎锦辉的“时代曲”的影响下创作《何日君再来》的,可以说是黎锦辉开创的流行音乐时代的一个延伸。⑥而由黄嘉谟⑦的填词则少不了带一点“软性”电影的意味。《何日君再来》唱红了上海滩,周旋从此成为一代歌后。随后上海沦陷,身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方被称为孤岛,这个比喻形象的说明了当时上海被日军包围的窘境,这是一个生活处处受限制,充满压力和不安的都市。与内地大后方的爱国电影,传唱的爱国歌曲相比,孤岛的文化是“堕落的他者”,[9]传唱《何日君再来》也自然被指控为“靡靡之音”,“汉奸歌曲”,甚至能够在上海活着都成为一个灰色的模糊问题,生存其中的人们所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首先是他们处于文化上的绝对否定,上海被认定是一个失节的城市,汉奸无耻玷污和阴谋破坏民族大业⑧,在此间的任何娱乐活动都会被意识形态的强大话语指认为是汉奸行为;其次他们处在西方列强、汪伪政权和日本侵略者的三重打压之下,生活处处受限,可以说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界限包含了地理和象征性的双重意义,极端明确的二元道德区分明确指认了上海的“他者”失贞。#p#分页标题#e#
其实如果我们在都市文化语境中谈“孤岛”文化则会发现,世俗层面的生存问题根本不是僵硬死板的二元对立的道德模式可以解说的。其实如果说抗战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借助民族主义话语对二元对立模式的强化是在文化上建立、稳固和控制道德化的界限以抵抗日本侵略[4]P85,那么孤岛中的“娱乐”和夜总会里传唱的《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则成为一种突破日本意识形态工具性最有力的方式,以酒吧、影院为核心的公共场所,创造了一种新的“想象的空间”[10]P7(imanginary),让大众参与构建一种新的娱乐话语,逃避日本的侵略文化。这种娱乐文化一方面是生存意义上的妥协,另外则是一种无言的抗争。《何日君再来》的歌唱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上的胜利,这是都市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此外,日军攻占上海使得大批内陆难民涌入租界,仅有10平方公里的租界人口从150万骤增至1937年底的500万,[4]P29,难民涌入,战争急迫,朝不保夕,自然是及时行乐,麻醉自己,《何日君再来》等流行歌曲久唱不衰自然是题中之义,“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更加微妙的是李香兰⑨重新演绎了《何日君再来》和《夜来香》⑩居然在日军中大受欢迎,最后日军斥责为涣散军心加以禁止,这一事件更加体现出流行音乐的多义性在文化政治上的暧昧。1957年刘雪庵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邓丽君的重新演绎版本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自黎锦辉开创的中国流行音乐历史才重新并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并随着“台湾校园歌曲”这一流行音乐变奏的盛行,《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童年》在中国内陆的行销,都市文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大众文化开启了新的篇章。
以《何日君再来》为代表的流行歌曲无法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成为一种主流话语的标志符号被拜入庙堂,而是成为文化和政治夹缝里的游鱼,游走在政治角逐、文化碰撞和时代变迁的所指之间,最终在80年代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中强势回归,代表着一种大众文化发展的最终大势,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流行歌曲作为意义不断被移植和填充的文本始终是一种被历史语境筹划的流动客体。对比历史与现实,重新思考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启示,无疑有着巨大的反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