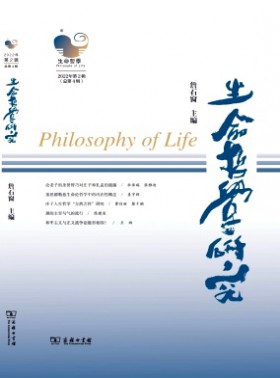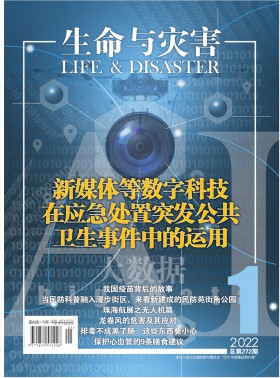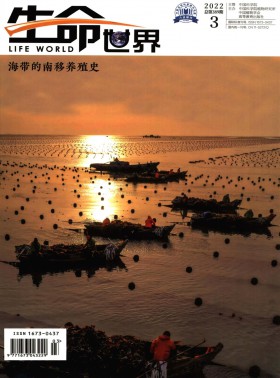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命美学的价值韵意,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喀斯特强烈发育的贵州六枝梭嘎,世居于此的长角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与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发生着紧密的共生、融合与互动关系。远古时代孕育斑斓的山地文化色彩,亟待人们去解读、感知那陌生神秘的苗族文化魅力,识别脆弱生境中民族文化的生成事象,更好地开创民族文化灿烂的未来。 一、六枝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活的生态标本 在中国乌蒙山区的贵州六枝特区与织金县交界处,距六枝县城38km,海拔1400~2200m,面积120km2的梭嘎乡,居住着一个古老神秘的苗族分支———箐苗,根据头饰特点又名“长角苗”。以12个社区(自然村寨)5000余人建立的中国与挪威文化合作项目,中国第一个也即亚洲第一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自1998年开馆以来,通过生态旅游开发,使原始、古朴、独特的文化艺术得到了有效保护。梭嘎生态博物馆由十二个村寨及建在陇嘎寨脚的资料信息中心组成。资料中心的寨门由圆石垒砌而成,两边伸出两只精壮的牛角状饰物,门内是一组杉木结构的房子,茅草顶、屋脊加厚堆高别是一番风味。屋子内记录和储存着本社区的文化信息,有录音记录下的口碑历史、相关的文字资料、特殊意义的实物、文化遗产登记清单和其它本社区内的遗产等。整个村寨都是博物馆的组成部分,以社区内群体亲自参与亲自管理为基础,要求每位居民都要小心地加以保护。它向社会提供和展示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经济社会文化整体。这一鲜活的标本,原封不动地把整座村寨连同居民的习俗当做“遗址”。在生态脆弱、气候恶劣、信息闭塞的大山里,以牛为图腾,以木角象征牛角表示对先祖敬意并诠释文化内涵的长角苗社区。苗胞长期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经济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世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民族内部联姻方式,地域文化景观。当前,大规模工业文明渗透,使得这一活态文化符码消失步伐在加快,文化变迁和异化尤其强烈,原生态文化保护面临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 二、长角苗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与生命美学多维价值形成机理透视 饱含生命气息的长角苗生态美学,生命、生存、生态鲜活地表现为身体—生存—生态美三位一体。正是对自由生命的执着追求,对存在的深层关怀给人以深刻启示;即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包容,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共同建构一个真、善、美的诗意栖居世界。 (一)自然环境中的原生态美 深居大山里的长角苗,基于对往昔历史的回忆和可能冲突的畏惧,造就了一种对自我生存境况的强烈保护。尽管斗转星移时代变迁,工业文明不断渗透到社区内部,仍顽强地守候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与认同。在漫长的适应中,长角苗整体地完成了对自我族群特色文化的延续和重塑。在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里,封闭幽谷滋养了神秘而古老的世居民族,形成了奇异的“孤岛文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苗民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芦笙歌舞表演、赛歌会、斗牛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活动,以歌为媒、以歌传情、恋爱人生(张晓松,2000),过着传统部落式的族群生活。通过独特的管理方式、婚恋丧葬、祭祀礼仪等活动维系族群内部和谐,与同时代的社区外部构成稳态结构。田园诗般的生活、古朴文化、自然色彩折射出原始的民主平等,别具风格的绘画、音乐、舞蹈艺术构成一幅幅精美的画卷。 (二)传统与现代交织畸变的社会美 伴随大工业化深度演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关注中心。当工业文明渗透农耕文明,社会变迁、分化重构就成为历史必然。尽管远离都市的喧嚣,但历时性共变与现实性共存使得深居大山的梭嘎社区同样未能幸免。梭嘎的一部分苗族同胞不再身着本民族服饰、不会说民族母语、也不再坚守本民族的信仰,异样的文化样态不断涌现。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转型社会,生态博物馆作为工业时代的审美文本,生活的审美化迫切地关乎人的生存问题。梭嘎苗民作为乌蒙山区经济社会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参与者,这一特殊文化坚守的族群正面临工业化严峻的考验。在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织、远古记忆与当下困惑、未来守望与现实图存中,文化基因发生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深刻裂变。长角苗的常态生活行为艺术,以一种社会的畸变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族群内外的矛盾冲突、焦灼与期待。 (三)多元化时代的生命美 诞生于西方19世纪末重要美学流派的生命美学,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考察为轴线而展开(王振君,2009),展示人的生命过程和呈现人生境界。生态美学作为自然、社会、生命三个维度的审美价值追求饱含着生命气息,在生命美学那里,呈现出身体美学—生存美学—生态美学的有机统一。美学价值建构中,身体作为生命的现实存在,具体处世表现为生存,生存的现代样态实为生态。长角苗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以生态可持续性、循环性给人以及给人存在执着关注和深层关怀。在多元文化时代,探究长角苗原生态文化生态美学,则发现潜藏在民族文化下的诸多生态智慧及审美理念。那就是通过民族节日、服饰、歌舞及丧葬等形式把原生文化的生命美、生命力展示出来。无不渗透着独特的生态美,构成了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的基质,以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动态平衡性及自生娱乐性表现出来(杨昌鑫,2010),彰显特殊地域文化生机活力。 三、脆弱生态、诗意栖居、诗画生存中长角苗文化的生命美学色彩表达 (一)自然生态环境中壮美的生命色彩 在长角苗源远流长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价值世界里,其独特的生态存在美学观呈现出浓郁的大地美学色彩、生命美学色彩和主体间性色彩。独特的审美观念与宗教观念、生活观念交融为一体,洋溢着的生命美贯穿于苗族文化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及社会生命中。自然的纯美、壮美,以一种明快的自然生命色彩展现出来。生活在箐林中的长角苗尊重爱护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命,以朴素的自然观构建一个诗画生存的文明世界。从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角度讲,苗胞们把对生命的挚爱和追求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不仅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生命最为质朴的理解,更保存了先秦时期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思想。通过村规民约较好地维系了社会和谐,使一个处于夹缝中生存的民族支系非但没有灭亡,反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创造出田园诗般的生活意境。通过个体生命、生命意志、社会价值的共生互动,实现生命意志与历史、宇宙的统一诠释着生命美学的最高境界。#p#分页标题#e# (二)社会生存环境中的生命色彩 1.族群内特殊的社会体系建构 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长角苗”家庭,民族内婚制成为维系长角苗村寨亲情关系的纽带。在长角苗社区,大小事宜自有寨老、寨主、鬼师这类自然领袖做主;他们事无巨细,各司其职,条理分明地对这个文明而蛮荒的古老村寨实施有效管理。在长角苗家庭中,财产继承权与传统家庭有着很大的区别。即财产不由长子所有而为小儿子来继承,包括父母的房屋土地、生产工具、牛马等大牲畜只能给小儿子。相应地,小儿子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他兄弟也有瞻养义务但不直接承担。族群内还有“三限”“五限”之分(周真刚,2006),经济社会地位最低层的苗族家庭为“三限”,较高家庭为“五限”。改变的现实与无法改变的历史共同建构长角苗社会,地位尊卑和等级观念具有浓郁的宗法制生命色彩。 2.天人合一的道法自然 尊重自然诗意生存作为长角苗审美化的外在表象,已成为一个重要方式和精神追求,和谐、友爱、自然、以歌教化的文化生态是个人得以社会化的一个途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构的一种非功利自由的和谐社会,实现人是自然的终极目的。长角苗苗胞们遵循的“生态平等”原则,将整个生态系统中人与万物的平衡态实施了科学的理性升华。审美化生存维系了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人性回归和终极关怀。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日益恶化的今天,诗意栖居中的“天人合一”,这一人类的美好愿景在长角苗社区得到了很好体现。审美化生存崇尚生态自然,不仅有充满令人身心愉悦飘扬着无拘无束的心灵牧歌;而且还营造了一种真实的“世外桃源”般意境,让人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感知生命中明快的亮丽色彩与高雅和谐之美。 (三)族群文化中的生命色彩 1.“写”在头发上的历史 据说,清初苗民先祖为躲避战乱逃到贵州西北部的六枝、织金、纳雍三县交界的箐林中以狩猎为生。生活在箐林中的这一苗族支系,因而被称为“箐苗”。当时为吓唬森林中的野兽,人们在头发中扎上牛角状的木梳,再在木角上用麻线、毛线、长发等假发盘结成以“∞”字形状的硕大发髻;头发重者2公斤有余,披散下来竟有3米。最早只有苗王才有这种象征权利和威严的头饰,今天成了这只箐苗的标志,并在硕大头发上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使发型显得庞大,妇女有保存先民“髻首”(椎发)之俗。每天把梳头时掉的头发用麻线编织起来,作为嫁妆传给闺女一代一代传下去。如今,女子仍用木梳,而男子不再戴角以头包青帕取代。 2.刺绣、蜡染———服饰中鲜活的先辈记忆 长角苗服饰色彩以红、黄、白为主,古朴艳丽,再配以硕大的头饰,看上去极像美丽的锦鸡。头饰为锦鸡的鸡冠,燕尾服一般的长披风,则是锦鸡美丽的尾巴。妇女上穿前襟至腰、后披至小腿的对襟上衣,下穿镶有花条的百褶裙,腿裹羊毛护腿,脚穿挑花鞋,头戴“V”状的木梳,配上雍容的头饰具有一种“公主”般的气质。妇女们的百褶裙色彩斑斓,背后沿腰际下垂的绣片花纹由千针万线组成,长长的绣片与短装上衣连接在一起。走动起来镶花的百褶裙如同一首优美的乐曲,极富韵律地晃动着,似乎在无声地吟唱千百年经久不衰的古歌。裙下隐约露出的白毡与桃红与天蓝色正好相衬,不仅展示女子美丽与聪明才智,更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过去,女孩五六岁就要开始学习绣花、八九岁时便懂得操持着学蜡染。一辈子最得意的是为自己亲手做的新娘妆,一般在十二岁时开始做直到出嫁前。个个都是画蜡高手,绘图仅凭头脑构思、手工绘画,所画直线、平行线、方块、圆形等图案规范而精巧,堪称一绝。很多绣品图案都以十二为单位,以红、白两色为主,辅以少量黄绿色的十字绣针法。一来象征十二生肖,二来象征梭嘎乡十二个长角苗村寨团结友好形成的地域文化奇观。 3.跳花场———独特的婚恋方式 男女青年谈恋爱,是从每年的正月初四到十四“跳花坡”走村串寨开始。此时小伙们身着盛装,拿上芦笙、口弦和三眼箫等自己擅长演奏的乐器,相约在寨中或别的村寨“走动”,找姑娘们说笑嬉闹、唱情歌。姑娘们穿上艳丽的服装,戴上长长的木角头饰、项链帕子等待小伙子上门来。小伙们一般隔着门与姑娘对山歌,小伙输了姑娘把门紧闭;如赢了姑娘打开门邀请进屋并向老人磕头,老人留吃留住与女儿对歌加深了解。要是天气晴朗,姑娘与小伙子们会到山坡上放开唱;男子吹奏乐器女子则唱歌应和着,数回合以后男女再开始对唱,如双方都有好感将互赠礼物。正月初十这天,也就是跳花坡节的最高潮期,恋爱中的男女必在这天围绕花场中的花树转上几圈,寓意这样的恋爱过程才完美。所有的歌舞表演全部由乡民们自己伴奏、歌唱,大部分节目是用苗语演唱,周围观众合拍共鸣。整整一天,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尽情地狂歌劲舞,度过属于他们自己最美好的节日。 4.“打亲”———别样婚礼进行曲 长角苗恋爱方式自由随意,但婚姻必须严格按规矩办,礼节冗长而繁琐。需履行各种“求亲”程序,比如媒人“说亲”,家长和寨老审查后“定亲”,婚礼进行时“打亲”。特别是婚礼进行时的“打亲”,主要是打媒人;进娘家与接出娘家,媒人都要挨娘家10来名姑娘们摆开“长蛇阵”的3次“痛打”。直到媒婆讨饶不已女方家这才作罢,方能使迎娶新娘的队伍上路。这时,新郎向新娘家长辈一一叩头,说些把新娘带走请父母放心之类的话,长辈也要叮嘱一番。据说打亲越厉害,姑娘到婆家就越得到好待遇,婚姻才能天长地久与幸福。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这一“习俗”,传递着世间质朴而浓烈的亲情、真情与挚爱。#p#分页标题#e# 5.“打嘠”———生命中的祈愿与人生归属 长角苗是一个特别重视死亡的族群,每一次死亡仪式都是与远古祖先进行心灵交流和沟通,是一次全族人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复习。在无数次演练中,不断强化民族记忆巩固群体意识。通过丧葬仪式,将远古逝去的祖先与现世家庭、族群凝固成一体;借助这种信仰和历史记忆,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得到完整保存。长角苗隆重的丧葬叫“打嘎”,灵堂叫“嘎房”,意为老人成神,把老人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打嘎”有极严格的规矩:死者必须是正常死亡,少年早逝者、暴病或遭祸殃而死者都不能进行这种仪式。老人过世,用“刺竹”的方式记录各寨亲友送馈赠的礼物和礼金。事毕当着死者和众亲友将礼金和礼品“报账”,无异议则烧竹毁绳,让死者到另一个世界勿忘众亲友的关怀,体现生命中的纯净与终极关怀。 6.神秘的祭祀与价值信仰 祭树节是农历二月第一个龙日,在寨子附近的茂林里寻一棵最古老高大的树作为祭祀对象。全寨人家凑集猪、鸡、粮食,等待鬼师或家师念完咒语后,接着在树下挖坑埋下4~5个装满水的土坛子,然后用石板盖住,此刻外人不得窥视,族内人也不准随便走动,妇女更不得参加。接着在树下祭祀,杀红毛公鸡请祖先享用并祈求保佑。事后全村所有男性痛饮一回,祭树方告完结。祭山节在三月第一个龙日举行,程序与祭树节一样,只是鬼师或家师要将埋下的水坛打开,观察水的盈缩,以预兆当年收成和祸福。众多祭祀充分展现梭嘎苗民生活中朴实无华的生命色彩是如此的淡雅有度。对山的敬畏、对树的虔诚,对人的纯真,对命运的不屈、以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信仰与山地文化景观。 四、结语 存在主义讲生命的过程就是生老病死向死而生,正好揭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天人合一思想、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命题、情景合一的美学命题等跟生命密切相连之关系(范明华,2010)。通过生态危机与生存原则对脆弱生境中的长角苗生态美学、生命美学加以思考,将在更深层面和更广视域增强学术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增强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积淀观照生态美学,让人看到了一个世居民族生命美学的理论疆域,使这一活态文化遗产的生命色彩更加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