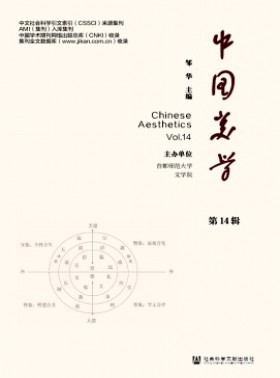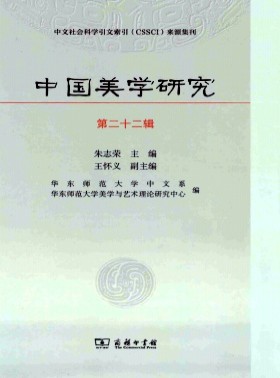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美学发展下的诗歌翻译,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因此产生了“作者中心说”;20世纪异军突起的英美新批评及俄国形式主义乃至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推翻了读者对作者信任的“作者中心说”,认为文学主角应该是“文本”,提出了“作品中心说”。这些学说的概念也影响了诗歌的翻译。传统的诗歌翻译理论坚持文本的第一性,诗歌翻译追求对原著的一种客观再现,把原文本作者看成是文本之父、意义之源,而对译者的主体地位及译者原有知识、经验、文风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较少言及。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负载着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文本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对象化、符号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召唤结构”。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等不同,从而形成了迥异的期待视界,也为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生成性,因此,翻译应该是作者表达与译者的期待视界相结合,以原文本作为媒介的完美互动,最终实现译本的多元创生。
一、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姚斯(又译尧斯)、沃·伊塞尔等。两位中坚人物分别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和《文本的召唤结构》,于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从此进入文坛。
接受美学以解释学、现象学、美学等为理论基础,其根本特征是把读者放到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重视读者与阅读接受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当时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研究由作者转向文本,再由文本转向读者这一大背景契合,因此当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理论一出现,就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1]
(一)“读者中心说”
在姚斯看来,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者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作品的存在与读者的阅读阐释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不经读者阅读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语词材料。
读者以阅读实践使作品从语词符号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意义。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文本最初由作者创作,并赋予意义,随后读者给文本注入了新的意义,作者原意渐渐湮没,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逐渐被丰富、充实并展示其价值和生命。
(二)“期待视野说”
阅读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在文本进入读者阅读之前,读者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所谓图式就是一种认知结构,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前结构”,而姚斯的接受美学术语则称之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姚斯的期待视界就阅读而言主要是指阅读前读者所拥有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等,包括对文学作品类型和标准的经验性掌握;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把握;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带入的是对生活世界的心理体验。
(三)“召唤结构说”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在了第一性地位而将文本放在第二性地位。伊瑟儿提出了“隐含的读者”一词。在他看来“隐含的读者”既非现实的读者,也非理想的读者,而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既体现了本文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2]206-216。意义的预先构成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伊瑟儿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召唤性,召唤性源于作品中的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期待视界与文本的差异所引起的心理空白就构成了文本的“召唤结构”。“召唤结构”无疑会激发起读者的创作冲动即潜在性的实现,这样读者的主体性就最终凸显出来。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集中反映了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惊人的交叉重叠性。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本和文本的意义、作者和作者的意图、理解的心理过程和思维过程、理解的主体(即读者)、主体在理解过程中的参与作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如评论文章、普通读者对理解对象的接受效果)与作者或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而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原作者和原作、理解的主体(包括原语读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主体的理解过程(特别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活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和原作者(或原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译作和原作是否等值,是形似还是神似,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或原作者,目的语读者阅读译作是否与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效果等同)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文本是否具有开放性,译者对文本的翻译是否也可以有译者主观意识的积极参与[3]。因此,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翻译问题的解决。接受美学从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当下的诗歌翻译提供了诸多启示:翻译应结合译者的期待视界,体现译者对原文本意义的主动建构,同时也应反映以审美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一)认识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
诗歌翻译同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在原文本进入译者翻译活动之前,译者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即“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
译者所拥有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等,包括对文学作品类型和标准的经验性掌握;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带入的对生活世界的心理体验等都被译者以已有思想、文化、知识与经验等所形成的阅读模式带入对原文本的认识、理解和阐释当中。译者的期待具有选择、求同的定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译者的期待视界已经预先决定了译本的最终产出。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关于看古松的不同态度:面对田园里那一棵古松,木商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他读解的是实用价值,是谓译其善;植物学家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心里决定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们何以活得这样老———他读解的是科学规律,是谓译其真;画家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他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55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他读解的是美,是谓译其美[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期待同样具有选择、求同的定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译者的期待视界已经预先决定了译本的最终产出。#p#分页标题#e#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把整个世界给了黄昏与我。
郭沫若译:暮钟鸣,昼已暝,牛羊相呼,迂回草径,农人荷锄归,蹒跚而行,把全盘的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丰华瞻译:晚钟殷殷响,夕阳已西沉,群牛呼叫归,迂回走草径,农人荷锄归,倦倦回家门,惟我立旷野,独自对黄昏。
三位译者的期待视界、审美角度不同,在表达形式上有一定差异。前两位的译文在情感表达方面表现的不够强烈,而郭沫若译文的一个“独”字与教堂的晚钟声、夕阳组成了一幅画面,很好地表现了老农内心的苍凉感。
(二)本体论:走向意义生成的译者
传统诗歌翻译认为原文本是客观的,翻译就是对作者意图的理解和再现,追求一种客观、普遍理解,以原文本为第一性,置译者的期待视界于不顾,扼杀了译本解读的丰富生成性。实际上,译本的意义应该是原文本和译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原文本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与意义的空白,召唤不同译者依据各自的知识、阅历、观念做出相近、相异的解读,这就是伊塞尔高度重视的文本“召唤结构”。文学作品是一个充满未知和空白的、并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来加以填补的未定结构,文本唤起译者的期待视界并在翻译过程中使之不断更新。翻译是在译者的期待视界和原文本“召唤结构”的互动中完成,翻译过程就是译者的期待视界与原文本潜在意义相互激发、构建的过程。诗歌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为创造的主体,逐步走向译本意义生成的前台。
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平衡,避免两种偏误的出现。
一是要重视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与功能,并加以合理发挥和利用。在一些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译者期待视界的译文所存在的问题。如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翻译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比较。
译文1.Seek,seek;search,search;Cold,cold;bare,bare;Grief,grief;cruel,cruel,cruelgrief.
译文2.IlookforwhatImiss;Iknownotwhatitis.Ifeelsosad,sodrear,Solonely,withoutcheer.(许渊冲译)译文1的直译版本看起来象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词语堆砌,虽然有评论者认为这是“译文形式与原文内容辨证的统一”[4];而事实上由于译者期待视界的缺失,没有让原文本的审美意义得以再现。许均认为:“……在文学翻译这个领域,绝对的忠实是行不通的,愚忠的结果必然导致死路。
译出的东西非马非驴,读者读不懂,与原文看似相等,实则相去甚远,传了形而走了神。”[4]译文2第二行说“不知寻觅什么”,是译者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结合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对原文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在前三行里出现了四次“I”,两次“what”,后两行中连续有三个“so”字结构———sosad,sodrear,solonely,与withoutcheer形成一体,强调了心神无主、愁绪满怀的苦闷。译者通过结合文本本身所想传达的意境和自己的诠释,刻画出一幅人倚黄昏、细雨洒窗愁更愁的秋景。整个译文自然流畅、主题明确、富于旋律美,再现原文本的情感意义。译文2显然比译文1更能体现原文本作者意义与译者期待视界结合的产出效果。可见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与功能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并加以合理发挥和利用。
二是要防止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过程的滥用,导致一种过度诠释而丧失了作品原有魅力。
有一些翻译由于太多专注于译者本身的理解,翻译完全以译者的理解为基准,意译失去了对原著的体现,从而导致一种由于过度诠释而造成译文脱离了对原作者的意义诠释。如:对李商隐《乐游原》的翻译,有的译者基于自己的理解想采用一种散体的形式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原文:“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译文:It’salreadylateintheday.Nonetoohappy,Idriveouttothehistoricfieldsborderingtheim-perialcity.Whataglorioussunset!Itwouldbeperfectiftwilightwerenottofollow.译者的翻译脱离了对格律体诗的翻译框架,使得译文看起来缺乏诗意且又松散寡淡,没能把原作的韵味体现出来。因此,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期待视界的介入应在一定的限制之下,不能脱离原文本的意义。有人把翻译比喻成“戴着镣铐的舞蹈”,也正说明了原文本、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
(三)价值论:多元价值系统的创造
译者不同的期待视界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预示着对文本解释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就文本本身而言,“文学作品也不是一个单元的价值载体,而是一个负载着以艺术(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2]267-268。对于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者的期待视野不同,也会对这一作品进行新的认识,翻译应注重对原文本共时和历时的考虑。因此,对原文本的翻译应该是一个开放、生成的过程,是译者个体精神与原文本潜在性的激荡、融合的过程。
译者应该放弃对原文本理解的惟一性、确定性追求,用多元、开放的眼光容纳其它不同观点的响应。
即当译者原有图式与原文本出现审美距离而不能同化文本时,就要求译者必须打破先前的习惯模式,调整视野结构,以开放的襟怀去接纳新事物。
在自己期待视界与其它多元视界两者对立、统一的过程中用超越静态、发展的眼光观察各种现象,不断提高、扩大译者的期待视界。
三、结语
诗歌翻译不仅是译者对原文本的一种简单的语言重现过程,也是一个译者与作者以原文本为媒介的对话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再现,也是译者对原作的一种加工、再度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潺入了译者自己的文风以及见解等个性化的内容,是作者原作与译者期待视界相遇的结晶。在诗歌翻译中,一是要重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重视译者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与功能,并加以合理发挥和利用;二是要平衡原文本和译者之间的互动,防止译者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过程的滥用,导致一种过度诠释而丧失了作品原有魅力。唐述宗先生在《也论译文能否超过原文》曾评论道:最优秀的翻译家虽然有能力写出比原文更优美的文字,但他们并不应该试图超过原文。因此,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己对原作的诠释,自身的创新加强了原作,使译文的意义通过译者和作者在以原文本为媒介对话和交互中更好地体现出来。#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