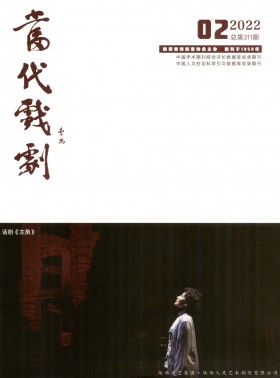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当代教科书的发展回顾及展望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我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属于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尽管有些夸张,但并不无理。
(1)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广狭之分所谓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宽泛和精确之分。宽泛之言,伴随着新式学堂课本的出现,一直往下走,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约在1897-1926年之间,可称之为黄金30年。精确一点说,这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904-1923年之间,从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产生,到奠定了现代学制基础的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出现,约20年黄金发展时间。我们持宽泛说,因为我们很看重在1904年现代教科书出现之前几年的学堂自编课本(以1897年南洋公学课本为标志),这可视为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启动时间,也看重1922年新学制后多种相应教科书的全面完成时间(1926年前),所以粗略的认为是30年,提出“黄金30年”的概念[5]。事实上,当今教育研究界特别是教育史学界,普遍公认南洋公学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多项开端意义,也比较看重到1927年的教育发展时期。比如,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2001),就将“壬戌学制”的推行实验期定为1921-1927年。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1997)把1915-1927年定位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时期。台湾学者陈启天著的《近代中国教育史》(1979),将1919-1927年划分为“新教育运动时期”。均说明这一时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
(2)教科书黄金时期的成就、影响与表现在教科书的黄金年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尤显辉煌。成就一,传统旧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教科书对教材取得全面胜利,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新式教科书体现出了对旧教材的极大优势。“四书五经”等在传统教育里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难“传之于人”的文本[6]。所以,在1903年新学制颁布、新学校普及、新课程实施以后,这种不分科、不分年级,不顾教与学、只重灌输的旧教材已经暴露出它的不适应性,理论上它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新学堂教材继续存在的基础。即便旧学人也不得不承认,新教科书注重方法“,使人一见而能”,此为过去所无,所以即便需要学习传统经典,也应该按新教科书编之。这相当于明确承认新教科书要优于旧教材[7]。基础不存,开读经课等各种抵抗均无济于事了。一味灌输的传统旧教材敌不过按照西方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教、也关注学的新教科书。旧教材被取代已经水到渠成,大势所趋了。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在文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以“教科书”全面命名的狭义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读本向教学结合的教科书文本的转型,传统广义的教材不得不迅速退出。成就二,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现代教科书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以普及。没有海量教科书,任胡适等知识分子如何呼号呐喊,白话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同理,没有白话文,现代教科书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迅速大规模被大众接受。尽管今天普遍认为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最早推动白话文实践的是教科书。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书室。早在19世纪末,这家规模不大的书室就编印了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研究者认为是清末民初白话教科书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物与机构之一[8]。
1903年开始,彪蒙书室编写出版白话读本蒙学丛书,包括《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系列等,据统计,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以白话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9]。事实上,由于西学中的科学教科书的传入,一些学科门类、一些科学公式、一些科学名词、一些科学符号在中国传统教材文本中很难呈现(试想一下,英文教科书或化学分子式要被中国传统文本的竖排方式理想地呈现出来有多么艰难),所以,白话文及其排版很早就在以量取胜的部分教科书中出现了。到1922年学制,所有教科书使用白话文。反过来,白话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书的流传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三,建立了教科书最重要的制度———教科书审定制,理性地对待国定教科书,从而使之成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为后来的教科书使用创设了榜样。当教科书大量涌现后,清学部首开教科书审定之风,民初教育部并没有让这一教科书事业中最重要的制度断裂,而是不断完善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审定蔚然成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尽管晚清学部自己编撰了国定本教科书,但在听取多方意见后,并没有(或有所顾忌)一意孤行地以政治与权势强行让自己的课本进入课堂,更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间教科书的存在空间。中央学部没有赋予自己费尽苦心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以使用的特权,而是依市场法则,高度赋权给地方、学校、校长和老师,把教科书选择权交给他们,质量优先———这一做法开了限定国定本教科书的权力空间的先河,明确了国定本不是垄断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局面,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这一优良传统对后来民国教科书制度都有重大影响与约束,有限的几次国定本也是在这一权力限定中展开的。进入全面抗战后,尽管这一非常时期需要统一教材,但中央政府在编撰好教科书后,也并没有指定某一家出版机构(包括中央自己的官方出版机构)来专营教科书,而是由多家出版机构共同完成。在三大直接成就之外,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19~20世纪之交,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国家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一批最不能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一本本教科书促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传播了各种新思想、新学术,启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孩儿。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前期之所以是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思想活跃、流派纷呈的时期,之所以是社会变革大起大落的时期,这是与输入思想准备舆论的新式教科书的大规模传播密切关联的。仅以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为例就可窥见一斑。章开源先生曾经为戊戍变法的失败找原因,提出“:百日维新是幸逢其时而不得其人。”[10]#p#分页标题#e#
其实,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幸逢其人而不得其时”。有皇帝、有康梁,难道还不能说“幸逢其人”?但为什么说“不得其时”呢?这因为新教育未开,新教科书未大规模传播,人们没有被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所触动,没有发现还有另外的制度、政治与社会。甚至在士大夫精英中,有新思想新知识者也寥寥无几。此时,任变法者的维新诏令雪花般飞舞,也只能看作主观的一厢情愿。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民众还没有准备好,心态、文化、思想、观念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变法。所以,不管是谁,都无法完成这场不能完成的变法,它失败得如此迅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几年后情况就变了,1898-1911年,几乎是新思想新观念如火如荼的涌现时期,教科书则把它们传播到千家万户,由此推动了近代中国群众性的启蒙高潮的形成。严格说,辛亥革命更没有“幸逢其人”的运气(武昌枪响时,孙中山还在大洋彼岸,黄兴也是半个多月后赶去武昌的),但它有幸“得其时”———民主、自由的思想,宪政、共和的观念随着海量的新式教科书铺天盖地而来??,民智为之而开,民心为之而新,武昌的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全国各地已经插满了革命的旗帜,读书声成就了枪炮声。“五四”运动之所以一呼百应,也有这一道理蕴藏其中。1912年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中仅《共和国教科书》10年间共销售7000~8000万册之多。还不包括大量形形色色的手抄本、翻刻本、盗版书。较之于教科书,《新青年》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作品的发行量简直就算不了什么。
据统计,《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从创刊时的1000册增加到1917年时的15000册左右。没有资料显示更大的发行量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许多被认为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就发表在该刊物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等。从发行量上看,至少当时这些作品的影响面还是有局限的。没有教科书的普及,就不会有大量学子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也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的普及。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广大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正是浅显易懂、深入千家万户、绝大多数人能够读到读懂的小小课本,而不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们犀利的著作与学说。除此之外,教科书黄金时期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是教科书数量和品种的丰富多样。在这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思潮与教科书的发展激荡辉映,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教科书铺就了30年发展之路。数量上、种类上都创造了中国教科书之最,质量上也达到了中国教科书发展的高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教科书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知识精英关注中小学生那小小的课本,多种类、多形式的教科书如潮水般涌进大大小小的课堂,被千百万学童捧在手中,由此达成了思想启蒙上的高峰。当时那种学术自由、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氛围,令繁星般的单品教科书与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大型成套教科书双轨并存,单品教科书特色各异,大型系列教科书气势开阔,手笔恢弘,颇显今日学者期盼的中国教科书气派??。尽管我们发现,在教科书发展的这段岁月里,教科书编撰的专业门槛比较低。产生的一些教科书非常粗糙,没有系统,没有规范,甚至错误多多。但是我们认为,对教科书这一新起的学术领域来说,这不完全是坏事。相关教科书大量涌现,尽管鱼龙混杂,却竞争性强,你进我退,危机意识强,更新换代快,使得这一领域保有必要的动力与活力。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这种混杂但生机盎然的时代,才能得以冲破僵化的旧教育的束缚,才得以突破传统旧经典的羁绊,才能适应社会文明的大变革,才能够吸引大量关注教育关注学童的组织与个人加入到教科书建设领域。这是中国教科书史上罕见的时期,新式教科书风起云涌,为重建教育和启蒙思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百年中国教科书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以后,特别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进和党义教科书的出现,教科书就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甚至沉闷的时期,意识形态控制日益强化,教科书黄金时代结束了。
后半个世纪的脚步:迈向一个多样化时代
1949年后的时期,可以划分为新中国17年、10年和改革开放后3个大的发展阶段。
1.教科书全面统一与规整阶段(1949-1966)
这是迅速结束新政权产生以前的一切教科书的时期,是用全新的教科书占领课堂的时期。1949年前教科书的遗产和传统对革命者而言应尽可能束之高阁。他们必须尽快地以统一的新政权思想与话语的教科书取代过渡过来的包括国统区、根据地解放区等各种背景的教科书。旧的遗存荡涤一空,新教科书横空出世。这一时期,新中国教科书出色地化解了社会急剧转变后带给人们的震动、不安与茫然,引导人们对正在兴起的共产党政权的发自内心的拥护。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科书而言,那个时代不主张柔情不主张多元,是反对个体的,它呼唤群众运动,呼唤统一、跃进、高昂、激情、美好、乐观。在整个1949-1966年这17年里,教科书编著者们经常面临各种困惑、困难与压力,来自不同力量(比如苏联与本土、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博弈没有消停过,这些博弈又微妙地影响甚至主导了17年教科书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时间段里,来自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它的冲击下,曾经让本土的教科书(甚至教科书的最高管理者)尽失颜面。1950年代初期,地理教科书在检讨、物理教科书在检讨、为《背影》入课文在检讨,文学与汉语教科书被否掉了、五年制小学教科书被否掉了。一个时间段里,集权与教科书的规整是至关重要的,它所向披靡,除了中央官方出版机构的教科书外,一切其他教科书被逐出课堂。一个时间段里,放权与教科书的实验如出闸的水奔腾向前,地方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各种学制实验教科书,全面开花,在17年统一、通用、国定教科书高歌猛进的路途,闪现了不长时间的一段难以忽略的、余味无穷的风景。这些探索给教科书建设带来了全新的主题、叙事方式、文本语言与编撰模式。但从长时段来看,留给教科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印记之一是自有现代教科书以来第一次全面清除了中央官方教科书以外的所有教科书,民间教科书彻底退出,地方的官方教科书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往往处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位。这样一种高度控制和垄断教科书的策略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某些问题纠缠了我们半个世纪,而且还会纠缠下去。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弱化了课程标准的威权性,过度强化了教科书的作用;二是无法适应千差万别的地方和学生差异,导致一则精英不能脱颖而出,二则教科书难度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措犹如钟摆,一刻也没有停过,一刻也没有均衡过,历届教育部没有摆脱这个阴影的缠绕,被这个问题纠缠了半个世纪[11]。#p#分页标题#e#
2.10年“”教科书阶段(1966-1976)
这是对正统意义的教科书进行彻底革命的时期,是全面构建红色革命课本的时期。对于受教育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10年“”教育是历史记忆中难以忽视的部分,那红彤彤的课本是那个时代革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具象。它把意识形态的演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把革命课本的渲染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课本比课程更加激进而无所畏惧地尝试着学科综合、知识与生产的结合、理论对实际的迎合“;”通过工农兵对课本的生产,使得“教科书”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平民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去权威性“;”课本封面和插图人物男的高大勇猛,女的丰满威武,适应特定的政治美学需要,也构筑了特定的教科书政治美学。红彤彤的课本成了非常年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它构建了崭新的一种教科书样式———一种革命版教科书。这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理念的标本,这一标本是对传统经典教科书的彻底革命或否定,尽管这一标本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嘎然而止,但它的方方面面:它的样式是那样的鲜明独特,它的话语是那样标准化且充满着火药味,它结构的雷同和奇特,它的生产者那形形色色的身份,以及它关注生产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便是那样的极端和功利),都具有教育史的经典意义。
3.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77~今天)
这是教科书统一与多样微妙博弈的阶段,是中央与地方均衡教科书权力的阶段,是最终初步形成了在统一要求下的教科书多样化格局的时期。以20~21世纪之交为界,又大致可以细分为两个亚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教科书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既有生机勃勃的局面,如8套半教科书的改革、实验教科书、地方教科书和乡土教科书的迅猛发展等(遗憾的是,这个局面没有延续下来,更没有被发展完善);也有相对单调的时期,因为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或动荡,总会迅速影响到教育,而教育上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教育内容的变化,这就必然集中体现在教科书的变化上(1990-1991年前后出现的大规模补充教科书———似乎原来的教科书不足以确保意识形态的稳定———就是教科书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教科书代表国家意志”的思想落实在主流的、垄断的教科书上的政策,以为高层出面一家垄断就一定能够编撰出“最好的教科书”,以为通过这“最好的教科书”就一定可以最佳地规训一代年轻人的主观意志,最终导致较长时间徘徊在没有为教科书制度史留下多少特别值得可圈可点的贡献的局面。整体上,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的教科书仍然具有鲜明的两大特性:一是泛政治性。背记,无休止的背记,而背记是与灌输密切联系的———这时期的教科书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它最标榜的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二是突出的垄断性和单一性,多样化进展缺乏制度设计与制度保障。即便是偶尔的、点缀意义的教科书多样化尝试,也在所谓通用的、统一的、国家的教科书等权威性说法面前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卑微,发行量和普及面上的绝对优势不证自明地成为了教科书质量的绝对荣誉,而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这些教科书的信赖。确实,教科书发行量一般可以被看成是与其质量成正比的,但如果这个数量是外力干预的,是因为绝无选择的可能与空间,那么这个数量不再附有质量价值。教科书的贡献并不能简单地以强制的发行量大小为准则。
进入21世纪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席卷全国,课程改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制度上把教科书建设推上了新的平台。过去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纲一本”的局面被打破,以多样化为标志在教科书发展史上有声有色的一幕掀开了,同时展开了对中国教科书现代化历程的强有力的制度性升华———走上了一条回归多样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在课程改革中看到的一幕,只有在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黄金期间才似曾相似:才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教科书发展行列,才调动起社会如此庞大的能量加入到教科书的建设之中,才让这么多学者专家如此微观如此细致地关注到课堂关注到学生。百年前教科书发展的一幕于不经意之间再次在百年后掀开。只是,这是一出在统一要求基础上的多样化的大戏,也和百年前一样,是缺乏强力制度保障,因而可能说变即变的大戏。我们已经注意到,经过“”后30年的发展,即便是21世纪10个年头过去后的今天,教科书多样化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以“传递国家意志”为标榜的“主流的”“、示范的”、“国定的”教科书声音不断回响,前行中的曲折与反复说来就来。在内容上我们认为,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曾经热衷于培育信仰、形塑思想、期盼理想,歌颂新的领袖与国家,建设新的社会与生活,对历史的继承与人性的尊重不太关心(这到60~70年代达到极致)。那么21世纪的教科书则对培育信仰、形塑思想、期盼理想之类的心灵培养已经没有强大的兴趣或能力了。这是一个要求最低限度的精神淬炼和鼓励最大限度的自我张扬的教科书时代,缺乏人心的敬畏和震撼,但充盈着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的关照———在教科书史上似乎还是头一回。对它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在制度上我们主张,在规范性与开放性之间,在统一性与多样化之间,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给开放性与多样化预留足够的空间,对地方进行必要的赋权,而不是追求垄断性的国定教材的“一统天下”,这有利于本领域永远保持一种“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简要展望
我们认为,100多年教科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前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发展史,是由开放、发散、学术自由慢慢走向意识形态强化的阶段,而后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历史,是一个由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渐向强知识、科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现代教科书正进入后现代教科书发展阶段。它将有3个重要标志:其一是教科书形式的革新。这与科技的革新密切相关,特别表现为互联网的出现。在传统的纸质教科书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电子教科书,并正在进入学生书包———电子书包。其二是教科书性质的变化。未来社会,教科书的政治色彩将会淡化,教科书发展将会越来越由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向强科学话语体系转变,纯知识的传播价值也弱化了,非知识的比如创造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素养的培育将在教科书中日益突显。其三是教科书意义的变化。互联网时代,教科书传播甚至垄断知识的作用下降。教科书被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知识传播的渠道,学生非常方便地获得教科书的内容,获得教科书的解答,获得教科书内容的链接与扩展。此时,教科书和非教科书的边界模糊,教科书和非教科书之间的关系走向了微妙的交往空间。教科书无处不在;教科书信手可得。以往学生主要依赖教科书获得知识的传统被打破了,以往教科书生产者不太看重使用者的传统被打破了。使用者会让生产者高度紧张,如履薄冰。互联网时代,教科书的标准性和权威性被大幅度瓦解。教科书将越来越频繁地接受挑战和质疑甚至批判,这些挑战质疑和批判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教科书不再只是作者、不再只是专家、不再只是教师的“言语”,而是可以在公共语境中被任意阐释的“语言”。谁也无法让教科书神圣化了。谁也垄断不了教科书了。教科书的权威将不断被大量制度上的非教科书所消解。教科书教者和学者、教科书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界限都被打破了,使用者可以成为生产者,学者可以成为教者。#p#分页标题#e#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所谓平等、对话、生成、用教科书教、教师是资源的开发者等等都是后现代思想对现代传统及教科书权威主义、教师中心、课本中心的反叛;是一个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历史———教科书的神圣地位逐渐被打破,人们对教科书的反思、批判加强。教科书是圣经,只有被记忆的可能,没有被反思批判的空间,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教诲,而今天这一点已经瓦解,教科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了参考性的,生成的,是为师生对话提供的道具。传统的极具权威性的教科书之死的阶段到来了,我们对之研究很少的新教科书时代正蹒跚而坚定地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行动与灾难赛跑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行动,互联网将替代我们行动,那将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结局。注释:??我们认为,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当时的中文名翻译称为“益智书会”而不是“教科书委员会”就是明证。“Textbook”以“益智书”对译也说明还没有使用“教科书”一词。事实上,19世纪70~90年代中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以“教科书”命名的实物,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当时一般称之为“课本”“、读本”“、启蒙”、“须知”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教科书”的书。??比如,1904年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一经出版便势不可当,发行后几日内便被抢购一空“,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1996年,第111页)。有传教士惊叹:商务印书馆“所编印的优良教科书,散布全国”,而对比维新运动时康有为那慷慨激昂的“公车上书”,也只能影响极为有限的部分学子。??以《共和国教科书》为例,它是民国元年根据中华民国新政体的要求由商务印书馆迅速推出的,该大型教科书系列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初小教科书及教授书20种140册(含挂图24幅),高小25种118册,中学36种53册。又如民国于1912年成立,中华书局同时成立,但到1913年初,中华书局就编撰出版中华系列教科书满足了民国学校的需要,其中小学教科书18种74册,小学教授书10种47册,中学教科书21种。普通的民间出版机构(其中一家成立才几个月),短时间适应新要求而编撰出涵盖了中小学、文理各科的这么多的教科书,实在可敬可佩,几乎难以想象,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以国家之力一家独大的出版社,也会汗颜的。
本文作者:石鸥 刘学利 单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