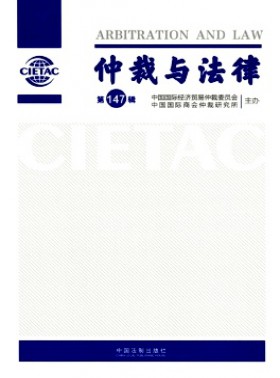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法律推理的基本特性,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法律推理是法学理论尤其是法哲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法学界和逻辑学界一直十分关注对法律推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我国的研究传统中,一直把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进行讨论,演绎三段论对法律推理有效性的保证是法律推理的重要表征之一。但是,随着我们对法律推理各个环节的展开研究,以及逻辑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或赞成法律推理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推理活动。 问题的讨论从法律推理的基本特征开始。1832年,奥斯丁著名的《法理学问题》中明确主张了法律命令说,把确定性视为法律的生命,认为法律规则和决定是直接从立法、先例中演绎而来的,法院的司法作用仅仅在于运用逻辑推理中的三段论方法将明确规定的法律适用于案件真实。[1]38在这样的观点下,法律推理呈现出严格的形式推理①特征,以成文法的法律规范或司法先例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司法审判的结果。三段论中的各项规则被严格保证,前提真,推理正确,结果也必然为真。 问题在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确定的法律规范,事实和价值层面的问题同样必须解决。在多个不同的维度下,如何保证大小前提为真不是形式逻辑能够解决的问题。法律推理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既包括选择法律规范,又包括确认案件事实以及把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并从中得出法律裁判结论的整个推理过程。在大量的法律案例中,我们面对的是不可重演,甚至不能模拟的过去完成时的行为链,任何新的证据都可能颠覆原有的结论,即三段论小前提的确证性不能被充分保证;另一方面,不同的环境、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取向,会让法官们在不曾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新问题前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判断;或者在面对多个可以适用于同一情形的法律规范面前,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选择,甚至是相互抵触的选择,即三段论大前提的确证性也不能被充分保证。当一个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都被我们质疑的时候,这个三段论结论的有效性也变得没有任何说服力。博登海默也指出,“形式逻辑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只起到了相对有限的作用。当一条制定法规则或法官制定的规则———其含义明确或为一个早先的权威性解释所阐明———对审判该案件的法院具有拘束力时,它就具有了演绎推理工具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当法院在解释法规的语词、承认其命令具有某些例外、扩大或限制法官制定的规则的适用范围或废弃这种规则等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时,三段论逻辑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不具有多大作用了。”[2]517 经典的演绎逻辑具有单调性(monotonic),它假定了一个所有有效推理的完备集。即对一个有效的演绎推理来说,不管你增加多少个新前提,结论仍然保持有效,即使是增加了一对矛盾的前提到前提集中,其结论有效性也不会改变。但是作为实践推理的法律推理则是非单调的(non-monotonic),即如果加入新的信息会让推理所处的情形发生变化,原有的结论也将随之改变,正如我们上面对三段论大小前提所分析的情况。法律推理的这种非单调性特征表达了法律推理既要求推理过程的逻辑有效性,又要求推理内容合理真实,而这是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的,必须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研究。 非形式逻辑(informallogic)是相对于形式逻辑而言的,前提可接受性和联结充足性是非形式逻辑的两个核心概念,而这两个概念也正是法律推理所必须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非形式逻辑具有认识论的性质①。非形式逻辑关心推理和论证的建构问题,强调对推理和论证的评价。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研究的区别还表现在语义、语形和语用层面上。形式逻辑的研究是基于语义或语形的考虑,而非形式逻辑则是基于语用的考虑,强调解决实际、具体的问题,其对象是实践性的。非形式逻辑不仅关心从形式方面对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研究,更关心问题的实质内容,具有具体、灵活性。 本文认为法律逻辑在本质上是非形式逻辑的,当然它可以用形式化的工具去刻画,也可以针对某些算子建立完全形式化的系统。非形式逻辑与形式化方法并不是对立的,非形式逻辑中也可以出现形式化的讨论,因为形式化只是一种逻辑方法,对于一个非形式化逻辑对象理论加以形式化意味着:(1)要用逻辑语义学方法对其重建;(2)要构建一种语法足够丰富的单义的人工符号语言,使之能够精确地表达其全部可能的不同的逻辑形式;(3)要选择有限的合式公式组成其形式公理集,并选择其合式公式的有限多变形规则组成其非空推理规则集;(4)对于所构建的形式系统做出其是否具有可靠性、协调性和完全性等元逻辑性质的讨论[3]310。这种方法既可以出现在形式逻辑的研究中,也可以应用在非形式逻辑的研究中。非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非形式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它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分析工具———逻辑形式的概念;其二,它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评价标准———有效性。非形式逻辑所关注的是自然语言的推理和论证,而不是形式逻辑关注的人工语言的推理和论证[4]。 法律逻辑研究试图探讨法律职业者如何分析问题、建立推理、论证其裁决结论等,这中间面对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心理问题千差万别。法律推理中存有确定前提下直接运用推理得出结论的情况,但那只是法律推理集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情况是推理者不能找到确定性要素,没有明确适用的法律规范;或者多个规范都可以适用,但其中存在明显差异或矛盾;没有直接证据提供;不断出现新的证据质疑甚至推翻原有的推断;不同地区或人群对同样事件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理解等等都是推理者经常要面对的情况。一个非单调性推理过程的构建,对已有推理的检验和评价也都是法律推理的应有内容,而这些更呈现出非形式逻辑的特征。我们举两个案例看看: 案例1:在某居民小区中,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之间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中有这样一个条款:“除非住户家中发现了白蚁,否则不能免费领取高效灭蚁灵”。物业管理公司的目的很明确,即如果住户家中没有发现白蚁,就不能免费获得高效灭蚁灵,以免灭蚁灵的过度领取。但是,当某住户家中真的发现白蚁时,物业管理公司就一定会提供免费的高效灭蚁灵吗?如果严格执行合同的条款,物业管理公司完全可以不提供高效灭蚁灵,因为条款本身是一个必要条件命题,表达的是一种无之则无的推理过程,其推理有效式为否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即当没有发现白蚁时,推出一定不能免费领取高效灭蚁灵;当已经免费领取了高效灭蚁灵时,推出一定是发现白蚁了。而由住户家中发现了白蚁,不能演绎的推出任何有效性结论。即使住户把物业管理公司告上法庭,如果法官严格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也只能判物业管理公司胜诉。#p#分页标题#e# 这样一个演绎推理的结果小区住户一定不会接受,他们会觉得在发现白蚁的情况下,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相关的药物是其基本的责任或义务,如果说条款中有什么表达歧义和问题,也是住户们被物业管理公司欺骗的结果。在实际法律案件中,法官们也决不会只考虑条款本身的逻辑推理问题。一般人对涉案条款的理解和预期、对消费者的保护、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等问题都将是法官在裁决此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此案的结论绝不仅仅是进行一次形式推理那么简单。 案例2:2007年,全国各地先后有数百名消费者向当地法院起诉脑白金违法宣传,欺诈消费者。问题的起因来源于这些消费者在购买“脑白金”产品前看到产品外包装上明确注明“脑白金里有金砖,上海老凤祥打造99•99%金砖,价值5000元”的字样,但购买产品后发现包装内却没有金砖。于是认为脑白金的销售方和生产方有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所以将其诉至法院。 各地法院做出的判决结果不尽相同。判决原告胜诉的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普通消费者,凭借该项文字的表述内容,足以产生凭借其购买脑白金这一商品的行为而获得价值5000元金砖的这一内心确认,但没有证据显示本案存在原告从被告所销售的脑白金商品中可以获取金砖的可能性①,被告在没有金砖获取的可能性的情形下,任其销售的商品标有“脑白金里有金砖,价值5000元”的字样,被告故意告知上述虚假信息,致使原告做出了购买脑白金的错误意思表示,认定被告的行为为欺诈。判决原告败诉的法院认为:虽然在原告购买的“脑白金”产品外包装上没有明确注明“脑白金里有金砖”是指有奖销售活动,但包装盒上显示了金砖的纯度和价值,原告认为“脑白金里有金砖”即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购买“脑白金”产品的消费者均可得到黄金,按此理解则被告生产和销售“脑白金”不但不能获利,反而会造成巨额损失,这种解释既与交易习惯不符,违背了商品经济活动的准则,又明显不符合情理,也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所规定“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所以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欺诈。 分析上述案例我们发现,无论法院最终判决的结论是谁胜谁败,但判决过程决不仅仅是形式逻辑所能解决的问题,被告行为对原告所引起的内心感受、不同证据的采信、一般交易习惯、商品经济活动准则、诚实守信法律原则等都是决定案件走向的重要因素。法律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包括认知、心理、情感、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复杂的操作过程,而这些因素在推理过程中的参与正是法律逻辑的非形式逻辑特征体现。 法律活动中的推理和论证并不像形式逻辑所希望的那样具有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法律逻辑作为以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法律逻辑是体现法律职业者独特的思维特征,法律推理的目的是寻求利益冲突的最佳解决办法,最佳解决办法有时并不等于完全正确的办法。所以,法律逻辑并不是将形式逻辑简单地应用于法律。法律具有实践理性,法律职业者的思维不能完全形式化,正如同波斯纳所言,法官不可能像一架自动售货机,“上口投入法律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口自动地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原汁原味”[5]29。其次,人们关注法律活动中的法律推理,主要关注的不是形式结构,而是推理的构建活动,亦即它的前提如何建立的问题。正如库德里亚夫采夫所言:“定罪时,主要的困难不在于从两个现成的前提中推出结论,而在于解决为了建立推理恰恰是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前提。建立三段论的规则没有回答这一问题。”[6]165第三,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例如,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律没有规定或无明文规定,法律规定存在缺漏;已有的法律规定含混歧义或笼统抽象;法律规定之间相互抵触,自相矛盾;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会造成与立法意图或法律精神相违背的结果;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会造成与社会公平正义相违背的结果等。面对这些情况时,法官需要设法消除法律中的模糊和矛盾,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在已有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公序良俗等众多因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途径涉及到的更多是法律内容、行为事实和价值选择,形式逻辑不能关注和解决这些困难。 上述分析彰显了法律推理的非形式逻辑特征,也论证了法律逻辑应该定性为一种非形式逻辑的学术观点。就像波斯纳所说:“法律总是吸引并奖励那些善于运用非形式逻辑的人们而不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谓词演算之类的;那些是吸引另一类人的逻辑。”[5]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