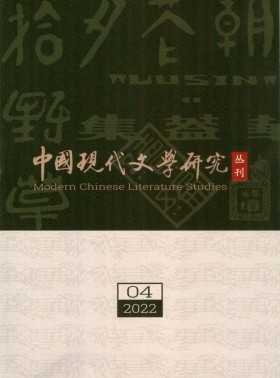摘要: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现代性”是绕不开的话题,它涉及到“现代性”从何时而起、如何呈现、具有那些特点等。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崛起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与西方不同,其启蒙、觉醒、反思、兴国、平俗等特征,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更为主要的部分,时至今日,还在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新文化
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显现
受《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的影响,过去很多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1919年,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新文学,也应该是从1919年开始(如周扬写于1940年的《新文学运动史提纲》[1])。而近年来,研究者对于新文学的原点定位产生了诸多分歧,把新文学起点从推移到1917年(文学革命)、1915年(《新青年》的初创)、1912年(民国元年)、1898年()、1892年(《海上花列传》的发表),甚至延伸到鸦片运动时期,以至于在断代分期上,就出现了很多语词,之前的“现代文学”“新文学”,到之后的“民国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等。无论哪个语词,都是从“现代性”方面着手,区分着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过去旧文学的新质。丁帆教授认为,“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2]。而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其给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的、阶层的、文化的……在之后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现代文学,到1919年,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已完成了“现代性”的革命,以至于丁教授旗帜鲜明地呼吁:“无论是从推翻封建王朝和孙中山倡导的民国核心人文理念与价值内涵看,还是从‘白话文运动’、通俗文学和‘文明戏’的发生与发展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都应该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2]这些争论本身是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努力,无论哪一个观点,无不显示了其背后所强调和突出的东西。《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面说得很清楚:“天下之是非,方演进而无定律,则不得不假新旧之名以标其帜。夫既有是非新旧则不能无争,是非不明,新旧未决,其争亦未已。”[3]新文化运动,其“新”和“旧”只是一个相对的称呼。但是界限在哪里,人们就各陈其词了,新旧冲突曾经一度显得相当尖锐化,且至今都未间断过。更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国外还提出并传入了“后现代”这个语词,以代替不断更新着的“现代性”。所以直到今天,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谁也没有道出最后的定论,但一代一代对于“现代性”的继承和反叛、纠偏和走极端恰恰在不断地丰富着“现代性”的内涵。如今,人们普遍认可的是,20世纪上半叶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曰新曰旧,显示出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新文化体系内出现了与旧有文化决裂的决心。而这场决裂究竟从何时开始,这就涉及到上述所讲的文学史切割问题。不同的划分方式会有不同的节点,但是无论如何,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特质,通常被认为是否是现代文学的标志。论争的焦点多集中于离意识形态有多远,离文学内在发展有多近,抑或是将两者部分地重合,可分又不可完全地分。周作人曾作过这方面的探究,他将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那场文白之争、新旧之辩,向前推进到晚明时期,认为明朝的文学运动和民国的文学革命“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4]27。周作人将文学源流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言志派”是随性所至一挥而就的,以明末公安派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袁宏道《小修诗叙》的“独抒灵性,不拘格套”是其文学核心主张;而“载道派”则是有意而为之,他认为唐宋文学显然属于载道派,认为文学史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切换和轮回。他还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晚周时期到民国,“所走并不是一条直路”[4]1,而是在“言志派”(重抒情)和“载道派”(重“有物”)的中轴线上左摇右摆,寻求平衡和突破,所以中国文学始终是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他惊呼:“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4]27周言不无道理,自有其苦心之处,力图建立非主流正宗文学的谱系,却失之粗糙,表面看来是打破时代的界限,探寻文学发展内在的规律,但是实际上自有其潜意识的意图,寻祖问宗,为新文学合理性造势和张本。钱锺书则对于一切的简单对立持有怀疑的态度。他力图还原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屏蔽先入为主的进化论发展论的观点,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审慎地梳理。他博闻强识心态开放,将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串联起来,谨慎地去处理和评判某一个历史阶段中文学作品的特质,包括“现代性”。他认为到底是“启蒙”还是“复古”,有时恐怕不太容易说清楚,“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5],暗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新质正是新一轮的“复古”而已,或者改头换面了的复古。“骖袒比美,正未容轩轾”[6]钱锺书的文学实践和他的文学观是相互印证的。他认为,对文体选择无论使用的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应该是自由的,白话文可以唱主角,但对文言文未必一定要割袍断交,有时甚至可以丰富白话的内蕴,作为补充未尝不可。《谈艺录》和后来的《管锥编》《七缀集》,无论文言还是白话,他都能做到运用自如。他还认为,从美学鉴赏方面来讲,“言志”“载道”是并行不悖的两条路子,不应将言志的“诗”和载道的“文”混作一谈,对于言志和载道的分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所以钱锺书肯定了周作人的有关“非正宗”的言志文学对于文学本质属性的探求,却也认为言志派也绝不能成为单一的模型,那必将是另外的一种形式的非自由。钱氏的“诗分唐宋”,将文学从风格意蕴上进行划分,但是唐诗的天籁醇厚,不只存在于唐代,宋诗的理趣新奇,也不仅呈现于宋朝。对于文学本体论,钱锺书一向反对概念先行,机械化地认识论,他认为,很多文章从体裁来讲并没有归入文学作品一类,但是其文质兼美,其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完全可以划入文学。钱锺书的这种超越两级对立,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进行比照融合的角度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既从根本上保留了本民族文学的特色,又能借鉴吸收西方文学的各种观念思潮,所以他能做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东西方之间自由切换,在新和旧的交汇中极为理智地处理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发展。如果说上述代表了本土就中国现代文学内在发展所作出的研究和努力的话,那么在海外,上个世纪的60年代,西方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则代表了以新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热潮的兴起。80年代开始,海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逐渐呈现于大陆,获得热议,以致出现“夏志清现象”[7]。经过前期铺垫,90年代后一些有关于现代性的关键词如“被压抑”“没有晚清”“上海摩登”“后现代”“抒情传统”“想象中国”更是让内地的研究者熟悉了李欧梵和王德威。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范畴的实证批评的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规避外部的(社会的、政治的、作者背景的)研究角度和宏大叙事的方式,而以纯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的点评方式来书写文学史;他们挖掘并让人们从新认识了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钱锺书等一批作家,对于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则进行了去政治化的解读;他们反思五四,反思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认为“感时忧国”“家国情怀”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旋律,突出晚清“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海外研究者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学史观显然和内地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很长时间里,受到内地研究者的质疑和挑战,却也在一定意义上也激起了内地研究者对文学史重构的热情。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摆脱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某种干扰,打破了近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将20世纪文学定义为“改造民族灵魂”[8]为主题的文学。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也在《上海文论》提出“重写文学史”,虽然刚开始的过程并不顺畅。时至今日,以文学革命(1917年)作为新文学的起点,已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就摆脱了过去的阐释框架,还原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把前后那段时期统称五四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在国内研究者内在的重述激情和海外学者新的研究视角的推动下共同发酵完成的。这也非常好理解。人们总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地理环境下展开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研究的(其中包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特定的存在、感知、取舍和建构,研究者者对此进行现实意义上的理解和重构,从而推动对未来的发展。而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客体,其自身也是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认知思维和关于这些文学作品的阐述表达,也带着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固有观念、意识和下意识的取舍,从而不断地重构着已知,探知和想象着未知,并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特点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到底有哪些特点?现在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产生的基础并不相同。西方的现代性是在基本完成了“蒸汽革命”“电气革命”“科技革命”的近代化进程后产生的,对物质生产力发展进行着不断的反思,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等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较为和谐配套,其启蒙性和理性成分占得更多。而中国的现代性则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承载了厚重的儒家文化,遭遇了肆虐的列强入侵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近代化”时间太短,又遭遇了社会动荡和军事入侵,相对来讲其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之后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战需倍增,给东南沿海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崛起带来了契机。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需要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敲打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现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来进行推动,其激烈的结果就是的爆发。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在江南一带及沿海沿江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它表现为告别过去,挣脱束缚,追求启蒙、觉醒、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当然,“现代性”在历史的维度和在审美的维度,自有其不同的阐释。前者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意识下的理性和智慧,是反思性的;后者体现为对人的潜在意识的尊重和对于人类一切的有意为之进行怀疑和批判,是反理性的。这两者缠绕在一起,造成了对其阐释的困难。而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况更加剧了这种复杂程度。19世纪中叶起,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人们认识到光有“兵事”是不够的,光有“洋器”也是不够的,更需要民智的开启。从到清末新政,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改八股取士为策论,这在启民智方面,虽未起到实质性作用,其实已撕开了一角,影响深远。开启民智,就是要让更普通的人群认识自己、建立理性智慧并且作用于社会。民国初年的政府也曾经在广开报社言路、破除封建迷信、兴办新式学校等方面作出多种尝试,“旧历三月十四日为香会节场之期……各乡乡人之迷信者举行朝山进香,故届期倍形热闹。自光复后,经官厅之取缔,此风稍杀”[9]。加上精英代表的著书立说,如梁启超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10],他主张“变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1],在他流亡日本后则更加意识到“新民”的必要性,主张开设新学堂、大办书局,且身体力行。中国式的“现代性”意味着和过去的蒙昧决裂,意味着对几千年封建历史的颠覆,意味着可以离“家”出走为自己而活,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王德威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能成为人们自觉追求,并非五四后才出现,在晚清就已生根发芽,反倒是五四的单一性压抑了晚清现代性的生生不息。所以我们不能生硬地把五四时期之前的作品,认为是“旧的”和作古的文学,这不符合作为启蒙的历史的“现代性”的尺度,也不符合“审美的”现代性的标准。如同一切过渡时期的产物,总会遭遇前后夹击的困境,晚清文学面临的尴尬也是如此。矫枉过正的五四人员将晚清彻底与现代文学隔断,为的是更好地摇旗呐喊和虎虎生风,研究者们也多有指出这一点。然而用“晚清”来代替“五四”作为新文化原点,很多学者对此持有谨慎态度[12],但是晚清“现代性”元素对于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已被学者们普遍地认可。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在于小说等文学领域,其除旧立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专制瓦解、王纲解纽、礼乐崩坏,人们时刻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于衣食住行、风尚习俗、文字语素,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这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震荡和转型的原因。可是中国的这种“现代性”的启蒙意识,如上述所讲,并不是在完成了“近代性”之后,由生产力发展和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为有力支撑后自然产生的,中国的现代性是人们在遭受列强打击,又对晚清的御敌能力彻底失望之后,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其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过于西方本土。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除旧布新的新文化运动由高涨转为落潮,新文学显然已经占了上风,当人们再次左右张望的时候,这种决裂、颠覆和出走,收获的是阵阵“彷徨”和不无遗憾的“伤逝”,发现西方所标示的现性,被一战的爆发证明是颓败了的,于是更为行之有效的“革命性”替代了茫然四顾的“现代性”,一切以激情澎湃的方式向前推进。曲折是不可避免,也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经历程,正如栾梅健教授所说:“在抗战爆发前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曾经在一个统一的轨道上行进过,并且非常深刻地经受着经济、文化与人才制度等方面的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是划时代性,是每个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途中都会出现的必然现象。”[13]当然“现代性”本体的多指向性和多元化,注定了这个概念是个综合体,不同学科、不同人群对此进行着不同的打造和阐释。哪怕是同属文学领域、同属“现代文学三十年”时期,也有不一样的视角和丰富的层次感、时期性等。审美层面的“现代性”,能够既站立于本土和本时代,又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突破它们的限制,不断地产生和成长,替代原有的东西,代代更新;审美层面的“现代性”,还将笔触由社会存在入手,直指人性深处,体现了更长远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在小说中,表达主题的现代性时,同样是描写的知识分子,“孔乙己”和方鸿渐,一个是“过去”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一个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从这两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自身在那个时代下的追求、挣扎和尴尬。《孔乙己》诞生于五四时期,反映的是二十年前,《围城》诞生于抗战后,隐约反映的是抗战时期,无论这两部作品的产生还是其反映的时代,之间有着二三十年的跨度。这两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对于具有局限的自我意识的认同和理想境界的追寻,同时又显示出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性。在孔乙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封建制度的毒害,造成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可悲可恨和可怜,加深了我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和否定,在方鸿渐身上我们解读到的就不仅仅是对旧观念旧制度的否定,更多的是对人、对时下人生困境的理解;孔乙己让我们感觉要赶紧推翻这样可怕的吃人的社会,方鸿渐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一个脚留在过去,一个脚跨出过去的尴尬时代及其尴尬人生;鲁迅在沉郁中想表达的是荒凉和悲哀,他在《野草》中用更曲折隐晦、沉郁悲情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墓碣文》),钱锺书在戏谑中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追寻或许有非凡的意义,或许又都是盲目的,至少说人类的理智有局限性。一切都无法定论,一切都悬而未决,一切都“尚未完成”,这也是中国式的现代性的困境。西方的现代性历程从17世纪就开始了,发展较为稳健。中国虽然早在明清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就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但是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出现则是要到清末民初,此时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繁荣的城镇,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应和着西风吹进,世道哗然,西方的启蒙思想、工具理性、意志主义等驳杂的观念开始对中国的思想界进行渐变的改造。人们开始关注和审视自己,开始注重平等和民主,开始追逐世俗享乐。一批精英人员通过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逐步向学生群体、市民阶层、向妇女群体等进行思想宣传,扩大这种影响力,无论是借助海外异质资源,还是上承古典传统浸润,都在沿江沿海一带演化生成了现代文学某种“新质”的滥觞。以上海为例,文学创作繁荣,图书出版业、印刷业发展迅速,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到三十年代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不同于北方的五四新文化场域,上海商业化、功利化的趋向非常明显。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新感觉派、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小说、左翼文学等在此起彼伏的世界各类文学思潮和五光十色的商业场域的背景下催生,并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青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出现,报刊业空前繁荣,在商业运作之下,文学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对文化经销商和报刊业界而言,利润是重要目标,对于创作者来讲,创作是谋生手段,一定程度上这些文化的新质刺激了创作者对读者的迎合,文化商品化、创作市场化变得不可避免。沈从文曾讥之为“海派文化”,这样的“海派文化”显然和步履从容古雅敦厚的京派文化有强烈的对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受其影响。周氏兄弟1924年在北京创办《语丝》时还指认其为“同人刊物”,意在这个刊物非商业性。1927年,由于北方动荡和政治高压,《语丝》迁至上海,此后,其商业广告也变得大张旗鼓起来。创作和办刊物成为很多文化人的生存方式,即便鲁迅也难免于此。北方避难的文化人涌入上海,留学归来的年轻学子也涌入上海(徐志摩、巴金、戴望舒等等),特殊的地域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得上海逐步取代北京成为新文学营地。创造社、语丝社、左联、新月社、七月社等流派在此竞相争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化人在此云集,他们不断尝试,标新立异,“重估一切”“为艺术”“为人生”,文学阵营里异彩纷呈。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无论是历史层面还是审美层面,都受到了西方“现代性”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同时,在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文明崛起时,也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其未经历如西方两百年那样漫长的历程,也没有稳固强大的工业文明作为经济支撑,之后还遭受着异常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危机,所以其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其步伐并非直线前行,却也并非随西方现代性亦步亦趋,其启蒙觉醒、反思传统、实业兴国、追求世俗平民化等特征代表着中国式的现代性中更为主要的部分,这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内需加外力推动下进行的。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跳出了20世纪的界限,并且看到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某些方面突破了时间和空间范畴,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影响着中国文学,如港台文学、网络文学正在以不断演化的面目出现,当然,这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参考文献:
[1]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文学评论,1986(2).
[2]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J].江苏社会科学,2011(1).
[3]汪叔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1).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33.
[6]钱锺书.钱锺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409-410.
[7]王海龙.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J].扬州大学学报,1998(5).
[8]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9]香会节场之种种[N].新无锡•地方新闻,1915-04-28(1).
[1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137-138.
[11]梁启超.梁启超散文[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11.
[12]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6-17.
[13]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1.
作者:胡晓文 刘琴 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