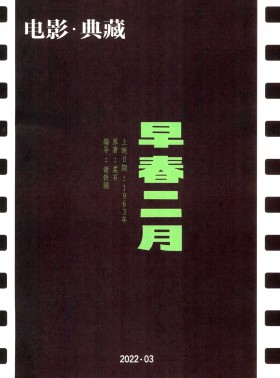【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的不断发展,电影的区域化生产愈发明显。2016年,贵州籍导演毕赣凭借作品《路边野餐》将贵州这片在电影中少有关注的土地以一种浪漫和神秘的美学方式推进了观众的视野,随后,随着《地球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和《无名之辈》的连续上映,毕赣、陆庆屹和饶晓志等贵州籍的新生代电影创作者们凭借着自己对生活与社会的独特理解,将镜头对准了自己成长的土地,将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生活体验融进影像,形成独具特色的电影美学特征。这些电影作品将贵州作为审美对象,反映着贵州的独特文化风貌,催生出了别具一格的贵州电影图景,形成了独具特征的“异托邦”空间,并通过对“异托邦”的透视,展现着乡村与城市、过去和未来、中心与边缘的纠缠与反思。
【关键词】贵州电影;异托邦;乡土中国;现代性反思
一、“异托邦”的建构
(一)自然景观的建构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全国各个地区的城市空间景观呈现出相似性,国内电影的电影景观也随着城市化发展而趋于同一,比如城市里笔直高耸的写字楼、繁荣的商业圈、川流不息的高速路和现代化的城市社区等。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电影景观出现了同一性,缺少多元性和生命力。即使反映的是不同城市的影像,也难以指认出空间的主体性。而贵州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为贵州电影“异质空间”的建构提供了天然的现实条件。中国西南部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高原山地和潮湿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都为贵州电影影像提供着鲜明的能指符号。地域影像的建构中,物理与地理上的自然景观的建构是最基础、最鲜明的部分,同时也是最具指向性、最不可或缺的部分。早在王小帅导演的“三线建设”代表作《青红》中,连绵的山脉和茂盛的绿色植被就已经作为自然背景融入三线建设这一历史前景当中。在新生代贵州籍导演毕赣的影像中,故乡凯里的自然景观被反复渲染,形成一种作者独有的表意方式。蜿蜒盘旋的盘山公路在漫长诗意的长镜头下被屏息注目,高饱和度的绿色植被始终占据着空间画面,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突然而至的降雨使得室内成为被分割的封闭空间。夏季闷热潮湿的天气、神秘昏暗的洞穴等贵州独有的自然景观,都在影像中具有了高度诗意的表意特征,成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鲜明可辨的电影符号。
(二)人文景观的建构
贵州电影空间的异质性不仅停留在物质空间的生产和再现中,学者陈旭光认为,电影空间的生产具有精神性。空间生产是一种具有精神尺度的社会活动。通过象征性的电影符号,创作者可以感受到空间的文化特质。而正是异质或者同质的文化,才是电影与观众形成关系的核心要素。社会学学者周怡在其所写的《文化社会学发展之争辩:概念、关系和思考》一文中,总结了各个学派对于文化的理论,提出了“文化”是某一种特定的总体生活方式,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共享的行为模式。同时文化业是由各个结构特征编织而成的象征符号体系以及外在的社会角色和制度化体系。而在文化地理学中,人们认为,“文化’是通过时间作用于‘自然景观’并且形成多种‘形式’的混合物,比如人口与交往方式;这些形式的混合物结合起来就成了‘文化景观”,因此学者们提出,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而文化景观是结果。在贵州电影异质空间的塑造上,也是如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一直是中国电影异质空间建构的重要手段和重要资源。从早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开始,如“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阿诗玛》《神秘的旅伴》等作品,即是在同质化强烈的电影模式下利用少数民族的异质文化,形成一种“陌生化”的电影空间。到近年来,藏族电影的异军突起,都是将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于电影大荧幕中加以呈现,形成新鲜生动的“异质空间”。贵州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其中,以苗族与侗族等少数民族为对象,以少数民族故事为蓝本的电影作品,如贵州籍导演丑丑的电影作品《阿娜依》《云上太阳〉等,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原生态的展现,电影中展示出苗族的古歌、刺绣、姊妹节等各种风俗奇观,呈现出未经沾染、原始纯粹的风俗、宗教、交往方式等特质民族文化,吸引着人们。在贵州本土的历史发展中,社会的政治历史变迁也深刻地影响并一同塑造着贵州的社会文化。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直指云贵,贵州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迎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他乡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作品中,作为一个“闯入者”,王小帅导演一直以一种“闯入的他者”的视角去记录和塑造他心中的贵州形象。连绵的密山遮蔽下的曲折山路,贫瘠的土地,灰色感的厂区生活以及急迫压抑的父辈形象,和贵州的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形成鲜活的时代标记。每一个电影创作者都是时代下具体的见证者,贵州和三线建设是导演王小帅重要的生命历程,也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
二、贵州电影的乡土性气质
“乡土”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在费孝通先生奠定中国社会学基础的著作《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些社会的广大基层,决定着中国社会基本的历史属性和文明形态,体现着中华民族基本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在乡土的村落中形成“熟人社会”,依次形成“差序格局”,这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模式,几千年来,在乡土家园之中劳作生息,积淀成安土重迁的厚重的乡土情怀。
(一)方言的运用
方言在近几年的影视剧中被广泛运用,以大力度地展示真实性和本土性。如贾樟柯以山西汾阳为主要坐标拍摄的系列电影作品,宁浩导演以重庆方言打造的极具戏剧化的“疯狂空间”等,2020年上映的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也大量运用方言以塑造整体影像风格。贵州电影的方言在还原真实的同时,与城市居民日常使用的普通话相差甚远,形成一种“远方”的间隔与想象,这种远方的想象,加之影像中的山河地理,形成一种城市人口对于过去的乡土文明的怀念与想象。如在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中,男主人公来到小城远方的土坡,这片土坡被茂盛的植被覆盖呈现出深度的绿色,而这片土坡正是主人公逝去的母亲的埋葬地,在已逝的母亲坟前,创作者用凯里方言缓慢说出独白,向后望去,可以看见小镇稀疏的楼宇。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随小镇一同,缓慢地、游弋地由乡土转向城镇,由过去走向未来。在陆庆屹导演的作品《四个春天》中,作者以真实的方式记录着家庭生活。在电影中,不仅是对话与日常用语使用方言未经修改,而且还大量展示了贵州独具特色的民歌和唱腔,自然真实地展示着父母两人自然而成的生活情趣。这样的民歌出现在父母两人上山上坡的劳动中,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感受到亲近的乡土性。
(二)少数民族与宗教文化
在乡土文明中,也从自然的土壤中衍生出一定的宗教文化。在所有的文明初期,都有着自然崇拜的宗教时期。中国的乡土文明依靠黄土而生,河流而长,如同一切农作物一样依靠自然生长,因此自然地产生了对土地、河流、山川等神明的想象与敬畏。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众多,其中不少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信仰,衍变出丰富多元的文化风俗,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对于已经习惯于都市文明的电影受众来说,具有贴近原始文化的神秘魅力,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在电影《云上太阳》中,电影讲述了一位外来者,即一位外国女画家病倒在苗寨被当地苗族人医治的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创作者将苗族的服饰、文化、风俗和宗教仪式等展现出来。其中祭祀的仪式和歌舞场面堪称文化奇观,在情节中,苗药师的身份既有宗教意味,又兼具着宗族色彩,极具少数民族色彩。在电影的推进中,苗族人们对于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也得以体现,苗族村民们将锦鸡作为自身宗教信仰中的神灵,锦鸡、祭祀、祭师等的表现都富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体现着苗族村民们对于自然、神灵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同时,贵州籍青年导演毕赣也是苗族人,生活在苗族的文化氛围之中。在他的电影作品中,虽然没有表现宗教色彩的直接指向,但他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对于事物的诗意认知,电影中人物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斥着某种潜在的神秘主义气息。无论宗教文化对导演个人的影响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浪漫又神秘的影响气质已经成为毕赣导演,甚至成为贵州电影的一个重要符号。贵州电影通过物质景观的再现在影像中重塑了贵州独有的地理山河,通过少数民族、宗教与历史等完成着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电影图景中迥异于主流电影景观的“异质空间”。但在贵州电影的发展与传播中,更为重要的是贵州电影如何获得了它的精神内核,并在地域之内与之外都获得了价值认同。
三、异托邦的精神内核:对故乡的深情回望
(一)小城镇的叙事选择
贵州电影的异托邦的建构,它与乡土文化的紧密勾连,是对工业化的一次反思,在不断向前的城市化趋势中的一次驻足回望。通过塑造与城市文明不同的电影景观,同构了人们对于农业社会的故乡的追忆,而在这种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的动机之下,贵州电影的创作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了处于原始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小城镇”。社会学与人类学家项飙先生曾在著作中表示,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依据自身特点,依靠乡绅和宗族制度逐步向前,具体而实在地参与社会,但社会现实中,原始的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已经被打破,外力而来的迅速的现代化带来了当代中国人对于周围社区空间的漠然和不信任,无法形成有力社群,人们只得寄情感于虚空的抽象概念,如网络社会以及抽象的国家概念。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公民难以获得真实具体的参与感,难以形成有力的社会。无论在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领域,对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思和追问已经大量涌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性的美梦”已经破灭,对于根基的寻找变得越来越迫切。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虽然没有大力将精力投身于现代化的理论批判之上,但他们凭借着敏锐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影像镜头由“完美”的城市转出,从而探向了东北农村、西南山野这样真实而粗砺的乡土空间。贵州电影正是如此,创作者们将镜头对准了城郊的小城镇,这一处于过去与未来、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的独特空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浪潮与全球化空间已经将所有事物都裹挟其中,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工业化与城市化、甚至接踵而来的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但在这样急促的城市化进程中,二三线城市与小城镇并没有如一线城市一般飞速发展,贵州便是如此。贵州地处西南边缘地带,离城市化中心的东部较远,未能像一线城市一样迅速进入城市文明。但在不可抵挡的潮流之中,它已经缓慢地上路。而这种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进度,在小城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许多贵州电影导演出生与成长于这样小城镇般的环境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的影响作品中。在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之中,一家人生活在改建的小楼里,这样的居住不属于原始的乡土,也不属于城市,院子里铺上石灰,将土地封存,但母亲仍坚持在院子里砌上鱼塘,以与自然相通。在《四个春天》中,一家人安静平和地度过舒适流淌的时光,影像中记录燕子、草木、山坡,在已不是纯粹农业社会的时空中,延续着乡土文明的精神渴求。在毕赣导演的作品中也是如此,《路边野餐》中所有人物生活在小城镇之中,通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见城区的楼宇,回头则是植被茂盛的山坡。正是基于这样独特的社会定位,贵州电影中乡土气息的影像弥散着对于过去美好的重塑和不舍回望。
(二)小城镇中离乡入城的人物设定
在后现代社会学家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中,他打破了传统的空间概念,指出人们日常熟悉的空间是被划分和区隔的,存在着不同的“异域”,每一个空间不是僵死的,而是镶嵌在关系之中,与知识与权力相联结,空间体现着知识体系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之中,已经完成成熟的城市化的一线城市无疑处于权力的中心。以前农业社会中以宗族和地方乡绅为代表的各地分散与平衡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化过程中,特大都市极大密度地集中着发展资源,成为现代文化、政治与经济中心。在这个权力中心之外的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奔赴城市,成为“打工者”和“外来人”,而这些由权力场域边缘而来的外乡人,多处于城市社群的边缘,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群之中,也无法回到故乡,成为城市空间中流离的边缘人物。在电影《无名之辈》中,来自乡村的两位主人公步入城市,却处处显示出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和错位,主人公一心想“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获得被城市所体认的成功,却显示出游离和笨拙。在陆庆屹导演的作品《四个春天》中,以一种真实记录的方式展现着离开家乡,去往城市的青年,每一年对于家乡母体的回归。青年一代摒弃掉“安土重迁”的观念,去往城市中心谋求生存和发展,留下父辈在故土生活,这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而在这样的现状中,多少青年失去故乡,又无法得到城市的接纳,游走在城市文明的边沿,失去自己身份的体认。因此当陆庆屹导演用纪实性的电影镜头,用看似与时间同速的影像速度,缓慢地记录家乡父母的生活,记录屋檐下燕子的回归和池塘中鱼的游动,记录每一年过去父母和故乡安静平和地衰老,让无数城市中的异乡青年得到故乡的安抚。
四、总结
贵州电影通过物理人文景观建构,塑造出一个与主流城市文化不同的异质的电影空间,这一电影空间的塑造,与福柯对于“异托邦”的理论不谋而合,贵州电影空间,是对城市这一新的权力中心的反思,弥漫着乡土气息,也展示着新一代青年对于乡土的迷恋与追寻。贵州电影,在创作者和无数观众的同构中,为城市中来自各地的他者实现了对于自己身份和自身价值的一次回溯和追寻,成为城市化进程里,人们对于故乡的一次含泪回望。
作者:李秭怡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