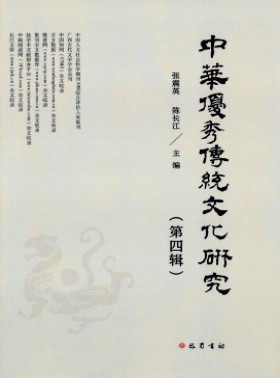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蒙古族宗教观念中的生态意识
自然崇拜、宗教信仰作为人类原初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懵懂无知和对自然力无法控制而产生的惊异、敬畏或困惑的心理。萨满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蒙古族等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宗教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在萨满教的原始观念中,天地、宇宙、人事都是由无法预测的神力掌控的。此外,萨满教认为,草原、山川、江河、树木等均由各自的神灵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思想、有各种魔力的人格化体系。在这个人格化体系中,这些神灵都具有神奇的力量,掌控着宇宙时空的升沉祸福。如果人类虔诚地敬奉并爱戴它们,它们就能够保佑人类;如果人类忤逆、违背它们的意愿,它们就会降灾于人类。而且,在神灵和人类之间,还可以通过交流来传达彼此的心愿或想法,这种相互沟通的媒介是通过祭祀来完成的,而萨满就是完成人神之间沟通的神职人员。原始先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敬重,以期获得神灵的庇护。同时,通过祭祀,他们也把神的旨意送达人间,用以表示神灵也会关注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告诫人们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善待生灵,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因而,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能够时时劝勉或告诫人类虔诚地善待自然、爱护自然。这样,人类就成为虔诚的生态保护论者,如同后藤十三雄所说:“化生万物的太阳、水和大地,对他们来说,恐怕不是所谓自然的抽象观念,而是切身感受到了太阳、水、大地的伟大力量,因而对它们都抱有一种神秘的情感。”久而久之,这种来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和神秘的情感就转化为先民的原始信仰。信奉萨满教,笃信万物皆有灵魂、深信灵魂不灭的蒙古人,把自然看作衣食父母和守护神,对其加以呵护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并传承下去,生生不息。蒙古族认为,广袤的大地是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根基。因而,蒙古族非常敬畏和爱戴土地之神,一切玷污和破坏土地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其原因就是怕惹怒神秘力量,导致灾难降临。这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修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族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生态意识,在他们祭拜天地、神山、圣水等各种习俗中也有集中体现。例如,蒙古族在饮酒时都要祭天,后来,这种祭天习俗逐渐发展为祭神山、祭敖包、祭神树等。在蒙古族先民的思维里,高山丘陵等突兀之处都充满了神秘感,它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是部落的保护神,也是通向天堂的幸福之路。对神山的祭祀膜拜,有很多禁忌。正是这些禁忌,使得蒙古族先民们不能肆意破坏自然。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中曾说,如果祭祀湖泊,就不允许人们吃湖泊里的鱼;如果祭山,就不允许折损山上的一花一果、一草一木。土地崇拜、神山崇拜逐渐演化为祭敖包。牧民把敖包看作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每方土地都有各自的‘精灵’———蒙古语叫‘土地之主’在居住,被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敖包也是蒙古族经常祭拜神灵、表达心愿的场所。敖包一般设在草原上地势开阔、风景秀丽的高山丘陵之顶、突兀之处或是要道之旁,它一般用石头堆砌成圆塔形的小山,顶端插着一根长竿,竿的顶端系着各种写有经文的布条。每年盛夏之际,虔诚的牧民从各处聚集,奉献牺牲(对牧民来说,祭敖包时供奉的牺牲是返还给造物主的),举行祭祀仪式。仪式由萨满主持,既要感谢自然神灵恩赐各种丰饶之物,又要向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牧草茂盛、牛羊肥壮。可以说,在蒙古族的心目中,敖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蒙古族先民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敖包是禁地、圣地,不准在敖包腹地破坏草木、掘土开垦、围堵狩猎。如若有人侵犯禁地,不遵守习惯法,将会受到各种重罚,甚至会付出生命。这种敬畏自然、敬重生命和神灵的祭敖包仪式,不断影响并铸造着蒙古族牧民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使蒙古族心存善念和感恩之心。爱惜生命、尊重生灵、热爱草原、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关爱生命的作用。
二、蒙古族天葬仪式中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
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即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生命的完整性体现为生与死的轮回过程。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在生前设计好死后的丧葬方式。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丧葬方式和人的诞生同等重要,甚至在原始先民看来,人的死亡比出生更令他们困惑和好奇。也正是这些令人不解的问题,促使先民非常重视丧葬仪式,希望亲人死后可以投胎转世,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为此,举行各种丧葬仪式进行祭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丧葬方式因受各自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各式各样,它透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对生死存亡、灵魂转世、生命轮回的认识与体悟。受自然天惠极少的蒙古族牧民,因受到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特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丧葬仪式。蒙古族的丧葬仪式中最具代表性和富含生态意蕴的是天葬,它折射出蒙古族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珍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人共存的思想,维系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关系,对本已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环境起到了缓解和调适的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虽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从而成为一种追忆,但回忆历史、追寻美好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启示,却是令人深思、意味悠远的。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万物亲密地存在,我如何表达谢意?要在深刻地考验之际去把握。”对此,海德格尔说:“考验必须透彻。必须使固执之心屈服,使之消隐。”“通过反反复复的倾听,我们将变得更有倾听能力,但也会更加留意那种方式。”蒙古族天葬的精粹在于它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传统的蒙古族天葬是将死者的尸体以白布裹身,面孔朝天,盖上一块写有经文的白布,放在荒郊野外,让鹰、野狗、狼等食肉动物吞食。三天后,死者亲属前来查看,如果尸体被鸟兽吃得所剩无几,就说明死者前世积德行善、乐于助人,死后灵魂借助鸟兽升天,同时也预示着子孙将获得吉祥福寿;如果死者的尸体未被野兽吞食或吞食得很少,就被认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连鸟兽都不愿以其果腹,这时,死者亲属就请喇嘛诵经超度,替死者忏悔、赎罪,同时在尸身上洒黄油或酒,直到骨肉尸身被野兽果腹,才认为对死者已尽心意。这一点与藏族的天葬是类似的,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略有差别。随着蒙古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其丧葬仪式逐渐失去了自身独具的特点,和其他民族的丧葬仪式逐渐趋同,墓(土)葬、火葬逐渐成为主要方式,而天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蒙古族游牧文明所承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为什么会出现天葬仪式?它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其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其天葬仪式产生与传承的文化根源。蒙古族信仰萨满教,其至高无上的神灵长生天与蒙古族原始先民的“狼图腾”崇拜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蒙古族先民认为,狼是长生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按照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观,人死后,灵魂尽快归天转世是一件既重大又吉祥的事情。狼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会飞的,当狼把人的尸体吃掉,天葬才算圆满完成。蒙古族天葬的产生,既与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有关,也与藏传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思想有关。对于蒙古族民众来说,不论是作为捕猎对象的禽兽,还是保证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家畜,既然都是由具有神力的自然赐予的,那就要对自然无私的赐福馈赠表达谢意,以自己死亡之后的身体进行天葬来回馈自然,就是一种向神灵表示感谢的现实举动。对大自然、长生天恩赐的每个动物,无论猎物还是家畜,“仅仅意味着是偶然的死,而求其生则是永恒的希望”。当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发生矛盾时,蒙古族人选择人类的利益,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不会像当今一些人那样毫无怜悯之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赶尽杀绝或将其看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蒙古族牧民或狩猎民会带着深深的歉意与动物对话、交流,以求得动物的理解、原谅,并怀着敬畏之心,举行各种仪式,以此表达歉疚之意。其二,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草原食物链的动态平衡,是蒙古族天葬仪式得以实施和传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地理环境、动植物和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肉食动物、草食动物与草地资源之间能否实现食物链结构的良性循环,直接关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及其功能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肉食动物通常处于草原生态食物链顶端,它们不仅以草食动物为食,也食腐肉。蒙古高原上大批肉食动物的存在,是蒙古族天葬得以实施、延续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天葬的亡者尸体被它们叼食腹中,避免尸体腐烂,发出浓烈腐臭味,滋生繁衍有害细菌,传播疾病、瘟疫,危及动植物良性发展及草原生态。其三,蒙古族自古天成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其采用天葬仪式的社会动因。自公元8世纪以来,蒙古氏族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氏族形成游牧部落,游牧生产方式借此产生。蒙古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先民不会选择砍伐树木制作棺椁,以破土挖坑、修造坟墓的形式来安葬死者。其原因是,这既不符合蒙古族民俗法规,也会破坏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植被;再者,对于“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固定居所、奔波忙碌的蒙古族先民来说,从遥远的地方骑着马或赶着勒勒车长途跋涉去祭拜亡者,既不合理,也不现实。蒙古族天葬是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它包含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种丧葬方式,既保证了草原食物链的良性循环,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又消除了修造坟墓、火葬等丧葬形式给草原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游牧人除了饲养家畜谋生以外,还猎杀一部分动物为食,所以,蒙古族牧民认为,人死之后以自己的皮囊肉身喂以鸟兽果腹来回报自然万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丧葬方式看似不合人情常理,甚至有些残酷无情,实则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水乳交融、和谐共生、生命同根同源的生态大智慧。当然,这种生命觉解的大智慧绝不是对各种区别的消融,而是与区别于自身的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即“奇异化之运作、畏惧之要求”,是一种对自然无限恩赐的感恩和回馈。
三、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珍爱自然的生态理念
在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处处体现着蒙古民族珍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理念和生态思想。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来说,自然就是衣食父母。也正因为此,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也形成了对自然的特殊感情。蒙古族牧民可以根据地形地貌来判断牧草的疏密、青草的发芽情况、水源情况,新生的幼畜在哪个位置可以躲避风雪、抵御风寒,甚至可以根据土地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来辨明方向和地理位置。蒙古族懂得过度放牧会危害牧场,草场的好坏和水资源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畜的生存安危。蒙古族牧民每年必须轮换牧场数次,由于冬季不备干草之故,必须调整移动路线,一般冬季就停留于家畜容易获得野生枯草和水源的合适场所。如果不长年逐水草而迁徙,那么,草场就会被牲畜啃光而无法休养生息,草原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牧民们就无法生存,这就是残酷的生存辩证法。因而,蒙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很多有关草原、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人们都自觉遵守,自觉维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使得蒙古族自然保护习俗传承至今。元代以后,有关环境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逐渐在蒙古社会广泛推行。如在《黑鞑事略》中就曾有“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的记载。由于北方草原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非常爱惜水源,不准以任何方式玷污水源。为了表达对水神的敬仰之意,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曾规定春夏之季,禁止人们在河流中洗涮、便溺,不得用金银器皿汲水,以免引起电闪雷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和自然环境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关系。1251年,当蒙哥称汗之时,便昭告天下:不允许各种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不准用骑行、驮用重物、绊脚绳和打猎等方式折磨家畜,使家畜疲惫不堪;要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原上跑的禽兽免遭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打扰。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也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游牧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价值观和生态理念。
四、结语
概而言之,蒙古族所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全面考虑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否则,将会制约游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牧草资源、水资源和畜群资源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线,它直接关系到游牧民族的兴衰,而生态保护意识的形成和传承直接关乎牧草资源、水资源和畜群资源的优劣好坏、兴衰枯荣。蒙古族正是以适应自然规则和人类挑战而产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使自己生生不息。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利用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作者:包桂芹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