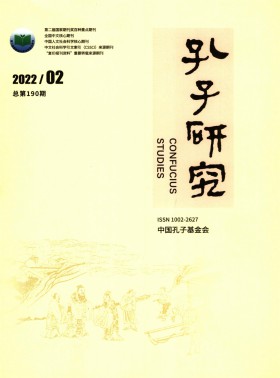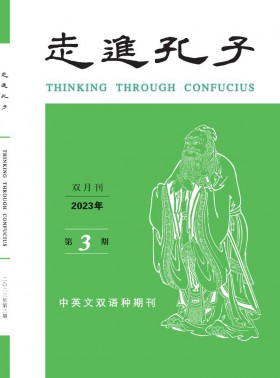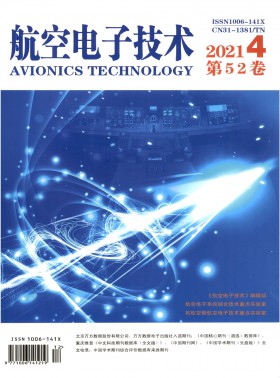孔子删诗说范文1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
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鏞”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鏞”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
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孔子删诗说范文2
由于对“留白”简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关系到对《诗论》简的整理、排序与读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目前学术界对《诗论》留白问题的讨论意见,曹峰先生最近已经作了很好的归纳。他把目前的不同看法大体归纳为“缩皱脱字说”、“先写后削说”和“残简说”三类,并明确指出“笔者认为,‘缩皱脱字说’与‘先写后削说’相对而言合理性较差。”并对彭浩先生在《〈诗论〉留白简与古书的抄写格式》中提出的“《诗论》留白简原是分三栏书写的,……其阅读秩序是上栏中栏下栏,各栏均由右向左。”并说这些留白简“应是另一个篇、章,不应归入《诗论》中”等看法,提出质疑,指出其误[i]。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我在未见到这些“留白简”的原件时,曾撰文对《诗论》的“留白”问题进行过初步讨论。我是主张“残简说”并推断“如此整齐的留白显然是预先预留的空白,不会是‘先写后削’。”“留白现象说明目前的简本是一件抄本,它所依据的底本本身原有六枚简已是残简,其缺失部分就在原简的第一道编线之上和第三道编线之下,抄写者无法找到其它本子补出,只能照原来底本的原状抄出。”[ii]。我现在仍然认为不误,但有再作修订的必要。
许多学者都提出,应把“留白”简与满写简区分开来,并且认为其内容有主题不同的差异[iii],对此,我在以前发表的看法中已经进行过讨论,至今仍然觉得原来的看法尚有一定道理。曹峰新近提出“留白简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内容都凸显它与满写简的不同,将两者区别开来,分头讨论,是整理《孔子诗论》的第一步。”的意见。我赞同他将“留白”简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的意见,但在讨论时还要注重其内容的相互联系,因为形制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单纯根据形制去分析这些“留白”简与满写简的区别,难免会导致舍本取末的结果。关于这些“留白”简与满写简在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我在以往的论述中已有详细的论列[iv],实际上,从内容上看,这些“留空”简与满写简是混编在一起的,所缺的内容经上下文比较是可以部分拟补的。因而单纯根据形制上的差异来判断内容上的分类是未必妥当的。
这次在上海博物馆仔细观察了《诗论》的几枚“留白简”后,发现原简两端确实经过书刀一类工具削去一层,应当承认周凤五教授原来的观察是有据的。并且在周凤五教授和许学仁教授提示下,我也看到二、三两枚简的下端在削去表层时,还是先用书刀横切较深然后翘起而揭起一层的。周凤五教授推测是否原来在第一、三两道编绳处以刀刻出痕迹较深,在埋藏过程中简端翘起失落了原来的竹表层,才形成这些“留白”现象。周凤五教授在和我的交谈中曾提出把这些两端削去的简称为“留白简”或“留空简”是否会成为一种误导,使人认为一定是预留的空白。我就此也请教了马承源馆长,他仍然认为是预留的空白[v]。
我觉得根据目前的认识,这些“留白简”的“留白”或“留空”是“预先留出的空白”的可能性仍然是极大的。至于为什么在留空白处还要用书刀削去两端,仍是费解的悬案。
就古代简策书写程序与常见制度言,竹简在书写过程中,如果写错了内容,其改正方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画除”,即涂抹已写的文字,以示舍弃该字句;一是“删削”,即用书刀削去已写字句,以便重写或更正。“删削” 是最常用的改正方法[vi]。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留白简”是否属于“删削”,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这些删削简是否“先写后削”,我则认为,目前虽然还无法遽作结论,但从原简上经过删削的部分仔细观察,看不出有原来书写过的任何痕迹。我向马馆长建议是否可用红外照相方法处理,看是否有“先写后削”的遗迹,幸获马馆长认可。也许能在不久以后会有一个可信的结果供我们深入讨论。但就目前观察的情况看,我们觉得“先写后削”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为,如果这些削出来的空白处确实是正常意义上在书写过程中为了改正书写字句所作的删削,自然应是“先写后削”。但值得注意的是,《诗论》中第二、三、四、五、六、七等六枚所有经过删削的简基本上都是上、下两端削去一层,而在第一、三两道编线内的内容却从无删削的痕迹。如是删削改正,为什么六枚简的错处都出现在两端?
由上海博物馆回来后,我反复考虑,仍然感到“残简说”是比较合理的解释。目前对这一问题所能作出的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部分简出现的删削现象是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有意作出的标记。极有可能是抄写者所据底本中的这六枚简原来两端已残,抄写者抄写时将这些残缺处留出空白,以待日后看到其他完善的底本时补抄进去,抄写者为了表示这些留白处并不是抄写时的疏漏,特别以书刀削去空白处的简面,引起以后补写的注意。以上看法未必妥当,但就目前的认识言,在找不出更好的合理解释前,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故不揣冒昧,抛砖引玉,向海内外同道请益,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以便寻求出合理的解释.
[i] 曹峰:《试论〈孔子诗论〉的留白简、分章等问题》,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六号(2002年7月出版)。
[ii] 拙著:《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留白问题》,《简帛研究》网站bamboosilk.org,2002年2月9日首发。
[iii] 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简帛网站》bamboosilk.org 2002年1月12日首发;又《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上博〈诗论〉简的作者与作年》,《简帛网站》bamboosilk.org 2002年1月17日首发;又《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iv]拙著:《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留白问题》,《简帛研究》网站bamboosilk.org,2002年2月9日首发。《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网站bamboosilk.org,2002年2月3日首发。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中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v] 2002年7月30日上午在上海博物馆地下报告厅前咖啡厅与周教授、马馆长交谈。如有出入,请两位先生更正。
孔子删诗说范文3
关键词诗经 荷马史诗 成书过程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Glorious beginning, Eternal Charmming
――Compare of Writing Process and Historical Status between the "Book of Songs" and "Homeric Hymns"
TONG Chen[1], WANG Hua[2]
([1]Library,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2]Foreign Language School,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
AbstractPasses through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two breakthrough point obtaining from the book in circulation, "Poetry" and "the Homer Epic poem"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the East and West earliest literature famous work, may see both to have many something in common; At the same time, to two classical work in East and West literature history huge influences and social history root, also has carried on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from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two aspects.
Key wordsBook of Songs; Homeric Hymns; Writing Process; Historical Status
1 《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比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作品,作为当时政府的礼乐、教育资料保存下来。有关《诗经》的成书,历史上有三种看法:
(1)采诗说。汉代学者认为,周代有令朝廷乐官“采诗”的制度,在上古时期,如不是由官府出面来主持采诗,单靠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力量,去完成这一间隔时间长、流传范围广的采诗任务,是不大可能的。(2)献诗说。这也是汉代学者的观点,认为周代还有让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从作品中看,《雅》、《颂》中歌颂诗和政治讽谏诗的存在,说明献诗的制度可能也是存在的。(3)删诗说。古代流行孔子删诗说,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据宋代学者考证,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定型,例如,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各国风诗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才刚刚八岁,显然不可能删定《诗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综上所述,《诗经》是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收集、加工、整理,最后在公元前六世纪经过删节、编撰而逐渐成书的。
再来看《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希腊南部半岛伯罗奔尼撒的阿开亚人因垂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特洛亚城的富饶,发起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亚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因果前后,民间流传了不少歌谣和传说,这就是《荷马史诗》的主要蓝本。
相传《荷马史诗》是公元前九到八世纪由一个名叫荷马的盲诗人编成的,其实,史诗的形成经历了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共四百多年的历史,以迈锡尼时代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歌谣传说为基础,经过包括荷马这类盲人行吟者的传唱加工,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才由学者正式写成文字。
对比《诗经》与《荷马史诗》各自的成书过程,可以看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部作品均是以民间口头创作并传诵的歌谣、传说为主要摹本,并经过了语言文字的加工整理。《诗经》从篇幅上看,民歌民谣占相当大的比例,是《诗经》的精华部分,作品的流传范围极广,不同方言的作品被采集到一起不可避免,因此在整理、删汰成书时,乐官还对其语言文字进行过加工;《荷马史诗》基本上就是根据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和传说编成,公元前六世纪写成文字时,所用的语言是埃俄利亚和伊俄尼亚两种方言的混合体,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成书时,所用的语言成为雅典最重要的阿提刻方言,因此,《荷马史诗》的形成也经过语言文字方面的加工。其次,两部作品的形成时间都很长。《诗经》所收集的诗歌,是流传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河、汉流域,定型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荷马史诗》主要描绘了以古希腊迈锡尼文化时期为主的历史生活,经过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约四百年的流传、加工,一百年后定型,与《诗经》几乎在同一时期。再次,两部作品都是由官方机构负责主持编辑成书的。《诗经》是由当时周代的乐官负责整理编集,最终成书;《荷马史诗》也是由具官方性质的亚历山大里亚博学园中的学者负责编集成书的。 (下转第254页)(上接第242页)
2 《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历史地位比较
《诗经》与《荷马史诗》是东西方最早的文学名著,是东西方文学发展的光辉起点,对东西方后世的文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它们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学发展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中国,由于《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并且反映了西周春秋近五百年的社会面貌,因此,后人对《诗经》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推崇备至,把它作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及博物学的教材,因此,到了汉代,《诗经》便成了儒家经典,成为后人入学进仕的必读书。
《荷马史诗》在古希腊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古希腊鼎盛的雅典城邦时期,史诗经常在剧院上演或吟诵,对人民进行历史和音乐的教育,其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使当时许多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如痴如醉,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在欧洲一直延续到近代,从形式到内容,从音律到语法,从神话传说到史实考证等,都有许多重要的成果。
《诗经》与《荷马史诗》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辩证地看,这种影响也具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先看积极影响。首先,它们都给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社会历史学遗产。《诗经》中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教科书。《荷马史诗》同样如此,“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或战车,用圆木或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希腊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其次,它们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创作手法、风格、语言技巧等各方面具有重要贡献。《诗经》开辟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历过许多次文学革新运动,都是以“恢复风雅”为主要目的,提倡《诗经》所独具的文学风格。同样,《荷马史诗》也是欧洲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史诗的楷模,后世出现的许多史诗和叙事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借鉴了它的创作经验,从而成为不朽名篇。
但是,另一方面,《诗经》与《荷马史诗》也微有瑕疵。如《诗经》中有一些夸耀奴隶主统治的献媚阿谀之作,后人对《诗经》的序、笺、传等注本,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从而淡化了它的艺术价值。《荷马史诗》中也写到神的意志主宰一切,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宿命论观点,给后世特别是欧洲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史诗还以歌颂的语气,赞美了作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英雄人物,这些违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也是要注意批判的。
本文为201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光辉的起点,永久的魅力:〈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
[2]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伍蠹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
[5]刘勰.文心雕龙.范文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孔子删诗说范文4
[关键词]述而不作方法论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中“述”是阐述、叙述的意思,“作”是进行新的创作之意,“述而不作”是指只阐述、叙述前人的理论、学说,而自己并不进行新的创作、提出新的见解的意思。新的创作不仅只是局限于文字上的,也指制度等方面的。《汉书.儒林传》中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这里,班固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只是叙述而不进行自己的创作。这种理解,从班固开始,延续至今。虽然,也有其他诸多的理解与解释,但这一解释一直占据主流。例如,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说:“述者,传于旧章也;作者,新制作礼乐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至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将“述而不作”译作“阐述而不创作”。
“一句‘述而不作’,成为孔子一生治学特点的权威概括,也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1],后来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据孔子的记述,殷朝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论语》中的相关言语,还是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人们一向都不太重视立言,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转·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穆叔对范宣子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要向古圣贤学习,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为圣人们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让后代的人觉得他们的言语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广招门徒,史书记载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来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编撰教材来传授弟子,他所编写的《诗》、《书》、《礼》、《乐》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的,《诗》本来有三千多首,经他删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诗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作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什么自己不独创呢?因为在他看来,先王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论传达出来就行了,只是当时世道混乱,“礼坏乐崩”,本来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他才会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来教授弟子,好传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贡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说,只是为了教授弟子才去说那么多话。在孔子生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专著,《论语》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为其编撰的。孔子不注重言还与他的教学思想有关。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更多地是从修身即道德方面来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只要道德修好了,学不学文都无关紧要,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去学文。从他对学《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兴、观、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更可以看出他“学以致用”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学那么多的诗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应用,学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传子夏传经,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都是来传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样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几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兰陵著书立说,他对为什么要学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经无所不包,只要学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的。
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后世的情况与前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贤的言论似乎已经不能包罗一切了,怎么办呢?于是后世的人们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从“十三经”的确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时代,并没有自封为圣人,《论语》成书后也没有很快成为经典,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才将《论语》连同《孝经》一起列为经典,才有“七经”说,唐代又发展为“九经”,宋代有“十二经”,将《孟子》列入经典后,便有了“十三经”之说。有了这些经典之后,历代的儒生们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条件和依据。他们只要去注释经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达,只是在注释的时候才阐发出自己的思想。注释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时间久了,前代人对经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释前代人的“注”,这便是“疏”,经历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经注疏”。可以说,在几千年的时间中,“我注六经”一直成为中国人著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经学的繁盛也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既然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都这么做了,后世的人还有谁敢不去照办呢?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才转向文学的创作,转向诗词歌赋和小说的写作,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学术风格或方法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它,学以致用,注重实效;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和说明,本是个人的学术自由,可是如果学术界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因为这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开发人。
孔子删诗说范文5
“……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卜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见于《大雅·大明》,则很明显前“怀尔明德”亦当为引文,《诗论》此简是引《诗》文而论《诗》。从“诚命之也”对应“有命自天”之形式来看,“怀尔明德”前当有一“谓”字,与“诚谓之也”之“谓”对应。《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一句,与此较接近,只是“予怀明德”与“怀尔明德”不同。当然,前面残缺之简文也有可能是“帝谓文王,予”几字。事实表明,这种猜想有其根据。
《墨子·天志(中)》有:
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1]
《墨子·天志(下)》 有:
非独子墨子以天之为仪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而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义,而顺帝之则也。[2]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段文字文意相近,所引之诗相对于《毛诗》即是《大雅·皇矣》。唯《天志(中)》所引同于今《毛诗》;而《天志(下)》所引多了一个“而”字3;两“不”字作“毋”;《天志(下)》所引称《大夏》而非《大雅》。
《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载有两篇考释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的文章。铭文中“我台(以)夏台(以)南”一语,考释者已对照《小雅·鼓钟》、《周颂·时迈》“以雅以南”指出:“夏”即是“雅”4。荆门郭店楚简《缁衣》中,简7与简35、36两处两次先后引大、小《雅》,其“雅”字皆作“夏”,裘锡圭、张春龙先生已指出:“夏”字“楚简文字习见,在此借作‘雅’”5。可见《天志(下)》所引《大夏》即是《大雅》。
而“尔”与“而”古通。如《易·颐》: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6。
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尔”作“而”7。又如《左传·宣公三年》:
予,而祖也8。
《史记·郑世家》“而”作“尔”9。更明显者为《尚书·吕刑》:
在今尔安百姓10。
《墨子·尚贤下》引“尔”作“而”11。可见,《诗论》简的“怀尔明德”同于《墨子·天志(下)》的“怀而明德”;《墨子·天志(下)》所引之诗与《诗论》所论之诗,至少在这一句上有同一师本。而且,下文将证明这个版本是合理的。
方授楚于《墨学源流》一书中曾指出,《墨子》中“引《诗》多散文化,《兼爱(下)》……云:‘先王之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今《大雅·抑》篇无两“而”字也。凡此改《诗》为散文,以就当时口语之体,昔人多未达其故。”12《天志(下)》此处也是有一个“而”字,但据《诗论》来看,这个“而(尔)”字并非“以就当时口语之体”,而是一个实词,不能去掉。《墨子·天志(下)》两“不”字作“毋”,这只是通假字的问题,如鲁诗便“‘不’一作‘弗’”13,并不影响文意。多或少一个“而”字,则大关文意。今《毛诗》对于这一句作如下解释: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传:怀,归也。
笺:天之言云:我归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广言语,以外作容貌,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者。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
疏:毛以为,天帝告语此文王曰:我当归于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归之。因说文王明德之事……郑以为,天帝告语文王曰:我之所归,归于人君而有光明之德……14
孔疏已发现毛、郑之不同。其实,补一“尔”字,文从字顺,即是:天帝告语文王曰:我心中怀藏着尔之美好德行——不虚广言语,以外作容貌;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虽未知,已顺天之法则”15而行之。正因为此,所以才有下文“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16。如果天帝告语文王的只是要归于明德,文王尚未有所表现,何来立即命之 “伐崇墉”?如果以 “伐崇墉”为考验文王能否为“我之所归”,那么天帝似乎过于残忍,万一文王不合所愿,天帝恐怕只好另请高明,再起刀兵了。总之,有“尔”字义胜。
不过,《中庸》文末有: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17
所引《皇矣》没有“尔”字!
子思所引之诗句不太可能是先有“尔”字,而后儒从《毛诗》或三家诗删改。后人多將子思所引之《诗》归为齐诗,这是用反溯之方法研究已失传的齐诗,然而将郭店简本《缁衣》引《诗》与今本对勘,异文不少18,恐不能将之定为齐诗。依一直流传的《毛诗》来看,《中庸》多有引《诗》与之不同者。譬如《中庸》中有: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19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大雅·假乐》,今《毛诗》作: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20
有四字不同。《坊记》中有: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21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卫风·氓》、《大雅·文王有声》,“履”字今《毛诗》作“体”;“度”,《毛诗》作“宅”;“惟”,《毛诗》作“维”22。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皆未改回。当然,改字与删字不同,上面的佐证并无力反证《中庸》原文本身绝对无“尔”字。若果有之,则注3所引吴毓江所谓后人据《诗》删掉《天志(中)》之“而”字之说倒可谓卓识;但后人并未删掉《天志(下)》中之“而”字及改“夏”为“雅”,则吴毓江之疑恐非是。而且即便有人改动《诗》文,这与本文所得之结论也并不矛盾。
此处子思有可能是截引《皇矣》,转换《诗》文,《中庸》中不乏其例,如: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23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卫风·硕人》。疏云:
案:《诗》本文云“衣锦褧衣”此云“尚絅”者,断截《诗》文也24。
又如前引《中庸》文末之: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商颂·列祖》,《疏》云:
《诗》本文云“鬷假无言”,此云“奏假”者,与《诗》反异也。25
此外子思亦因文意而直接引《诗》入《中庸》,不加“《诗》曰”,如前引《中庸》文末之:
“《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对于《毛诗》,出自《大雅·文王》,子思直接引入文中。
子思于《中庸》文末之意是想说明以声色、以德化民,不如上天化民之至境。因此“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当是截引,“予”并不用《毛诗》“帝”之义,而是紧接上文指“君子”,以《诗》文来形容君子,用“不大声以色”来代表“笃恭”,用“天下平”来说明怀有明德之效。《毛诗》以“予”为“帝”,释“怀”为“归”放在此处显然是不合文意的,因为《中庸》后文又说到“上天”。一般认为,殷周之际“天”与“帝”在表示至上神之意时,是一个概念26。因此,子思所见《皇矣》当有“尔”字。
子思之截引《皇矣》,如何反与后来的四家《诗》文及《墨子·天志(中)》一致了呢?书阙有间,现在笔者只能推断说,可能因《中庸》引用该《诗》,而后文又有“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一句,后人遂以为《诗》本来是孔子所引27,《诗》之原文如此,因而改从之。 据《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8
虽然所谓的子夏至毛公一系《诗》说没有间断地流传了下来,而且可能是孔子真传,但“儒分为八”,每一儒家别派都可能有其《诗》说乃至传颂的《诗经》版本,《毛诗》说所宗的《诗经》本文,有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有所改变。因为古人经、说分开,各自单行,《诗经》由于讽颂、传抄特别是音假、方言等缘故,小有差别,在所难免(由此遂至四家《诗》多有不同),至秦末又逢焚书,有所疑惑,无从改正。而由于孔子、子思的身份关系,况且儒家八派中有“子思氏之儒”29,《汉书·艺文志》还列有《中庸说》30,这一派影响当很大,在《诗经》出现问题时,从《中庸》确实是较好的选择;而子夏虽以《诗》闻名,但《汉书·艺文志》中未见《卜子》,其《诗》说可能有变迁,后人无法取其文作为佐证。
但是,《皇矣》的两种版本见于《墨子》,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天志(中)》所引与今《毛诗》完全一样,虽不能说就是《毛诗》,但它与《天志(下)》一“而”字的区别,却足以说明当时的墨家受儒家的影响很大。我们知道,墨家弟子也常常称引《诗》、《书》,今本《墨子》中引《诗》达12处,为先秦非儒家诸子书中,引《诗》最多者,说明墨家也以《诗》、《书》教。这并不奇怪,因为据《国语》等古籍的记载,《诗》、《书》一直是当时流行的启蒙教材。但是从墨家引《皇矣》有文字不同这一有趣的现象可以看出,不论墨家是在用哪一种《诗经》版本来教导弟子,墨家至少有一派在用儒家的《诗经》。因为儒家的教材偶有了小变化(没有“尔”字),墨家便跟着变(《天志(中)》也无“尔”字)。儒墨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原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作者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生)
--------------------------------------------------------------------------------
[1] 见吴毓江《墨子校注》306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2] 见吴毓江《墨子校注》323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3吴注:“‘而’字毕本无,旧本并有,今据补。”见《墨子校注》335页注94。另:吴于《天志(中)》注80认为:“《毛诗·大雅·皇矣》篇文与此同。下篇‘怀’下有‘而’字,疑《墨子》引《诗》原文如此。此无‘而’字,疑后人据《诗》删之。”见《墨子校注》306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4 见《文物》1989年第4期53、59页。
5 见《郭店楚墓竹简》132页注[二二],135页注[八六],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6 见《十三经注疏》41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7 见《文物》1984年第三期《马王对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第2页。
8 见《十三经注疏》1868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9 见《史记》176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 见《十三经注疏》249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1 见《墨子校注》97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12 见《墨学源流》46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中华文史精刊》本,据中华书局1934年版复印。
13 见王先谦《诗三家义疏》85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 参看《十三经注疏》522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5 从《荀子》杨倞注,见王先谦《荀子集解》34页,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16 见《十三经注疏》522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7 见《十三经注疏》1635——1636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8 参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考》,《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19 见《十三经注疏》1628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0 见《十三经注疏》54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1 见《十三经注疏》162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2 见《十三经注疏》234、527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3 见《十三经注疏》1635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4 见《十三经注疏》1635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王先谦等以为齐诗作“衣锦絅衣”,若如此则亦无齐诗传人改动《中庸》。
25 见《十三经注疏》1466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王先谦等以为齐诗作“奏假无言”。
26 参看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1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10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 今人为子思之作品如《坊记》、《表记》等加标点时,引《诗》、《书》之文亦算作孔子原话,如此恐将取消“子思作”之意义。然此习惯或即本于尊孔。
28 见《史记·孔子世家》193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孔子删诗说范文6
语文课的“灵魂”是什么呢?或者说,语文教学的本体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语文教学的本体:一是以语言教学为本体,二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体。
对于初中生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学习语言。《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可见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初中语文教材选文大都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人文精神的逻辑起点是字、词、句。语言是载体,承载着思想、文化、情感等。抓住了语言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根本,在接触语言的过程中就自然接触了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渐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和谐发展”。
语文课是美的,它潜伏在语言的深处。我们要加强语言学习,回归语文教学的本体,还原语文教学的本色,引导学生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语言丛林之中,吸收美词佳句的芬芳,感受美化美奂的人文气息,积淀博大精深的文化涵养。那么,如何进行语言教学,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语言的效率,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学生整体语文素养呢?
二、语言教学对策:朗读和品味
1.通过朗读,触摸语感
新课标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
我在上莫怀戚《散步》时,始终确定这样一个核心目标:通过朗读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全文,充分地触摸语言,通过各种形式的“读”来“披文以入情”。我的放手换来学生的放声、放胆、放情。通过这一流程,学生完成对课文的整体感知。有的学生在交流中,谈到了一家人互相包容、互相体谅的精神,谈到了可贵的亲情、温馨的气氛,谈到了尊老受幼的美德,谈到了春天美丽的景色、生命的气息。其次,让学生个性化品读文本。新课标指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教学中,我请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或一句话读给全班同学听,并说明理由。有一个学生认为第6段写得好,认为这是全文的关键,分歧的产生使文章进入一个小高潮,她声情并茂地朗读了第6段。我马上引导其他学生对这个学生的朗读进行点评:有的学生认为,她总体读得不错,但作者当时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不充分,读的时候应该突出“都”字;有的认为,还有“早已”、“还”、“在外面”要稍稍强调一下。因为这几个词语是具体说明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原因。而且三个人听从“我”的原因也不一样,母亲对“我”的依赖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早已”要重读;而妻子是因为给“我”面子才听“我”的,因此,“在外面”要重读。有的认为,“我说,走大路”读得太平淡了,要读得语气很坚定,才能表明作者对母亲的孝顺。我请这个学生来示范朗读:“我说:‘走——大路。’”我乘胜追击,要求全班学生一起朗读该段。学生们读得入神传情,好比经过了一次精神洗礼,个个精神焕发。
2.比较品味,领悟语感
在语言品味中,最适宜用比较式,以达到学习语言、培养语感之功效。其方法择要如下:
(1)添加。所谓“添加”,就是在原文上添加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文本的语言。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原稿中有这么两句诗:“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后来编入教材时删掉了“那怕”。教师指导学生品味这两句诗时,可将“那怕”重新加入诗句,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那怕”是一种猜测的语气,而去掉“那怕”更能表现诗人大胆的肯定和浪漫的理想。
(2)删减。所谓“删减”,就是在原文上删减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如莫怀戚的《散步》中介绍一家人散步时写道:“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引导学生删掉定语“我的”,语意有何改变?通过比较体会学生不难发现原文写得很庄重很严肃,大词小用、小题大做,是本文语言的一大特色,所以学生朗读这一句时要庄重、严肃,马上可把他们领入文本意境之中。
(3)调序。所谓“调序”,就是调整原文的词序、句序、段序,变换其在文中的位置,让学生品味语言的妙处。如朱自清的《春》,文末用三个比喻句总写春天:“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将这三个比喻句顺序调换,让学生品味出原文是从“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青年”的年龄顺序来描写,写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景象,即春天是新的,是美的,是健壮有力的。
(4)置换。所谓“置换”,就是采用置换课文的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的办法,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课文的语言。如朱自清的《春》中:“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若把这句中“偷偷地”改为“暗暗地”,好不好?通过比较品味,让学生明白“暗暗地”是“在暗中或私下里,不显露出来”的意思,而“偷偷地”是“形容行动不使人觉察”的意思,有调皮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