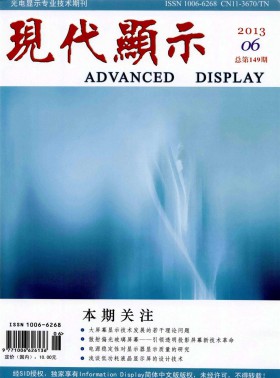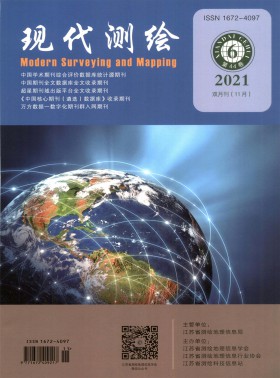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小说非主流传统与白先勇写作的相关性,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谈论传统与个人的关系,关注的有两大方面,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现代小说传统主要指由小说写作形成的现代书写传统,包括观念的、技法的和意识形态的,也包括对“现代”以来中国人性格命运的表现,它随着现代小说的发展而沉积和增生,是流动和变化的;而小说内涵体现的文化传统,如现代小说对古典白话小说美学意蕴的继承、小说描写的文化特征和人物形象的精神传承等,是现代小说对已形成的文化传统的观照,在白先勇小说研究中,这方面的论述较为多见。本文思考的主要是白先勇小说写作(特指20世纪60~80年代的短篇)与现代小说书写传统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与影响关系。
一、时间
自五四时期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之际,短篇即成为相对完善的小说品种,因较早具备成熟形态,其传统也较其他小说体式更丰厚,形成了诸多小说内涵和写作思维形态的脉络。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与问题小说、现代抒情小说和具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特征的小说即已出现;20年代中期乡土小说集中涌现,这一个十年也是短篇小说的年代,在论述上,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在帮助读者接受现代短篇小说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①至30年代救亡图存、左翼思潮兴盛之际形成“正格”的写实小说和战争时期的戏剧化小说模式,以及本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30~40年代的个人化小说等,这些小说现象在短篇中均有突出体现,且与社会风潮、时代精神息息相关。而白先勇文学成就的高峰也是以《台北人》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所以本文虽然没有做出特别区分,但论述主要基于短篇小说形态。
在现代小说的演进脉络中,大致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状态:五四至20年代的多元小说形态到30年代随左翼文学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正格”的写实小说一脉占据小说主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直至成为新中国后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小说意识形态。这种格局的形成自有原因,马克思主义文论在30年代已经成为有影响的小说理论;战争时期“历史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决定了作为主流派的中国小说的创作面貌及其理论形态”,②文学也更加强调反映“历史规律”、表现典型和本质,出现对社会关系理解上的简化和纯化,以及戏剧化的小说模式。人物关系、情节组织更强调对立冲突和矛盾斗争,直至号召书写“英雄形象”,体现出明朗、昂扬、崇高的美学追求。但研究者也早已注意到,即便在战争期间,文学也存在着西方现代主义的输入和背离戏剧化小说的别种体验。30年代的沈从文和40年代的张爱玲均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之路,加上京派、海派的其他作家,形成了与时代主潮相异的又一小说流脉。他们也被文学史家们归纳为“个人化小说”,以区隔于“正格”的小说主潮。沈从文“是以一种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作为他的小说观的基础的”,“所面对的是未经加工改造的原生形态的自然与人性,也就从根本上拒绝了将生活结构化、典型化的努力;而且他所关注的中心是‘变’中之‘常’,也即自然与人生命中神性的永恒、庄严与和谐以及这种生命神性的表现形态(形式),与前述主流派作家从社会历史的变动中去把握、表现对象,俨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③张爱玲在解释自己写下的人物时这样说道:“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④其实,沈从文与张爱玲所属的京派与海派,彼此间在小说观念、书写内涵与风格方面存在龃龉或分歧;但是在与时代主潮的关系上,他们又是相同的,均在审美格局、意识形态上保持距离。而从更长的时段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上看,他们的命运也有相近之处。因此在谈论小说脉络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作家个性或写作内涵等等的异同,因为这一类差异无处不在;而是看小说史中的位置,而位置又往往视其与主潮的关系而定。
再看60年代在台湾大放异彩的白先勇。作为一个在政治军事斗争中败北的群体的后裔,白先勇没有机会与意愿承袭30~40年代的小说主流传统,他的短篇写作中充满着流离者对逝去时代的追忆、对当下境遇的感伤和对文化传统的缅怀,交织着50~60年代台湾无根心态带来的惶惑与迷惘,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灵魂挣扎,加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无论文学观念、写作内涵还是技法均与“正格”的小说主潮相异。如果在现代小说脉络中确定白先勇的位置的话,他显然更接近于30~40年代个人化小说的精神,与沈从文、张爱玲的脉络相连。已有众多研究者注意到白先勇与张爱玲文学气质的关联,毕竟他们共同拥有的那种苍凉的美感、繁华散尽后的悲凉,以及《红楼梦》式的对器物、感觉、环境、语言和心理的精细描写,让我们足以自然地将他们联系到一起。而在具体写作形态上,沈从文与白先勇之间并不会产生直接的联想,散发着自然与人性光辉的宁静乡村与饱尝离乱的流浪的中国人似乎并非共生在同一时空下;“在沈从文这里,绝不可能有‘戏剧’,只能有‘散文’与‘诗’。”⑤而白先勇的短篇写作不追求“抽象的抒情”,带有“戏剧”与“诗”相融合的特征,手法上现代色彩更为突出。他不具备沈从文的安详,更注重情感和内心的表露,也有为历史和群体立言的意图。而在时空调度、人物类型、作者情感侧重点上也不同于张爱玲的细腻琐碎与冷峻旁观。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白先勇是沈从文或张爱玲在台湾的传人,但是在更大的论述架构内,在现代小说传统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在小说观念、艺术价值取向、情感和理智抉择等方面的相通之处,这不是说具体艺术表现上的彼此相像,而是骨子里的契合,以及一种近乎于命运共同体般的境遇。正是这一切使他们成为同一小说脉络的维系者和传承人。这种取向、选择与境遇的相通点大致如下:
首先,他们均拥有“回望”的姿态与悲悯的情怀,其共同关注点在于现代中国动荡时代的离乱与创伤,而非革命与胜利。他们以“悲”为情感主调,无论是悲凉、悲哀还是悲悯,都是对逝去风景的凭吊,而与革命的激情南辕北辙。这种本质的契合更多在于表现世事之无常,那种离乱、沧桑中的常与变;对战争、人性的存在体验和苍凉悲怆的美学风格,以及个体式的生命体验。以沈从文而论,尽管他专注于性灵和生命的升华与超越,但“如果读不出沈从文用‘和平’的文字包裹下的心灵下的‘伤处’,是读不懂沈从文的这些乡村牧歌的:这是他的流浪于现代都市,受伤的充满危机的生命和着意幻化的‘平静乡村人民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一个融合。”⑥如果说沈从文更关注“变”中之“常”,想以文字保有永恒的生命状态的话———诚如他的短篇《新与旧》那样,宁静恒常的生活状态一旦被打破,引发的精神崩溃令人无法承受;那张爱玲与白先勇似乎更注重由“常”到“变”过程中,时代和个人的破碎感,强调命运之手的拨弄,无论是《倾城之恋》还是《一把青》、曹七巧还是尹雪艳,或为命运的化身,或为命运所左右,完全看不到所谓本质与规律、社会意识与明朗风格,以及人物的英雄主义气质,只有在繁盛与没落的映照中发出的慨叹与悼亡之思。这是因为,作家与他们的人物大都是时代大潮中的被放逐者或自我放逐者,他们从来都沉浸于回忆之中而不展望未来,他们的人生体验和美学趣味使之无从乐观,进而在时间之河中逆流而上,在向后看中获得耽美、怅惘和安稳;也是因为,追忆与缅怀本身就是文化传统和文学美感的重要来源。正如张爱玲所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⑦白先勇则从文化传统中为自己的小说情怀寻找依据:“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⑧这些表述似乎概括了从沈从文到白先勇一脉的小说价值取向,它们与同时期大陆中国的社会主潮相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然在这一语境中处于个人、边缘和非主流的位置。
白先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接续上述小说脉络的同时,又继续以个人和群体的共同经验丰富和拓展了这一脉络的审美内涵,他以无人替代的角度和视野,书写了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迁徙之中和之后的群体与个人的命运和情感,并创造出了现代短篇小说书写中的诸多“第一”和“唯一”的文学经验。“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⑨《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⑩描绘的“流浪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底层草民,所透露的现代版的兴亡沧桑几乎无人可及,而且,从北到南、从中到西,作者是在更阔大的场景中整合这些经验的。“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悲得多”,也可以说,与张爱玲的冷峻旁观相比,白先勇更多了温润与悲悯;这种温润与悲悯源于身在其中、推己及人的情感抒发,也源于对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感慨和对古老文明走向沉落的不舍。归根到底,白先勇比张爱玲有更大的企图心,他要为历史中的失意者和一切已逝与将逝的美好作见证。
第二,这一小说脉络在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上也持相同的立场,即执着于艺术追求,反对文学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远离文学的宣传功能,认为艺术性才是写作的立身之本。这仍然是他们与主流相悖的重要原因。按照沈从文的说法,“近二十年来的文学风气,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以来,他就应当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检查’了,‘批评’了,他的主张意见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但我们可不必为这事情担心。”“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像样些。”沈从文心中的“希腊小庙”供奉的是艺术、人性与真善美;他追求“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张爱玲也在前述文章中谈到:“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这些针对批评所做的辩解也体现了作家对主流的敬谢不敏。白先勇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一直表现着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以社会政治改革为目的,不是以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或功能为标准,而是把文学定为社会改革或政治变更的工具。”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使文学艺术丧失了独立性,而“成功优秀的作品都是在社会意识及小说艺术之间取得了平衡妥协后的成果。”这种文学观念的相近之处也是非主流小说脉络形成的又一依据。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沈从文的乡下人、张爱玲的都市人,直至白先勇的流浪的中国人,都已成为现代小说史上不可取代的经典艺术形象。
二、空间与经典化问题
也许,空间是上述小说脉络的又一重要意义之所在。以上谈论的基本上是时间维度的描述,而没有空间维度的参与,这一脉络的意义也将很不完整。1949年以后,在大陆,解放区文艺在新中国的延续居于绝对的主流位置,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和小说主流在不违背《讲话》精神的前提下也获得了认可。30~4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典型论“十分奇异而又似乎顺理成章地被‘改造’成了‘党的文学’与‘工农兵的文学’的新规范、新模式。”“40年代及以前多种小说观念、创作形态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局面,基本上已告结束。”“这导致了小说作家的大规模更替的现象,也导致小说取材、人物类型、小说语言、艺术风格向着某一确定方向集中的情况。”所谓大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阻断了小说的丰富性,短篇小说———当然还包括其他文学形态———趋向规格化,以至于会出现关于《百合花》、荷花淀派等一体化内部的批评论争,即在基本实现一体化的前提下,内部的艺术风格差异也会引发质疑。50~60年代短篇小说名家,如赵树理、孙犁、峻青等均隶属解放区文艺一脉,他们风格各异,但基本精神趋同,即向前看、明朗的美学气质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对新政权的肯定与赞美。任何涉及内心、个人私生活,或仅仅是涉及阶级内部人性弱点的文本都受到批判和整肃,至于具有叛逆观念的文学家,如胡风等则遭受灭顶之灾。30、40年代超越时代规范、非主流的小说家或沉默或皈依,均销声匿迹;沈从文和张爱玲或被迫噤声,或主动逃离,其影响完全被抹去。而在当时全中国的文学地形图上,客观上延续个人化小说的是台湾的白先勇和他的同伴们,他们与大陆的小说主流虽无任何交集,却同时代表了20世纪50~70年代短篇小说的两大书写面向。
不过由于空间的变动,白先勇与现代小说主流的关系却与他的前辈不同,因为这一主流并不与台湾语境构成直接冲突,或者说,由于1949年后的两岸隔绝对峙和这一主流的左翼色彩,它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可能在台湾得到官方的和公开的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小说脉络没有生存空间。在白先勇开始写作的年代,台湾文学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写作,如反共文学与战斗文艺,但不足以一统天下。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和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促使文学寻找书写人们焦虑和苦闷的独特方式,直接导致现代主义的兴盛。在政治宣传的文学甚嚣尘上之际,现代主义文学也逐渐生长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失去了在台湾传播生长的可能,但是在批评家、理论家的倡导下,非左翼文学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获得了高度推崇。尽管沈从文的作品由于他身在大陆也曾被禁,但这一脉络,特别是张爱玲在台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构成了颇有意味的文学空间形态:30年代以来的小说主流汇同解放区文艺在新中国获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在台湾却处于被禁绝的状态;而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的个人化小说由于与新中国的文学功能和美学气质完全不匹配,在1949后被彻底遗忘,直至8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但在台湾却代有传人。这两支从大陆生长的小说脉络在不同空间的此消彼长形成了独特的演进曲线,分别被阻断,又分别被延续。
白先勇幸运的是,他没有直接面对与主流的冲突,他的艺术经营、回望姿态、为逝去时代唱挽歌的写作不但没有受到大陆政治大格局的影响而湮没,而且引领了台湾小说的时代潮流,并将在大陆被中断的小说脉络发扬光大。他对社会政治左右文学、忽略文学艺术性的批评,也是在考察了现代小说发展历程后的认知,而不是遭遇直接压力后的辩解。沈从文和张爱玲却没有这么幸运,在汪曾祺1980年接续沈从文的一线香火之前的30年间,沈、张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大陆的现当代文学论述中。原来非主流、进而中断的小说脉络经由白先勇的努力在台湾重现生机,这种不同空间主流与非主流位置的互换恰是这一脉络奇异的命运。当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生发有着文学内外的多重原因,其中的许多作家与大陆现代小说传统的关联并非像白先勇那样明确———这也更突出了白先勇个人在小说脉络中的重要性———但是对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却十分接近。沈从文、张爱玲在新中国的境遇与白先勇在当代台湾文学中的位置其实是一回事,是同一文学脉络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处境。完全可以设想,白先勇如果出现在同时期的大陆,其境遇无疑会与他的前辈完全相同。当我们关注白先勇写作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意义的同时,它在大陆语境之外的意义同样需要再加详察———虽然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将白先勇写作放置于台湾小说发展进程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与大陆小说流变相类似的情形,即同样存在不同理念的小说功能观和不同的写作形态,当然并未出现某一脉络彻底压抑其它脉络的状况;研究者将白先勇与陈映真相对照而梳理出的小说脉络,也在昭示台湾语境下他们各自的文学史意义。这也启发我们整合同一研究对象在两大语境中的全部意义。
80年代沈从文、张爱玲在大陆的重新出土、海外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引进,其实也是影响随后的文学史重构热潮的因素之一。除文学史论述的大幅度调整外,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沈、张重新成为文学经典,汇入现代小说传统之中。这当中,文学史论述、作品选本、大学教学等均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而自白先勇短篇小说于70年代末进入大陆以来,也因其艺术特征和成就加入了文学研究界重塑文学经典的过程,研究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他与现代小说非主流脉络的相关性和独特性的。其实,早在白先勇短篇小说诞生之际,这种相关性和独特性就已然出现,因为白先勇已经用他的写作连缀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空,“滋养了白先勇写作才华的熙熙攘攘的社会,值得我们在这儿褒扬一笔,因为后产生中国近代文学初期果实的,也正是同样的土壤。白先勇和他的同时期的作家们承继了20年代和30年代西化的中国作家的精神。”这段写于70年代中期的论述强调了白先勇的写作空间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性,也将白先勇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流脉中。无论如何,经典化需要文本具有穿越时间、空间的力量,这是最根本的。白先勇之所以令人意识到他在中国现代小说传统中的位置,或者说已经构成传统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小说公认的艺术成就。???经典化还需要一个时期和特定空间内艺术趣味的遴选,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评价标准的转变使非主流小说传统获得了肯定,也使它们的经典化成为可能;同时,经典化还需要研究者的论述和一个恰恰可以安放、无可替代的位置。就白先勇小说写作而言,这些条件均已具备。
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张爱玲和60年代的白先勇,是中国现代小说非主流传统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之外,还有众多参差多样的小说脉络,如讽刺小说、乡土小说等等;作家个体之间也存在各种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大而化之的描述只是突出了上述三位作家与现代小说主流关系上的相似性和他们对艺术经营的共同追求,尚未对所涉及的诸多现象、概念做出认真辨析,也没有将大陆与台湾的各个小说脉络平顺自然地整合到一起,仅仅期待从现代小说传统的角度思考白先勇的位置和贡献。
本文作者:计璧瑞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