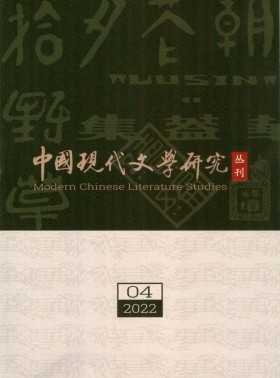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叙传小说,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自胡适的话剧《终身大事》和鲁迅的小说《伤逝》之后,娜拉式的中国女性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地书写与演绎,女性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成为“五四”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在第一代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取材于自身生活与情感经历的自叙传小说中,都弥漫着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身影。“五四”以后,苏雪林的《棘心》、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白薇的《悲剧生涯》、苏青的《结婚十年》和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等自叙传小说,在叙事上都关注女性反封建的努力,用不同的叙事策略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女性冲破家庭拘囿走上自我解放之途,勾勒出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较为清晰地揭示出现代女性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逆来顺受走向反抗的心灵嬗变。从成长视角来分析这五部小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发掘女性自叙传小说的性别意义,重审女性解放之途,为当下女性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一、在时代夹缝中求生
《棘心》以苏雪林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塑造了杜醒秋这个在旧与新的时代夹缝中艰难挣扎的女性的成长经历:出生于封建家庭,从小性格像男孩,淘气好武,六岁上家塾,受叔父与兄长熏陶,阅读传统小说与典雅文言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民国初年,现代文明对杜醒秋潜移默化的熏陶促使她去教会学校就读并决定报考省城女子初级师范学校,遭到祖母阻挠,醒秋以死抗争。自女师卒业后,醒秋拒绝包办婚姻坚决要求升学,后如愿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因缘际会赴法留学。在异国他乡,醒秋为爱情所困,为母亲所苦,最终扼杀了自己的初恋,用理智战胜了情感,转而将情感寄托在素未谋面的未婚夫身上,并用传统的婚恋观念来慰藉寂寞芳心。在精神极度困苦中,醒秋皈依基督教,由五四时期的唯理性主义者成长为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在杜醒秋的成长道路上,以“民主”、“科学”为表征的“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给予她以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但因身处新旧文化的转型期,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文化共同构建了醒秋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时代新女性,醒秋有明确的个性解放追求,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对封建礼教尤其是孝道扼杀人性的罪恶有切身的体验,强烈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受困于封建婚姻和抗拒包办婚姻,是醒秋所处时代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境遇,同时也是苏雪林那一代女性真实处境的反映。醒秋已具备时代赋予的新品格,但旧的传统文化根基却不时羁绊她。在留法期间面临突如其来的甜蜜初恋时,她虽对浪漫爱情充满憧憬与期待,却不时用母亲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对母亲的“孝”来扼杀汹涌澎湃的爱情。个人情感的受挫、兄长的病逝和母亲的病重不断加剧醒秋内心的冲突,在妥协与抗拒间不停地拉锯,无尽的内心痛楚将她推向了基督教。但这种皈依缺乏稳定的心理根基,因而这种信仰一旦面临现实考验,就将如风雨之中的飘萍摇摆不定。母亲疾病的加剧迫使醒秋以家庭期望为重,中断留学生涯回国完婚,并期望在包办婚姻中享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情感的满足。醒秋在与未婚夫的通信中,就已感知两人性格旨趣间的巨大差异,感情一度走向破裂,但思想上旧与新的二重性使得她仍寄希望于将来,并对婚姻抱有极大的热忱。从小说最后一章未婚夫读醒秋来信时的心理,我们可以预见婚姻的美满只能是醒秋的一厢情愿。从醒秋的童年—求学—抗婚—升学—留学—皈依宗教—归国完婚这一成长过程来看,醒秋的自我意识仍处于蒙昧状态,抗婚也好,完婚也罢,都只是内心冲突的外化,明确的女性意识还处于潜伏状态。醒秋的个性解放只是时代裹挟下的一种不自觉的折射而已。醒秋的婚姻悲剧恰恰是五四那一代女性进退维艰的真实生活写照。
二、忘记自己是女性
与夹缝中求生的醒秋不同,《女兵自传》中的鸣冈虽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家庭成长环境相似,都受包办婚姻之困,但因主体选择的差异而呈现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女兵自传》叙写了“我”的成长经历:20世纪初期出生于一个思想正统的封建家庭,母亲泼辣专断,父亲传统但不保守,三岁订婚,六岁采茶,八岁裹脚,十岁进私塾,十二岁入大同女校读书。童年时代的“我”酷似男孩,上山下河,野性十足,为求入学而绝食。入女校读书后,“我”在二哥的指引下阅读大量的新文学作品,男女平权意识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得到强化,也是在二哥的鼓舞下,抱着女人也是人,女人也要投入社会洪流的信念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哥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时刻提醒“我”要“忘记自己是女性”,不断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引导“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以寻求自我解放。二十岁时“我”从军北伐,成为一个革命女兵,用火热的青春谱写革命激情。北伐失败后,“我”回到家庭要求退婚却遭母亲禁闭。历经四次逃婚后,“我”终于摆脱包办婚姻辗转到上海和北京求学,并实现了婚姻的自主。穷困与饥饿成为“我”生活的常态,尤其是女儿出生以后,生活更是拮据不堪。婚姻破裂后,为改变生活困境,“我”被迫以写作为生。物质生活虽然困顿,但“我”要求上进的心却从未因环境而动摇过,一有机会就赴日留学,实现深造梦。东北沦陷后,“我”毅然归国,投入到火热的运动中,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尽绵薄之力。后辗转到福建教书,半年后再度赴日留学,却因爱国而被关进日本监狱,身心备受摧残。被营救回国后,母亲病逝,抗战爆发,“我”离开病重的父亲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在火线上劳碌奔波。
“我”从出生到抗战这一段人生,物质上尽尝饥饿严寒,空间上不停地迁徙,在新化乡—益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东京—厦门—东京—长沙—重庆等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我”虽为女流之辈,却用一系列去女性化的从军、抗战等行动投入革命洪流,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摆脱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将自我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兵。“我”最初的成长动因源自逃脱封建婚姻的羁绊,寻求自我解放,国家的落后与民族的苦难在成长的道路上起了催化剂作用,使“我”深切感受到一种源自现代文明的身份焦虑,成长的困惑亦如影随形。“上路,是成长小说中最基本的结构要素之一。上路也意味着行动,行动的过程往往反映在上路后的行程中”[1]85。“我”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流徙,用“在路上”的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我”虽以压抑女性性别的“拟男化”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成长,有意忘记自我的性别却时时被提醒,并与传统观念不断造成矛盾与冲突,以致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说叙述“我”作为一个革命女性的成长,在参与国家、民族的建构时,是以压抑女性的情感为代价的。国家的兴盛2与个体的情感满足在“我”身上很难得到协调,“我”的成长虽与时代主潮同步却同样充满苦涩。#p#分页标题#e#
三、寻求女性的生存真相
《悲剧生涯》真实记录了白薇从1925年至1935年间的感情纠葛,以艺术化的手法抒写了女主人公苇十年间的情感炼狱与精神成长。苇与展分分合合的十年,恰是苇寻求女性生存真相的痛苦过程。苇从包办婚姻中出逃到日本,与花心自私、不负责任的展发生恋情,但这段情感却让苇从肉体到灵魂都受尽煎熬,身心布满无法弥合的创伤。从展身上传染的淋病,因无钱医治而让苇心力交瘁。性给苇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漫长的身体痛楚与灵魂撕裂。苇一次次地与展断绝关系,却又一次次地复合,十年的分离聚合,真实地体现出苇作为一个女性的懦弱与依赖心理,虽让人可怜可叹,却写出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娜拉面对社会、面对爱情、面对革命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2]。对肉身的体验,是女性成长之途的必修课,也是女性感知自我与他人关系、建构“我”与他者关系的起点。小说真实刻画了苇恋爱时的肉身体验:火热的红唇、热辣的拥抱、男女间的肉体依恋,从女性的性别立场彰显经验。小说侧重从女性性别视域出发揭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威压。亲友的误解,社会的歧视和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弱势,给苇的生存带来种种难以排解的压力。与展的爱情破灭后,苇对于自己情感的懦弱进行深刻反省,意识到女性必须在人格上与男性平等,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叛与对现代独立人格的追求,是苇历经爱人的背叛、家庭的遗弃和革命团体的排斥后仍矢志不渝的信念。苇在日记中对于爱情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自身的忏悔,是对社会规范和男权中心主义的质问,对女子真相的寻求实际上就是展现女性生存真相的过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若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寄予在爱情与婚姻中,只能是一厢情愿;同样,投入社会革命团体也无法扭转女性的真实处境,无论是私密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女性都无法确证自我。从这一层面来讲,苇的十年不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产儿两性剖析图”,而且“也是那一时代女性群体生活的解剖对象,一个可供后人反思、认识、回顾的立脚点,一个不曾淹没于男性话语中的女性生存的见证”[3],是女性真实处境的写照。
四、职业妇女的“入城”与“出城”
与二三十年代在家庭与社会间苦苦寻觅出路的女性作家相比,四十年代的女作家更侧重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叩问生存本质。《结婚十年》和《退职夫人自传》即从日常生活出发,关注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于细微处发掘生活中的幸福与苦涩,在婚姻生活中完成女性的成长。《结婚十年》讲述了苏怀青琐碎的十年婚姻生活:从新旧合璧的婚礼、婚后读书的情感插曲、怀孕生女到组织小家庭,再到丈夫移情别恋后的分道扬镳,刻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家庭妇女是如何一步步通过写作谋生而成长为职业妇女的艰辛历程。个性倔强、自尊好强的怀青,出嫁后在大家庭中面对严厉的公婆、刻薄的小姑,一时无法完成身份的转换,妻子、母亲、儿媳、嫂子等多重角色让她渐渐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过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而已。到上海组织小家庭后,大男子主义的丈夫百般阻挠怀青看书写作,怀青只能郁郁寡欢,压抑自己的求知欲和写作欲,委曲求全做一个称职的太太。丈夫发迹后的百般冷落与背叛,经济上的受窘,太太梦的破碎,迫使怀青走上自立之路,于艰难时世中寻求生存。怀青结婚的十年,是婚姻理想的幻灭和女性自我的觉醒。十年的婚姻促使怀青在“入城”后主动选择“出城”,经济上开始独立,不再依赖男性,虽然这种转变实非怀青所乐意的,但却真实勾勒了19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处境。
《退职夫人自传》中的“我”从小叛逆、乖僻、追求独立,因在家庭中缺乏关爱而逃离,投入有妇之夫的怀抱。离开有妇之夫后“我”四处求职,走上职业妇女的道路,并一度成为上海媒体界的中心,随后与阿乘恋爱结婚。与陈浩、松元、邵平、阿乘、阿康等异性的感情纠葛,让“我”对女性的经济独立有了更透彻的领悟。婚姻让“我”看清男性的本质,心智走向成熟,打破了将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的迷梦。虽然“我”处处流露出女性的怯懦与柔弱,终究跳不出男权社会的传统藩篱,很多时候以男人对自己的爱来肯定自我,但“我”在婚姻中主动选择“退职”,即是“我”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坚决反抗。“我”虽出生于1920年代,但“我”对情欲的追求,对贞洁的蔑视,对纯粹爱情的渴求,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种种桎梏。时隔多年,仍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潘柳黛的小说“不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就是今天来看,也是开了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柳黛比苏青走得更远”[4]。
与《棘心》、《女兵自传》相比,《悲剧生涯》、《结婚十年》和《退职夫人自传》关注的是女性“围城”里一己狭小的天空,是女性在婚姻中寻找自尊、确证自我的痛苦挣扎。醒秋、鸣冈、苇、怀青、柳思琼这些女性,虽生活在不同年代,但都用行动演绎了一个共同的故事:个人经历虽不同,但都彰显现代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解放的时代命题,用爱与痛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这五部自叙传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大多与作家的亲身经历有着同一性,用沉静的笔调来叙述既往的生活,重新揭开生活的疮疤,这本身就体现了作家思想上的一种成熟。“为什么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叙述?叙述其实就是一种反思。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混沌的人生,人们需要通过反思找到新的生活起点和方向”[1]175。从这一层面来讲,女性作家对于自我成长的叙事更值得玩味与深思。
醒秋是五四时代的产儿,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无所适从,追求解放却无法实现自我解放。醒秋为了母亲而牺牲个人幸福,恰恰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先驱们对“母性”过度关注的投射。身世凄迷的白薇以苇的痛苦爱情续写着五四的时代命题:“出逃”的女性在极度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如何与生活顽强抗争,如何苦苦寻觅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真相。苇所经验的肉体与灵魂的涅?,又一次确证女性在社会中的“他者”地位。与醒秋、苇相比,鸣冈在女性解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将生命的热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洪流,成为一个和男子一样有用的大写的“人”。小说文本对个人爱情、婚姻加以回避,对离婚也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集中在从军救亡,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对个人情感加以规避,在一定程度上也与1930年代的文学主流相吻合。苏青与潘柳黛由于时代环境和生活境况的制约,对于自我成长的关注更多侧重于婚恋家庭,从日常生活层面展现知识女性生存的无奈与悲哀。婚姻是女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也是女性认识自身、认知社会的重要途径。怀青、柳思琼这类女性,对异性与婚姻满怀期待,在满腔热情的付出后,换回来的是婚姻美梦的破碎。梦醒时分,现代娜拉却仍奔突于自我解放的坦途,用肉体的疲惫与心灵的辛酸换取生存的尊严。#p#分页标题#e#
总的来看,这五部自叙传小说描写了中国知识女性由清末民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成长历程,展现了现代女性挣脱父辈与夫辈编织的家庭牢笼,投入到社会中去寻求自我解放的历程。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叙事,正是中国现代女性寻找自我解放之途的真实映照,也是中国式娜拉与男权社会抗争的历史见证。娜拉的身影虽已随着时代渐行渐远,但其间留给当代女性的心灵启示,却有待我们去不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