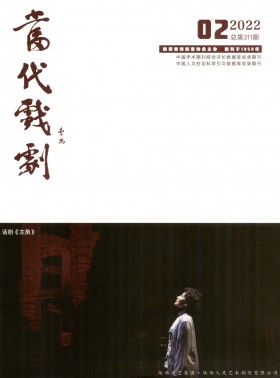本文作者:赵雷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家作品是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基础,对作品的阐释更是文学史书写的重点。面对一部文学作品,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借鉴,也需要独出机杼的新观点、新发现。纵观1949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品分析模式可以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分析式和感悟式。前者类似于“二分法”,即把对象划分为思想内容(包含故事梗概、时代背景、思想认识、社会意义等)和艺术形式(囊括结构手法、人物塑造、语言特色、情节设置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后者更多地将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分析时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感悟和阅读体验。二者间的区别不仅在于治学路数,也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前者则更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有一套可资遵循的既成的思路和操作规程,只要将作品套入其中就可得到结果,近似于一种模式化的知识生产;后者更多地是一种类似中国传统文论“整体感悟”的艺术体验,要求写作者有较强的艺术敏感和概括能力,有时甚至需要一点“灵感”。这两种作品分析方法原本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却是,分析式的作品分析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以至文学史书写的固定模式,而感悟式的作品分析方法却几成绝响。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建国以来的学科发展历程,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对两种作品分析模式进行初步评价。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中,王瑶是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分析的,并未将其条块分割。例如他对《阿Q正传》的评述:这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漫画式的集中了一切民族的弱点而写成的农村无产者的浮浪的性格。在这里,对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那时革命形势的实际的表现达到了可惊的成功,(但这并不是主题,只是侧面的背景的描写。)而且说明了革命的动力是要向背负着封建历史重担的农民身上去追求的。鲁迅先生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这就说明了他底现实主义眼光的敏锐。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已有了好几年,”就因为他老早感觉到,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不可分离的因素;“辛苦而麻木”的农民生活,也和整个他所感到的中国灰色的人生调子很调洽,这样,就自然集中地成了他所要讽刺的影子。实际上,阿Q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而缺乏反抗意识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但他却多少是漫画化了的,就是说阿Q那些特征并不是农民所独有的,而是集中了各种社会阶层的,特别是新旧士大夫型的缺点和毛病的。鲁迅的人间爱深深地藏在那些嘲讽的背后,他要我们正视我们身上的缺点,勇于洗涤我们自己的灵魂。事实上,自从阿Q被创造出来以后,我们民族是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在做着不断地洗涤自己的工作的。周扬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这话主要是指《阿Q正传》说的。〔1〕
此外,书中比较重视作品创作背景的描述和介绍,并且往往将其放在首要的位置。比如论述《彷徨》,第一段如下:《彷徨》中的十一篇是一九二四年开始写的,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新青年》初期,鲁迅就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他既“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又“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终于“呐喊”起来了。而且这声音是如此的宏亮,立刻摇撼了青年人的心。到《新青年》分化以后,鲁迅是游勇作战了,正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时候,但他并没有停止了战斗,他是“荷戟”的;而且这韧性的持久战是一步步更深入了。当然,看见很多战友的中途变节,心境是凄凉的,《彷徨》中就不免带点感伤的色彩,热情也较《呐喊》减退了些。他自己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是实在的。但鲁迅是并不会孤独下去的,当他默感到革命的潜力和接触到青年的热情的时候,他的战斗是极其尖锐的,这在杂文的成绩里就更可找到了说明。〔2〕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史稿》最突出之处无疑是在作品分析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卓越的概括能力。作者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的独特风格和整体面貌,语言优美而精炼。如把庐隐小说的主人公概括为“负荷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热情而又空想的追求人生意义,苦闷彷徨而又狂叫着自我发展;是那么脆弱,那么焦灼的青年”〔3〕;将朱湘的诗歌特色描述为“作风恬淡平静,也以文字韵律的完美著称。诗中还保持着一些五四时期的高亢的情绪;歌唱着对世界的温暖的爱,而又找不到思想的归宿,这就是率直而到处碰壁的诗人的写照”〔4〕;俞平伯的散文则被贯以“文字不重视细致的素描,喜欢‘夹叙夹议’的抒写感触,很像旧日笔记的风格。文言文的词藻很多,因为他要那点涩味;絮絮道来,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洒脱与趣味”的评价等等〔5〕,均妙语连珠而简练贴切。尤其王瑶先生对《野草》的经典阐释:“这是诗的结晶,在悲凉之感中仍透露着坚韧的战斗性。文字用了象征,用了重叠,来凝结和强调着悲愤的声音”〔6〕,寥寥四十余字胜过成篇累牍的条分缕析而抓住了作品的神采与韵味,堪称神来之笔。此外,他还注意对艺术上具有相似性的作家进行比较,明确各自的独创性,找到“同中之异”。例如分析王统照的小说“和初期叶绍钧的作品相似,都追求着人生的真意义,但他却更憧憬于美和爱;后期的热情虽然少了一些,也并不像叶绍钧那么‘客观’”〔7〕。#p#分页标题#e#
《史稿》因其“个人化”的写作特点,较少带有后来文学史著述的“体制化”痕迹而更多带有史家个人色彩。注重艺术分析和史著语言的锤炼,而在运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上则较为机械,更多带有尝试的意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理论与文学感受二者间的某种“分裂”。对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定的“落后”作家及其作品过于肯定(虽然是在艺术层面)缺乏批判,便成为《史稿》受到严厉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王瑶的《史稿》作为学科开山之作,一方面许多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处理,可资借鉴的前人经验和知识积累不多;另一方面,这也给了作者极大的自由,可以不拘一格,少有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势和种种既成的框架。这二者结合起来的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书中最精彩、最为后人称道之处,是他对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作者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却也是传统的论述模式。说它新,是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在文学史中运用过这一方法;称其传统,则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评论样式。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感悟式”的作品分析范式。它更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注重从整体看待对象的思路,善于对作品进行全局性的把握。对研究者来说,这并不是忽视作品的多层次性,但在思维和论述中常常不把它分割开来,而是努力将其融和在一起。尤其艺术性方面,不是条分缕析的“拆零”,而是整体的“体验”,即借助研究者的艺术感知去体味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整体风貌。这种处理不是借助把作品拆分为语言、叙述、人物等零散的诸多方面来进行,相反,它是依赖于在阅读中产生的直接的心理活动和审美体验,其中也许不乏理智的认知,但更多的却是个体的艺术感悟。在将主体所把握到的作品之“味”完整地传达出来的过程中,行文也是高度简练和艺术化的。寥寥几句诗一样的语言,就把对象之“魂”勾勒出来,颇有传统写意画的趣味。大概也只有这种艺术化的语言方能较为完整地表达阅读者的审美感受并使其在由思维到语言的转化过程中尽量不走“神”、不变“味”。读《史稿》犹如欣赏中国画的大写意,所专注传达的是对象之“神”而非对象之“形”,在生气淋漓间尽得各中真味与意趣。需要指出的是,《史稿》走的是“个人著述”的路子,以一人之力写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书在这一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下册在此方面似乎稍逊一筹)。而此后流行的集体合作、分工撰写的组织方式似乎并不适合运用这种更体现个人能力、依赖主体感受的研究路数。但此一方法也非完美无缺。首先,它对研究者从艺术敏感到文字表达的诸多方面的才力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感知力不强,就难以体会和把握作品的艺术魅力;文字功夫欠缺,则无法准确传达已有的审美体验。其次,如果将之作为个人学术路数,研究者还可以有所选择:胜任者自可侍才逞能,任意挥洒而左右逢源;不济者也可知难而推另寻它途。但作为教材的话,恐怕未必那么适合。
在现代学科体系和教学体制中,作为教材,既需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又必须通过示范和学习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和研究的方法。这样一来,学习内容就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传授者也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而且,教学还必须有能够量化的检验标准,需要通过考试来测试学生的掌握情况。且不说学生的知识能力千差万别,并非人人皆有此艺术敏感,即使了解其间门径,在具体运用中也是人异言殊,有时还得靠点“灵光一现”式的锋机与灵感,很难通过“教”与“学”的过程予以传授和掌握,也难于进行正误评判。这都和学校教学的要求有所差异。换言之,它更适合作为一部优秀的专家之作,供研究者借鉴参考,也可让专业以外的读者兴趣盎然,却不适合作为教科书让学生学习模仿。《史稿》的上册于1951年出版,被不少高校用作教材,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批评者所针对的是其政治思想方面的“严重错误”,主要是收录作家作品的标准在政治上把关不严,让一些“落后”以至“反动”的作家也进入文学史;此外对作品的分析也被认为忽视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具有“唯艺术论”的倾向。批评者所依据的显然是一种与时代合拍的、具有方向意义同时也更为激进的历史观念和艺术标准。作者也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省,在1953年出版的下册中不难发现这一思路调整的痕迹,但似乎仍无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其后著述及其作者的命运便都经历了一番曲折坎坷。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言辞尖锐者,参与讨论的人们都是热情而不乏真诚的。但论者似乎较少注意到这部专著所表现的另一层面的、也许是更具有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学批评方式如何通过现代转换而被运用于现代学科体系里的文学研究之中,扬其长而避其短。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曾被归纳为民族化和现代化两条基本道路。那么,中国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是否也需要在将外来的理论、观念、方法民族化的同时,也将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进行现代转换呢?王瑶先生为现代文学学科奠基的同时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可惜的是,此后的时代风云变幻,基于主客观多方面的种种因素,别的研究者没有继续沿着这条初现端倪的路子走下去,《史稿》遂成绝响。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分析式的作品分析方法得到众多文学史的广泛运用。一方面说明“二分法”自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研究者已经将这一模式驾轻就熟以至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分析文学作品,必定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板块。共同的思路、重复的模式、相似的语言不能不说是导致众多现代文学史著似曾相识、面目雷同的重要原因。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出版较之《史稿》晚了四年,自然力求更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一个突出表现是《史略》将作品的思想内容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予以关注,艺术成就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作品“写什么”比“如何写”更加重要。如分析叶圣陶的代表作之一《倪焕之》,首先是思想内含的分析:“首先,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这是第一部。其次,有意地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受了时代的潮流激荡,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其后又用两段的篇幅论证小说主人公“可以说是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8〕;紧接着又是如下的一段分析:“这就说明了当时作者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认识还不够深入,只是看到了革命遭受挫折的暂时现象,而没有看到革命在工农大众中的深厚力量。作者在本书中对革命者王乐山的描写,便可以证明这点。王乐山是比倪焕之更了解革命的意义的,但作者却没有表现出他做了怎样推进革命的工作,读者只能隐约推求他的活动,而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另外,二十二章中的倪焕之,似乎已经加入了一个政治集团,但以后倪焕之的行动都不曾明显地反映出集团的背景,仍是个人活动。而倪焕之参加革命后就写得有些概念平面,没有凸出。这些都是由于作者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革命知道得不大清楚的缘故”。小说的艺术成就则被拆解为三个方面:“就人物形象方面说,它塑造了革命阵营中一些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就结构方面说,可以称得上谨严完整;就语言方面说,字斟句酌,十分精炼”。《倪焕之》被称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确能部分的反映了时代的真实”〔9〕,从而使得《史略》的作品分析带有某种“题材决定论”的意味。#p#分页标题#e#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在《史略》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政治意义、阶级分析作为作品分析的核心。例如书中对鲁迅前期小说的分析,分为思想意义、人物阶级、形式独创三个部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的思想意义“、“《风波》《明天》《故乡》等作品中的主人公的阶级性”、“鲁迅初期作品在形式上的独创性”。不过,书中对于如何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运用政治理论仍旧处在探索和尝试之中,二者的结合较为生硬,有时过多的思想定性和阶级划分反而掩盖了作品自身,使其成为政治理论的材料和论据。如分析郭沫若的《卓文君》,先通过引用卓文君与卓王孙的对白来说明女主人公“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来反对封建伦常的束缚”,“仍未超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水平”;再以卓文君和程郑的对话表现后者“荒淫无耻而又满口孔孟道德文章的封建文人”〔10〕形象,最后总结“《卓文君》所提出的问题,是表现在婚姻问题上的人性解放问题。卓文君的解决办法,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个人主义的奋斗”〔11〕。这一分析模式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以《狂人日记》为例,《初稿》首先论述的是其“标志着鲁迅创作事业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开端”的文学史地位〔12〕,其次是介绍作品“借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来暴露封建社会的‘人吃人’的悲惨事实,来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传统和因袭的罪恶”的内容,并着重指出其“超过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并且开始包含着极其显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的意义〔13〕,最后则是艺术分析:“《狂人日记》只是十三则不记月日的日记,但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表现得十分鲜明、十分完整。这一方面说明了鲁迅的创作正是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严谨、洗炼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同时,《狂人日记》这个标题是采自俄国作家果戈里在一八三四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篇名,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把这种重要影响首先带到中国文学上来的,正是我们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14〕
这一模式的集大成之作,是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唐弢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唐弢本”)。以书中对《女神》的分析为例,先概述了诗集的文学史地位和开创意义;接下来简介其写作背景;其后分析了作为代表性篇章的《凤凰涅搫》和《女神之再生》;随之按照题材分类论述诗集中的四类作品;最后综论诗集的艺术特色。不仅面面俱到,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有时还将多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如《子夜》一节中,在分析吴荪甫时融会了人物形象的定位和塑造手法的分析:举出其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又以“个人利害的筹虑”为中心的事例,一方面证明了作者“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借此阐释了主人公作为精明强悍与软弱并存的“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的性格特征〔15〕。尤其唐弢撰写的鲁迅专章,纵向上历时地再现了作家数十年的创作历程,囊括了其各种文体的全部创作,横向上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时代背景、历史意义等均进行了分析和描述,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也设置了专节(如《阿Q正传》)。原本内容庞杂而头绪繁多,却安排得不蔓不枝,结构匀称而舒缓有致。为文学史该如何写法提供了一个优秀(但不是唯一的)的范例。从《史纲》到“唐弢本”,对作品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一脉相承,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和规范的分析范式,从而在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有绝对地位,成为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写作的既定模式。分析式的方法的突出特点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将文学作品进行逐步的剥茧式的分解,第一层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前者又划分为分为背景、主题、社会意义等,后者则解析为语言、形象、结构手法等,由此层层深入,步步为营,达到对作品的“解构”。如果说前述感悟式分析注重的是整体的话,分析式的思路就是逐步细化,犹如由江河到水滴再经分子而原子、电子的科学观察过程。
面对丰富多彩的作品却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虽有重复呆板之嫌,却也颇有自身的特点和长处:其一,有一套成型的分析思路,也提供了具有可重复性的操作规程,以及一套与之相配套的名词术语,不管什么样的作品,只要按此方法处理,就好比把原材料放进机器,可以得到同样质量、一个模子的产品,学术研究在这里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化的知识生产;其二,由于上述特点,这一方式更适合教育教学的需要:对学生来说,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就能大体不差地对付任何一部作品(当然也有不那么适用的,比如某些现代派的作品),对教师而言,因其方法、思路的整齐划一,也便于对教学成果作量化的检测和考评。由此,它受到文学史撰写者的青睐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都是高校教材,所担负的首先是知识传授和思维训练的任务,就适应建国后“一体化”的现代学术体系尤其是教学体制而言,“分析式”的作品论述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其三,这一模式也适应了常用的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教材编撰组织方式。编写者之间知识结构、学术取向乃至识见高下的差异本属人之常情,这一模式化的方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个体间的种种差异而代之以统一的思路和语言,把彼此间不一致的流露的可能与范围限制到了最小。而其相应的结果便是著述个性的消弭,众多文学史无论篇章布局还是分析论述,都大同小异,行文风格也趋于一致。对研究者个人来说,这种模式也许太过呆板,不免画地为牢,限制了研究的突破和思路的拓展。但天才和大家终归是少数,开一代风气者也要有天时地利之便。更多情况下,多数人只要按着既成范式按部就班兢兢业业,也会有所斩获。这也是推动学术研究稳步前行的动力所在。
分析式与感悟式相比较,前一种方式的广泛运用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更符合学校教学的需要,适应多数学生的水平,可以作为“传授”与“学习”的对象。虽然条分缕析的分析与整体感悟的体验相比各有优劣,也有不同的适用对象,不能说哪一方就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任何一种方法,无论其自身如何科学和有效,一旦成为了无新意不断重复的模式,后果不仅是众多文学史著述的低层次的重复性,还导致研究思路、学术视野的僵化,这才是需要研究者注意和警惕的。自《初稿》之后,文学史个人写作的传统中断近三十年,直到1984年才有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予以再续。关于这一“断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评价也需要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予以观照。毕竟,没有哪一种史著体例称得上完美无缺,也不会有“万金油”式的写作方式、分析路数。除去学术发展的阶段性和个人才力、学识等因素外,时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过多的限制固然可能“屈才”,但百无禁忌(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也会令人无所适从。在这方面,文学史写作者和研究者是应该有更多的历史眼光和开放思维的。#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