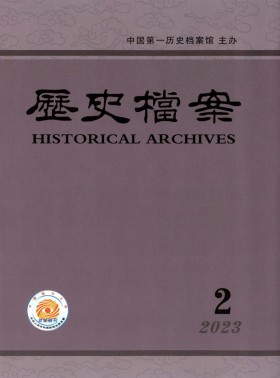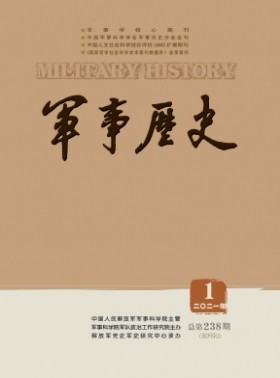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历史文学的虚构传统,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司马迁撰述《史记》之时,文、史、哲仍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文的自觉”的时代还没有来临。然而时代的局限似乎并没有妨碍司马迁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以至于古往今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小说家)不能不视《史记》为取经的圣地。托尔斯泰说:“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①故而研究《史记》的文学性,就应该考察《史记》的虚构问题,由此或许能够接近《史记》艺术的本质特征。实际上,虚构已经成为研究历史叙述者所无法绕行的高山。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历史小说研究领域,虚实问题会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一《史记》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可以任意虚构,因为它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应责无旁贷地对历史演变的轨迹以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加以真实记录,否则既会愧对像齐太史兄弟那样的不惜以生命和鲜血维护历史真实的前代史家,也会招致后人以“曲笔”相评的指责。司马迁的光荣在于,来自于这两方面的遗憾均与他绝缘,从而令人欣羡地赢得了“实录”的桂冠。《汉书•司马迁传》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由此可知刘向、扬雄等汉代学者的史学“实录”观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史家须对史料下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功夫,做到“事核”;另一层是指史家要遵循求真原则,准确记录历史事件,做到“文直”。“文直”与“事核”导引史家进入“不虚美、不隐恶”的境界。以这一“实录”观衡量《史记》,便知汉代学者对司马迁的评价是发自肺腑的。《史记》内容的可信性,已被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所证实,比如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就证明《史记》对商代世系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然而,在赞赏《史记》“实录”品格的同时,也需指出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即《史记》存有不少刻意违逆史实的文字,韩兆琦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将其大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诸如“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庄严地写入传记”,“张扬天道鬼神,故作痴傻,实际是借用这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某种态度与信念”②等。有意思的是,这些失实的笔墨,并没有使《史记》失去“实录”的美名。为什么?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史记》有文献依据。例如伯夷的确是莫须有人物,但其人其事先秦典籍均有记载;二是《史记》失实之处多属枝节问题,如对伯?、子路结局的处理等,其误谬虽早被研究者指出,但由于所涉及的均非《史记》的主要人物,故而给人以白璧微瑕、无关宏旨之感;三是传统观念的庇护。古人囿于科学水平的低下,知识阶层迷信鬼神的也不在少数,对《史记》中的神怪内容,尽管有少数学者指瑕,但没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这一切,使《史记》两千多年来得以一直保有其“实录”的美名。
当然,绝对的“实录”著作,从来就不曾有过。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的“前言”里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③故而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实录”,更何况它还存有上述种种失实之处。值得深思的是,古今研究者所举出的《史记》“非实录”笔墨之例证,如洪迈《夷坚志•自序》所举秦穆公、赵简子、长陵神君、圯下黄石等事,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所举刘媪交龙、武安谢鬼④,以及韩兆琦先生所举伯夷、伯?等⑤,竟往往不属于《史记》文学传记中旋律最为动听的乐章。也就是说,这些笔墨与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虚”的概念贴得最近,其文学色彩理应最为浓郁,理应最能展现《史记》的文学魅力。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这一尴尬同样出现在对《左传》等先秦史著之虚实特征的研究上。
朱熹认为“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事”,钱玄同、顾颉刚等则进而将《左传》归入《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类。⑥支撑他们观点的,便是《左传》中的非信史文字。前人于此多有考论。傅修延将之概括为如下两种情形:其一为“喜语神异”,“左氏记述的神异包括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其二为“记述无凭”,“经不住认真的推敲与追究。”⑦《左传》第一种情形的文字,与《史记》中的神鬼故事一起,均构成后世志怪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自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不过,这些鬼怪故事绝非《左》、《史》最出彩的叙事片断。再看《左传》第二种情形文字,则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古今学者所举之例证竟是如此的贫乏,仅限于少数几则,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亲逃隐前的对话,宣公二年??自杀前的自语等。其中后一事例,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左传》记述该事曰: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纪昀质疑道:“??槐下之词,……谁闻之欤?”(《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李元度亦云:“又谁闻而谁述之耶?”(《天岳山房文钞》卷一《??论》)面对他们的质疑,《左传》作者必当无言以对。的确,??自杀前身边没有旁人,其自语自然无人知晓,况且他自语后随即“触槐而死”,没有将其自语转述他人的些微可能。这段文字纯属虚构,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不过,类似这样的“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⑧而无所依凭的事例,在《左传》中毕竟为例不多,更何况它们同样也不是书中最出彩的文字。以传统虚构的概念衡量《左》、《史》,竟会身陷如下怪圈:本意是想由此拥抱这两部书的文学精华,但没料到抓住的却并不是想象中的瑰宝。问题出在哪儿呢?
二叙写同样一段历史,不同作者的笔下会出现不同面目的作品。比如同样写西汉史,司马迁的《史记》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便给人以天上人间的不同艺术感觉。前贤多指出《前汉演义》艺术逊色的原因之一是太计较史实的真伪⑨。蔡东藩本人在历史小说能否虚构的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也坚定了人们的这种评价。他曾多次愤愤然地指责历史小说的虚构现象,如对唐史小说的批评:“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又如对宋史小说“荒唐者多,确凿者少”的批评:“龙虎争斗,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p#分页标题#e#
种种谬谈,不胜枚举。”(《宋史通俗演义》自序)他认为历史小说任意虚构将“导善不足,导欺有余。”(同上)扫除历史小说中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虚构史实的现象,成了蔡东藩从事历史演义创作的一个目标,他声称:“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唐史通俗演义》自序)蔡东藩能否在创作中捍卫其理论主张呢?翻阅蔡东藩洋洋大观的演义小说系列,能够找到不少令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文字。即以《前汉演义》第二十四回为例,开篇描述项羽杀回彭城,刘邦落荒而逃,被楚兵追赶得无暇小憩。紧张之际,蔡东藩宕开一笔,将一段儿女情长插入文中,写刘邦夜晚逃入一处村落,巧识戚氏父女。戚老汉见“汉王容止,不同凡人”,遂将女儿许配。戚女就是赵王如意的母亲戚夫人。《史记》、《汉书》均未提及戚夫人的身世,更未提及她与刘邦的结缘始末。因而上述描写只能是蔡东藩的虚构。蔡东藩似乎忘记了自己反对虚构的慷慨主张,不但不因此而自愧其理论的自相矛盾,反而以这段文字为得意之笔,在文后评点道:“汉王既入彭城,应该亟请老父,乃耽恋美人宝获,置酒高会,……濉水之败,乃其自取……况孑身避难,一遇戚女,即兴谐欢,父可忘,妻可弃,兄弟家族可不顾,将帅士卒可不顾,而肉欲独不可不偿,汉王亦毋乃不经乎?……本回叙及戚姬,所以原人彘之祸,……详正史之所略,而惩劝之意寓于中,是亦一中垒之遗绪云。”⑩在这里,蔡东藩指出戚姬一节文字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意蕴方面,讥讽刘邦贪恋美色,人品低劣;二是在结构方面,为后文吕后残酷迫害戚夫人母子作铺垫。从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戚夫人的首次出场给人的感觉像是个木偶,与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还相距遥远,但蔡氏设计这段故事的一番苦心倒也值得首肯。
蔡东藩采用难以徵信的野史轶闻和民间传说,其事例是不胜枚举的。11从蔡氏作品大量的夹注与回评中,能够看出他对小说不同于史书的一些特性是颇有体悟的,如:“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化正为奇,较足夺目,能令阅者兴味无穷,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也。”12可以说,历史小说的这种长处,也是蔡东藩花费心血创作演义小说的动力之一。即以《前汉演义》而言,蔡东藩以为自己写作该书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关于前汉史事,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都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然“二书繁博,非旬月所能卒读,且文义精奥,浅见之士,尚不能辩其句读,一卷未终,懵然生厌,遑问其再四寻绎乎?”(《前汉演义•自序》)相反,稗史能够“令人悦目,固较正史为尤易也”。正是意识到这种差别,才促使他“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同上)为了取得“令人悦目”的艺术效果,蔡东藩的确动了不少脑筋,其徵象之一即表现在他所虚构的情节故事本身,能够透示出他运用小说技巧的得心应手。比如他深知文脉的一张一弛,能在叙述紧张残酷的军国大事时,插写一段轶事以松弛读者的精神,像第二十五回对薄姬身世的描写即属此类,蔡氏为之评述道:“中插薄姬一段,更于战云阵雨之中,辟出风流佳话,尤足生色。”13很显然,小说第二十四回涉及戚夫人的虚构笔墨,也有这种妙处。另外,蔡东藩驾驭文字的功夫也值得称道,他的一些想象性的文字也能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像第三十一回写项羽被围垓下,兵败自尽。其内容源自《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对项羽被围垓下而“四面楚歌”的描写堪称《史记》最生动感人的段落之一: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四面楚歌”乃汉军的攻心术,它使项羽痛切地品尝到兵败的痛苦,从而萌生深入骨髓的酸楚而无法成眠。司马迁以“四面楚歌”为铺垫,引出项羽的“悲歌慨”,令人倍感英雄末路的悲痛。对比太史公的绝代佳文,读者必会觉得蔡东藩对“四面楚歌”的描述亦颇为出色:项王才就榻睡下,虞姬坐守榻旁,一寸芳心,好似小鹿儿乱撞。甚觉不宁。耳边又听得凄风飒飒,?栗呜呜,俄而车驰马骤,俄而鬼哭神号,种种声浪,增人烦闷。旋复有一片歌音,递响进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声高,一声低,仿佛九皋鹤鸣四野猿哀。虞姬是个解人,禁不住悲怀戚戚,泪眦荧荧。蔡东藩转换叙事的视角,将四面楚歌的感受者由项羽换成虞姬。女性天生较为敏感,故而从虞姬的角度细腻地叙写楚歌的悲凄,显得十分贴切。蔡东藩自注曰:“从虞姬一边叙入楚歌,尤觉凄切。”14虽属自我褒扬,却也合乎实际。分析至此,笔者感觉又身陷另外一个怪圈:尽管包括《前汉演义》在内的蔡氏演义小说系列,绝对进不了优秀历史小说的行列,但遵循蔡氏虚实理论考察其《前汉演义》中“虚”的文字,却并未找到原以为会很糟糕的笔墨,因而也就难以据此对作品的价值作准确的评价。笔者不能不再次自问:问题出在哪儿呢?
三问题出在传统虚实学说所固有的理论误区上。古代小说理论中的“虚”的概念,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虚构”概念,二者的内涵并不一致。了解古人在小说领域对“虚”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古人在历史小说能否有虚饰成分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从这一分歧点入手,或许就能明白“虚”的意义指向。概括而言,古人的争论分为两大派,一派以陈继儒、胡应鳞、蔡元放、蔡东藩等为代表,认为历史小说要与经史相表里,成为“世宇间一大帐簿”;内容须“事核而详”15,不能虚构史实,若离开史书编造故事,便是“大可笑”16。另一派的倡导者为熊大木、金丰等,其中又以金丰的看法为最典型。金丰在《说岳前传序》中对演义小说的创作发表了一番弥足珍贵的见解。他认为那些可读性强、“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的历史小说,其出奇制胜的妙方是“实者虚之,虚者实之”。17并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虚”呢?金丰认为是“不闻于史册,不著于纪载者。”较之胡应鳞、蔡东藩等注重史实真伪、强调历史小说须处处有来历的观点,金丰的见解无疑要通达得多;而他对“虚”的定性,则代表了古人对“虚”这一概念的一般认识。后来章学诚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杂记》)评价《三国演义》,其对“虚构”之理解,便与金丰的看法别无二致。#p#分页标题#e#
当今学者大都接受了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虚构观,承认“即使以真人真事为主体,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同样离不开虚构”。18但在分析传统历史小说时,却又不自觉地沿用了古人的虚构理论,如仍有人认为:“虚实之分,盖当以史实为界”。19受这种观念影响,人们以为历史小说就是史实加虚构,而虚构与否的标准则完全是看小说内容有无文献材料作依据。表面看来,该理论模式好似清晰、合理,而实际则含糊、偏颇;因为它将原本应是浑然一体的历史小说内容人为地割裂成真实与虚构两个部分,而这种割裂的思想根源便是出于对历史这一概念的简单化理解,忽视了历史文学研究中本应最值得重视的环节:即将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贯通成一个完整世界的作家主体意识。
对历史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卡尔•贝克的认识堪称精辟,他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20据此,史学著作隶属于贝克所谓第二种历史。这种历史之所以是相对的、变化的,就在于它有心灵的介入。史料固然可分为可靠的与诞妄的两种,但即使是所谓可靠的史料,也毕竟是以文字载记的方式存在着,其中不能不打上记录者的心灵印记;而这种史料一旦进入史家的视野,经其选择、加工而成为著作内容的组成部分,该史料就又增添上这位史家的心灵印记。以往将史书(包括历史文学作品)的内容分成真实与虚构两大部分,但即使在有可靠史料依据的所谓“真实”的部分中,也有“虚”的成分。往昔虚实理论的误区,便是只胶着于史料诞妄不实之“虚”,忽视了在人为划分的“真实”与“虚构”的内容中,都回旋着“虚”的影子。显然,影子所反映的就是作者的主体意识。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大宇宙,主体意识可视为心灵世界的小宇宙,它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复合体。其中影响历史文学面貌的最为活跃的元素,当为主体的审美个性及艺术领悟能力。先看审美个性。不了解历史文学创作甘苦的人,会想当然地觉得这一行当较之纯虚构的文学创作要相对容易。殊不知,面对积箱盈箧的史料,缺乏创作素养的人,会因史料的头绪繁杂而不知所措,会身陷素材的大海而辨不清创作的方向。史料始终处于蛰伏的状态,等待着世间活生生的心灵与之碰撞。史料是被动的,作者是主动的,而作者的主动性又是由其审美个性所左右的。这在《史记》当中有典型的表现。
司马迁的审美观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爱奇”的倾向。古人对《史记》的“爱奇”早有发微,如生活年代稍后于司马迁的扬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然而古人对司马迁“爱奇”的认识,多停留于他选择素材的“旁搜异闻”,而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鲁迅对《史记》“爱奇”倾向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21刘振东依据这一论断,进而指出:“说到底,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22可谓抓住了司马迁审美观的核心。
“爱奇”审美观极大地影响着司马迁对传主的选择,如郭解、朱家等游侠义士虽不为当权者所容却得以正面讴歌,项羽虽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死敌却得以深情颂赞,李广虽未被封侯却得以美名流传……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审美光芒的照耀,他们的人生经历及人格魅力才被后人津津乐道。《史记》聚焦于这些人物,显然与司马迁的审美个性紧密相关,这是无需过多论证的。笔者以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审美气质还表现在对史料的加工上,使得那些即便是有可信史料支持的内容,也飘浮荡漾着司马迁本人所特有的审美气息。例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大败于垓下之战,最后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兵;在“自度不得脱”的危难关头,项羽尽显英雄本色,对士卒慷慨陈词,表示要“为诸君溃围”,以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不仅以其实力震慑住敌手,使“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更让他的士卒非但没有丧失反而是增加了对他的崇敬,皆伏曰:“如大王言。”面对司马迁所描绘的这幅气势悲壮、使天地动容的画卷,读者能够通过人物语言的媒介,既感受到司马迁对项羽神勇过人的钦服,也能看出他对项羽至死不悟其失败缘由的惋惜。按照以往史实加虚构之二分法的理论思路,会因《项羽本纪》的记述内容符合垓下大战的基本面貌而将其归入“真实”类,殊不知其中也存有虚饰的成分。该虚饰主要来源于司马迁对反秦英雄项羽的格外欣赏,来源于司马迁“爱奇”的审美个性,否则他完全可以用寥寥数笔交代清楚垓下之战的过程及结果,而不必浓墨渲染项羽的上述豪言及壮举。再看作家主体意识的另外一个组成要素———艺术领悟力。历史小说家有其特有的烦恼,常因受题材的制约而不能像一般小说家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任意设计人物故事。但与此同时,历史题材也能激发出作家的创作潜力,使他们享受到因迎接特殊挑战而带来的旁人所体会不到的喜悦。法国传记作家安•莫洛亚曾以雕塑家的创作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形:“米开郎琪罗与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伟大的雕塑家从他们的暴君与资助者那儿得到大块大块的往往奇形怪状的大理石,不得不奉命利用这些大理石。然而,常常从这奇形怪状中雕出最优美的姿态;石头的抗力迫使艺术家发挥创造力。……某些小说的不幸在于其构思过于自由。”23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素材的先天局限与特殊优势。可以说,历史小说家要想取得成功,关键看他能否驾驭好题材,而这与他的艺术领悟力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小说家的领悟力,指的是作者在与题材的精神碰撞中,能够激发起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将勃勃生气灌注于作品之中,使作品的各个细胞在历史、现实与个体的三维空间中产生共振。在《史记》优秀的传记篇章中,司马迁的艺术领悟力往往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表现为他具有研究者早就指出的塑造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的能力,如明人钟惺所说的“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史记钞》),更在于他具有将题材内涵、个人感受和时代精神完全打成一片、熔铸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比如在范蠡、文种身上,折射出刘邦屠杀功臣的血腥现实;在伍子胥的身上,便能看到司马迁反抗暴政、欣赏忍辱奋斗的思想追求;而在孔子身上,则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追求所产生的无限向往之情。在优秀的历史小说家那里,审美个性、艺术领悟力等主体意识的诸要素有条不紊地作用于小说创作过程,从而赋予作品以一种生命活力的东西,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将其称为“历史情味”24。它的醇厚与否,应是检验历史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主要尺度。《史记》含有司马迁所酿造的含有其深邃博大之主体意识的“历史情味”,因而尽管他没有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但仍能令人惊奇地在历史学的园地里开放出历史文学的花朵。而蔡东藩之所以相形见绌,就在于他的包括《前汉演义》在内的演义小说系列缺乏“历史情味”的芳香。他试图让沉睡的历史复活,让民众因熟悉历史而激发起爱国求存的力量,这一意愿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是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他也试图让其笔下的人物故事生动起来,从上文对《前汉演义》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他是具备小说家的虚构能力的;但可惜的是,他缺乏深厚亮丽的审美个性,更缺乏以时代精神穿透历史素材的能力,从而使他难以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p#分页标题#e#
四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大家庭中,该如何确立《史记》的地位?笔者以为可以《三国演义》的问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创作的“不自觉”阶段,《史记》代表了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后一阶段是“自觉的”创作阶段,独占该阶段之鳌头的,便是《三国演义》。《史记》之前,《左传》已能用典雅简洁的文笔从容不迫地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刻画出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对此唐人刘知几有一段不无溢美的评价,即:“《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诡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史通•杂说上》)不过,《左传》也明显存在两大弱点。其一,它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系于书中某年某月的历史事件既孤单又琐碎,使初读者容易陷入历史事件的大海而找不着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鲜活形象在读者心中的树立。其二,由于它的素材主要来自于各诸侯国不同史家的记述,故而在成书前,它虽经过某几位史家的整体润色,但编撰者的个性色彩却并未因此而凸显出来。
这些缺憾均不见于《史记》。究其缘由,首先,司马迁创造性地发明了纪传体的撰史体例,第一次树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读者从此不但不易被历史事件的大海所淹没,反而能由一斑而窥全貌,透过人物的经历,清楚地?望历史大海的波澜壮阔。其次,司马迁曾阐明其创作《史记》的目的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加之他又是一个情绪热烈的人,“他的情感象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25这就使《史记》既是体例严谨的通史,又是展现司马迁人格魅力的宏大诗篇。司马迁之前,史家的个性从未有过如此淋漓尽致的张扬。文学是人学,须揭示作品人物及作家本人的灵魂,《史记》恰好契合文学的本质规定,故而司马迁得以拥有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显然,司马迁原以撰史为己任,是完全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成为历史文学家的。这种“不自觉”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史料“虚”“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如前所述,《史记》尽管主观色彩很浓,以至于即使是在有史料依据的内容中,也闪烁着“虚”的影子,闪烁着司马迁的审美光辉;但他在下笔前毕竟是非常重视史料的,不仅在原则上反对随意杜撰,甚至还注意甄别材料真伪,如其记述黄帝的事迹时,手头的材料十分丰富,有“百家言黄帝”,可因“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就毅然舍弃,不予采用。对史料可靠与否的重视,决定了司马迁难以任意撇开史料虚构故事,其“一家之言”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历史情味”,只能是在不违背史料规定的前提下,主要通过语言设计、细节描写等环节发送出来。这种情形使得《史记》的第一身份永远是史学著作,而不是历史文学作品。
《史记》在史学领域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尽管不少学者因强调《史记》的文学虚饰成分而将其等同于小说,如郭沫若便说可以把《史记》看成是“一部历史小说集” 26,但绝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仍把《史记》当成绝对正宗的信史。他们很重视汉代学者以“实录”一词称许《史记》的观点,认为《史记》的内容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这似乎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定论。笔者对此亦深表赞同,因为前文已经指出,司马迁尽管有违逆史实的笔墨,但它们基本上属于细枝末节,未对《史记》的“实录”面貌构成威胁。此外,司马迁的确具有难得的求实精神,特别是他记述西汉史时表现出的勇于抨击时弊的精神(最典型的是对当朝君主汉武帝的批判),表现出可贵的史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史记》的实录印象。然而笔者试图提醒人们,《史记》固然是研究秦朝至汉武帝时期的最基本、最权威的史料,然而其权威地位的建立又与它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秦汉史的史书有关。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其中既有私人记述,如陆贾的《楚汉春秋》,更有官家档案,即司马迁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但可惜的是,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都散失了,使后人无从细致研究司马迁是如何处理秦汉史料的。如此一来,《史记》秦汉部分也因其独家记闻的性质而成为后人据以辨别真伪的前提。一般情况下,若违背了《史记》的记述,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其可靠性,就像《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的春秋史,后人述及这段历史而与《左传》有所出入,若无其他过硬依据,便难免招致旁人对他的质疑与匡谬。《史记》成为秦汉史的第一手史料以后,人们实际上已经很难全面论证其内容的真实性,这种情形对《史记》身份之鉴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影响了对《史记》主体意识的深入挖掘,不利于对《史记》文学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史记》的史学地位却能因此而得到巩固,它的史学身份自然同时也得到了强化。
司马迁之后,纪传体史书的编撰成为绵延古代中国数千年的独特文化风景线,产生了蔚为大观的二十几部“正史”。这些“正史”的文学性较之《史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无论是史家的具体写法,还是史学理论家的宏观指导,都表现出对史学面目的有意识强化,以及与文学家族的主动划清界限。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族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以《三国演义》的成书为标志所出现的历史演义体裁,却毅然不去攀附地位显赫的“正史”,而“自甘堕落”地加入“低贱”小说的队伍之中。《三国演义》是一部有着自觉创作意识的历史文学巨著。尽管他的作者们并没有喊出明确的口号,但作品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其已完全脱离“正史”的阵营。如果说《史记》在虚实方面表现出文学创作的不自觉的话,那么《三国演义》则在这方面表现出彻底的自觉。
即以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为例。《三国演义》以诸葛亮《隆中对》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等数句为依托,演绎出洋洋洒洒的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作者有意不让诸葛亮本人出场,借助烘云托月的方式,间接地展现诸葛亮超凡脱俗的形象。毛宗岗深得个中三昧,评点道:“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鳞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雅;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27的确,诸葛亮虽然还未正式在书中与读者见面,但通过第三十七回的铺垫,读者已对他的神采风姿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三国演义》的作者们极尽曲折之能事地虚构出刘备次次扑空过程中与诸葛亮亲朋好友的言语交往,令人不能不承认其文学虚构能力之高妙。若联系《史记》作进一步的追问,则《三国演义》的虚构与《史记》的虚构有明显的不同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虚构的成分有繁简的不同。《史记》在描摹人物的对话、行动方面,虽然较之《左传》、《国语》等先秦史册要细腻深入得多,但它呈现出的描写方式毕竟是如董乃斌先生所概括的“史事纪要式”28的,其细致程度不如“叙述宛转,文辞华艳”29的唐传奇,更不如“文章之最妙者”30的《三国演义》。其次,就对史料的态度而言,在司马迁那里,追求真实是第一要义,而《三国演义》并不刻意追求历史真实,它只求大体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人物故事的鲜活生动为《三国演义》所孜孜追求,因此只要有利于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安排,它就敢于大胆地撇开文献史料。《史记》也出现过有意撇开史实的现象,但它毕竟是偶尔的,少量的,而《三国演义》则是经常性的,大规模的。量的积累引起质的变化,尽管《三国演义》大量取材于《三国志》,但它与《三国志》却分属不同的家族,一个姓“文”,而另一个姓“史”。《三国演义》的“文学”身份是自觉追求的结果。不仅《三国演义》,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主动与“正史”分了家。它们自然不敢与地位崇高的“正史”争锋抗衡,顶多把自己比作“正史”的羽翼罢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愿把自己混同于“正史”,而是从“正史”的“文字深邃”、“艰于记忆”31等短处中,找到了各自生存的价值所在。当然,仅仅将人物故事写得比“正史”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还不足以跻身一流小说之列,最关键的,还要看作品中“历史情味”的质量。受“滚雪球”式成书过程的影响,《三国演义》蕴含的“历史情味”是多元的,混合着民间艺人及最后写定者罗贯中的审美气息。这种混合,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添了《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传统演义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p#分页标题#e#
学术界公认其他演义小说均未能超越《三国演义》的成就。何以至此?笔者以为原因之一来自于传统虚实理论的误导。如前所述,尽管在虚实问题上大致出现了两大派,但反对虚构的一派无疑占了上风,以致当有人以“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批评清末吴沃尧的《痛史》时,他欣然表示“今而后尤当服膺斯言矣”32。这种观念无疑限制了历史小说家的才思,使他们往往为史料所左右,只想把干巴巴的史料转换成通俗生动的故事,而忽视了对“历史情味”的酿造,蔡东藩的历史小说系列,显然为这一结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看来,只有了解了古人对虚实问题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剖析一般传统演义小说的病症;同时,也只有打破传统虚实理论的局限,才能真正捕捉到《史记》等优秀历史文学作品的精华。《史记》与《三国演义》分别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创作“非自觉”阶段与“自觉”阶段的两大高峰。正如《史记》的诞生是个奇迹一样,《三国演义》的问世也是一个奇迹。它历经民间艺人的打磨与罗贯中的锻造,成书时间不可谓不漫长,但却没有遭到传统虚实理论不良倾向的侵蚀。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探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理论还没有出现,当然也就无从影响它的面貌。这既是《三国演义》的大幸,也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