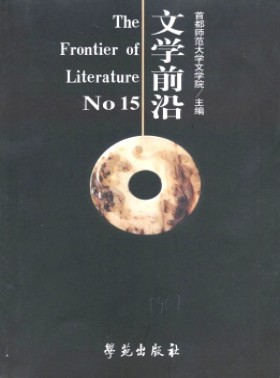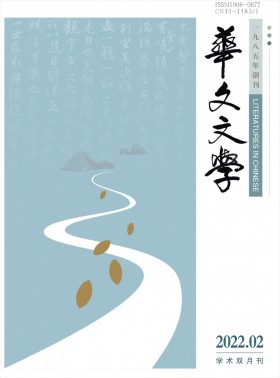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朗读的声音造型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陈朝霞 单位: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可听可感:儿童文学诵读的声音造型艺术品质
儿童文学诵读是诵读主体对文字和声音的双重感知,是通过声音强化文字语言的独特感情,以营造童心永恒的艺术意境。声音负载着文字思想与情感的内在活力,诵读主体依托思想与情感的运动状态,由语气把它们贯穿起来,形成动态的声音走势,呈现出的声音的规范性与适应性、音色的可变性与多样化、语言的动作性与音乐性以及形象塑造的角色感与个性化,无不造就了可听可感的审美创造活动,打开了通往有声语言造型艺术的审美空间,也提升了儿童文学诵读的声音造型艺术品质。
(一)声音的规范性与适应性诵读声音造型的基础在于规范,在保证字音清晰的前提下,要扩大与美化声音,具体到吐字用气发声层面,呈现的是清晰、松弛、通畅、圆润的自然状态。为满足传情达意的再创作,诵读主体在音声创造中,要让气和声形成互动相随的关系,以情带声,以声传情,气随情变,声随情走,达到情声和谐。[1](P99)儿童文学诵读用声尤其要落在自然的中声区,以实声为主,虚实结合,朴素的口语声流托出声音造型的底色,避免华丽的朗诵腔。诵读有声语言的音声性特质,决定了诵读主体的声音形式对文学作品中变化的情感要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应服从作品情感基调,并唤起外在情感的冲击力,或委婉细腻,或高亢激昂,都需要有相应的情态语感来表现,否则如果仅限于诵读主体本色流露的范围内,语言表现将缺乏活力与张力。其次,声音要适应不同作品风格的需求,如叙事作品的娓娓道来,对于低幼文学故事更要传达出平和温馨的色调。此外,声音还要适应不同表达技艺的特点,如表演式的诵读相对于亲子诵读,声音变化幅度较大,空间感与达远性较强。
(二)音色的可变性与多样性音色是声音造型极具表现力的元素,精当地处理语音链上的长短、高低、轻重、疾徐、抑扬、顿挫、明暗、刚柔等对立因素,取得刚柔并济、纵收自如的富含伸缩性与可变性的声音弹性,是诵读主体在声音技术层面的重要任务。声音的弹性变化是以多种对比项目的复合形式出现的,其喷弹力度、抑扬幅度、快慢速度、疏密张度、明暗限度等共同组合成一种多维度的动态体系[2](P260),语言表现力的外质———音色就必定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从儿童文学抑或儿童文学诵读的受众来看,儿童受众群体对声音色彩的感知更为敏感,诵读主体需要通过音色的多姿多彩来获得情感色彩的万紫千红,获得声音造型创造的动力。冰波的童话《小青虫的梦》讲述了一条小青虫蜕变成美丽的蝴蝶的故事,从最初偷偷躲在树上听歌到在音乐会上翩翩起舞,文字优美而富有情致,语言的节奏随情感而绵延起伏,诵读的音色是柔和的。文中两处拟声词“吉铃铃……”,犹如给梦幻般的画面增加了声响效果,第一次从近处入耳,声音清脆,有穿透力;第二次是小青虫躲在远处听到的,可以采用弱读的方式,语节拉开,为作品预留想象的空间而不显得单一寡味。雷抒雁的《燕子》首尾以问答的句式形成呼应,“如果是一只鸟,你愿意是喜鹊还是杜鹃”,“我愿意是一只燕子,我向往广阔而自由的空间”,音色明朗坚定,并且注重浓淡相间的运用,语势推进至“将和命运死死地搏斗在云端”唱出最强音。
(三)语言的动作性与音乐性美国心理学家加登纳认为,七岁儿童具有对审美特征的明显感受性,而且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整体的节奏感与平衡感。[2](P(155)儿童文学学者汤锐对早期阅读的研究指出,幼儿在听成人朗读作品或自己阅读时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是由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所引起的,例如,铿锵动听的词语构成的韵律、节奏,循环往复的作品结构,象征、比喻、拟人、夸张的修辞表现手法等,都带给幼儿极大的快乐。[3](P(181)儿童文学诵读语言外在形态的动作性与音乐性体现了儿童的审美心理需求。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精美词语和动态的描述,展现了富有色彩和音响的流动的画面,通过声音再现文字画面的过程中,听觉形象很好地转化为视觉形象,更富有立体感、节奏感。要使语言有动作性,必须重视动词的运用,以产生与表达内容相适应的语言动势,如表现走、跑、跳等不同动作状态中的说话感觉。蔺力的《会打喷嚏的帽子》里的大耗子偷帽子的细节充满喜剧色彩,“一步一抬头,防着帽子里的那个呼噜突然钻出来咬他。也真巧,他刚走到老爷爷床跟前的时候,呼噜不响了。这下,大耗子可得意啦,原来呼噜怕我呀!”诵读主体要尽力表现大耗子从害怕心理下的轻手轻脚到得意时的肢体放松状态,夸张灵动的语调不仅要营造立体的环境,还要展现动感形象。语言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节奏上,由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回环往复造成和谐均匀的音响效果。诵读主体的声音处于积极状态并生发一种内心期待,引领着身体节奏、心理节奏、文字节奏与声音节奏合拍,以唤起听者的艺术关注和审美愉悦。儿童文学诵读的节奏实质是有形多变的,要避免落入固定腔调或貌似抑扬起伏,却完全没有生命的语言外壳的表达误区。金波的儿童诗《春的消息》旋律清新明快,表达了对大自然生命活力的无限热爱,诵读的声流在蓬勃着大自然生命律动的诗情画意间流转,语气中流淌出童真的质朴与美好,展示暖融融的、活泼的声音意象,诵读时应避免一味地“演”节奏以及让声音在顿读的形态中运行。
(四)形象塑造的角色感与个性化儿童文学叙事类作品中的形象刻画,需要以真实情感为依据,从语言内在实质出发去寻找外在的体现方式。多数作品往往人物众多,外形特征和性格特点区分度明显,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元素符合儿童的欣赏期待,诵读也应该以儿童的喜好为依据,突出角色感与个性色彩,做到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的统一,以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首先,应抓住形象核心,并加以放大,来寻找形象的声音质感,如《两只笨狗熊》里的大黑小黑的浑浊感和狐狸大婶的尖细感,《猜猜我有多爱你》里的小兔子的稚嫩感和大兔子的慈爱感,《渔夫的故事》里的魔鬼的沙哑感,等等。其次,运用咬字和发声等各种语言技巧参加造型,以满足不同的形象要求,如青蛙的声音可用跳字及咧嘴发出的扁形字音表现其活泼,猪的声音以撅嘴发出的后吞感音质显示其笨拙,小孩的声音发声位置靠前,老人的声音发声位置靠后,等等。儿童文学的浅近性并非促使我们一味模仿角色可能有的语调和稚态,而是唤起对心理状态和生活世界的体验和认识,“在角色的身份、性格和行为中进行注视、思考、自语等艺术创造”[4](P75),达到形神兼备。以保加利亚的笛米特•伊求的故事《婴儿》为例。作品细致刻画了儿童的好奇心理,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童心。开掘由此生发的童趣,诵读的基调也就不可避免地映射出幽默风趣的风格。文中这对低龄的小姐弟,人物对话充满稚气,他们的好奇的眼睛,他们的观察思索,他们的担心忧虑,以及严肃认真的谈话和洋溢于浑身上下的那种神秘感,需要诵读主体调动声音技巧完成听觉与视觉形象的创造。语言造型应突出稚嫩感,可适当以顿读的方式来丰富人物的语态,连续的对白应学会在瞬间全方位快速转换,以加大姐弟俩与另一人物桐尼叔叔之间的角色造型反差。冰子的故事《没有牙齿的大老虎》中,林中之王居然被狐狸骗了,故事的趣味性来自老虎的一次次上当受骗。对狐狸善用计谋的刻画和勾勒,使得这个“反派”人物格外灵活生动和富有魅力,所以,狐狸才是有声语言关注的焦点。狐狸每次对话都是话里藏话,要读出其中的“假”来。可以在狐狸的音色中添加些甩腔,放大其“反派”特征。老虎在故事中是被嘲弄的对象,音色上可以含混些,以与狐狸的精明诡诈形成对比。#p#分页标题#e#
二、吟唱童心:不同儿童文学样式诵读的声音造型艺术创造
存在于相对独立于成人世界的儿童生命空间里的儿童文学,以儿童为视角,以儿童为本位,洋溢着纯真、美好、质朴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特性。儿童文学诵读追求情理之美、韵律之美,诵读声音造型艺术是富有灵性的,是童心的吟唱。
(一)抒情性儿童文学作品诵读———再现情思情致,朴实而灵动抒情性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诗与儿童散文为主。儿童对诗歌散文的节奏、韵律以及广阔的意境空间有着天生的敏感,他们能从诸多元素中得到发自内心的愉悦。通过诵读形式参与儿童文学阅读活动,有利于挖掘儿童天然的语言能力,对儿童心灵的成长大有裨益。因而,抒情性儿童文学作品诵读的外在声音形式重在朴实而灵动的画面感与音响效果的创造,随着倾力又自然的传达,凸显了情感张力。儿童诗具有丰富感性的儿童心灵世界,充满独特想象与真挚感情,作为诵读主体声音造型最重要的要素即对诗情、诗意、诗味的传达,是不事雕琢的,自然明快的音势、声流更能契合儿童的率真天性。以傅天琳的《我是男子汉》为例,“如果今天夜里突然起风/不用害怕,妈妈/我是家里的男子汉……”多次反复的“我是男子汉”强化了母子之间的美好情感。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他要用自己的陀螺鞭子把吓人的风赶走,他想从夜空中摘来一颗星星为妈妈照明。如此令所有母亲感到欣慰的男子汉宣言渲染出浓浓的儿童情趣,声音元素构成的抒情语境细腻丰富又连贯畅达,透着淳朴的韵味。邱易东的《妈妈,不要送伞来》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呼唤,欢快、轻松、跳跃的节奏语态构成了声音造型的主旋律。儿童散文是儿童性灵的体现,把真纯融入字里行间,从而流淌出童稚的情感和意趣。这种重抒情重想象很有亲和力的文学样式,诵读时,通过形象感受的运用,能让诵读主体很快获得内心视像,把弥散在字里行间,发自心灵和肺腑的感动和跳跃的文字,幻化成有声的情景画面,托出本真的精神世界,以品味蓬勃的生命感觉,声音的通畅性和疏密度绘就了平实真切的交流感和写意性。以陈木城的《春天的小雨嘀嘀嘀》为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叮叮咚咚’打在篷顶上的波浪板上。‘滴滴答答’打在树枝里的叶子上。‘叮叮当当’打在铁皮的屋顶上。”诗化的语言表现扑面而来的春天意境,景语情语浑然一体。诵读时,要处理好拟声词在质感上的差异,它们的音色发展是由低到高,由沉闷的重锤敲鼓声到清脆的鼓点声,观雨者也被大自然充满灵性的声响打动,情绪随之逐层高涨,语言的节奏也应随之丰满。随着场景的转换,视角不同了,或仰视或俯视的感觉要透过声音散发出来,吐字伴随一定的气音,将气息舒展地呼出,使曼妙柔美的意境在娓娓道来的语气中得以升华,以增添音韵回旋感和整体谐和美。
(二)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诵读———绘形传神,如幻如真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同属于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都着力于营造故事的内核。故事是儿童发自内心的原始需要,而诵读则将文本故事转化成了感性的视听故事,有利于儿童主动参与到文学活动中。因而,诵读主体与受众共同参与审美创造,还原鲜明的形象,再现奇特的情节,激活了文字内涵的感性色彩,呈现出动态的立体画面。童话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以愉悦陶冶性情为要旨,是富于感性化表现的最强的文体。对于诵读主体而言,鲜活有力的感性化作审美动力进入声音外化阶段,首要的任务是焕发童心,酝酿声音气质的底色,使之与作品内涵气质相符。童话形象在从内到外的勾勒中又激发了童趣,绘声绘色的语调编织着如幻如真的动感画面,浓浓的艺术情趣在活灵活现的声音与听者的回味中蔓延。当代童话如吕丽娜的《我的感觉和你一样》、汤素兰的《好长好长的名字》,富含诗意的人文情怀,传达出悠远开阔的经典艺术色彩,需要诵读时用充满笑意的温暖的声音底色来构筑。而对于那些夸张色彩浓烈的童话作品,语言的夸饰性要凸显,语势的起伏变化幅度大,语调的上扬和下行可以超越常态。以王一梅的《书本里的蚂蚁》为例,一只偶然被夹进书本里的蚂蚁,成了一个会走路的字,这是一篇画面感明晰的童话,因而,要注意视觉感受的层次,用富于质感的语言去呼应,在故事情节逐层铺展的进程中设计声音的强弱高低以及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的节奏感,同时,由于作品诗意化的文字效果,适宜采用清丽的叙述基调营造美好的艺术效果。寓言以说明道理为旨归,往往是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的深入揭示和批判,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嘲笑,更是一种精神省思。寓言的寓意往往是开放性的,诵读主体应抓住本质,鲜明又含蓄地表现形象,声音形式的音势幅度要大,用声外形对比强烈。
对于不同性格的人物,音色造型应追求神似,如只在语言外形上夸张,而忽略作品形象的内化,将使表达变得哗众取宠。如对于《井上历险记》中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和顽固派形象代表的青蛙,《谦虚过度》中由于过度谦虚反而弄巧成拙的狐狸艾克,诵读时,可以用粗声粗气以及快慢交替的语调表现青蛙的愤世嫉俗,用粘字、甩腔以及华丽女高音似的语调表现狐狸的不切实际的浮夸。以孙建江的《鲳鱼拍照》为例。作品中的鲳鱼这个生动具体同时又充满象征意味的寓言形象,让人反思那些总把自己的无知当有知的人性深处的痼疾,带着滑稽的喜剧色彩。诵读的核心是对形象定位和形象造型,应着力表现鲳鱼的无知、愚蠢而又自以为是,要善于安排好笑声的位置———“请问,我怎么只有一只眼睛”,以达到让人发笑后引发思考,这样就不是单纯的滑稽色彩而具有点醒的幽默效果。儿童故事直接取材于现实儿童生活,强调情节的动态起伏,以满足儿童奇趣、险趣、情趣的永不厌足的心理期待。诵读时应有意识地控制叙事的详略疏密,把阅读过程的趣感通过张弛有致的声音再现出来。如苏联的奥谢耶娃的《好事情》在想象和现实的反差中对“做好事”进行了生动的诠释,诵读时,需要尝试必要的情感体验,从语感上把小尤拉“想”的和“做”的区别开。“想”的内容带有大量假设成分,音色上可以虚幻一些,语势的起伏度应适当拉开距离;“做”的内容存在于现实之中,应以实声为主,并凭借音调和语速的适度改变表现小尤拉极不耐烦的神情,从小尤拉想象怎样做好事直接跳转至生活中不愿意做好事,以此构成戏剧性反差。儿童故事诵读的声音基调要统一在文本思想内涵的主旋律中。如桂文亚的《这样做,是对的》着眼童年成长中生成的美好善良的人性,散发出质朴无华的温暖的情怀。#p#分页标题#e#
故事的主体由“我”的内心感受、思绪与独白构成,诵读的基调应平和,以中声区为主,声音自然平稳亲切,采用独白的语气,节奏舒缓,语调幅度较小,而人物对话与叙述语言之间形成明显落差,声音的错落感尽现。在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故事之《会叫的皮鞋》中,“以后你跟我玩,小老鼠就跟小鸟玩”,轻轻一语,故事就笼罩在浓浓的情感韵味中,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用轻快跳跃的语气表现儿子活泼可爱的性格特征,用平稳却又不失俏皮的语气表现爸爸善良快乐的性格特征。儿童文学诵读这一有声语言艺术,拥有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创造性,其可听可感的声音造型艺术品质,加深了儿童受众对儿童文学文本意蕴的感知,打开了通往有声语言造型艺术的审美空间。诵读主体对声音造型的创造,凸显了儿童本位及儿童气质,可以达到内感外动的诵读艺术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