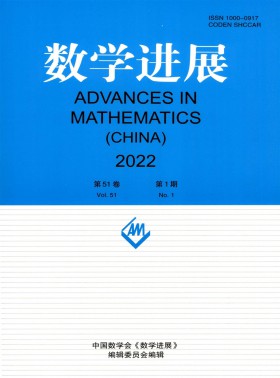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数学文化与宇宙理念探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刘鹏飞 徐乃楠 周巧姝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里维奥(MarioLivio,1945-)撰写的科普名著《IsGodaMathematician?》中提出一个疑问,并指出这个疑问曾令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贤们苦苦思索了几个世纪: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些正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的特征[1]。数学似乎不仅是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最复杂的人类活动。
1数学何以有效
古希腊时期,数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信仰而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数学逐渐促使人们从盲目的信仰转向理性。随着数学理性的发展和希腊学术的复兴,一批具有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提出宇宙的设计主要是数学设计,上帝成了数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成为最神圣的事业。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理论、科学公式的定量化、演绎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方式为人们所把握,人们终于抛弃了世俗的上帝,开始走向无神论和泛神论。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宇宙统一理论的理想,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成为支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已经深深融入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18世纪的西方数学家,对于在宇宙体系构建上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古希腊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通过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上帝看成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探求看成宗教追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坚信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劲千辛万苦才能理解[2]。一直到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的斯宾诺莎式的上帝概念[3],自然神论———泛神论才成为爱因斯坦以及之后很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信仰和感情的基础。非欧几何诞生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数学的真理地位丧失了信心,对非欧几何提出了众多质疑,它能描述我们居住的物质世界吗?但当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回答时,数学这种神奇的有效性又使众多数学家陷入思考,有些人开始认为数学是原本存在的,我们只是进行不断的发现而已,有些人坚持认为数学只是我们的一种创造,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然而数学何以这么有效呢?爱因斯坦也惊叹:“数学,这个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的人类思维产物,怎么会如此完美地与物理现实中的物质相一致”[1]?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4]。
非欧几何在相对论理论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数学的观念逐渐地发生转变。对非欧几何的确认,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从古希腊以来的、以数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观”的终结。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绝对位置,但它与物理世界很相契。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法。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数学都是有力的知识工具,即便是被赋予神学意义的时候仍认为上帝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们在近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中见到的,数学是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髓。尽管数学结构本身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1830年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的过程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2]”黑洞理论是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形之一,在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情形下,作为数学的模型被发展到非常详尽的地步。的确,这经常是反对黑洞的主要论据: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其依据只是基于令人怀疑的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的对象呢[5]?尽管数学因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地位,以及哥德尔定理导致的数学家们对数学基础论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数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如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的:“也许人类的数学仅仅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也许自然本身更为复杂或者并没有什么固有设计。但是,数学仍不失为一种探索,是掌握自然的一种方法。在那些数学行之有效的领域,它是我们的全部资本;如果它不是现实本身,它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与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数学也是一样,尽管它也仅是一种理想。也许细想这一理想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我们该选择什么方向才能获取真理”[4]。
爱因斯坦相信人类的数学只有一少部分由实在主导。他在《相对论的意义》(1945年)中说道:“观念的世界看来不能用逻辑的方法从经验中推导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就没有科学。尽管如此,这个观念的世界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本性,正如衣服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身体的形状一样”[2]。对于数学为什么有效,那些较早世纪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在现代被抛弃了。不过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提出的“宇宙似乎是由一位理论数学家设计的”这一问题,他认为“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科学现在给大自然所描绘的图像(看来只有这些图像能够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是数学化的图像……大自然似乎精通纯数学的规则……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有意识的数学心智根据同样的规律来运作。”著名数学家齐民友先生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是科学,它首先关心的当然还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数学的探索意义究竟何在?就在于它对认识宇宙的本性上有重大贡献。我们不赞成狭隘的近视的看法,认为一切数学研究都必须有某种具体的目的,或者用现行的说法叫做“有应用前景”。其实所谓的“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眼前”固然是“前”,“前瞻若千年”也是前,区别在于人类社会在文化和物质上的发展程度。发展向上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文化、科学和物质生产水平,同样也就会更认真地考虑各门科学的前景。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数学的研究不能在“认识宇宙”上开花结果,数学研究还有多少价值呢!“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否则数学也就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内省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用“改造自然”的说法,因为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简单地按人类的需要来“改造”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懂得了人必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找到正确的相处关系。我们一再强调过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端抽象的、甚至有时被误解为“毫无意义”、“脱离实际”……的数学研究,可以根本改变人对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人们很难回避一个结论:数学是人类全部技术的最重要的基础[6]。#p#分页标题#e#
2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按照数学模式来解释世界、构造天文理论,从其初始的一种宗教式崇拜,后来演化成上帝用数学设计世界。蕴含于其中的数学理性,最终把西方天文学导入了现代科学的数学理论框架之中。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空有辛勤准确的观测记载,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明确可遵循的理论体系。例如,哈雷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有30多次之多的记载,但中国的天文学家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构造它的运行轨道,结果这个发现被18世纪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获取。因为哈雷发现每隔76年出现一次的记载,恰是彗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的周期。这个史实足以表明,在经验和知识充分积累之后,如果没有深层的理性构造就必然导致科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7]。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对宇宙问题有过思考,《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即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庄子•天运》中记载:“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天文学非常依赖,很早就注意观测和记录各种天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了日食、月食的记载。有关流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异常天象,中国古代也都有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的《甘石星经》已有115颗恒星的坐标位置。可以说在天文学史上,中国人的经验知识以及观测记载堪为世界第一。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先生在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其它民族的天文学成果相比较时认为:“中国人在阿拉伯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在许多场合(例如对彗星,特别是对哈雷彗星重复出现的记载)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了良好的结果”[8]。
中国很早就创立了干支记法和二十八宿的独特测天方法。战国时代已有五星记载(金木水火土),在汉代时测得更为精密。中国古人把整个天空分成四宫,就像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而每一部分都有一种象征性的古代动物代表,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照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被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而这种五行观念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之中。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即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又有很大差别。中国古代信守“天人合一”的理念,历代帝王治国安民,无不求端于天,传说自三皇五帝开始就有历法。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所测得五星的度数以及会合周期的精确度已经相当高。根据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统计,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历法共有104部之多[9],经历了准备时期、古历时期、中法时期、中西合法时期和公历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准备时期以《夏小正》历法为主,古历时期从春秋到汉武帝期间主要是《颛顼历》,中法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的《太初历》和直到明朝的《大经历》,中西合法时期是以明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历书》和清朝《时宪历》、《癸卯元历》为代表,公历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开始实施的公历,也即格里高里历[10]。
3基于中西文化史的思考
中国最初在天文理论构思方面(盖天说、浑天说)也不逊于西方天文鼻祖托勒密。而且从实际上说,托托勒密构造的“地心说”,并不具有比“浑天说”更多的经验支持。有人曾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同时代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天文理论作过比较,发现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依据张衡的假说所绘制的天文图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图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1]。遗憾的是张衡并没有明确提出像托勒密那样的地心说理论模型。李约瑟曾评价说:“把中国的星表和伊巴谷、托勒密的星表对照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后者不仅年代较晚,所载的恒星也少三分之一,……周、汉之间中国人在方位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应在科学史上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世界通用的天球坐标系基本上是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这一点似乎也值得强调”[8]。从中西方数学文化史比较的意义上看,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理论模式是以数学崇拜为基点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构思却是建立在《周易》衍生出来的阴阳五行解释系统之上的。作为一种理论的构思,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中国与古希腊天文理论在数学理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早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写入《崇祯历书》,但后来还是被否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唯有地静说才是公认的观点。
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确定日月星辰的位置,观察记载它们的运动,寻找季节变化的规律都必须以数学的计算为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这种应用的层次上当然也是依凭数学的,尤其是在历法计算方面,唐代的僧一行运用的插值方法与西方相比非常高超。但是,当涉及整个天文学理论模式构造,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实际都是把观测经验和计算数据容纳在一个按《周易》思维方式构造出的模式之中。有的学者评述时说:“查阴阳五行与天文历法,有的部分是巧合,有的部分是勉强牵强”[12]。其实巧合也好牵强也好,这些理论构造在其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致命的危机潜伏在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面。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显然,刘徽是在《周易》解释宇宙万物的指导下来建立“九九之术”的。显然,作为一种理性,中国古代数学在它构成第一本数学著作时,就成为《易经》的“婢女”,而不是像《易经》那样获得在中国文化中解释宇宙万物的地位。齐民友先生曾指出数学理性精神、数学探索精神“其实只是西方文化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作为永恒的主题这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把进行这种理性的探索看成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只是对西方人而言的。中国人生活在天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和谐中,精神生活早已得到满足,哪说得上要什么思想解放呢”[6]?中国以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为表象形式,形成中国整体相关、整体互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以农耕生存、家庭和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中[13],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特定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中不像西方那样以数学理性为主导。#p#分页标题#e#
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建立在《周易》和阴阳五行的理性结构之上,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它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天文学“缺少理论是缺少演绎几何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8]。其实还应进一步说明,中国天文学缺少的不是作为操作手段的演绎几何学,而是缺少作为深层理性结构的数学理性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在发现盖天说的解释困难之后,浑天说或者宣夜说也没有像欧洲天文理论那样形成逐步淘汰的竞争态势。这其中的症结在于,这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周易》阴阳五行这种直观表象的同一模式上。因为《周易》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不具备更新或竞争的内在动力,它们也就无法竞争高下了。东汉末年,蔡邕在《朔方上书》中早就指出盖天说的计算错误,认为“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14]。但实际上,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并存,而且各自都在发挥自己的理性解释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人的信念中,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知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一种信仰情怀,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了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既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思(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15]。
数学理性作为一种民族理性中的重要因素,它会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形成了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也影响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理性从古希腊的数学神秘主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数学理性的吸纳,直到牛顿、爱因斯坦确立数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数学理性伴随着圣经的浸染一直是西方文化理性的主导。而中国传统数学虽与《周易》共同起源于原始的数字神秘主义,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陷入了实用主义泥潭,而《周易》则逐渐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主导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圣经》血统,东方文化无论再怎么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易经》血缘”[16]。如果在以往中西文化分离状态时考虑上述问题,这些数学理性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并不会被人们所关注。但在今天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进程中,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数学理性开展文化史意义上的对比分析,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从而推动中西文化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