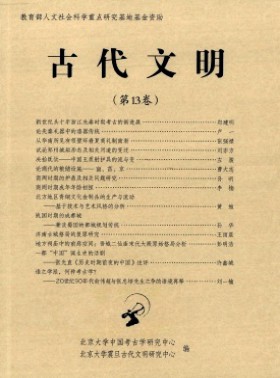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文学语言研究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
在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进行的研究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性的基础研究,即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一个整体性描绘与把握。无须讳言,这一工作颇具难度,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作极富宏观的梳理。我们选择的具体做法是,基于一个特定的视域———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语言学基础和雅俗格局视角的考察,期望能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勾勒。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处于一种“杂文学观”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般应用文与“纯文学”的分野。可比较今人的“文学”概念,一般认为“文学”是“文学艺术”,似乎表明它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而不是一种文章学问。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非独立性,反而使得它在语言文字上带来审美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描绘,实质上就等同于对中国古代书面体系的描绘。因为在古人眼里,能够称为“文学”的语言必然是以典雅的文言为基础的,并且它的功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往往审美功能与其他功能混淆不分。如周祖谟的看法:“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著作服务。”[1]先来看一种西方语言文字观,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2]
进而,索绪尔对“文学语言”有一个语言学视野的分析:“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3]索绪尔注意到“文学语言”的产生使得文字重要性得到增强,但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下,索绪尔对文字的意义并不认可。这种基于西方语言文字情况归纳出的情形,当然会与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可提及一个辨析:“目前‘汉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基点,是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具体说来,就是把‘汉字’从‘汉语’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来,仅仅将‘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一种无关乎汉语本质的游离性与工具性的存在。传统的‘小学’虽然在具体研究中区别语言和文字,但因为‘小学’并没有一个西方式的以语音为中心的整体性语言概念,所以被分而治之的语言和文字在学者的观念中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当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的‘语言’概念输入以后,中国传统对语言整体的模糊想象被改造为德里达所谓以‘语音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清晰的语言概念,在这个清晰的语言概念中,原来不可分割的语言和文字不得不拆开来,其中语言(汉语)是根本的、本质的,文字(汉字)则是非根本的、非本质的。”[4]因此,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不能以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影响的语言文字观念,来机械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现实情形。
二
从语言学的层面,具体说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分野,即在语言与文字的分野之中,我们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主要走的是一条脱离语言,极端重视文字的道路。在中国古人眼里,文字甚至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刘安在《淮南子》中道出汉字创造时的奇特情景———“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的“文言”,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古代以文字为基本思维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脱离语言作用的书面语体系。这必然会与西方文化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形成的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截然不同。文字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文字的种种特点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种种特点。有论者认为:“从最基本的层面进行考察,中国文学思维的个性主要是由于思维材料———文字的特异决定的。这种特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汉文字有一个以表形字为主体的历史阶段,即使过渡到了以形声字为主体,也非纯粹的表音文字,这就使得中西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的表音字使文字与语言具有同一性,而汉文字则可脱离语言成为独立的表达系统;第二,汉文字是一种单音节文字,即一个文字只发一个音,这就造成‘字’与‘词’的分别,而西方为多音节文字,‘字’与‘词’往往合而为一;第三,汉文字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发展阶段性,这种阶段性不仅表现在自行的构造的演化上,也反映在‘单字’与‘组合字’数量比例的变化以及‘文’与‘语’契合关系的变化上,且当下仍处于变化之中。”[5]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口语与文字的分离,造成一个重大的后果,即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言文不一致”的突出现象。因为,“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此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6],“由于单个文字以及以单个文字为表达单位的书面语无法和口语一一对应,以文字为载体的‘文言’文学与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就此两分。”[7]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书面语系统得以建立。康有为对此有一个集中的描绘:“自秦、汉后,言语废而文章盛,体制纷纭,字句钩棘。盖作始也,以代言;其承变也,以驾异。其始之达书名也,恐人之不徧解;其后之务文词也,恐人之易解。是故一文也,诗赋与词典不同,散文与骈文不同,散文与书牍不同,公牍与书札不同,民间通用文字又与士人之文、官中之牍不同,是谓文与文不同。”[8]由语言和文字关系而产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现象,在其中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内部高下、雅俗等级的判断,这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雅俗格局形成有基础性的直接影响。赵毅衡曾对口语和有文字的书面语有一个一般性的比较:“书面文本大不相同,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可重复性———可以保存,可以重新阅读,重新抄录或重新出版。因此,它必须比较严格地尊崇社会规范。文化责任给书面文本带来意义权力,不识字小民也知敬惜字纸。口头‘文本’虽然能用师徒记忆方式代代相传,但传授不可靠(变异可能太大),渊源也不可考。因此口头文本是一种不具有历史性的文本,它的存在是即刻的、此时的、非积累的。它基本上处于文学史之外。”[9]费孝通认为:“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记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学习上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常常用,很容易遗忘;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话不同,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就会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须另外学习;文字所记载的又多是官家的文书、记录和史实,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民没有多大用处的。”[10]钱穆更是从雅俗关系出发,对中国文学的语言与文字,实际上就是口语与文字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即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早已分途;语言附着于土俗,文字方臻于大雅。文学作品,则必仗雅人之文字为媒介、为工具,断无即凭语言可以直接成为文学之事。”[11]的确,不少的中国古代口传文学,如民歌并不具备书面的形式,其载体是语言,是声音,故长期被视为鄙俗的地方性存在,可见脱离语言的文字是形成中国古代雅文学语言的重要条件。#p#分页标题#e#
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还带来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材料的方言与共同语的分野。十分明显,“雅”的定位与共同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源流来看,“雅”与“夏”互训,西周建都丰镐,为夏故域,周初人自称为夏人,所用语言称“雅言”,所作诗歌称“雅诗”,是采用京畿一带的语音为当时的标准音,故《诗经》有“风、雅、颂”之分。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说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刘台拱《论语骈校》上的解释:“夫子生于鲁,不能不鲁语,唯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也。”可见,从很早起中国文学的语言基础就有方言与共同语的区别。一般说来,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再加上政权的力量,作为共同语的“官话”多被认为是“雅”的,方才有进入雅文学的资格,而各地的方言是“俗”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固然,在中国古代有“采风”的传统,但各地民歌是必须经过乐府的加工和不断的文人化才能存在,并且加工后最多保留极少的方言词汇,绝对不可能在文学语言中对“雅言”产生威胁。陈平原认为:“生活在方言区的诗人不一定用超方言性的通用语言(如先秦时代的雅言、明代的官话、鸦片战争以后的普通话)讲话,却必须用它作诗———借助于韵书,各方言区的诗人获得了同一种声调,但这必须以舍弃充满生活实感的口头语而归附书卷气十足的书面语为代价。诗人想要使自己的诗篇进入文学交流系统,为各方言区的读者所接受,就必须在前人的书本中学通用语言,尽管也有诗人别出心裁,以方言土语入诗,但那只能偶一为之,出奇制胜。”[12]这带给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超越地域语音的特点,在广袤的国土上,它对于维系中国文化的统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俗文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却并不受这种共同语规定的制约。以白话文学主流文类的小说戏曲为例:中国古代方言白话小说,或是具有方言成分的白话小说大量存在;对于不同区域的地方戏曲而言,方言(唱腔、唱调、旋律、行腔)更是与其艺术生命休戚相关的语言存在。
三
毫无疑问,在语言学的层面,只有通过文字建立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书面语形式,方能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的雅文学语言,这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也给其审美实践带来种种特点。陈平原认为:“中国表意文字创造的艰难,再加上远古文人书写条件的限制,自然形成汉语简洁的表达习惯;汉语没有严格的数、格,少复句,逻辑性不强,故中国人相对长于‘醉’的诗而短于‘醒’的文;文言文言简字赅,语义含糊,故重意会,重领悟,这促使中国诗人避开‘易于穷尽’的‘正言直述’,而言比兴,求含蓄。”[13]由于士大夫超越口语的文学实践,只能在书本中学习书面文字,意味着就只有在学习先前的古代典籍之下,只有在“言文不一致”的情形下,方能进行文学创造。这样就形成中国古代雅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复古”思维,以及独特的书面音韵系统,维持了中国古代雅文学语言在很长时间中具有大致的同一性。于是乎,中国古代雅文学只能成为士大夫的一项特权,并形成自己固有的文学传统。陈平原还看到:“远隔千年,中国人仍然可以凭借书本跟先秦诸子直接对话,这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也正因为这种语言文字的便利,中国人容易养成深厚的历史感与崇古的价值取向。对于文学传统的形成,中国表意文字的延续性和相对凝固的特点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4]在维•什克洛夫斯基眼里,则是这样的景象:“中国文学不仅表现于文字,表现于象形字。它同时还是建立在独特的、某种象形文字思维的基础上,建立在概念对比的基础上。我冒昧地说一句,在这种文学里,对象似乎胜过动作,胜过动词:这一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视觉的。”[15]
我们可作一小结———“与政治统一密切相关的文字统一,直接造就了文化、文学的统一。借助于统一的文字这个优势。文人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人物类型的存在,使得文学的观念和审美也趋于统一了。这个观念和标准是如此深固,成长于士阶层内部的文人,其群体虽在上下流动之中,犹能不轻易失却。因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及语言才能显示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性,在白话文兴起之前的上下两千年中,始终具有不为时空所限的力量。”[16]在文言之外,汉语史家还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之中另一系统的白话的发展情形———“白话文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影响文言文,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话口语成分,进而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并对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汉语另一书面语系统。”[17]具体说:“古白话书面语系统在整个历史时期内并不完全相同。它逐渐演变,以适应口语本身的变化。在古汉语的两个书面系统中,文言文处于主流地位,白话文则作为旁系而存在。语言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旧的不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逐渐消亡和新的能适应需要而有活力的东西不断增长,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规律。古白话书面语系统中的口语成分在长期的发展中有一个量的逐渐增长过程。”[18]
在唐宋之后,使用古白话的俗文学在创作中,不断取得实绩,并诞生一些经典之作,在今人看来白话已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特别是在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已成为了后人眼中“一代文学”之代表,即这一时期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都是有区别的。虽然较之文言,白话文与口语更为接近,向来被称为“语体文”,但它也不可能就是口语的记载。宋代的话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口语的成分,但随着白话小说的发展,后来的章回小说虽有某些话本的遗迹,但已基本脱离了口语,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听—说”到“读—写”的转变,成为定型的书面文本。在宋元后,一些文人也加入到小说和戏曲———向来被认为“鄙俗”的领域———进行创作,使之具有“雅化”的倾向,获得了更高的艺术品位。但是,这一局面仍无法改变中国古代文学雅俗格局中,与文学语言密切联系的文类等级,即便在都拥有书面文本的明清雅俗文学中,我们仍可以粗线条地说,以文言为语言基础的“言文不一致”的诗文仍占据中心地位,以白话为语言基础的小说、戏剧仍是边缘的俗文学。尽管在今人看来,后者在宋元后的中国文学史上,更具艺术性和影响力。但不管后世人们如何推崇《牡丹亭》《红楼梦》,它们在所产生的时代就只能是诗文之外边缘的存在。另可以说明的是白话小说为俗文学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创作的小说中,一些士大夫创作者甚至不愿署名,或者只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别号,如“兰陵笑笑生”,似乎作者并不想与它发生直接的联系。#p#分页标题#e#
这使得后世的研究者对不少中国明清小说的作者的认定,需要作不少艰难的考证。这一切造成中国文学与文学语言在雅俗格局上的普遍区分与认同,如果有人在文学创作上违背这一关系,那可是不小的话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一则记录:“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19]这一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和章回小说的雅俗距离是绝对的。对于士大夫的文学创造而言,雅俗格局是一个必须遵循的现实问题,否则就将是一个“终身惭愧”的严重事件。
四
郭绍虞根据中国文学中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将中国文学史重新全面考虑,值得参考。他在一般意义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全景的描绘,划分为五个阶段,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况:1.诗乐时代,这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时代。语文合一,声音与文字语在此时代中犹没有什么分别。2.辞赋时代,沿袭以前改造语言的路线,逐渐造成离开语言型而向文字型演进的趋向,因此也可以称是语言文字开始分离的时代。3.骈文时代,这才是充分发挥文字特点的时代。利用字形之无语尾变化,于是可讲对偶;利用字音之一音一意,于是可讲声律。对偶是形的骈俪。再加文学的技巧,又重在遣词用典,剪裁割裂,以使错综配合,所以进到此期,文字的应用之能事已尽,可以说当时是文学语言以文字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4.古文时代,大抵骈文家所注意者,只重在发挥文字的特长,而不曾顾到语言的方面;所以这种文学语言可以和口头语言距离得很远。不仅如此,有时襞积累叠,甚至气不能举辞。这是骈文时代末流的主要缺点。至古文家则虽用文言(按即古代与口语接近的文辞),仍与口语不同,然而确是文字化的语言型,是摹仿古代的语言型的文学语言。因是语言型,所以骈文家只能讲声律而古文家讲文气,声律属于人工的技巧,文气出于语势之自然。又因是文字化,是摹仿古代的语言型的文学语言,所以不合口头的声音语,由于这种关系,所以古文家也讲音节。5.由此再进,索性应用当时的声音语以充分发挥语言的特点,于是遂成为语体的时代。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剧的发展,都在这个时代,甚至方言的文学亦以此时为盛。所以至这一时代而语言的应用之能事亦可谓发挥殆尽了。[20]
在郭绍虞描绘的图景之中,充分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文字与声音方面的特点,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俗文学的逐渐崛起,即声音的地位不断上升的事实,这可以和我们已论及的中国古代文学雅俗格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加以参照和互补。固然,郭绍虞向我们展示的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图景是在后世文学观念下的一种理解,并没有在具体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文学生态系统作出雅俗分野的分析,但我们并不难分辨其中雅俗构成的情形。这样,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语言学基础与雅俗格局作出一定的辨析,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构成了日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必须面对的“传统”。所谓“传统”,如阐释学者伽达默尔的看法:“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时间中的一种进程,而不是在过去已凝结成型的一种“客体”;“传统”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代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因此,在这一传统观的视野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建构之中,仍然重复着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诸如口语、书面语、雅俗格局等核心的命题。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构想贯通中国文学而形成整体性的视野,即是在中国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沟通与关联之中,考察中国文学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部多维度的复式结构,以切实追问各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纠葛,以切实追问“断裂”何为、“现代转型”何为,从而真正敞亮中国文学语言探索所曾达到的精神与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