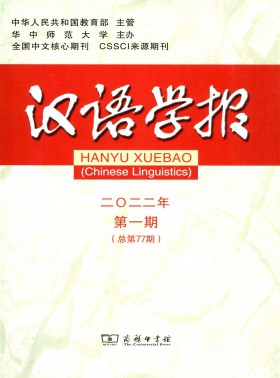《圣经》(TheHolyBible,简称TheBible)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一部文化大书和文学巨著。《圣经》文本最早于唐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景教传教士带入中土,“翻经书殿,问道宫闱”,可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记载。《圣经》最初翻译成汉语时,当时的译者按照我国把重要著作称为“经”的传统,取其“神圣典范”、“天经地义”之意,译为《圣经》(乐峰、文庸,1995:345)。实际上,“圣经”汉语书名曾有“真经”、“圣经”和“古新圣经”、“圣书”和“新/旧遗诏书”、“旧新约全书”或“新旧约全书”的历史沿革。如今“圣经”一词也成了华人世界对这部基督教的经典的专称。本文拟对汉语“圣经”书名的由来和演变做出综述性的探究,以厘清汉语《圣经》版本的历史脉络。 1、唐代的汉语“圣经”书名 《中国翻译词典》收录的“中国翻译大事记”(林煌天,1997:1134—1146),列举了从唐代至1919年间的汉语《圣经》翻译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这份记录虽然涵盖了《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1)对唐代的《圣经》译本表述模糊;(2)遗漏了两个《圣经》重要版本“巴设译本”和《古新圣经》;(3)官话和合本的出版时间有误,确切时间是1919年4月22日;(4)未收录1919年之后《圣经》汉译的重要事件和《圣经》版本,特别是中国翻译家的《圣经》单卷或片断翻译。(任东升,2007:114)有的学者(文庸,1992:31)根据唐代《圣经》汉语文本的卷数和音译名判断,景教士的翻译蓝本是古叙利亚语《圣经》。翻译出来的《圣经》书卷有《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多惠王经》(即《大卫王诗篇》)、《阿斯瞿利容经》(即《福音书》)、《浑元经》(即《旧约创世记》)、《牟世法王经》(即《旧约出埃及记》)、《启真经》(即《启示录》)等三十部(赵维本,1993:9—10;邹振环,1996:38)。可惜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景教《圣经》的正式译本,或可能早已失传。所谓“《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所经》译成”之说,不够严谨。景教士初来中土,他们不懂汉语,协助他们翻译或撰述以《圣经》为主要内容的景教经典时,也像佛经当初传入中国一样,只能是西人口述、华人抄录、迻写。中国学者认为该书乃“补缀新旧两约圣书之文”(朱谦之,1993:118)。 2、明末清初的汉语“圣经”书名 17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盛文学于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被迫融入这种环境。耶稣会士以“经”来对应基督教的圣典,借助于“经”这个字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的传统,同时把基督教的著述与这个儒家和佛教的“经”摆在同一个水平。耶稣会士在“经”字前加入了“圣”字,以表示他们的“经”具有神圣的启示,《圣经》乃“神启”的文本。1635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取材于《新约》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故事的著作《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刊行,该书标题有一注释:“即万日略圣经大旨”。“圣经”一词最早公开的出现应该如是。1636—1642年间,阳马诺(ManuelDias,jr.,1574—1659)的14卷巨著《圣经直解》印行,应是“圣经”一词首次出现于书名,但该书不属于《圣经》的中文翻译。罗马教廷驻清庭的公使贺清泰(P.L.Depoirot,1753—1814)于1750—1800年间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382—405),用官话翻译了除大部分先知书和《雅歌》之外的《旧约》和《新约》内容34卷,取名《古新圣经》,但是没有刊行。不过,这是“圣经”二字首次正式用于《圣经》译本书名。《古新圣经》虽然没有刊行、流传,然而解答这部书的白话《古新圣经问答》在1862年刻印出版,遂使《古新圣经》的名望传播开来。 3、19世纪的汉语“圣经”书名演变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进入中国,便着手用汉语翻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和米怜完成整部《圣经》的翻译时,取名《神天圣书》,共21卷为线装书。后来,麦都思、郭实腊等修订马礼逊译本和重译《圣经》,用过新/旧“遗诏圣书”和“遗诏书”。1843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2人在香港召集有关圣经翻译的专门会议,他们决定用简明的“圣经”二字来代表基督教经典的书名。传教士认为,“圣经”二字也可以指儒家的所有经典,等于在基督教传统与儒家传统之间设置了独特的平行。1853年至1868年翻译出版的“高德译本”,取名《圣经新旧遗诏全书》。这里我们查考一下“太平天国”推出的所谓“圣经”。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基督教会通用的主要《圣经》为郭实腊译本(谢雪如,1984)。郭实腊(K.F.A.Gutzlaff,1903—1851;又译“郭士立”)曾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四人翻译小组,重译过《圣经》,其中《旧约》差不多出自郭实腊一人之手,取名《旧遗诏书》。郭实腊后来对四人小组译本中的《新约》部分做过反复修订,取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陈惠荣,1986:16)。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洪秀全于1853年“钦定”推出了几部以郭实腊的译本为根据、经过删节的《圣经》版本。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太平天国使用的《圣经》,除了一部取自《新约》的《钦定前遗诏圣书》,其他均为经过删节的版本,名称多样。如《旧遗诏圣书》封面醒目的汉字“旧遗诏圣书”两边为一对飞舞的双龙,上方为一对凤凰,封面顶部“太平天国三年癸好初刻”字样。迟至1920年,周作人仍然把汉语《圣经》称作“圣书”。#p#分页标题#e# 4、和合本《圣经》的两种版本 最著名的汉语《圣经》,即1919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最初的书名即不叫“圣经”,也不叫“新旧约全书”,而是叫“旧新约全书”,这倒符合《圣经》中“旧约”在前、“新约”在后的文本编排。该译本在1939年更名为“国语和合译本”。1962年和合本《旧新约全书》的书名正式改为《圣经》。1962年推出的新版和合本“得到了热情的接纳和深深的赞赏”(尤思德,2002:346)。1988年,香港“联合圣经公会”推出了经过简单修订的《新标点和合本》,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代替了旧的标点;将诗歌体裁的译文改用诗行排列;《新约》和《旧约》的用词得到统一,使用了更通用的地名,人称代词男性河同性用“他”,女性用“她”,动物用“牠”,指代事物用“它”,使读者更容易辨别。《新标点和合本》简体中文版于1989年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在大陆推出。直至目前依然流行于中国大陆流行的和合本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分为“上帝”版和“神”版两种。这是由于《圣经》汉译史上对“造物主”名号译法的不同主张导致的。所以,“上帝”版的扉页或版权页上标有这样的阅读提示:本圣经采用“神”版,凡是称呼“神”的地方,也可以称“上帝”。同样,“上帝”版《圣经》也有相应的提示。 5、结束语 1968年以后,华人学者推出了几个汉语《圣经》全译本,均沿用了“圣经”的名称,如天主教推出的“思高本”(1968)、基督(新)教推出的“现代中文译本”(1979)和“新译本”(1999)。此外,鉴于中国读者阅读《圣经》全译本时会遇到语言和文化知识两大障碍,不少中国翻译家和学者精选《圣经》中故事性和文学性强、具有典故寓言性质的圣经片断,自取名称,出版发行。应该说,《圣经》汉译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无数中外译者为《圣经》汉译付出了精力和心血,由此各种名称的汉语《圣经》版本是中国版本史上不可或缺的史料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