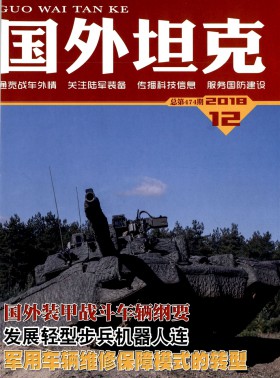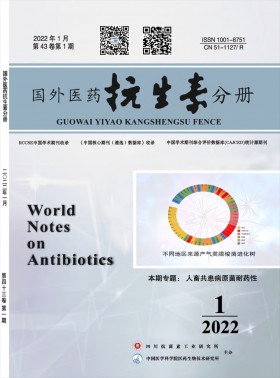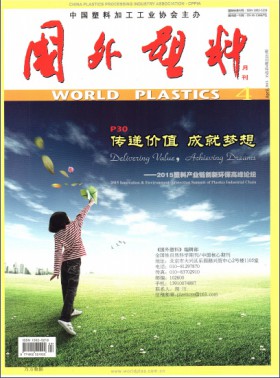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国外面对货币升值压力的经验借鉴,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日本经济崛起与日元升值压力 1.日本经济崛起。二战后,日本相对于美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1955年,日本GDP还仅占美国的6%,德国的56%,但到1968年就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从GNP增长率来看,1961-1971年,日本平均GNP增长率为10.4%,超过美国的3.6%。1973-1980年以及1981-1985年,受尼克松冲击和两次全球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日本经济发展势头有所放缓,平均GNP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但仍然高于同时期美国的2.5%和2.4%水平。从劳动生产率来看,1961-1971年,日本平均劳动生产率为9.8%,远远高于美国的2.9%,这也与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日元严重低估且汇率稳定,日本出口在趋势上大于进口,经常项目保持持续性顺差相吻合。1973-1980年以及1981-1985年,日本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降低,分别为6.1%和5.3%,但仍高于美国同期的1.6%和3.7%。从失业率来看,1961-1971年日本平均失业率仅为1.2%,低于美国同期的4.8%。1973-1980年以及1981-1985年,日本平均失业率虽然有所上升,分别为1.9%和2.5%,但远好于美国同期的6.6%和8.3%。从通货膨胀率来看,1961-1971年以及1973-1980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分别为5.6%和9.5%,高于美国同期的2.8%和8.5%。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和美国通胀形势出现反转,1981-1985年,日本平均通胀率降至2.7%,低于美国同期的5.3%(见下页表1)。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里根政府试图通过高利率政策吸引外资和解决国债购买问题,并维持国际收支失衡,但高利率让美元走强并令脆弱的制造业雪上加霜。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约占一半。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部门、国会议员等利益集团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更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要求日元兑美元升值。相比于美国经济颓势,1985年,日本GDP占美国GDP比重已达32%,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日本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制造”商品行销全球,对美贸易顺差增加和日元资产需求上升都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外压力(王允贵,2004)。因此,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前,日本经济实力就已达到改变对美经济关系的地步,而协议的最终签署只不过是日美之间经济关系再调整的反映。 2.日元升值压力。1949-1971年,日本实行固定汇率制,日元与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状况。然而,随着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不断接近甚至大大优于美国,日元兑美元的升值压力陡增。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Agreement)”签署为标志,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308日元兑换1美元。随着1973年日本正式实行浮动汇率制,日元升值压力得到释放并由此走上了一条升值之路。从1973年至1980年,除石油危机造成日元1973-1975年短暂贬值外,日元基本上保持升值态势,从1974年的300.94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80年的203.60日元兑1美元。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为240∶1,但到1988年1月就升值到了121∶1,并于1994年突破了80日元兑1美元的大关。总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元升值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3-1985年,属于缓慢升值期,这一升值阶段的特点是幅度不大,但周期较长持续了10多年;第二阶段是1985-1995年,属于快速升值期,这一升值阶段的特点是幅度较大,没有太多的反复(见图1)。从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来看,日本经济的黄金增长期是战后的20多年,但日元升值则相对滞后了10多年。从美国对日元升值施压来看,虽然有学者认为战后日本与美国结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其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因此,当日本对美国构成挑战时,日元面临的升值压力比对美关系相对松散的德国马克大一些。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归根结蒂还是日本战后经济相对美国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对美贸易持续顺差等内在压力所致。 二、德国经济崛起与马克升值压力 1.德国经济崛起。战后德国通胀严重,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不足,直到1952年,经济发展才接近战前水平,但在随后的二三十年,德国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要好于美国。从GNP增长率看,1961-1971年,德国平均GNP增长率为4.2%,超过美国的3.6%。1971-1981年,德国与美国持平,同为2.5%。但是,1981-1985年,德国平均GNP增长率仅为1.2%,低于美国的2.4%。从劳动生产率看,1961-1971年,德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为5.5%,高于美国同期的2.9%,这也与在此期间德国经济稳定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并在1971年外汇储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情况相吻合。从1973-1980年以及1981-1985年,德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4.0%和3.9%,均高于美国同期的1.6%和3.7%。从失业率来看,在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61-1971年,失业率仅为0.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4.8%。1973-1980年以及1981-1985年,受德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失业率有所上升,分别为2.9%和7.1%,但仍比美国同期的6.6%和8.3%要低。从通胀率来看,1961-1971年,德国平均通胀率为2.8%,与美国同期持平。从1971-1980年以及1981-1985年,德国平均通胀率有所上升,分别为4.9%和3.8%,但仍低于同期美国的8.5%和5.3%(见表1)。 2.马克升值压力。德国战后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1949-1960年,马克与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4.2马克兑1美元。随着德国经济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持续加大,1969年德国政府主动将马克与美元汇率调整到3.66马克兑1美元,但仍没有彻底反映德国经济日益强大的现实。为了维持马克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德意志银行大量购入美元,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基础货币(BaseMoney)大量投放,并直接威胁德国物价稳定。1971年“尼克松冲击”发生后,面对美元大幅贬值,为避免通货膨胀,德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马克升值压力也随之开始释放并走上了一条升值之道。总体来看,马克兑美元汇率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4-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从2.59马克兑1美元跌至1.83马克兑1美元;第二阶段是1980年至1985年,德国经济增速下降和受1978-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影响,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了短暂贬值,从1.82马克兑1美元升至2.9马克兑1美元;第三阶段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达成了包括马克在内的世界主要货币兑美元上调,加上德国经济实力回升,马克兑美元汇率迎来了持续升值,从1985年的2.94马克兑1美元跌至1995年的1.43马克兑1美元(见图2)。#p#分页标题#e# 通过回顾日本、德国经济崛起与日元、马克升值压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以下四个鲜明特征:第一,相关性:日德相对于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引致日元和马克升值;第二,滞后性:日元和马克快速升值阶段与日本和德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并不完全同步,前者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第三,阶段性:本币升值并非贯穿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主要发生在起飞到成熟或者经济破坏后的重建阶段;第四,诱发性:日元升值虽然不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元凶”,但日本政策应对失误导致“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甚至二十年,还是由此而生。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本和德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曾经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最为耀眼的“明星”,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与日本有所不同的是,德国对外贸易顺差更多集中在欧洲,对美国虽然也有贸易顺差,但远不如日本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而且差额比较大,因此,马克遭受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相对要小一些。 三、日本、德国应对本币升值压力比较 20世纪60、70年代后,如何应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本币升值压力一直是困扰日本和德国的难题。然而,由于日本和德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因此,这也给两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由于比较研究重在异,而不在于同(白钦先,1989),因此,以下将主要从日本和德国在面对本币升值时所采取的不同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搭配来进行比较分析。 1.被动大幅升值与主动渐进升值的汇率政策。面对经济崛起时期本币面临的内外升值压力,德国和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具体而言,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色彩极为浓厚,在20世纪70年代较长时间内,日本银行一直通过干预来压制日元升值,但最终囿于国内外形势又不得不允许其大幅升值,从而丧失了对整体经济的可控性,直接导致了70年代的高通胀和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相反,德国对汇率调整更为主动,马克汇率变化轨迹相对日元更为平缓。德国在每年预先宣布次年的货币增长率指标,以让公众相信央行确定的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在可控范围内的基础上,渐进地完成了马克升值过程。以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为例,1973-1979年,日本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为0.34,而德国为0.20,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干预上显然更为频繁(张斌、何帆,2004)。 2.依附于汇率目标的货币政策与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通常情况下,一国尤其是大国,如果面临内外均衡冲突,一般都会优先考虑内部均衡,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在国内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日本政府选择了更为偏重汇率稳定的政策,试图通过低利率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最终导致大量流动性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导致严重的经济泡沫(EconomyBubble)。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银行业造成了巨额呆账、坏账,银行信贷配置中介功能失灵,日本经济陷入了信贷紧缩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困境。相反,在应对马克升值期间,德国央行的重心是国内经济均衡,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地位,没有像日本通过连续减息来抑制马克过快升值,反而实行加息政策来抑制通胀,对马克汇率波动采取了一种善意的忽视(BenignNeglect)。1985-1987年德国马克兑美元累计升值达99%,与同期日元升值幅度相近,但并没有像日本陷入经济金融泥潭而难以自拔。 3.依附于汇率目标的资本管制政策和放松资本管制。日本在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增加,日本银行多次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避免日元币值过度波动,直至1979年才正式取消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在日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但也使国内产业政策调整严重滞后,并最终导致比不实行资本管制的德国更为剧烈的汇率波动。一国经济在崛起初期进行资本管制本意是避免资本自由流动对本国汇率稳定造成过度冲击。然而,从德国的经验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除了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稍有限制外,基本上取消了资本流入管制。1974年后还彻底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主要源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德国较早看到了资本管制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以及对这一政策的执着和坚守(王信齐,2011)。 4.政策搭配应对失误和政策组合应对有效。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后实施“双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根源,而随后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把泡沫挤破又是造成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此外,日本没有充分利用日元升值的大好机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依旧延续了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夕阳”产业,错过了以信息、生化等行业为代表的“朝阳”产业,并将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定为主导产业。由此可见,在本币升值条件下,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搭配不当会给一国宏观经济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相反,马克总体升值速度虽然很快,但德国贸易顺差以及出口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主要得益于德国政府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并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发展顺势而为,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德国企业也视马克升值为一条“鞭子”,不断鞭策自己提高生产效率,加之汇率政策从属于货币政策,以及举国上下对经济自由主义信念的秉持,德国最终实现了马克升值与经济平稳发展的双重目标。 四、对缓解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启示 当今的中国与20世纪60、70年代后的德国与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本币升值之前经济崛起大国都经历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转化为汇率升值的动力。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外向型程度都较高,甚至都是贸易“立”国,货币当局都面临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的政策权衡。本币升值前三个经济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盛松成、周鹏,2006)。然而,由于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当年的日本和德国不同,因此,还不能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人民币升值策略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p#分页标题#e#
1.坦然面对经济崛起时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虽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鉴于日元被动升值的历史教训,人民币升值应建立在我国经济金融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升值幅度与节奏应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相适应。具体而言,应区别对待人民币升值压力类型,对于外部性升值压力,如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甚至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转嫁危机提振本国经济而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要与其进行“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斗争,具体可采取“无为而为”的策略(刘刚,2010)。但是,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升值压力则应采取“疏堵结合”的策略。相比较而言,一国面临的结构性升值压力更具长久性,若本国货币汇率长期失调或者低估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或低效,不利于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导致社会资源向贸易部门过度集中,造成非贸易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日本当年制造业发达和服务业落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是最好的佐证。 2.实行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多元化策略。根据日美汇率博弈的历史可知,日元贬值(升值)与日美贸易顺差(逆差)之间并不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美国却以对日贸易逆差为幌子不断逼迫日元升值(刘刚,2012),由此而来的启示则发人深省,即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必须逐步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尤其是新兴经济大国和老牌经济大国之间更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贸易“双赢”,避免因双边贸易过度失衡而导致“贸易战”和“汇率战”。鉴于目前欧美国家深陷金融危机泥潭,居民购买力下降的条件下,我国一方面应生产一些适销对路和性价比高的出口商品,另一方面应创造条件增强与危机外围国,如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等一些国家的贸易联系。在实施“走出去”策略时,要鼓励技术需求型企业、市场需求型企业和资源需求型企业走出去(邱嘉峰、王珊珊,2009),而对于产业转移应有所区别,要避免因升值幅度超过实体经济部门承受能力后,出现大批企业破产或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以及海外转移,造成失业率急剧上升和有效需求内部不足的问题(夏国栋、胡德,2007)。 3.增强外向型小微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能力。与日本注重以独立知识产权为主进行研发,坚定发展自主品牌不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是由于社会内部生产要素价格抑制处于扭曲状态,劳动者工资、环保成本等生产要素长期被严重低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刘刚,2011)。然而,这些外向型小微企业吸纳了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并为当地政府创造了可观的税收收入,因此,提高外向型小微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能力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安全与稳定等核心利益。基于此,外向型小微企业必须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促进小微企业产品的结构性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政府应制定财政、金融、税收、科研自主创新转换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鼓励外向型小微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转型,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型密集产品出口的卡特尔,并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建立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国际卡特尔(贾根良,2010)。 4.继续推进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汇率是一种价格机制,因此,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质就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而不是简单调整汇率水平(王元龙,2005)。有鉴于此,我国应逐步取消结售汇制度,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逐步淡化中央银行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增加人民币汇率自由波动的幅度。同时,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此外,我国金融业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对内开放,应积极扶持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提高融资效率,鼓励私人投资。只有当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时,货币错配(MoneyMismatch)现象才会逐步消失,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可通过多种市场化手段予以消化。最后,当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最终实现完全自由可兑换时,长期以来被迫通过以外汇占款形式发行基础货币的局面就会大幅改观,我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也将由此得以实现(张志华,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