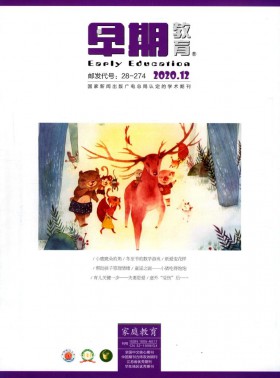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早期文学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1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2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3
一、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总结
中国古代向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一个现代政党而言,文学不但是承载、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首先,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但更侧重于古典小说、传统戏剧文学和其它民间文学等方面。他们对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正统文学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对其所轻视的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基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和题材,则极力发扬。同时,他们还继承近代以来的实证之风,对一些在历史上被歪曲的文学作品,加以历史的还原。下面,仅以其对旧体诗词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为例:旧体诗词的主要特点是对韵律、格式和字数的严格限制,不利于通俗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早期中共的基本观点是:旧体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同时,又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应当时的文学潮流和社会需要,反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做旧体诗词。陈独秀的理由是“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陷入窠臼”。对于做旧诗的人,他的做法是“讽劝他,叫他自己省悟。”①20世纪30年代,北京个别大学开设关于“词”的讲座,并提出了“昌明词学”的口号。张天翼就指出:“鼓吹青年们作词”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从其对旧体诗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中共反对盲目摹拟传统的文学形式,而阻碍文学作为思想载体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进行自由交流。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早期中共为向广大下层民众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扫清障碍的必然要求。
就古典小说而言,早期中共的学者们主要是将它们作为了解、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的历史材料来对待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在创作上“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②。因此,小说本身就是历史材料。在《〈西游记〉新叙》中,他认为:“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在研究时代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③对古代白话文进行了明确的肯定。1921年7月,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该文被后来的大陆红学研究者认为是“我国第一篇以崭新观点评论《红楼梦》的文章。”④该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入手,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深入剖析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对宿命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的中心”的观点。早期中共重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首先是因其描写的对象大多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这符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取向;其次,古典小说在当时仍是下层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早期中共通过对其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中发现其吸引广大民众的原因,并在自身的宣传工作中加以借鉴。其次,早期中共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主要有两点:一,理性审视和批判继承的思想的初步确立。张天翼认为:“对于旧的作品,我们并不抛弃,正相反:我们要全盘承受……把它们用来做我们的滋养料……承受旧的技巧,通过科学的辩证法,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⑤艾思奇也认为:“接受文学遗产是要从里面找到滋养的食料,以助成新兴的文学。”⑥二,提出了研究传统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目标。就方法而言,1922年11月11日,茅盾在致汪馥泉的公开信中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分组不如分段。”即主张以年代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划分标准,反对以体裁来划分。因为“中国书里,伪托极多”,要“查清伪书……按着时代分段来研究,似乎比分组好些。”同时,可以避免“研究文艺思潮的人不能不兼研究文艺的各支———诗歌、小说等”⑦的状况,从而避免人力的浪费。就目标而言,早期中共研究传统文学是为了在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克服它的不足,吸取其可资利用的方面,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他们认为,“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旧的中国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⑧只有这样,才能“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⑨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目的,即如恽代英所说:“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10。总之,早期中共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于配合其政治、军事战线上的斗争,建立、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学问题的价值重估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做了大量打破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束缚人民思想和观念的启蒙工作。但在当时,这种启蒙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运动后期分道扬镳,早期中共是其重要的一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学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价值重估。同时,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一次再检讨。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是比较全面的。郭沫若在当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定性:“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徵。”○11同时,他们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传统文学的目标远没有达到,它只是在没有对传统文学展开彻底革命的情况下,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并把这种文学称为“贵族文学”、“绅商文学”,把表述这种新文学的语言称为“梁启超式的白话”,认为“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12并将失败的原因推给了胡适一派。瞿秋白严厉指责蔡元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对反对文学革命的阵营采取了妥协态度。由此也就隐含地指出:早期中共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文学革命前进方向的代表。综观早期中共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走了这样一条路子,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的文学形式,提倡新的文学形式———反对旧的语言形式,提倡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始终贯彻着新旧之争,但争论的范围却一再减小,范围减小的同时,一些传统文学的成分就被搁置、保存下来,甚至被人为地利用。#p#分页标题#e#
三、早期中共与其它文学派别就传统文学问题的论战与汉字拉丁化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13。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所谓的“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复古派。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结合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于1930年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养料。他们的策略是不从正面冲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是也拿中国传统文艺当靶子,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戴起‘革命’的假面具来抨击中国旧传统文学”○14,希望以此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争夺阵地,从而以超阶级的“民族”概念,抽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烧得正旺的釜底薪火。现在看来,撇开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谈,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这些复古派的观点有很多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早期中共对于上述复古派别的批判也基本上没有失实,实际上是各自从自身角度出发,各说各话,在争论的方式上也是“只放不收”。但是,当时的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尽量地争取群众,过多的思想派别存在,势必影响群众的视听,分化其力量,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的御用文人借文化问题打压自己。因此,争论在所难免。茅盾为批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专门写成《“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文中最后一句为:“紧接着一阶段的,将是什么?是滔天的赤浪扫除了这些文艺上的白色的妖魔!”○15这里,已明显地透露出时已在组织上脱党,但作为党领导下的“左联”领导人的茅盾的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学得以延续几千年,“书同文”是技术上的根本保障。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文学大众化运动以来,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语言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文言文,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也在排斥之列。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所用的语言是大众所不能“听得懂”的。他们强烈要求创造“大众语”文学,甚至要求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这种做法无疑与当时极“左”思想的统治有关。同时,也是在人为降低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以适应大众的理解力。瞿秋白认为,要实行“文艺革命”,必须首先实行“文腔革命”○16,而要实行“文腔革命”,就“必须废除汉子,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17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学“仍旧是读出来听不懂的文字……不看汉字只听声音是不能够懂得的。”○18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目标是音形一致,即不看字形,只听发音就能会意。这无疑是出于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现实需要,但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观点比较理性、温和。郭沫若就认为,语言仅仅是思想的载体,不主张以运动的形式,人为地强行将文言文逐出文坛,他以严复在清末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说明“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算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19。茅盾则说得更清楚:“我们并不主张白话文中必须排除一切从文言文中来的字眼,我们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口头上活用的文言文字眼是主张容纳的”○20。
四、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改造与大众文学观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大众化成为进步文学家们一致的诉求。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学形式和作品被引入中国,同时,受近代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创作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作品。一时间,大量标榜新文学的团体、刊物相继出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21就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文学现状而言,早期中共认为,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普遍生活在传统文学的笼罩下,“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22“广大民众依然浸淫在‘孔家老店’招牌下的‘旧文学家’的宣扬‘道统’的文学作品之中。”○23张天翼指出,中“所谓文学革命是造成小白脸文化的……过去的作品……适应着小白脸,适应着小康之家的学生们。不是大众的。”○24这里所谓的“小白脸”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传统文学充斥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冻结了其所蕴含的革命能量。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4
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维萨利昂•别林斯基(1811-1848)对俄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却长期在俄罗斯和中国学术界遭到了严重曲解。一方面,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与德国文学理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肯定其后期思想进步意义的同时,却忽视了他早期批评中的许多重要见解。因此,重新认识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正确评价他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或许是对这位批评家最好的纪念。
一、在早期论文《文学的幻想》(1834)中,别林斯基通过对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历史回顾,反对盲目摹仿西欧文学,热切呼唤一种真正植根于俄罗斯生活的民族文学。为此,他从史雷格尔兄弟那里借取了一个重要观念,即把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人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现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1]10。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107。以这一标准来考察,别林斯基不禁深感失望,因为一部俄国文学史,“不过是通过盲目摹仿外国文学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这种失败尝试的历史而已”[1]110。甚至在普希金的创作中,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也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因此,别林斯基热情期待着这样一天:“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到了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文学,我们将不是欧洲人的摹仿者,而是他们的劲敌。”[1]124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再次采纳了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文学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大类。他指出:“诗人或者根据全靠他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来决定的他那固有的理想,来再造生活;或者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147与此对应的,则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客观诗人和以席勒为代表的主观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别林斯基看来,莎士比亚没有理想,没有同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那广无涯际的、包含万有的眼光,透入人类天性和真实生活的不可探究的圣殿。”[1]152而席勒的作品却是为了表现诗人的思想情绪而创作的,它“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1]157。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往往将上述见解视为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石,但这一判断却是大可怀疑的。诚然,别林斯基在此多次使用了“现实的诗”、“生活的诗”等字眼,但我们却应当认识到,有关“理想的诗”与“现实的诗”、“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所作的区分,早在浪漫派批评家那里便已明确提出,何以一经别林斯基转述,就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何况除了俄国作家之外,别林斯基赞誉的是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拜伦、乔治•桑和詹姆斯•库柏等人,他们的创作与通常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也相去甚远,何以仅凭几个概念就断言别林斯基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在此反复强调了文学创作的非目的性和非自觉性。在他看来,“创作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这便是它的基本法则。”[1]177具体地说,当诗人产生创作冲动,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是自觉的;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孕育中的作品就不再被诗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创作又是无目的和不自觉的。别林斯基甚至宣称:“诗人是他的对象的奴隶,因为不管是对象的抉择或是它的发展,他都无法过问,因为如果没有那绝对不依存于他的灵感,无论是命令、订货或是本人的意志都不能使他创作。”[1]180显然,这与他后期评论中坚持艺术必须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评述别林斯基的论著。不过,在他的早期批评中,还有三个理论问题应予以重视。这就是形象思维、典型化和有机整体论问题。虽然我们不难在德国批评家那里找到他们的理论渊源,但由于别林斯基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发挥,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
如果说有关创作非自觉性的说法主要来自康德的话,那么,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理论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强调:“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索,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实,不过不是表现在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思维;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96然而,尽管形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了别林斯基对艺术规律的探讨,但所引发的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首先,由于该理论把诗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导致文学研究忽略了作品文本而滑入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领域。其次,形象思维的说法过分看重视觉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其他艺术技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视觉意象只是诗歌艺术中的各种技巧之一,并不比其他技巧更特殊、更有效。而这也正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别林斯基也高度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把典型化视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他指出:“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化……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个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191在此,别林斯基借鉴了黑格尔的见解,将典型看作是体现某种普遍概念的代表,认为典型化就“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2]102。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典型应当是高度个性化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条件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2]25同样,有机整体论也是别林斯基早期评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没有最好的场面,因为里面也没有最坏的场面,一切都是出色的,都是艺术地构成那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142他甚至借用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艺术作品比喻为植物的生长,“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2]251尽管这似乎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别林斯基强调的却是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表明了他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放弃了这一评价标准,代之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p#分页标题#e#
二、1841年,别林斯基雄心勃勃地计划撰写一部系统的诗学著作。从写作计划来看,此书规模相当庞大,意在“有系统地认识美学法则,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有系统地认识祖国文学史”[3]2。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并未完成,仅仅写出了四篇论文———《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艺术的概念》、《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和《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就完成的这些论文看,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不多,许多见解仍然来自于德国文学理论。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贬低别林斯基,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不难发现,别林斯基的体裁理论基本上照搬了黑格尔的观点,只是在个别细节上作了若干修正。在他看来,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歌、抒情诗歌和戏剧诗歌三类。叙事诗歌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诗歌,宛如建筑、雕刻和绘画;抒情诗歌是主观的、内在的诗歌,可以比作音乐;而戏剧则是叙事的客观性和抒情的主观性的统一。别林斯基称颂歌德和席勒是“抒情诗歌的两个完整世界”,也赞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司各特和彭斯的创作,而法国却没有抒情诗,其水准绝不超出民间歌谣之上。就戏剧而言,首先是莎士比亚,其次是德国悲剧,法国戏剧则“属于服装、时装以及良好古老时代的风习的历史的范围,但却跟艺术史毫无任何共通之处。”[3]79由此可见,直至19世纪40年代初,摒弃新古典主义趣味,拥护浪漫主义文学,仍然是别林斯基批评活动的基本倾向。
《艺术的概念》一文开宗明义,对艺术作了如此界说:“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思维。”[3]93关于形象思维,这里无须赘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样两点:首先,别林斯基在此论述了黑格尔的哲学,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从宇宙到人类的精神,都看成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运动。而人类的精神发展则经历了从神话到艺术,最后到哲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次,所谓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其“直感”就意味着“存在以及毫无任何媒介而直接发于自身的行动”[3]103。别林斯基强调,“直感的”与“不自觉的”并非同一个意思,“现象的直感性是艺术的基本法则,确定不移到条件,赋予艺术崇高的、神秘的意义;可是,不自觉性不但不是艺术的必要的条件,并且是跟艺术敌对的、贬低艺术的”[3]107。这表明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已发生了变化,早期所推崇的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此时已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别林斯基也强化了历史主义观念。他指出:“文学的意思是指历史地发展起来并反映出民族意识的文辞作品。”[3]117“发展的有机的连贯性,构成着文学的特点,这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有别于文辞和文录的地方。”[3]120因此,不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就不可能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不了解17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也就不可能理解现今的法国文学。但与《文学的幻想》不同的是,别林斯基在此承认,俄国民族文学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从来不曾有过,并且现在也不可能有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3]155。
《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继续讨论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由于别林斯基此时已较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因而他强调民族性只有与“一般人类事物”的共同性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正如他所指出的:“人们在文学中仅仅要求写出‘民族性’,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在文学中要求完全不写‘民族性’,认为这样可以使文学为所有的人所理解,成为普遍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的东西,也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很显然,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3]186然而,贬低民间文学的观点却依然如故。因为,在别林斯基看来,民间诗歌产生于一个民族尚未自觉的婴儿时期,其内容只能为本民族所理解,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3]211。这当然是一种错误见解,在大量文学史事实面前将不攻自破。
三、大致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与前期推崇客观诗人而贬低主观诗人的立场不同,他转而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强调诗人的个性和激情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与前期崇尚艺术的自足性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三,前期所持的有机整体论开始松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并越来越多地从内容方面来看待文学作品的价值。当然,所有这些变化是与他整个世界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所知,别林斯基的早期评论是完全倾向于客观诗人这一边的。但在《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2)一文中,他却出人意外地把诗人的主观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来,果戈理迈出的重要一步,便是在《死魂灵》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主观性。这当然不是指那种歪曲客观生活的主观性,而是强调作家在真实描写外部世界的同时,又注入了创作主体的强烈爱憎。正是这种主观性,“不许他以麻木的冷淡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世界之外,却迫使他通过自己泼辣的灵魂去引导外部世界的现象,再通过这一点,把泼辣的灵魂灌输到这些现象中”[3]414。因此,在别林斯基看来,《死魂灵》并不像那些御用文人所说的那样,是对俄国社会的丑化,而是对这个社会的丑恶现象的鞭挞,其中“洋溢着对俄国生活的丰饶种子的热情的、神经质的、带血丝的爱”。
在鸿篇巨制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中,别林斯基更把这种主观性称为“激情”,认为它是理解诗人个性和创作特点的关键。他指出:“每一部诗情作品都必须是激情的果实,必须被激情所渗透。没有激情,就不可能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诗人执笔作文,给予他以力量,让他有可能写完一部篇幅浩繁的作品。”[4]336当然,艺术中的激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理智对意念的简单的理解转变为精气充沛的、强烈追求的对意念的爱”[4]335。就此而言,激情既是体现于作品中的统一的精神,也是创作活动本身的驱动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如果一个诗人决心从事创造活动,这就是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不可克服的热情推动他、驱策他去写作。这力量,这热情,就是激情。有了激情,诗人就爱上意念,像爱上一个美丽的、活生生的人一样,就热情如焚地被概念所渗透……”[4]334在早期批评论著中,别林斯基曾多次表述了有关艺术的自足性的思想。他声称:“诗人如果在作品中力图使你们从他的观点来看生活,那时他已经不再是诗人,却是一个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恶劣的、用意不良的、该诅咒的思想家,因为诗歌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目的的。”[1]24但在后期的批评活动中,别林斯基却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中强调:“我们的时代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赋予19世纪的艺术以历史倾向,这就意味着:天才地猜透了当代生活的秘密。”[3]584#p#分页标题#e#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5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6
一、散文与散文文学 散文以其庞大的数量、繁多的品种在万紫千红的文学百花园中呈艳丽于一坛。散文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别于其它文学形式。 一篇优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诗歌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散文与散文文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的。广义上的散文是指书面语或口头语的非格律形式,是韵文的对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词prose最初源于拉丁语prosa(oratio),它的原义是“直截了当的谈话”。十一世纪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后,随着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国词汇之时,prose一词才由古法语变成了中世纪英语词。由此,人类最初是从语言的形式上获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体与文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只有当散文脱离了纯实用性目的,成为部分人或作家个人为解释某事,或对某一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成为散文文学。正如原始人类在高兴时所表现出来本能的手足动作尚不是舞蹈艺术一样。小说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但散文作家的写作主要在于针对事实的逻辑性陈述与解说,以及他们的观点与态度,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讲故事本身。 散文文学同样贴近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内容,文学性的散文有个人事务、情思、哲理、历史、科技、传记、游记等方面。就其文体形式,有小品、随笔、素描、特写、书信、扎记、演说辞,也有语言优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诗。散文文学既可作茶余饭后、或劳顿疲乏的消遣休闲手段,亦可作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辞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学求知的师友。散文拥有比戏剧、诗歌、小说更多的读者。无论文人墨客,学者仕人,还是市井平民,没有人从来没有涉猎过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学的这个特点,使它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能成为繁荣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语散文的特点 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散文还处在早期阶段。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民族历史进程相联系。公元5世纪时,欧洲大陆日尔曼民族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部落相继迁入大不列颠岛,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国。公元7世纪时,英伦岛上的诸小王国才慢慢统一起来,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语散文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语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语写成,而是用拉丁语写成。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英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读书写字的文人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的宗教活动使用的是拉丁语。因此,用拉丁语写文章便成为时尚,是少数人的特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彼德(Bede)就是这类写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务于教会,著作颇丰,论涉广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语写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记载了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到公元8世纪前三十年英国历史的全过程。 人们能够用古英语读到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是在9世纪末了。尽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但这本书仍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彼德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而不是“英国散文之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古英语写的散文是于9世纪末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发起翻译与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部编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逐年记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教会人士。 因此,它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一名叫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僧侣精通拉丁文。他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语写的散文几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经解说文。这类作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学创作。 早期英语散文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后的英国。1066年,讲法语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英国建立了盎格鲁•诺曼王朝。英国正式步入了封建社会。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逐步演变成夹杂着大量法语词汇的中世纪英语。语言的演变也引起了英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诗让位于讲述亚瑟王和他的园桌骑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广泛流传民间的民歌民谣,特别是关于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民歌。传奇与民歌多用韵文形式,且不是个人创作的作品。这时的散文也加入了这个文学大转变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亚瑟王与园桌骑士传奇故事的却是作家个人。十五世纪的托马斯•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讲述骑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写文章要用外语的古风在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着。他著名的《亚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虽然不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先用法语写成,然后马洛依自己把它译成英语散文。英国早期散文以拉丁语或法语写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上半叶。汤马斯•莫尔(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然后译成英语。这种习惯直到英国文艺复兴后才最终结束。 三、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英国 “散文之父”的产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时间上比欧洲大陆慢了一拍,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经转入尾声。而在英国,此时文艺复兴正是高涨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汤马斯•莫尔,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集中地通过他的散文著作《乌托邦》(Utopia)表现出来。《乌托邦》用拉丁文写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译成英文。《乌托邦》不再是讲述传奇故事的文体,而是采取三者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在这种散文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短篇小说型的散文体。#p#分页标题#e# 16世纪后期,一种新型文体盛行于英国,即“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小说散文”虽然包含有一个简单的故事,通常是个爱情故事,但结构并不复杂。作者并不以创造故事情节为主要目的。 “小说散文”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突出某种语言风格的散文体裁。这种语言充溢着结构长而复杂的句子,讲究音调的平衡,句子的对仗、排比、使用人工雕凿的,牵强附会的修饰或比喻。这种散文文体又称为“华丽散文”,英文为“Euphuisticprose”,与中国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相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文体极其盛行于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交际中,特别是名媛贵妇们不仅要会说法语,而且要学会用Eu-phuism体。 英国第一个“小说散文”的作家是约翰•李利(JohnLyly)。这种文体名称“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变而来。词藻华丽的骈文似的散文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没落了。但是这种文体使英国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 在英国文学发展道路上,这种文体为散文的繁荣,为十八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的文艺复兴是“英国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纪末产生的催生婆。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场奋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终成为了英国“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学研究兴趣,从事科学实验与哲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培根在记录和发表他的科研成果报告时,也是用拉丁语写作。而在他科研闲遐之时,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或感想时,他才用英语写出来。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书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问世。 这就是英国第一部以英文写成的散文文学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断扩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会,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见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失它的正确性。《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言,被人们反复引用,已经变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识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语言高度精炼,简洁。尽管有人说培根的散文集是他严谨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副产品,但它的价值永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在他的写作尘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后,英语散文文学进入了繁荣与具有自我特点的发展之路。培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给后世英国散文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的末期,十七世纪初的另一个影响到英国散文进程的大事便是《圣经》全文的英译本完成与出版。中世纪的英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圣经》是直接用拉丁语诵读的。十六世纪时,《圣经》仅只有片断,章节英文翻译本。160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了47个学者进行《圣经》全文的翻译工作。 经过七年的集体努力,英文版的《圣经》全文终于在1611年问世。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称为“国王钦定圣经”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经》英译本除了诗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体译成,它的英语纯粹,表达力强,文辞生动优美,并且摆脱了“华丽散文”Eu-phuism体的文风。 十七世纪初英国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发表的散文著作《忧郁症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医学书或医科教材。实际上,作品涉及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把社会与政治弊端与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疾病相比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风活泼,文句幽默而机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散文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议会的横蛮态度终于导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是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反映英国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学随之兴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清教徒诗人,《失乐园》(ParadiseLost)作者约翰•密尔顿(JohnMilton)的早期写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资产阶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的散文小册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权等各种问题,成为资产阶段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复辟时期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学评论上。这个时期之前,英国尚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而又客观的文学评论作品。被人们称之为“趋炎附势的两面派”作家约翰•德来顿(JohnDryden)虽然在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散文著作《戏剧诗歌论》(AnEssayofDramaticPoesy)却是英国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著作中,德莱顿以对话的形式,对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家作出了他的评价,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他以两分法的观点,指出了莎士比亚的问题,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但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语作为对莎士比亚的总结: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译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为莎士比亚就像生长在低矮篱笆丛中的参天柏树一样高大、挺拔,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德来顿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人评论的基调。他的文学评论散文思想敏锐,语言简洁,风格质朴,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华丽文体天壤之别,与同世纪的密尔顿的复杂长句亦不同。正是这样,有人称德来顿为“英国的文学评论散文之父”。#p#分页标题#e#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经历了反复,以向封建王权妥协而告终,但是夺取政权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工业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群众,以取代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封建思想。这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时代”。英国启蒙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这时的散文文学的发展为整个英国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异彩。特别是散文的写作风格更是异军突起。 十八世纪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英国文坛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文学部门,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国小说之父”之誉,《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开始编辑出版了英国的第一个期刊《评论三周刊》(Review),发表讨论政治、道德与文学等方面的散文作品。虽然笛福开英国期刊散文先河,但是这个时期在期刊散文文学上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们共同编辑撰稿的期刊《闲谈者》(TheTattler)和《旁观者》(TheSpectator)。这两个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他们以清新流畅,简洁生动而带有淡淡讽刺味道的语言论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观者》中的文章影响深远。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他小的时候,是如何模仿《旁观者》中的文章练习写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散文文学的不同风格更是各具异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讽刺文风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讽刺作家的声誉。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成为了英国讽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满怀深切的同情与忧虑描写了爱尔兰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文章却以满篇反语讽刺的语言写成。贬语咒骂变成了深沉的爱,奉承与褒奖成了切齿之恨。作者的文句构思与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这位讽刺大家的非凡写作技巧。与斯威夫特散文风格迥然不同,撒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散文则充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约翰逊博士以编纂了英国的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巨大成就而记入史册。而他的文学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驰名文坛。约翰逊散文典雅庄重,文思睿智,才气横溢,文句优雅。他绝少用俗语和口语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对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发展成三联排比,把散文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辞典》最终完成引起了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风波,这导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笼。这封信是英国古典主义散文书信的典范,历来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而他为自己的《辞典》所写的一篇《序言》,则远远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论文,后半部分则是抒发感情的优美散文诗,把他编写英语大辞典时既自信而又胆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三联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约翰逊这一位其貌不扬,却又才智过人的奇才,“约翰逊俱乐部”的头人,英国才有了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詹姆士•波士威尔(JamesBoswell)。波士威尔成天与约翰逊形影不离,车前马后,把约翰逊的言行统统记录下来,终于成就了他的《约翰逊传》(LifeofSamuelJohnson)这部巨著。这是英国传记文学最早的一部经典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英国也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历史散文巨著《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来辛勤收集资料,访问调查的结晶,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语言精彩,文笔优雅,是英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大发展还表现在演说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写了一系列语言雄辩有力的演说散文与书信体散文。他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散文《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语言苍劲优美,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与反对。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英国在该世纪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过渡,而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反映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中丰富了它的题材种类。 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散文的题材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与多面,直接地批判种种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代,当英国还是浪漫主义思潮统治着文坛时,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进散文家就写出了许多议论时政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思想激进,内容新潮,文笔犀利,反映出被压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权利的心声,提倡改革与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农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创办的《政治纪事》周刊前后持续达三十多年,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了选举中的丑行,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对英国的农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乡村骑行记》(RuralRides)既写了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写了社会现实生活。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自然美景与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作者的情怀。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虽然在诗歌领域,但这个时期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还有兰姆(CharlesLamb)、赫兹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兰姆从一个业余诗人成为英国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爱。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尝试,但没有人像兰姆那样能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复述莎剧中的故事,让那些不懂戏剧原文的人,甚至儿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兰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亚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亚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风格柔和、优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与哀怜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页标题#e# 赫兹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内容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评论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学批评著称。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个英国抽鸦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鸦片的经历,进而联想翩跹。散文词藻华丽、风格轻漫,有“散文诗”之称。德昆西关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评论散文亦引人入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宪章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在英国文学战线上的反映就是“宪章文学”。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册子在宪章文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号召性的散文册子、书信、演说词与战斗的诗篇一起为工人运动宣扬了舆论,号召了群众,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们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在品种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数目之众,也是史无前例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长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家。一个由苏格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莱尔(ThomasCarlyle)擅长于文学评论和演说散文写作。他对彭斯(RobertBurns)的评论散文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评论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认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众的觉悟,害怕群众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会的“英雄”。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演说散文集《英雄与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无遗。麦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则以他生动的语言写历史散文。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断代史,却又不是断代史。他以小说的描绘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历史事件写成生动的描述文,读起来令人兴趣横生。腊斯金(JohnRuski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散文家。他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蘸注在绘画、建筑的艺术评论上,他的关于中世纪建筑艺术的评论《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响到欧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纽曼(JohnHenryNewman)的关注则投向大学教育方面。马休•阿罗德(MatthewArnold)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文学与社会评论家。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英国散文文坛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题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会势力的阻挠,达尔文主义尚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更不为普通劳动人民所知晓。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来,以演讲,写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演说词散文《一片白垩》(APieceofChalk)把进化论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人们熟识的事实,解说了进化论的精髓。尽管人们普遍将赫胥黎列入科学家名单,但他的作品开创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风格。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包括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英国文坛上泛起。人们熟知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魏尔德(OscarWilde)被称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却是散文起了先锋作用。首先在英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理论的是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艺复兴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唯美主义的宗旨。因此,魏尔德是用他的艺术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图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较现实与客观的态度评价了狄更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另一位广为读者所知的小说家,《金银岛》(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义小说一样,写了许多散文游记、随笔和小品,为本来已经题材品种相当丰富多彩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游记散文。 五、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概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世纪的英国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国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加残酷。国内劳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觉醒。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国最终沦落为美国的帮凶与仆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文学领域有深刻的写照,英国散文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同样映照了时代的变迁。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高峰时代。 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仍然被一些作家继承着,但小说和诗歌领域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作品各显其能。未来主义(Futur-ism)、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种文学思潮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英国散文文学也以它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大变化的文坛上展现一角。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散文文学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散文写作转向非严肃性的主题。由于文学创作越来越商业化,散文写作不再用来讨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而用以服务悠闲阶层的娱乐,或供茶余饭后的消遣。过去英国散文传统的严肃主题被轻松的议论所取代。 #p#分页标题#e# 由于轻松散文的繁荣,幽默、机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讽刺语言便成为了这类散文的基调。小品、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充溢于报刊杂志和集子。传统的英国散文中,典雅优美的语言风格被大量的习惯口语化的词语所代替。这类散文的代表有麦克斯•比尔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与旧》(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琐事》(TremendousTri-fles)、《差异的运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说来》(GenerallySpeaking);贝洛克(HilaireBelloc)的《论没什么事》(OnNothing)、《论每件事》(OnEverything)、《论任何事》(OnAny-thing)、《论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还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展着。尽管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支配着这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但散文仍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文学有以下特点。这个时期,传记散文有了迅速的发展。传记的写法突破了旧传统,从注意积累详细而充分的史料事实,按岁月的进程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到有选择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中期,“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国兴起。 “小说散文”的文体人们并不陌生,英国在十六世纪就盛行过。约翰•李利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创造了骈文式的Euphuism体。他死后,这种文体在英国衰落下去。我们在浪漫主义散文家兰姆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一点“小说散文”的痕迹,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内容构思方面。二十世纪的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说散文”的创作形式,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奥威尔的“小说散文”也包含着一个由简单的小故事所构成的情节。但他的语言却简朴无华,没有牵强的比喻,不刻意运用排比对偶的语言效果。没有华丽的词藻,文句却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杀记》(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写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缅甸当警察时的经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作者以小说心理描段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对缅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夹叙夹议,把内心的矛盾,迟疑犹豫的心情袒露在简单事件的处置上。文章对射杀大象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散文具有小说的特点。 然而,奥威尔的政治态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在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有的转向了左派,而奥威尔却在二战后完成了从左派到右派的大转变。二战后他的小说以反苏(联)反共为主题。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恶意攻击,为帝国主义的“冷战”帮了忙。英国散文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突出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在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些进步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论文学现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福克斯的文学评论著作《小说与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欧洲与英国文学作了批判性评述,遣责了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作者坚定地指出,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才有文学的繁荣,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小说与人民》一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人的灵魂而战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克斯能有这样的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德威尔是英国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集中在相继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临终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与现实》中,科德威尔的评论重点置于诗歌方面,但所用的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作用,认为诗歌也要渗入到社会的变革中去。在《临终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观点评论了戏剧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和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亲自投身革命活动。福克斯和科德威尔二人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旅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遗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家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册上没有给这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留下应有的一页,正如宪章运动中的宪章文学和作家们不被重视一样,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真正反映了英国劳动人民的心声,他们是英国先进思想家在文学上的代表。 六、小结 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文学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文学发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特点。文学发展的道路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纵观英国散文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似乎觉得英国的“散文之父”有点姗姗来迟,这正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尽管散文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俱来,但长期使用拉丁语和拉丁语散文创作习惯推迟了真正英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但是一旦英语散文文学兴起后,它的发展就异常迅速,并给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英国散文文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了辉煌的成就,它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载入了英国文学史册。战后的英国散文文学在进步与反动,理性与沉沦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艰难地发展着,历史将会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体裁与题材。#p#分页标题#e#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7
一讨论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不应以创造社的“前”、“后”分期,而应以“元老”和“新锐”划界。其理由主要有二:一、创造社“元老”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创造社“前期”就已经发表涉及“革命文学”问题的文章。比如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都发表于1923年5月,都被文学史家看作是“革命文学”的先声。李何林认为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简直是‘革命文学’的呼声了”[1]110。刘绶松把这两篇文章都判定为“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运动倡导的前奏了”[2]131。二、虽然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在“五卅”以后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总体看来仍保持着前后的一致性,且后来的变化也与创造社“新锐”们的观点明显不同。按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3]84中的说法,创造社“元老”们在“五卅工潮”前后的剧变,“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在他看来,“这个目的意识是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战士之决定的标准”。持有这种“清晰的目的意识”的,正是创造社“新锐”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 创造社“元老”们在创造社前期主要以张扬浪漫主义文学闻名,并没有过像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那样,在较为固定的报刊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其“革命文学”的观点都零星地发表于刊物之上,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只把它们作为创造社“后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芽,并认定其中“包含了许多不正确的观念”[2]131;对于“五卅”以后“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言论,一般文学史著作多从同一团体的角度强调其与创造社“新锐”们的一致性,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使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的真实面目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笔者认为,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并列的重要文学观念,可以也应该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那么,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创造社的“变”与“不变”。 创造社以善变闻名。最明显的或者说是“翻着筋斗”的变,是从崇尚“天才”、注重“灵感”、标榜艺术的“无目的”、追求文学的“全”与“美”,到遵从“时代”、主张“写实”、强调艺术的“功利性”、赞美文学的“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善变”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掌握话语权的成员的变化而显现出“团体性”的变,二是它的一些重要成员因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文学观点的变。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元老”们的“革命文学”理论,在创造社的前、后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其前期只是零散的萌芽,而直到后期才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理论观念的改变。 1925年底郭沫若在《〈文艺论集〉序》[4]146里就曾开诚布公地说过,他的思想、生活和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变化是确实存在的。比如,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3]3中是把“无产阶级的精神”与“精赤裸裸的人性”并列的,他既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也要“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而他在三年后发表的《革命与文学》[3]32中,则明确表示“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5]46中“大声疾呼”的,是基于“反抗”意义上的“斗争”而不是“阶级”;而在三年多以后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5]287中,他则“断定”:“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6]205一文中还强调“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但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6]241一文中,他就呼吁“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但是,这就是创造社吗?笔者以为不能这么说。 善变只是创造社的一个方面,甚至极端一点地说,还只是创造社理论观念层面的一种表现。创造社其实还有许多不变或只是变形而没有变质的东西。这在个性鲜明成就非凡的“元老”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创造社的理论观念与意识本质相分裂的状况,王富仁、杨占升在《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文中曾有一段分析:“在他们那里,先进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主张’,只要有了这种‘知识’和‘主张’,他们便以为完成了自己的‘奥伏赫变’,因而先进理论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身外物、异化物,而自己的意识本质、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旧的一套。”[7]12虽然王富仁、杨占升所指称的主要是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创造社与太阳社,但把这段话移用到创造社“元老”们身上,也是非常适用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元老”们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因素,或许更能体现其“革命文学”的真实内涵。#p#分页标题#e# 二这些“真实内涵”,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论文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表明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非常注重文学形式的感染力。郭沫若文艺论文的这种特点特别突出。他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自然与艺术》、《桌子的跳舞》等一系列论文,都不讲究严密的论证逻辑,而是洋溢着一种澎湃的诗情。不少学者曾尖锐地指出过郭沫若谈论文艺的文章,存在概念含混和误用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其实,这正体现出郭沫若那种容易冲动、多变的诗人特性。郁达夫的文艺论文同样富有文学感染力。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从“风光明媚,空气澄清的奥灵泊斯(Olympus)山”说起,又以诗性语言结束。文中不断出现的充溢着作者个人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带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的句子、以及流贯在整篇文章中的那种无法抑制的激情,都能给人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力。相比而言,成仿吾的文艺论文显得朴实些,逻辑思维严密些,但其在语意回环中突出重心的技巧,如《新文学之使命》,在嬉笑怒骂中点破疑团的功夫,如《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以及对后浪推前浪式的表达思想的气势的强调,如《祝词》,也都颇具文学特色。 另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观念也始终注重文学。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再三强调:“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两年多以后,在特别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时候,他在《英雄树》[3]44中仍然说:“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在《桌子的跳舞》[3]51中又重申:“文艺是阶级的勇猛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6]89中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五年后他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6]248中还是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郁达夫的“革命文学”观念与郭沫若等人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的重要作用方面,他们还是一致的。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认为:“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活剧。”后来在《创造月刊•卷头语》[5]183中仍然表示:“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创造社“元老”们注重文学,源自他们对“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等基本概念的理解。虽然他们的理解同中有异,但导向的都是对文学的看重。 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是“进化论”意义上的“革命”,他只是在社会进化的宽泛意义中加进了“阶级斗争”的“进化”模式。他说:“革命本来不是固定的东西,每个时代的革命各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不过革命的形式总是固定了的。每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每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的反抗。”郭沫若理解的文学,是基于人的“气质”和“感情”意义上的文学。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神经质的人感受性很锐敏,而他的情绪的动摇是很强烈而且能持久的。这样的人多半倾向于文艺”,所以,“文学家并不是能够转移社会的天生的异材,文学家只是神经过敏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罢了。”郭沫若所理解的“革命文学”具有动态的特征。 他认为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是不断地革命着前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一变,革命文学的内容便因之而一变”。“所以革命文学的这个名词虽然固定,而革命文学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既然把革命看成是一种进化,把文学看作是神经敏锐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感情活动,文学家能够最早感受到阶级的压迫,能够最早喊出反抗的呼声,那么,文学就不但是“和革命是一致的”,而且还是“能为革命的前驱”[3]37-39。他注重文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郁达夫对革命的理解也是基于社会进化的角度,不同的是,郁达夫的阶级意识并不够强。他特别强调,谋取“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是革命的一个阶段,“革命的最后的目的,是在谋绝对全体的绝对幸福,不能说少数人就可以牺牲不顾的”[5]287。这种人类意识,使得郁达夫对于一些人可能“利用民众”来压迫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郁达夫对文学的理解是众所周知的自叙传思想。这与郭沫若基于“气质”和“感情”的文学观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郁达夫更强调直接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主张“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他坚信:“无产阶级的文学,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5]341他把文学的作用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所谓“消极的”文学的看法。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不过他们的战斗力不足,不能战胜这万恶贯盈的社会”,“只好逃到艺术的共和国里……以表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怀抱着的悲愤”。郁达夫对文学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成仿吾的观点也很有特色。他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一文中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跃进”。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存在“被移动着”和“有意识的能动的跃进”两种。至于文学,成仿吾也是把它看作与革命相一致的,他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总可以说是革命的。”但不同的是,成仿吾基于人性的立场更具体地论证了“一般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不同。他认为“一般文学”如果同时具备了“真挚的人性”和“审美的形式”,也就具有了它的“永远性”。而“因为革命文学究不过在一般文学之外多有一种特别有感动力的热情”,所以,永远的革命文学=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尤其是,成仿吾理解的“革命文学”更多地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而不特别强调其“时代效力”。他说:“一个作品自成一个世界,它是不受时代效力的影响的。”在他看来,拜伦的《哀希腊》“在希腊已经独立自由了的现今”,我们今天仍然能“感到他原来的热力”。#p#分页标题#e# 创造社“元老”们是以强调文学艺术要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而走上文坛的。文学艺术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是他们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媒介。深厚的文学修养、过人的艺术才华、以及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深深热爱,使得他们无论接受什么新奇的理论,都无法割断与文学丝丝相连的血脉姻缘。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不忘文学的重要作用,完全合乎他们的“个性意识”,也可以说,这正是他们借以表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 (二)始终强调“叛逆与反抗”的精神 创造社“元老”们的“阶级对立”意识有一个从获得到逐渐清晰和成形的过程,而“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则贯穿了他们文学活动的始终。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叛逆与反抗”。他之所以要掀起“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新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扬子江”能够做到“有崖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由此,郭沫若进而得出结论:“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郭沫若的这种“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在他的思想发生“剧变”之后同样存在。他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把革命理解为“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的反抗”,把文学的进化看作是线性的一种思潮取代一种思潮的“反抗斗争”。在《英雄树》一文中,郭沫若更是直言“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应该“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郁达夫与郭沫若有些不太一样,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着鲜明的“叛逆与反抗”精神。当然,在郁达夫看来,所谓“灰色和感伤的情调”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绝了望”[5]46以后的反抗。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把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归结为艺术家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直至1926年,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郁达夫还是言词恳切地希望《创造月刊》“能坚持到底”,“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成仿吾更加特别。郭沫若、郁达夫毕竟都属于“神经质”一类的创作家,他们的文章虽充满了浓烈的叛逆情绪,却具有情感的亲和力。成仿吾的理性制约情感的能力相对较强,他的文章原本就显得比较生硬,再加上经常出现真理在握的教训式口吻,因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粗暴”的特点。他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甚至使用“十万两烟火药”那样的文字,来表达他对“北京的乌烟瘴气”的不满。他此后不久发表的《打发他们去!》[8]152一文,又把军事名词“工事”应用于文艺斗争中,主张必要时需用“武力”“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踢他们出去”。其实,就成仿吾整个的“反抗斗争”思想而言,他是很注重理论的“分析与批判”的。他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主张:“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四年多以后,他在《〈洪水〉终刊感言》[9]501中还诚恳地反思自己“只是反抗,也教人反抗”,却“不曾有观察与推考的余暇”,“忘记了这种种旧的恶势力的批判”,他为此感到遗憾。他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更是全面地分析了“批判”的涵义及目标。他把批判理解为“文艺理论方面的努力”。所谓的“全部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所指的“横扫一切”,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它的各种形成要素(包括他所理解的“纯经济过程”、“生活过程”、“意识过程”等)的“全面的批判”和“表现方法的批判”。他认为经过批判,既“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变”,也“把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转换方向”。 (三)或隐或显地张扬自己的个性意识 从显在的观念层面看,创造社“元老”们的个性意识随着他们接受并倡导“革命文学”而呈现出逐渐消减的趋势;但从他们说话写文章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倾向和气质特点来看,骨子里仍然保有浓厚的个性意识。王富仁、杨占升说的创造社理论观念与意识本质相分离的情况,在个性意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郭沫若前后“剧变”的具体表现非常典型。他公开对自己的个性意识展开批判性分析是在1925年底。那时他在《〈文艺论集〉序》里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所以他主张:“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先不论他的这种逻辑是否合适,仅就他对个性意识的态度而言,也是既有批判,也有肯定的。他所批判的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自我的个性与自由”,仍然肯定“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与自由”。而且,他的那种“拯救大众”的豪情,牺牲自我的悲壮,也正是其个性意识的一种无言的展示。 郭沫若的这种思想在他1926年发表的《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章中,还在不断地重复着。直至1928年发表《英雄树》一文,号召文艺青年们“当一个留声机器”,要做到“无我”,才可以说他对个性意识真正进行了“清算”。但是,郭沫若的这种“清算”仍然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必说他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对无产阶级的想象,仍然带有浓厚的个性意识,他把无产阶级想象为“他们是日日站在生死关头与死神搏斗;他们的生产力、爆发力,是以全生命、全灵魂为保障的”,仅就他在《英雄树》中鼓吹的“睚眦必报”的精神和“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的率性生活,在《桌子的跳舞》中强调的“作家也要费无限的心血然后才能”“把捉着时代精神”的艰难过程,和“不怕他昨天还是资产阶级,如果他今天受了无产者精神的洗礼,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的自信而言,都散发出了浓浓的个性意识。#p#分页标题#e# 郁达夫的情况与郭沫若有些相似。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大谈文学“对现世社会的厌弃与反抗”,但并不否定个性。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目下的政府法律和道德”都是“箝制个性发展的”,应该成为“攻击最烈的目标”,自然主义文学“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的发扬个性”,应该成为反抗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对“有权有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态度,以及“即使失败了,死了”也“非要一直的走往前去不可”的决心和意志,也鲜明地表达出了他的个性意识。直至1926年,郁达夫的这种矛盾依然存在。 他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还是一方面哀叹“社会的混乱错杂!人世的不平!”一方面又坚持宣称:“我们所持的,是忠实的真率的态度!”与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没有那么自信,没有像郭沫若那样发生天马行空式的剧变。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认为,人的感情和个性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学习和改造可以根本改变的,始终坚持文学创作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和个性,坚持“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他批评那些“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人“是不忠于己的行为”。他把文学的阶级意识、社会责任与作家的个性意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如果两者不能够做到统一的话,则把前者作为一种目标和理想来推崇,而在具体创作中则依然强调的自己的个性。 个性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矛盾,在成仿吾身上也是长久地存在着。他发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时,一方面极其坚定地认为“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一方面又热情地鼓吹“文学的感化的功劳实在不小”;一方面强调“维持自我意识”与“个人感情”,一方面又主张“维持团体意识”和“团体感情”。既然文学的根柢在人性,人性又是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改造的,那么,把文学应用于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因为人性具有永远性,那么“革命文学”也具有永远性。在1927年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文艺战的认识》、《文学革命与趣味》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依然坚持这种矛盾着的思想。只有在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他强调“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要“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要走向“农工大众”,才可说他不再从理论上论说文学的人性,不再强调作品的个性精神,而专注于文学的社会使命了。这种思想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更明确地表述为:“我们的文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实行方向转换的阶段”。转换的内容,一是“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二是“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 但成仿吾的这种变化,更多地也还是在观念层面进行。不必说他文章中那种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气势,即就他文章中时时流露出来的一些与他的早期个性思想极为相似的词句,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所隐伏着的个性意识。比如,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他告诫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要“自觉地参加这社会变革”,“莫只追随,更不要再落在后面”,要“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他反复强调“有意识”:“我们有意识地革命”,“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诸如此类的词句,在他前期主张自我表现的文章中是屡见不鲜的。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8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